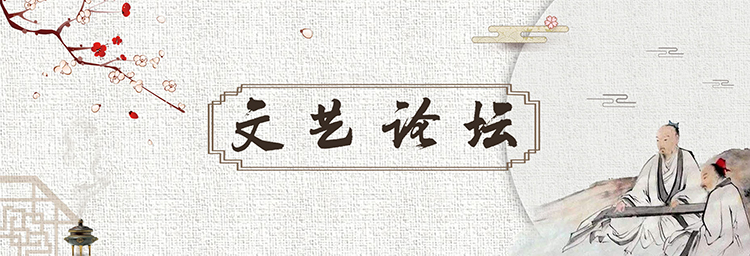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新世纪20年新主流电影发展景观
文/张燕 姚安颉
摘 要: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产业化体制的发展完善和市场潜能的持续开发,中国电影产量持续跃增、创作品质不断提高。其中,新主流电影在传承此前主旋律电影内涵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价值的有效对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艺术创新,创新创建了新主流大片。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主旋律电影;新主流大片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步入世界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作为区域电影的中国电影被迫融入全球电影版图,内地电影市场被迫逐步开放。庞大的观众规模和商业潜能,犹如一座待开发的“钻石矿”,令全球影坛欣喜,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争相涌入,好莱坞电影更是垂涎欲滴。内地电影在严峻挑战之下,市场被动激发、快速扩容,原本娱乐竞争力羸弱、体制尚未成熟的创作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此外,进口影片的价值观和文化意识输入,也对本土电影的创作生产与文化表达形成较大冲击。因此,国产电影亟需快速提升产业竞争力,力争突破进口片的挤压包围,找到可行有效的生存发展之道。
应对新形势,内地相关部门积极调整电影政策,大踏步推进电影产业改革,努力优化电影产业模式。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与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良性电影管理体制、完善电影市场体系为目标的多项措施。2002年2月《电影管理条例》实施,赋予民营公司独立制作、发行、上映影片的资格,为中国电影投资多元化进行政策性松绑。此外,电影管理部门全力推动 “院线制”改革,将单一的多层次发行转变为以院线为主体的一级发行模式,打破行业垄断、拓展发行领域、疏通放映体制,促进产业结构日趋科学合理。
在此背景下,主旋律电影作为长久以来与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共同建构中国内地电影的一种独特形态,逐渐转型发展为“新主流电影”。
一、“新主流电影”的内涵与发展
一直以来,电影学界和业界围绕“新主流电影”概念的讨论持续不断。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新主流电影”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出现的“主旋律电影”,并在传承其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演进。
(一)主旋律电影的开启与发展
1987年3月,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中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号召,并阐发了主旋律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强化了表现正在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这个主旋律。二是强调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①随后1987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这标志着主旋律电影创作延伸至“现实生活”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两大范畴。
“现实生活”强调的是表现真实题材、采用日常化描摹和伦理化书写进行创作的影片,比如取材于现实人物和真实事迹的《焦裕禄》(王冀邢,1992)、《孔繁森》(陈国星,1995)、《蒋筑英》(1992,宋江波)等英雄模范片;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指用写实性手法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进行回顾与展现,对当下观众起到教育警示意义的影片,比如《巍巍昆仑》(郝光、景慕逵,1988 )、《开国大典》(李前宽、肖桂云,1989)、《大决战》系列电影(李俊、杨光远,1991—1992)、《大进军》系列电影(韦廉等,1996—1999)等重大革命历史影片。
这一时期,管理部门也提倡“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电影要把娱乐还给观众”②,为更好地寻求主旋律电影与观众喜好接受之间的有效对接,众多电影人开始自觉探索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转型发展,多种类型元素被精心融入,主旋律电影逐渐产生了类型化发展趋势。比如将爱情元素融入抗日战争题材的《黄河绝恋》(冯小宁,2005),基于真实事件展现中国民航英雄无畏与人道主义精神、借鉴灾难动作片的模式进行创作的《紧急迫降》(张建亚,2000),等等。这些电影不仅在创作中加入商业类型元素,还专门邀请时下热度较高的明星出演,视听制作也更加精良。
(二)“新主流电影”的构建与内涵
2003年以前,围绕着中国电影格局的描述主要是“三分法”,中国电影业界和学界主体上采用“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个相互独立的类别来分析,三者之间在概念与特征上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界定。
但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越来越明显地趋于转向创作类型化和市场运作商业化,且商业生产机制日渐完善,主流价值观诉求也越发地自觉融入、并予以普世化传达。由此,“主流电影”与“新主流电影”的概念逐渐出现,并引发学界持续的热烈探讨。尹鸿教授提出“所有的主旋律电影必然是商业的,必须具有商业性;而所有的商业电影则必须是主流的,应该表达社会的核心价值观”③,郝建教授主张“将主旋律电影融合为‘主流商业片’和‘主流大片’”④、贾磊磊研究员建议“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⑤、饶曙光研究员提倡“当下中国的主流电影一方面必须‘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必须要适应‘电影产业化’”⑥等观点。
由此,从理论到创作实践,2000以来的主旋律电影日渐成功转向,并发展成为新阶段新主流电影的特定发展样貌。大体来说,“新主流电影”的内涵应该涵盖以下多个维度:1、思想性,“新主流电影”应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参与国家形象建构、文化软实力承载,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宣教与引导功能服务;2、商业性,“新主流电影”应坚持类型化创作的方式,强调娱乐化呈现和商业化运营模式;3、艺术性,“新主流电影”中应体现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多元化、探索性。
二、新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重构
从内涵上看,“新主流电影”代表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服务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教功能。“主流”的含义,不仅包括国家和集体在统治层面提倡并主张的意识形态,更包括广泛的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后者又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诉求的个体所构成的。
(一)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和价值的有效对接
对“新主流电影”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价值的有效对接,始终是其重要的使命所在。
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中多见以有血有肉的个体为载体的影片,形成国家利益与主流意识与个体的理想价值之间的双向交融,避免言之无物、虚浮的口号式呈现。如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等联合执导,2019),影片聚焦七位身份各异的平民百姓生活、工作与梦想,将小人物与大时代紧密相连,展现出始终与个体生命价值息息相关的国家进步和社会历程。影片《攀登者》(李仁港,2019)中,主人公的攀登理想不仅以其个人追求为出发点,更是以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为第一动力,在为国攀登的艰辛道路上实现了个体的人生价值,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统一融合。
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价值的有效实践,新主流电影将意识形态的主体回归到个人层面,并对内涵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阐释。冯小刚电影《集结号》(2007)描绘了战争中人性与责任使命之间的残酷抉择,在展现英勇杀敌、永不放弃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又借由主人公对真相的追问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将主题思想进行深化,表达了对战争价值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反思,展现出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的影像表达。《十月围城》(陈德森,2009)中,民族责任感体现在香港各行各业小人物身上,捍卫正义的武侠江湖梦想与保卫革命的家国使命交相呼应,形成了影片多层次的价值理念。
(二)伦理化策略与平民化视角
相较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有了较大转变,在建构革命历史事件时不再一味强调完整性和崇高性,宏大叙事不再成为主流,而更多采用伦理化策略和平民化视角,对小人物、小事件等细微之处进行观照,力图深化特定情境下的主题内涵,从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有效重构。
影片《张思德》(尹力,2004)讲述了勤务兵张思德在根据地延安为革命默默奉献的故事,采用张思德这一平凡小人物的视角,描摹他在日常生活中心系群众、在困难面前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涵。片中建构的毛泽东伟人形象,采用了伦理化、日常化的手法,树立起了一个具有生活气息、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伟人形象。影片《生死牛玉儒》(周友朝,2005),在传统英模片中加入家庭伦理元素,既表现了家人对牛玉儒不顾病情工作的劝阻和反对,也呈现出家人对牛玉儒的默默支持与陪伴,从家庭角度对符号式的英模形象进行人情味的刻画,使人物形象更真实立体。《中国合伙人》(陈可辛,2013)、《夺冠》(陈可辛,2020)等片则把镜头对准了好兄弟、好“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与团体协作,通过描绘平凡人物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展现个体在激荡的大时代浪潮中不忘初心、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品质,传递普通人可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中成就“英雄”梦想的理念。
(三)历史的新发掘与新书写
革命历史向来是主旋律电影重要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真实历史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表达往往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多元丰富的角度,对历史中的素材进行整合与重构,力图实现旧事件的新发掘与新书写。
众多新主流电影,从时代洪流的局部景观介入,在革命历史史实中进行提炼与升华。影片《邓小平·1928》(李歇浦,2004)讲述了国共内战时期青年邓小平与国民党特派员在暗中角逐较量的故事,将伟人年轻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革命斗争史呈现在观众面前。《毛泽东与斯诺》(宋江波、王学新,2000)则借助一位美国记者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的过程,为人们开辟了走近伟人生活的全新视角,在书写领袖为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创下的功绩时,更赞颂了两位主人公跨越国族界线的深厚友谊和共同理想。《湘江北去》(陈力,2011)聚焦毛泽东从参与学生运动到走上革命道路中的青春历程,着力表现有志青年救国意识的觉醒。
与此同时,电影创作的题材拓展与娱乐形式丰富、市场票房的日渐攀升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巧妙内置,使得新主流电影蕴含的巨大潜力逐渐显露出来。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多阶段实施以来,伴随着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繁荣发展,许多香港导演也积极加入到“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行列中来。香港导演浸润成长于香港商业电影,从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对革命历史与现实题材的主旋律电影进行全新的写作。
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历史、民族史实、现实事件等,香港导演予以重点观照和精心表达,涌现出多部精彩的作品。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2017),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军90周年的献礼片;李仁港执导的《攀登者》(2019),以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为题材,将小人物与大时代有机融合;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2016),根据著名“金三角案件”改编,开拓了内地题材、类型创作、奇观视听的创作路径。上述影片以小人物个体叙事为切入,与具有社会时代纪念意义的集体/群体背后的国家叙事紧密融合,实现了爱国主义、国家情怀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的融汇表达。
另一方面,香港导演以敏锐的商业触角选材创作,“反贪”“反腐倡廉”等当下政府举措、大众关心的社会热点现象,及时地被香港电影人捕捉并创作,逐渐形成新时代华语电影银幕上备受关注的类型。林德禄执导的《反贪风暴》系列、麦兆辉编导的《廉政风云》(2019)等影片,将香港经典的警匪、动作、悬疑元素与新时期国家大力倡导的反腐题材巧妙结合,情节引人入胜、悬念精巧、节奏紧凑,使主旋律电影呈现出高度的类型化特征,既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兼具“港味”电影文化。
三、新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探索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不断完善、企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国营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日渐形成多元化投资结构,主旋律电影不再仅仅依靠国家资金扶持和政策红利生存,而逐渐自觉地考虑商业市场与观众接受。由此,兼具商业性、思想性、艺术性的“新主流电影”应运而生,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探索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路径。
(一)类型化创作
在新主流电影自觉向商业化摸索的过程中,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成为首要的转型突破口。在以往中国电影“三分天下”的局面中?譿?訛,类型化作为商业电影所独有的特征,似乎与主旋律电影的性质格格不入。而“新主流电影”则重在融入并强化商业类型特点,在保证优质内容生产的前提下,以多类型杂糅叙事和艺术审美为媒介,将主流价值观自觉地融汇于商业娱乐中。影片《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与《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以真实事件或现实题材为创作基础,讲述警匪缉毒、撤侨战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糅合英雄叙事、动作叙事等商业类型元素,富有戏剧张力与叙事层次,并在制作层面大幅度提升视听效果,集现实化、类型化、奇观化于一体。
新主流电影通过类型化情节叙事,与深植故事内里的现实美学、情感精神相吻合,在多部影片中实现了“思想和情感融合的瞬间”?讀?訛。影片《云水谣》(尹力,2006)、《秋之白华》(霍建起,2011)将爱情片的元素与战争历史相结合,在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凸显战争残酷与革命艰辛,呈现出艺术表现力和情感感染力。同样是战争题材的电影,《风声》(高群书、陈国富,2009)与《密战》(钟少雄,2017)则高度具有谍战片的类型特征,生死攸关的紧张氛围和环环相扣的悬念设计,使影片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代入感。《金陵十三钗》则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对战争史诗题材进行类型化的改造,并在剧情中引入了国际化的人物形象,对跨越国家和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了讴歌。
除却经典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类型化创作,新主流电影还积极发掘和尝试新类型,创新性地推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进程。郭帆电影《流浪地球》(2019)借鉴好莱坞类型模式进行本土化实践,以刘慈欣原著小说为蓝本,大胆开创中国式科幻片的类型模式,票房位居中国电影史上卖座电影总排行的第三位,用科技手段打造高概念的科幻影像奇观,并将之与“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家国情怀紧密缝合。
此外,英模片的表现对象也在伟人、领袖之外不断拓宽新的可能性,灾难面前的“个体英雄”成为了英模片的新类型化趋势。《逃出生天》(彭氏兄弟,2013)和《救火英雄》(郭子健,2014)、《烈火英雄》(陈国辉,2019)等影片,积极开掘消防题材的商业化创作,在灾难叙事中融入动作、伦理等元素,既呈现消防员日常生活真实,又呈现出现场救援的影像奇观,实现主流意识与文化情感的银幕共振。
(二)商业化运作
因应创作方面的商业类型化探索,新主流电影在市场运作方面也自觉采取商业化包装策略,运用多种媒介进行及时有效的市场推广、整合营销,创造新主流电影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商业市场的公平良性竞争,并且注重发行放映与衍生产品开发。
新主流电影自觉配置明星阵容的超强影响力、势能IP的深度挖掘、续集和系列的品牌开发等多种商业元素,力图打破观众与主流题材电影之间的既有隔阂,引导观众转变主旋律电影主题先行的观影印象。再加上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质量已有明显提升,大众对新主流电影的态度已呈现出由“被迫宣教”到“主动买单”的发展趋势。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的《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两部影片,和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2017),都以国家、党和军队的建立为题材拍摄,开创了全明星阵容与史诗写作的有机结合。《战狼》《战狼2》则为军事题材的主旋律影片创作打开了新视野,围绕拯救国家、保卫人民的“战狼”军人冷锋这一核心的个体英雄形象,在商业化、娱乐性的故事中承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打造出具有可持续性和巨大市场潜力的IP资源。影片《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紧急救援》(2019)则着力打造在内地颇具号召力的林超贤品牌、博纳品牌,知名香港导演与内地影视集团的强强联合,为这一系列新主流电影在创作水准和资源整合上给予了双重保障。
高概念大片与奇观化的视听影像,是当下新主流电影重要且典型的商业特征。这些影片多是高投入、大制作、多明星、大场面,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融合视听觉方面的特效技术,力图为观众打造具有强烈感官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影片《建国大业》在邀请重量级导演和全明星阵容加盟之余,通过电脑特效技术对多个历史场景进行生动复原,再现宏大庄严的时代氛围。《智取威虎山》则利用先进的3D动画特效技术,将林海雪原的场景和栩栩如生的老虎进行逼真演绎,为经典作品赋予了全新的影像活力。
四、新主流电影的艺术创新
随着电影产业体制的发展完善、中国电影的产量持续跃升,大众精神文化需要和审美诉求的提升,不断助推中国电影趋向内容为王、质量为先、艺术创新的创作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主流电影也在与时俱进、不断突破。艺术创新,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发展的鲜明特点。
(一)艺术创作的个性化探索
沿袭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仍是新主流电影的思想内核。但就从创作层面而言,新世纪以来随着创作氛围的宽松、创作理念的开放和电影政策的松绑,创作者们涉足主旋律题材时,不论革命史诗、英雄传记,还是现实事件、传奇人物,可以拥有更前沿的视野、更多元的手法、更丰富的想象,从而产生了诸多在影像和叙事上具有个性化、创新性艺术探索的新主流电影佳片。
陆川导演执导的影片《南京!南京!》(2009),在冷静沉郁的风格化视觉表达中,加入不同身份的人物视角,对战争和人性赋予了深刻的哲学人文意味。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2014)将女作家萧红的一生作为创作原型,以细腻笔触对萧红漂泊动荡的生命历程展开书写,融合了纪实性、史诗性和时代性的表达方式,将宏观的历史篇章与微观的人物命运交相呼应,呈现出散文化的风格特征。2018年,文牧野执导、徐峥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以好莱坞类型叙事模式为借鉴,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大胆观照,既有主人公在利益面前的心理动摇与关键转变,又有一帮小人物从加入队伍到履行使命的心路历程,更有身处疾病圈外的警察面对人性与法律之间的抉择,故事曲折、情节细腻、层次丰富,人物形象也较为真实立体,实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缝合。此外,冯小刚电影《芳华》(2017)以小人物的视角,观照时代中抗争的青春、战争中塑造的英雄。陈德森电影《十月围城》以小人物叙事为主导,将港式个体价值与内地集体意识对接,呈现江湖梦想与家国情怀的统一。
(二)新主流大片的探索与建构
近年来,在充分借鉴外国电影类型模式的基础上,新主流电影不断创新推进,逐渐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创作体系,实现了与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之间的高契合度,培养出本土电影不断提增的强竞争力。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潮流中,这一发展趋势尤为明显。集合内地的充沛资金、巨大市场、文化资源和香港的影人素养、娱乐理念、类型优势,两地电影人更是在主流电影范畴中创新创建了新主流大片,并持续将之改良推进、系列打造,不仅创造了主流电影回归市场主体地位的商业佳绩,而且成功将新主流大片推向引领中国电影类型美学、文化意识审美提升的先进地位。
新主流大片以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为典型代表,打造出内地题材、又契合香港精神的创作模式,将战争、警匪、动作元素与现实题材、英雄事迹有机结合,并特别注重大场面、高强度的视听效果,将舍身取义、救国救民的主题思想融入片中每一次的惊险爆炸、枪击肉搏,使观众感受到惊心动魄的同时,为英雄们勇敢无畏精神所动容。新主流大片实现了意识表达、艺术探索与文化表达的新平衡,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主义表现力。与纯粹的警匪动作等商业电影不同,新主流大片中“激战”元素的存在,是为了烘托主题而必要的有机存在,就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引导而言,起到了结构性的功能意义。片中任务设置、使命传达和胜败拐点等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命运,背后都有某种从始至终的精神信念作为支撑,将全片的行为逻辑和推进动力串联起来。可以说,新主流大片的出现,标志着可被借鉴和推广的主旋律电影新类型形态的创新孕育,也为中国电影类型格局的拓展丰富融入了具有市场潜力的新力量。
在意识形态书写、商业化转型、艺术化探索等多方面的共同进步下,新主流电影告别以往主旋律电影“被边缘化”的被动局面,呈现出日渐提升的市场主导力,爬升至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排行的第一梯队。在与进口大片的同台竞争中,以林超贤电影为代表的新主流大片,更是展现出不俗的优势竞争力。
但客观地说,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水平并不整齐划一,众多影片质量不尽如人意,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创作中简单粗暴的戏剧冲突二元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刻意高大全、扁平化的英雄主义塑造,以及类型发展形态不完善等。此外,放眼全球,新主流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大多数影片国内票房抢眼、但海外市场平平,未能实现娱乐故事、人文内涵的有效对外输出和国家形象建构。长风破浪会有时,期待未来新主流电影的整体品质提升与全球市场突破。
注释:
①滕进贤:《稳步前进,寻求突破》,中国电影家协会、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编纂:《中国电影年鉴1988》,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第3—7页。
②史东明、尹鸿:《主流价值、商业诉求、电影产业——关于主流商业大片的对话》,《当代电影》2010年第1期。
③郝建、邓双林:《主旋律电影创作与阐释的“主流化”趋向》,《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④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和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⑤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主流电影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⑥[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张燕 姚安颉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