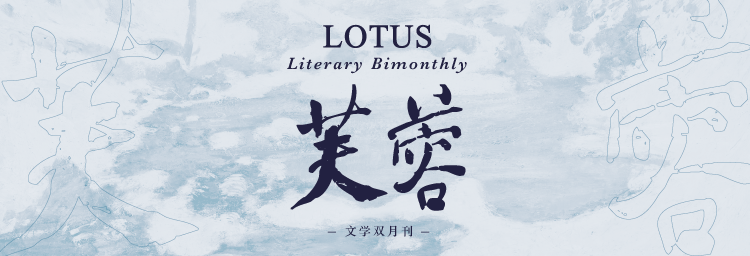

品论/摄
永生门(中篇小说)
文/刘鹏艳
A1
×年×月×日
今日立冬,风开始硬起来了。天冷得发灰,也许不久之后就会有一场雪。路边的银杏给这个平庸的冬天添了些许色彩,金黄的落叶堆了满径,踩上去,像踩着软软的时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潘岳已经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弱小无助的孩子。但在我眼里,他依旧是襁褓之中的婴儿,随时会受到意外的伤害。请原谅一个母亲的焦虑,且允许她静静地悲伤。我为无数人解决过难题,抚慰他们的心灵,疗愈他们的伤痛,鼓励他们重新面对破碎的生活,但我自己的难题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我曾经有一个执念,比孩子多活一天,但上帝显然没有接收到来自我这个异教徒的祷告。现在,我终于要接近那个答案了……
——摘自岳小聆日记
送走最后一个咨询者,岳小聆一头栽倒在门口的浅咖色布艺沙发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突然而来的眩晕褫夺了她的意识,使她瞬间抽离那副四十四公斤的躯体。她瘦得厉害,相对于一米六八的修长身材,这么一点重量实在压不住生活的风浪。风稍微大一点,她就会因为过于骨感而致使空荡的衣袂四处翻飞感到羞耻。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为克服自己的羞耻感付出巨大的心理能量。要说服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人迈不过那道坎儿,只是因为不愿抬脚。她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抬起那只被潜意识束缚的脚,不过,这并不代表她本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双脚。
“岳老师,您需要休息一下吗?”她的助手为她端来一杯黑咖啡。姑娘才从大学毕业,脸上有种未经世事剥蚀的饱满光泽,询问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打扰工作严谨、作风洗练的岳小聆。
“谢谢,”岳小聆报以虚弱的微笑,“你可以先回去了。”她是一个敬业而近乎严苛的咨询师,当天的案例报告总会及时地整理出来,这意味着她的助手也必须刻不容缓地配合她。然而今天,她实在是太累了。
沙游室里空荡荡的,除了沙盘和那些形态各异的沙具,并没有多余的摆设,岳小聆凝神观察了一会儿,把每个细节都刻入脑海。虽然主要部分已经拍照存档,但由于角度不同,会影响她对现场的判断。她围绕沙盘又走了一圈,回想着那个九岁男孩摆放沙具时的神态和顺序,仿佛看见一个封闭的世界在缓缓打开一道缝隙……
“没有了。”男孩面无表情地说。他刚刚在沙盘里随手放下一只帆船,但随即表示没有兴趣再继续玩下去。
“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吗?”岳小聆用笔尖指指对面的沙具架,那里摆满了惟妙惟肖的微缩玩具,足有上万件,诸如潜艇、飞机、赛车、加特林、火箭筒等男孩子喜欢的玩具应有尽有,然而眼前的这个孩子似乎不为所动。
“我不喜欢。”他伸手划拉着面前的沙盘,原先平整的沙子被搅乱了,东一堆西一堆的,有些地方露出海蓝色的木制底盘,那只帆船也有大半被埋进沙里。
“哦,这倒挺有意思,”岳小聆向前倾了倾,露出惊喜的神色,“我还从来没发现过呢……”
男孩不解地看了她一眼。
“瞧,这些奇妙的山川,”岳小聆指着被搅乱的沙盘,“就像一幅地图!嗯,可以和我说说这艘船的航行路线吗?”
男孩挑了挑新月似的弯眉,岳小聆把这个细微的面部变化记录在她的笔记本上。一弯初生的月亮从干涸的谷底升起,她看着他笑,瞧见他欲言又止地翕动了一下嘴唇,似乎在考量面前这个陌生而亲切的妇人在沙盘里的位置。
接下来男孩又在沙盘里放了一些贝壳和石头,他说这些都是爸爸的“遗物”。但男孩的父亲并没有去世,事实上,送男孩来咨询室的,正是这个“被死亡”的父亲。
解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件很神奇的事。岳小聆花了十多年在这件事上,走进过无数别人的世界,但她依然讨厌别人问她:“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不,我不知道。”她总是这样回答他们。
“你不是心理师吗?”
“我是,但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对这些猎奇的人,她毫不客气,但当男孩的父亲焦虑地问她:“你知道我儿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吗?”她却感到了不可遏制的悲伤。
因为行为不端,男孩不得不休学。无论父亲怎么教育他,或者教训他,他都沉默不语,但受伤的号啕从未停歇。她用笔帽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盯着那只帆面上已经有了明显破洞的帆船——沙具架上有很多船,大大小小不下数十只,男孩却始终偏爱这艘破帆船。他没有向她解释他的选择,只告诉她,船上有宝藏。
男孩还向岳小聆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挖宝藏的锄镐和风钻,那些工具看起来很有历史感。他一度认为那些工具和宝藏一起留在沉船上,打捞它们有很大的风险,首先得花一大笔钱,况且也不一定捞得上来。父亲可能遇上了风暴,也可能是海盗袭击了他的宝船,但他的尸体不在船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游戏治疗,岳小聆和男孩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他希望岳小聆替他保守他们共同历险时发现的“秘密”。但现在,她不得不背叛他信任的眼神。
“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办,不能再陪你玩了。”岳小聆对男孩说。
男孩正玩得不亦乐乎,略微诧异地抬起头,但接着就乖巧地把手中的微缩玩具放下,学着岳小聆平时的口气说:“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岳小聆有些感动,她摸摸他毛茸茸的脑袋,合上了手中的笔记本。
把男孩转介给另一位儿童游戏治疗师,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她的主治医生告诉她,她已经不适合工作了。
助手依依不舍地送别她时,红了眼圈儿。这位姑娘心地善良,甚至在为她整理案例报告的时候,也常常在手心里扣着一张纸巾,以备不时之需。“这些档案可不能当作小说来读。”岳小聆通常会轻啜着姑娘送上来的黑咖啡,慈爱而不乏严肃地告诫她。姑娘的脸上马上腾起一小朵红云,局促地扯着衣襟旁一片略显夸张的叶形装饰说:“岳老师,我明白的,看来我还要接受您的督导。”
她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满打满算只有十个月,不过,在这十个月里,她对姑娘很满意,尤其是姑娘冲泡的黑咖啡,味道醇厚,香气四溢,让她想起很多复杂的滋味。她时常闭着眼睛,享受那杯滋味复杂的黑咖啡,感受其中明亮的苦涩。
是的,明亮的苦涩,岳小聆轻轻吐了口气,发皱的脸上努力展开一个笑容:“挺好的,这样你就不用经常加班了。”
风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她吹得东倒西歪,她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几欲腾空而起的单薄身体钉在大地上。现在,她要去见自己的督导师。一个心理咨询师总是会接触到大量的负面信息,所以,即便是最优秀的咨询师,也必须定期接受专业的心理督导。
海浪一波一波温柔地涌上来,一种慵懒惬意的漂浮感弥漫全身,她感觉自己像是透明的晶莹水母。天空蓝得饱满欲滴,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片新鲜的湛蓝。岳小聆放松地半躺在软椅上,背后是金黄的沙滩。温柔的水波从双脚漫过来,漫上脚踝,漫上小腿,漫上膝盖,漫上腹部,漫上胸腔,几乎溢出眼角……
这种冥想让她放下很多不合时宜的负面情绪,包括莫名的愤怒,四处漏风的悲伤,如影随形的焦虑,不能再继续陪伴那个男孩的愧疚,以及,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
人人都热爱生命,而不愿意谈论死亡,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延年益寿。在那些自欺的生命中,还有一些更为可笑,比如曾经的岳小聆。
曾经,她以为自己是不怕死的,那时候她正年轻,岁月鲜花着锦地铺展开来,一端是掌声和赞美,另一端是舞台的追光灯,而潘正峰对她的爱更是烈火烹油,一切都那么圆满……
不过她好像忘记了,残缺其实是圆满的一部分,就好像,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悚然一惊,她懊恼地醒来,背部僵直,喉头发紧,发现自己正坐在咨询室里。周围是一尘不染的米白色乳胶漆墙壁,一盆妖娆的绿植把督导师那张凹凸不平的阔大脸盘掩映得恰到好处。
“你好像还是放松不下来。”藏在龟背竹后面的督导师送上一个暖洋洋的微笑。
“是的,很难。”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拿起身边的一次性纸杯。她喝水的样子十分焦渴,要是在往常,她是很抵触使用这种再生聚乙烯合成的廉价纸杯的。
督导师也陪着她叹了口气:“这的确很难,有些事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他转身为她又倒了一杯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见我。”
一股西伯利亚寒流正从窗外掠过,城市在渐渐暗下来的时空里瑟瑟发抖。岳小聆望着窗外苍茫的暮色,怕冷般抱紧了双臂,身体里充盈的海水正在退潮,岸上一片琐碎和凌乱。她哆嗦着嘴唇说,她真害怕那一天,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怕得厉害。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现在才知道,恐惧就像退潮后的滩涂上留下的满目疮痍,时间只是把她的恐惧切碎了,却没有清除这些足以伤人的碎片。
忧伤的情绪在不足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流动,那盆龟背竹似乎受到了某种触动,翠绿的叶片开始微颤,宛如蚊蚋的隐秘振翅。督导师交握着十指放在颚下,因为身体前倾,膝盖上的两只手肘撑住了上半身的重量,大脸盘上坑坑洼洼的麻点清晰可见。“没关系,”他以抱持的姿态接住了她心脏部位渗出的一滴泪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感到害怕的,我们可以慢慢来……”岳小聆苦笑了一下,她并没有足够的时间配合督导师的共情,龟背竹光滑发亮的革质叶片反射出耀眼的光斑,她的瞳孔本能地收缩了一下。
气氛还是不错的,分手的时候督导师甚至和她开起了玩笑:“你看你无论何时都是美美的,而我,”他指了指自己坑坑洼洼的大脸盘子,“一辈子颜值都是负数。”
她感激地回报给他一个明媚的笑容,是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羞于启齿的难堪瘢痕。而她现在还有必要感到羞耻吗?
她拨打了潘正峰的电话,用轻松的语调告诉他,接上潘岳,他们一家去欢乐颂广场的必胜客餐厅,好好地吃一顿比萨。
她能想象出潘正峰的表情,那个善于隐忍的男人掩藏不住自己不期而至的讶异,擎着移动电话的手有些僵硬,或许在判断前妻的来电是清醒的邀约,还是出于不可描述的谵妄状态。
“唔……好,好的,”潘正峰飞快地转着念头,“我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无法分家,但岳小聆的电话总是能让他在第一时间快刀斩乱麻。分开这么久了,他还是有点怕她,不,是爱她。
欢乐颂广场的必胜客比萨店永远是上座率最高的一家餐厅,如果没有预订,很难在周末的晚上享受一顿从容的晚餐。岳小聆一家赶到比萨店的时候,客人已经塞满了餐厅,连门口等位叫号的长椅也被全部占领,显示出人头攒动的拥挤和热闹。潘正峰的脸色有些为难,在熙攘失序的公众场所,他这种有身份的人实在难以做到如鱼得水,况且他们一家三口,多少与这欢乐的人群有些格格不入。
并不是他不愿意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他最渴望的,就是和岳小聆一起,带着潘岳,像普通家庭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一样,轻松愉悦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他现在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时他也会带着妻女去酒店餐厅,但他心中总有一种负罪感,感觉岳小聆冷峻犀利的眼神始终携着时间的呼啸,箭无虚发地扫射在自己身上。那是一种如芒在背的怵惕之感,他试图说服自己,并不是他抛弃了岳小聆母子,事实上,当初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他十分不舍,并且相信再也不会遇上比岳小聆更适合做自己伴侣的女人了。
眼下,这个优雅而聪慧的女人正看着自己,眼里有一抹蜜糖样的底色,但他不确定这种质地黏稠的眼光是否含有成分复杂的讽刺和讥诮。一旁,潘岳正流着口涎趴在餐厅的落地玻璃窗上,朝里兴奋地观望着。他粗短而弯曲的手指像壁虎那样吸附在光洁明亮的玻璃上,嘴巴和玻璃之间哈出一团白气,模糊了餐厅里欢乐的情景。但可以看出靠窗的一家人立刻有了反应,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被吓着了,她的母亲抱起她,父亲则厌恶地瞪了一眼窗外的潘岳。潘岳还在挤眉弄眼,过宽的眼距和上斜的外眼角使他看不到别人异样的眼色,再说,他也不在乎,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没有那么健全的心智,如果不是岳小聆及时拉开他,他一定会隔着玻璃把那个小姑娘面前的提拉米苏小蛋糕舔食干净。
潘正峰知道自己肯定又皱眉头了,他无能为力,原先设想的那套克制忍耐的办法一点派不上用场,就是这样,本能越过了理性,他不敢奢望岳小聆对他的印象有什么改观。
“进去吧。”岳小聆提醒他,前台那个负责叫号的胖乎乎的女服务生刚好叫到085号,正是他手中的号码。
一家三口走进餐厅的时候,潘正峰感觉到女服务生夸张的黑框眼镜里放出奇怪的光,在他们身上来回扫视了两遍。这种感觉太熟悉了,潘正峰冷冷哼了一声,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服务生的无礼表示不满。
岳小聆握住了他的手,他一个激灵,前妻亲密的举动让他受宠若惊。
“我们,”她在他耳边吐气如兰,还是上大学时那种让他神魂颠倒的娇嗔神态,“只是好好地吃一顿饭,好吗?”
他愣了愣,潘岳已经快乐地找到了自己的位子,旁若无人地挥着手:“妈妈,快来!”立刻就有人投过来奇怪的眼神,在先天愚型的孩子和美丽优雅的母亲之间来回碰了碰。岳小聆春风满面地走过去,夸奖潘岳聪明能干。潘正峰却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脚步多少有些迟疑,但那只柔软的手牵着他步入人群,温柔而坚定。他决定听她的话,屏蔽所有无关的目光。
只是好好地吃一顿饭。
潘岳已经香甜地沉入梦乡,扁平的后脑完美地贴合在枕头上,好像他的脑部从来没有发育过。这个嗜睡的孩子喜欢他的床,岳小聆抚摸着他细软的头发,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虽然隔着一道厚实的承重墙,潘正峰还是从门缝底下捕捉到了那缕幽秘的叹息。他搓着双手坐在客厅里,等待她的吐露——今晚很不一样,他感觉到她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他。
岳小聆从潘岳的卧室里走出来,轻轻带上了房门。那声轻微的咔嗒声像是在潘正峰的神经上咬了一口,他没来由地从软软的沙发上坐起来,正了正身体。
“最近还好吧?”岳小聆的声音波澜不惊,不像是要宣布什么重大的消息。事实上,他们分开以后,他没有再参与过她和潘岳的生活,好像他从来不曾是她的丈夫,也不是潘岳的亲生父亲。他成了局外人,没有资格见证母子俩生活中的重大时刻,也没有理由探听他们的隐私消息。岳小聆似乎很理解他,尽量不去打扰他“正常”的生活,把所有的不正常都留给了自己。这让他又感激又惭愧。
“还行吧。”他摸不准她接下来话题的方向,狐疑地盯着她好看的脸。岁月不曾善待她,那么惊艳的美,终究也染上了沧桑。
夜色深沉,一轮钩月半明半暗,就像十年前,他和她分手的那个夜晚。
云层很厚,月晕迷离,岳小聆盯着窗外的月亮说:“我们离婚吧。”她背对着他,他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是全然的鄙夷,还是有那么一丝的留恋?
他竟然没有勇气反驳她,也许她早就看穿了他的懦弱和无能。他的母亲,一位聒噪而强势的老太太,已经开始替潘家物色新媳妇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智力低下的孩子让他们全家后继无望,他这个独子总不能太自私。
借口,都是借口。他懊恼地揪着自己的脑袋,明白那不过是自欺的口实。
“你可以放心地离开,我只要潘岳。”岳小聆的口气又冷又硬,像块荒凉的石头。
从那以后,他就知道不可能再和岳小聆复合了。这是个嘴硬心硬的女人,他母亲这样评价她。也好,快刀斩乱麻,他母亲拍着大腿说。既然孩子不可能丢掉,只好把媳妇丢掉。这老妇人的逻辑十分符合趋利避害的世俗标准,作风也雷厉风行。她告诫过媳妇,趁着年轻,赶紧生孩子。可是媳妇把她的话当作耳旁风,硬是拖到三十多岁才把备孕提上日程。人家医生都说了,年纪大了,生孩子风险就大,潘岳长成这样,就是因为岳小聆的卵子老化。潘正峰向老妇人解释过,现在环境污染这么厉害,空气啦,食品啦,辐射啦,都不安全的,并不一定是高龄孕妇的原因。但老妇人仍然不能释怀,她说你们别以为我不懂科学,别的原因我管不了,就是不能排除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岳小聆一意孤行造成的,所以岳小聆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再是两口子的事儿了,岳小聆就扔给潘正峰一个后背,说好吧,潘正峰,你走吧,我的儿子我自己养。潘正峰说儿子也是我的,凭什么?岳小聆冷笑了一声,凭什么?就凭你带孩子出一次门都恨不得拿条口袋把自己兜头罩起来!
潘正峰没法子再犟嘴了,岳小聆说的都是事实,这才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真相。
他忧伤地看着她,时空在无尽的黑暗里迅速流动,能听到“咔嗒、咔嗒”的细微声响,那是一道道沉重的心门在他们之间悄然关闭。
“我能理解你。”岳小聆轻轻地说,“我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接受内心的羞耻感。”
是的,她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周围目光的焦点,他甚至有点惊讶,她怎么能旁若无人地抱着那个口眼歪斜的孩子走到人群里去?但是,她竟然做到了。
“其实并没有,”多年之后,她才向他坦承她的愧疚,“我很遗憾,没有早一点看到潘岳的成长。我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同样在意那些异样的眼光。我们不说这些了,作为潘岳的母亲,我无可逃避,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潘正峰惶惑地看着她,她正从标有“省立医院”字样的资料袋里缓缓抽出一份医学检测报告,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悸。(本文节选自《芙蓉》2020年第5期刘鹏艳中篇小说《永生门》。)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逾百万字,多部作品被权威选刊转载或收入重要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天阉》、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童话《航航家的狗狗们》,曾获多种文学奖项,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
来源:《芙蓉》
作者:刘鹏艳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