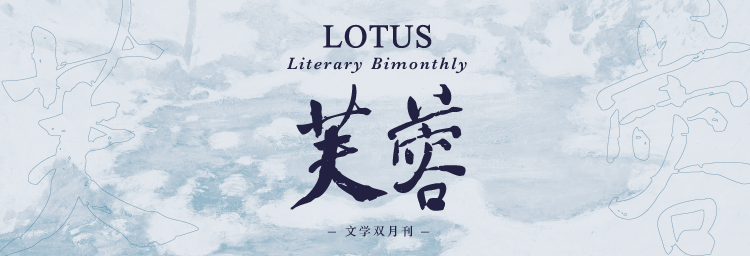

陈敏捷/摄
黄豆开门(短篇小说)
文/晓苏
1
腊月二十七,黄朴携着妻子陶艳从县城回到乡村油菜坡,陪父母过年。他本来可以早点回来的,学校几天前就放假了。但陶艳不愿意早走。她开了一个女子美容店,春节前生意特别好,每天的收入是平时的几倍。如果不是黄朴低三下四地跟她说好话,她恐怕要拖到腊月二十九日晚上才肯关门。
村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樟树,上面架着两个鸟窝,还有一个高音喇叭。黄朴的父母就住在离樟树不远的一个院子里,从樟树下能看见院墙。院墙是用土砖围起来的,颜色金黄,给人一种古老而温馨的感觉。
下午四点钟左右,黄朴把车开到了樟树下面。隔着玻璃,他看见他们家院墙上的大门敞开着。他还看到了他的父母。父亲站在房子门口的台阶上,两手插在袖筒里,显出怕冷的样子。母亲靠在父亲身边,拄着一根拐棍,似乎有点体力不支。他们都抬着头,眼睛看着樟树这边,显然正在盼望着儿子。
然而,黄朴却没有马上将车开回他家院子,而是突然停在了樟树底下。同时,他把目光也转了半圈,直直地看着院墙下面的一栋老屋。那是村里的旧仓库,还是生产队时期遗留下来的,已经废弃多年了。
陶艳奇怪地问,你怎么在这里就停了车?黄朴说,仓库里好像住了人。陶艳连忙从靠背上直起身来,看了看仓库说,真的是住人了,屋顶换了石棉瓦,墙头还伸出来一截烟囱,烟囱还在冒烟呢。黄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仓库前面的晒场上还晒满了东西,我看不清是红薯还是萝卜,你能看清吗?陶艳睁大双眼说,不像红薯,也不像萝卜,倒是有点像天麻。她停了一下又说,肯定是天麻,我曾经在菜市场上看到过,有人买回家炖鸡吃。
他们正这么说着,仓库里走出了一男一女。男的走在前头,戴着一顶老式的瓜皮帽,一手拿着一个塑料口袋。女的跟在后面,头上盖着一条毛巾,手里提着一只撮箕。两个人看起来都有六十多了,女的仿佛还要大一两岁,是个驼背,像一棵被大雪压弯的竹子。他们径直走到了晒场上,然后就开始把晒场上的天麻往塑料口袋里装。男的用双手把口袋牵开,女的先把天麻收进撮箕,再端起来倒进口袋里。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眨眼的工夫,他们就装好了鼓鼓囊囊的两大袋,看上去犹如两头怀孕的母牛。
这时,父亲终于发现了停在樟树下的车。他扭头给母亲说了一句什么,接着便和母亲一起歪歪倒倒地朝院墙的大门口走。父母都快八十岁了,身体虽说没什么大碍,但体质都比较差,大病不犯,小病不断。尤其是母亲,腿脚不太好,经常麻木酸胀。一看见父母艰难地走过来,黄朴就再没心思关注仓库那里了。他迅速把车开进了院子。
黄朴是个孝顺的人。下车后,他连车门也没顾上关,就快步朝父母跑了上去。他一手握住父亲,一手握住母亲,两眼在父母脸上不停地移动。半年多没见面,父母又明显老了不少。他这个学期教高三,又当班主任,每个周末都要补课,实在没空回来看望两位老人。幸亏有堂妹黄豆,长年在家里陪着父母,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陶艳随后也从车上下来了,双手各提一个行李包。包里,除了黄朴给父母和堂妹买的过年礼物,以及几盒点心,其余都是她自己的衣服和化妆品。见到公公婆婆,她礼节性地叫了一声,接下来再没有多的话说。她生长在县城边上,自认为是城里人,对乡下总是冷眼相看,与公公婆婆也没有多少感情,更没有共同语言。当年,她之所以嫁给黄朴,是因为黄朴读过大学,又在县一中当老师,既有地位又有稳定的收入。女儿结婚之前,她很少跟黄朴回乡村过年,差不多都和女儿待在城里。女儿嫁人以后,她觉得一个人在城里过年太孤单,才极不情愿地跟黄朴回油菜坡。
黄朴拉着父母的手进到房子里,穿过厅堂,直接进了烤火屋。这里烧着柴火炉,十分暖和。在火炉边坐定后,黄朴先询问了一下父母的近况,然后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了院墙下面的那个仓库。
仓库里住的是什么人?黄朴问。
父亲说,一个做药材生意的,打南漳那边来,名叫党生。他租了生产队的仓库,专门收药材和卖药材,生意还不错。据说,他以前在老家开过中医诊所,因此大家都喊他党医生。
那个女的呢?黄朴又问。
母亲说,她是党医生的内人,党医生叫她茯苓。她勤快、能干,不光给丈夫煮饭洗衣裳,还能帮丈夫打理药材。她待人和善,有空了还来陪我坐一坐,说点儿家常话。她也很舍得,送了我好几袋晒干的艾蒿,让我熬水泡脚。
黄朴听了父母的介绍,感到很高兴,觉得这一对夫妇的到来,无形中给父母带来了快乐与温暖。他不禁从内心深处对他们生出一种喜欢,甚至是感激。沉吟了一会儿,黄朴又问,他们不回南漳过年吗?父亲说,本来是要回去的,可收购的药材还没卖完,他们有点不放心,就决定不回去了。母亲补充说,主要是有些药材还没干,他们要赶紧晒,不然会长霉,一长霉就卖不出去了。
在烤火屋坐了半小时,黄朴从行李包里拿出了三件颜色不同的羽绒服。他先把灰色的递给父亲,再把蓝色的递给母亲,然后让他们穿到身上试一下大小。父母穿上一试,都很合身,脸上顿时绽放出幸福的笑容。还有一件黄色的,是他专门为堂妹黄豆买的。可是,他一直没见到黄豆的影子。他去灶屋看了一眼,也没看到黄豆。
黄豆呢?黄朴拿着黄色羽绒服问。
父亲说,她要是不在灶屋里,八成是去菜园了。
那我到菜园去看看。黄朴放下羽绒服说。
母亲说,她晓得你今天回来,早就炖好了羊肉,这会儿去菜园剜芫荽了。
听了母亲的话,黄朴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他觉得黄豆真是太好了,对人总是这么真诚,这么善良,又特别勤劳,干起活儿来像一头黄牛。与此同时,他更加觉得黄豆是个可怜的人,因为她不能说话,天生是个哑巴。
菜园在房子后面,靠近厕所。黄朴出门后正要往菜园走,陶艳也从房子里出来了。她说要去上厕所。走在路上,陶艳不停地发牢骚,说没见过把厕所建在房子外面的,撒泡尿也要跑几里路。黄朴忙做解释,说父母不习惯把厕所建在房子里。陶艳冷笑了一声,说乡下人都是死脑筋。
黄朴没再搭理陶艳,心里又想到了黄豆。黄豆年轻时曾嫁过人,还生了一个女儿。男人是官帽山的,长一脸麻子,像米筛上的眼,人称麻壳。麻壳脾气暴烈,经常虐待黄豆,张口就骂,伸手就打,有一次还将她打昏过去。公公和婆婆也欺负黄豆,看见麻壳打她,连拉都不拉一下。起初,她把唯一的寄托放在女儿身上,指望女儿长大后对她好。没料到,女儿读到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嫌弃她了。那天,她去学校给女儿送作业本,女儿当场就冲她发火,说她一个哑巴,不该来学校丢人现眼。那天晚上,她哭了一夜。第二天,她主动和麻壳离婚了。当时,她爹妈都已去世,哥嫂又不让她回去。在她无路可走的时候,黄朴把她接来了,让她和父母一起生活。
不知不觉,黄朴已走到了菜园边上。黄豆果然在剜芫荽。她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铲刀,已剜了小半筐。在油菜坡这个地方,人们吃羊肉都爱放芫荽。它不仅去膻味,而且增添香气。黄豆一抬头看见了黄朴,急忙直起腰来,看着黄朴笑。她笑得很甜,脸上红红的,像贴了一层糖纸。
厕所在菜园旁边,紧挨着院墙。陶艳从黄豆身边经过时,只跟她点了个头,便匆匆忙忙地进了厕所。
大约过了五分钟,陶艳从厕所出来了。她刚出来,一个驼背女人突然来到菜园。黄朴一眼认出了她,就是党生的老婆茯苓。茯苓之前显然听说过黄朴,一见面就仰起头来叫他黄老师,同时还对陶艳笑了一下。黄朴也热情地跟茯苓打了招呼,并感谢她为母亲送艾蒿。
茯苓是来上厕所的。她在菜园边只站了一会儿,就急忙进到厕所里去了。陶艳没想到茯苓会来这里上厕所,觉得不可思议。当茯苓进入厕所时,陶艳瞪大眼睛瞅着她弯曲的驼背,露出了一脸鄙夷的神情,眉头皱得像花卷。
从菜园回房子的路上,陶艳对茯苓上厕所的事仍耿耿于怀。她问黄豆,茯苓一直到这里上厕所吗?黄豆把头点了一下。她又问,难道仓库那里没有厕所?黄豆又把头点了一下。陶艳看见黄豆连续点头,便拧过脖子,对着黄朴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家的厕所已成公共厕所了。黄朴没搭腔,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感到哭笑不得。
2
瘟疫说来就来,令人猝不及防。它像一股穷凶极恶的龙卷风,张牙舞爪,横冲直撞,几天前只在省城武汉盘旋,一夜之间便席卷了大市小县,连油菜坡这个偏僻的山村也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腊月二十八晚上,黄朴和一家人坐在烤火屋里看电视。新闻里报道说,一种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瘟疫正在四处蔓延,已经死了好多人。看到这则新闻,一家人都感到十分恐慌。陶艳惊叫了一声,脸都吓白了。黄豆也不由一怔,仿佛打了个冷惊。父亲和母亲都哆嗦了一下,同时把怀里的手抱得更紧。过了一会儿,父亲回忆说,瘟疫厉害得很,听老辈子讲,我们这里在乾隆年间出现过一次,人差不多都死光了,到后来连尸体都没人埋。父亲话音未落,陶艳又惊叫了一声,像是被蛇咬了。其他人都没吱声,却面如土灰。黄朴心里虽说也害怕,但表面上还是很镇定。他说,我们也不要过于紧张,上面会有办法的。黄豆听他这么说,马上起身往火炉里添了几块柴,又给每个人的茶杯里加了一点开水。
第二天一大早,黄朴躺在床上看本地电视台的新闻,得知县里已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县委书记亲自担任指挥长。看到这个消息,他非常兴奋,正要起床告诉家里人,架在樟树上的那个高音喇叭突然响了。他听见村支书在扯着嗓子喊话。村支书先传达了县里的紧急禁令,抗疫期间严禁串门,严禁拜年,严禁聚餐,必须居家隔离,严防死守。随后,村支书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凡是发烧的、咳嗽的、呼吸困难的,要及时向村里报告,倘若隐瞒不报,将追究法律责任。黄朴一边听,一边跟陶艳感叹说,他们反应好快啊!
黄朴起床后来到烤火屋,黄豆已把火炉烧上了,屋里暖融融的。父母都听到了高音喇叭,正在议论着县里的禁令。父亲说,我活到将近八十岁,还是第一回听说不许拜年。母亲说,不拜年也好,以免人来人往闹哄哄的。黄豆不在烤火屋里。黄朴问,黄豆呢?母亲说,茯苓刚才在门口喊她,她出去了。
黄朴随即来到门口,果然看见了黄豆和茯苓。茯苓送来了一钢精锅魔芋,正弓着腰在给黄豆讲烹饪方法。她说,可以用酸辣椒炒了吃,也可以下火锅。黄豆双手端着魔芋,一边听一边点头。黄朴走到茯苓身边说,谢谢你又送我们东西!茯苓仰起头说,不值得谢,这魔芋是我昨天晚上自己磨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黄朴看了一眼魔芋说,难怪颜色这么纯呢,肯定好吃。他停了一下又说,县城里也有魔芋卖,但都不纯,不是掺了土豆就是掺了地瓜,颜色白卡卡的,吃在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茯苓脱口说,是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掺假。比如做药材生意,有不少药材贩子往天麻里掺白萝卜,但我们从来没掺过。
茯苓说完,转身朝厕所那边走了。黄朴没有立刻进房子里去。他静静地站在门口,默默地目送着茯苓艰难移动的背影。在他眼里,茯苓的身体虽然弯曲了,但她的形象却是笔直笔直的。
八点钟,黄豆做好了早饭。她心灵手巧,热菜和凉菜摆了一大桌,还特地用酸辣椒炒了一盘魔芋丝。陶艳一向喜欢吃魔芋,认为魔芋既防癌又美容。她看到桌子上有魔芋丝,两眼不禁一亮,马上就吃了一大筷子,还一边嚼一边点头叫好。夹第二筷子的时候,她问,这么纯的魔芋是从哪儿买来的?黄朴说,茯苓今早送来的,没掺任何假。黄朴一提到茯苓,陶艳脸上的表情顿时变了,像晴天转多云。她板着面孔问,茯苓是不是又来院子里上厕所了?黄朴一愣说,是的,怎么啦?他话刚出口,陶艳便赶紧把夹在筷子上的魔芋丝放回盘子,仿佛魔芋丝里夹了一条臭虫。
不能再让他们来院子里上厕所了。陶艳厉声说。
母亲吃惊地问,为啥?
如果他们身上携带着新冠病毒,那我们就会被感染。一旦被感染上,我们都会倒霉。陶艳说。
父亲说,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仓库这里,又没去过武汉,怎么会有病毒呢?再说,仓库那里没有厕所,不让他们来我们这里上,那去哪里上?
陶艳听了父亲的话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气愤。她把筷子往桌子上使劲一拍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这也是为大家好。黄朴没料到陶艳会这样,感到非常尴尬,急忙用手肘碰了一下陶艳,暗示她冷静。然而,陶艳却越发来劲了。她指着黄朴的鼻子,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去跟茯苓讲一声,让他们不要再来上厕所了。黄朴苦笑着说,我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陶艳一听,猛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张大嗓门说,好,既然你不好意思开这个口,那我就自己去找他们说。
陶艳说完就气冲冲地朝房子外面走,还把身上的口罩掏出来罩住了自己的鼻孔和嘴巴。你们不怕死,我怕。她边走边说。
黄朴顿时急了,赶紧劝阻说,陶艳,你不要这么冲动,那对夫妇都是善良的人,我们不能伤害他们。他们一没咳嗽,二没发烧,三没呼吸困难,你怎么能随便怀疑人家身带病毒?陶艳却没有理他,只顾继续往前走。
陶艳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忽然说话了。她说,陶艳,请你等一会儿。陶艳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母亲接着说,茯苓是个可怜的女人,年轻时上山采药,不小心从山上摔到山下,摔断了一根脊梁骨,打那次以后背就驼了。她驼了背,一直找不到婆家,到了四十多岁,才碰上死了内人的党生,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真是够可怜的。说到这里,母亲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又用求情的声音说,陶艳,你能不去找她吗?但陶艳没有回答,沉默了片刻,还是往门口走了。
黄豆听母亲讲茯苓时,不知不觉淌了一脸泪。她以为陶艳听了母亲的话会转身回来,没想到陶艳头也没回。眼看着陶艳就要走出房门了,黄豆突然从饭桌上拿起一个包子,一边擦泪一边朝门口跑去。她很快跑到了陶艳跟前,先把包子递给陶艳,然后举起一只手,在陶艳眼前使劲地摆动。然而,陶艳却假装看不懂她的手势,仍然不管不顾地出了门。黄豆呆呆地站在门口,垂下双手,神情黯淡,显得无比伤心。
大概出去了一刻钟,陶艳回来了。黄朴不冷不热地问,你真去找他们了?陶艳没有理睬他,脸一扭直接去了卧室。
整整一个上午,黄朴都没看见茯苓来院子里上厕所,也没见到党生来。他是一个细心人,每隔半小时,都要从烤火屋里出来一次,再沿着院墙转一圈。他希望能在院子里看到茯苓或者党生,可始终没有看到。他曾想过去一趟仓库,问候他们一声,顺便观察一下他们的情绪,但又觉得不好意思面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吃中饭前,他从院子里回到烤火屋,低声跟父母说,看来陶艳真去仓库找过他们了。父亲想了想说,党生每天都是正午来上厕所,几乎雷打不动。他假如今天正午不来,那就说明陶艳真的去过。
这天中午,黄朴睡了一觉,起来已是午后两点半钟。他来到烤火屋,一见到父亲就问,党医生来过院子吗?父亲没说话,只是有气无力地摆了摆头。看见父亲摆头,他的心陡然往下一沉。虽然这个结果早被他料到了,但被证实之后还是让他感到惊异。他好半天没说一句话,心里老想着党生和茯苓。他想,党生和茯苓肯定会恨他们这一家人,觉得他们自私、冷酷、无情无义。想到这些,他更加感到忐忑不安。
坐了不到半个钟头,黄朴离开了烤火屋。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决定让黄豆送一盒点心去仓库。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党生和茯苓表示一下歉意。
点心放在卧室里。黄朴走进卧室时,陶艳正在和女儿通过视频聊天。因为上厕所的事情,她和一家人闹得不愉快,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卧室里,吃饭也不上餐桌,把碗端到卧室里吃。女儿说,她所在的那个城市也有染上病毒的,并且死了好几个人。女儿还说,据专家介绍,尿液和粪便也是传播途径。聊到这里,陶艳马上对黄朴说,你听到没有?尿液和粪便也带病毒,所以不能与外人共用厕所。黄朴没有搭腔,提了一盒点心就出来了。
吃过中饭,黄豆就开始在灶屋里打橡子粉。橡子果是她从山上一颗一颗捡回来的,晒干后先去壳,再放入清水中浸泡,泡透了再磨成浆,然后把果浆煮开、过滤、冷却,最后就成了橡子粉。橡子粉柔软细嫩、清凉爽口,堪称美味佳肴。每年春节到来,黄豆都要打橡子粉。她打的橡子粉格外好吃。
黄朴提着点心来到灶屋时,黄豆已把橡子粉打好了。她正在往一个钢精锅里装橡子粉,一连装了四大块。黄朴觉得那个钢精锅有点眼熟,仿佛见到过。他很快想起来了,原来是茯苓送魔芋时端来的那一个。装好橡子粉,黄豆端起钢精锅便朝房子外面走。黄朴追上去问,你要去哪里?黄豆停下来,用手指了一下钢精锅,又指了一下院墙外面的仓库。黄朴马上明白了,她要去给茯苓还钢精锅,同时回赠她一点橡子粉。黄朴把点心提起来说,太好了,你顺便把这盒点心带给他们,再替陶艳道个歉。黄豆欣然接过点心,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冬天风大,吹在脸上如刀子刮。黄豆从仓库回来时,脸都冻僵了。黄朴赶快把她推进烤火屋,让她暖和一下。母亲一见到黄豆就关心地问,茯苓他们在哪里上厕所?黄豆快速举起了一只手,再快速放下,做了一个打锤的动作。母亲一眼看懂了她的手势,叹口长气说,唉,上个厕所还要跑到铁匠铺去,路远不说,还要经过一个陡坎,真是为难他们了。
黄朴听了母亲的话,鼻子不禁一酸。他知道铁匠铺,也知道那个陡坎。那个陡坎是一块竖起来的岩石,年轻人上下都很困难。
3
大年三十,油菜坡下了一场大雪。雪是从半夜开始下的,神不知鬼不觉。黄朴早晨起床后拉开窗帘,发现整个村子都已被积雪覆盖。仓库顶上的石棉瓦看不见了,像是换上了一床厚厚的白棉絮。那棵绿色的樟树也变了模样,看上去仿佛披了一层孝布。不过,树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响,村支书依然在重复宣读着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十条禁令。
院子里也积满了雪,到处白雪皑皑。黄朴从卧室出来,看见黄豆正在通向厕所的那条路上铲雪。她双手握着一把铁铲,一下一下地铲着,显出很吃力的样子。她实际上只比黄朴小两岁,过完年就满五十五了。黄朴有点心庝她,快步走了上去,说要替她铲雪,边说边夺她手中的铁铲。可黄豆不让他铲,紧握铁铲不放。黄朴没有办法,只好回房子里另外找来了一把铁锨,和黄豆一道铲雪。他铲得很卖劲,把铲起来的雪块扔出去老远,像农民在晒场上扬油菜籽。黄豆看在眼里,脸上不禁泛出笑色,还对他伸了一下大拇指。
吃罢早饭,黄朴便进到卧室开始写对联。自从大学毕业后,每年春节的对联都由他自己写,并负责在中午吃团年饭之前贴到每张门上。院子里大大小小的门有十二张,他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把十二副对联写完。
黄朴写完对联来到烤火屋,黄豆正在用猪油渣包饺子,母亲则在用艾蒿水泡脚。他问母亲,是茯苓送你的艾蒿吗?母亲说,是她送的。她这艾蒿真好,用它泡一次脚,好几天腿脚都是热乎的,既不麻也不酸。黄朴没见到父亲,便问,父亲呢?母亲说,他去党医生那儿了,想找他要点白果树叶。他愣神地问,要白果树叶做什么?母亲说,他的降压片喝完了,党医生曾跟他说过,用白果树叶泡水喝能降血压。
听说父亲去了仓库,黄朴心里有点害怕,害怕他走在雪路上摔跤。他赶紧起身,想去路上搀扶一下父亲。然而,他正要走出烤火屋,父亲就拎着一包白果树叶回来了。放下白果树叶,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落座。他久久地站在火炉边上,显得心事重重,脸色也十分难看。黄朴疑惑地问,您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母亲又问,你到底怎么啦?直到这时,他才开口说话。
出事了。父亲沉重地说。
出了什么事?黄朴和母亲同时问。黄豆也呆住了。
茯苓早晨去铁匠铺上厕所,回来爬那个陡坎的时候,刚爬上来,脚一滑又摔了下去,把左边的胳膊摔成了骨折。父亲低声说。
天哪!黄朴和母亲又同时惊叫了一声。黄豆没叫出来,却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看上去像一个小碗。
沉吟了好半天,父亲才坐了下来。他蹙紧眉头,补充了一些茯苓摔跤的细节。早晨,茯苓比党生先起床,一起床就要去铁匠铺。党生发现下雪了,担心茯苓一个人驼着个背走在雪路上不安全,便让她等一下,说等他起床后陪她一道去。但茯苓急着上厕所,就没等。党生起床后,刷牙洗脸耽搁了一会儿,想到今天过年,又刮了一下胡子才出门。当他走到陡坎那里时,茯苓已经摔倒了。她弓着背蜷缩在雪窝里,用右手按住左边的那只胳膊,嘴里不住地呻吟……
母亲听了叹息说,唉,大过年的出这种事,真是造孽啊!黄豆不声不响地流泪了,流得满脸都是。黄朴焦急地问,茯苓现在的情况怎样?父亲说,党生把她从雪窝里背回来,给她正了骨,敷了一些药膏,又撕了一条旧床单,把摔断的那条胳膊绑起来了。这会儿,她正在屋里躺着,嘴里还在呻吟。
都是陶艳惹的祸!黄朴愤愤地说。
话未落地,黄朴忽然听见门外有一丝动静。他慌忙扭头去看,原来竟是陶艳。她直直地站在烤火屋门口,满脸都是惊愕的表情。黄朴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但可以断定她已经听到了茯苓摔跤的事。看到陶艳,黄朴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索性对她劈头盖脸吼了一通。吼过之后,他似笑非笑地说,一个可怜的驼背,现在又摔断了一只胳膊,你应该感到高兴了吧?陶艳没有像平时那样顶嘴,只尖厉地哭了一声,然后就抱头跑回了卧室。
黄豆把包好的饺子送进灶屋后,好半天没回烤火屋。母亲说,团年饭十二点半才吃,现在做饭还早吧,黄豆怎么不来烤火?黄朴说,我去灶屋看看。
黄朴来到灶屋,却没看见黄豆,只见灶屋的后门开着。他从后门出去,发现黄豆正在水池边洗一个搪瓷痰盂。这个痰盂还是前年父亲在县城住医院时买的,出院后,黄豆一直没舍得丢掉。看见黄豆洗痰盂,黄朴觉得莫名其妙。他走到黄豆身边问,你洗痰盂干啥?黄豆直起腰来,转过身子,伸手朝院墙外面的仓库指了一下。黄朴问,你是要送给茯苓吗?黄豆点了点头。黄朴惭愧地说,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黄豆洗好痰盂,拎着它直接朝院墙外面走了。黄朴站在水池边,看着她踏着积雪由近而远,心里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因为一家人的心情都不好,黄朴就没有把他写好的对联贴到门上去。团年饭也吃得索然无味。黄豆精心做了一满桌子菜,可好多连筷子都没动过。开饭之前,黄豆专门去请了陶艳。陶艳还算给面子,马上就跟黄豆来到了饭厅。但她一点胃口也没有,只吃了几个饺子就下桌子了。
雪仍然下着,时断时续,上午停了一会儿,午后又下了起来。吃过团年饭,黄朴没急着去睡午觉。他在烤火屋陪父母坐了许久,还烧了一壶开水帮父亲泡上了白果树叶。直到两点钟,实在犯困,他才去卧室。
进到寝室的时候,黄朴看见陶艳正忙着收拾她的行李。他深感疑惑,正要问她想干什么,陶艳先开口了。她说,我要走了。黄朴一怔问,去哪里?她说,回城里去。黄朴睁大眼圈问,为啥?年还没过完呢。她说,我在这里惹了祸,大家都不待见我。我走了,以免你们看见我心烦。黄朴冷笑着说,我看你是疯了,大过年的,怎么能走?再说,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走?她说,不要你管,我自己开车回去。她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对着黄朴晃了几下。黄朴发现她去意已决,便没再劝阻。他知道陶艳的个性,再怎么劝也没用。
陶艳背上行李包,转身就走出了卧室。黄朴没有送她,对着她的背影说,我看你真是疯了!
直到吃晚饭,父母和黄豆才知道陶艳走了。他们都埋怨黄朴,说他不该让陶艳走。父亲责怪说,别人过年都是一家人团圆,你们倒好,反而故意分开了。黄朴说,她执意要走,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打了一下他的手肘说,你也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连自己的女人都留不住。黄朴说,她个性太强,我不能把她的腿捆起来。这时,黄豆举起一只手来,伸出大拇指,勾着小指头,贴在耳朵上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黄朴猜到了她的意思,马上掏出手机给陶艳打电话,想问她回到县城没有。陶艳的手机很快拨通了,却久久没人接听。她还在生我的气,不接电话。黄朴说。
黄昏时分,雪下得更大了,仿佛有人在天上往地下扔棉花。气温也降了,差不多到了零度。晚上,父母和黄豆坐在烤火屋里看春节晚会。黄朴也陪着看了一会儿,却心不在焉,什么也看不进去,不到九点钟就一个人去了卧室。到卧室后,他又拨了一次陶艳的手机,但仍然没人接听。
大约十点钟的样子,黄朴正打算上床睡觉,突然听见有人喊黄老师。声音不大,像是从院墙大门外面传来的。他感到有点儿奇怪,迅速从卧室跑出去,直接跑到了院子大门口。
院子大门外站着一个人。在雪光的映照下,黄朴看见那人戴着一顶瓜皮帽,再仔细一瞧,原来是党生。他手上提着一个痰盂,就是黄豆送去的那一个。
黄朴问,党医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党生说,我刚才去铁匠铺给茯苓倒痰盂,经过那棵樟树时,发现树下有一辆车,车里头还有一个人,好像是你的妻子。
黄朴顿时慌了神,拔腿便朝樟树下跑。路上结了冰,他像溜冰一样,跑得东倒西歪,还滑倒了两次。跑到樟树下,他果然看见了他们的车,车顶上盖满了雪。透过车窗上的玻璃,他看见了陶艳。陶艳仰面靠在驾驶座的椅子上,双眼紧闭,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车窗锁住了,他使劲地敲门。敲了好半天,陶艳才慢慢挪动一只手,摸索着将车门打开。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陶艳已经昏迷得不省人事了。
黄朴张开双手,将陶艳紧紧地抱在怀里。回到院子门口时,他发现党生还站在原地。党生对黄朴说,你妻子可能是冻昏了,你最好熬碗姜汤给她喝,汤里放点红糖,这样她会醒得快一些。黄朴感激不已地说,谢谢你,党医生!他说着就进了院子,直接把陶艳抱到了烤火屋。
看着黄朴抱着陶艳进来,父母和黄豆都吓坏了。他们赶紧站起来,目瞪口呆,惊慌失措。黄朴说,她冻昏了,要烤一下。父亲和母亲连忙走到墙边,把靠墙的那张沙发床拖到了火炉跟前。黄朴随即把陶艳平放到沙发床上,然后坐在床边看着她。她脸色苍白,嘴角干枯。黄豆愣了半天,这时才回过神来。她先给火炉添满了干柴,又出去找来一条毛毯,盖在了陶艳身上。过了一会儿,黄朴猛然想起了党生的话,便抬头对黄豆说,请你去熬一碗姜汤来,最好加点红糖。黄豆听了,一边点头一边去了灶屋。
黄豆端着姜汤回到烤火屋时,陶艳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红晕,嘴唇同时也张开了一条缝,像是要喝水。黄朴接过姜汤,赶快给她喂了几勺。吞下几勺姜汤后,她的嘴巴张得更开了。慢慢地,黄朴把一碗姜汤都喂进她的嘴里。
大概过了半个钟头,陶艳终于睁开了眼睛。一家人都喜出望外,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聚到了她的脸上。我这是在哪里?陶艳迷迷糊糊地问。你回家了。黄朴笑着说。陶艳把眼珠转动了一圈,在每个人的脸上停了几秒钟,眼神显得十分柔软,似乎还含了泪花。
接下来,陶艳说她很后悔,不该说走就走。开始,她没想到抗疫期间会封路,等她把车从油菜坡开到省道入口处,那里早已被防疫指挥部堵住了。她给那几个站岗的人说尽了好话,还试着上烟、塞钱,但他们不吃这一套,坚决不肯放行。她在省道边上滞留了几小时,进退两难。挨到天黑,她实在无处可去,只好掉头返回油菜坡。然而,把车开到了樟树下,她却不好意思再往前开了,于是就停在了樟树下面……
陶艳讲完,泪水已溢出了眼眶。听了她的讲述,一家人都感叹不已。父亲说,你这孩子,回自己的家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母亲接着说,就是,你也太见外了。黄豆抽出一张纸巾,给她擦了眼泪。末了,黄朴问,车里有空调,你为什么不打开?陶艳细声细气地说,我打开了一会儿,后来没油了。
黄豆知道陶艳还没吃晚饭,便主动去灶屋给她煮了一大碗饺子,同时还蒸了一碗鸡蛋花花。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陶艳一边吃饺子一边问。
黄朴说,发现你的不是我们,是党生。
党生是谁?陶艳愣着眼睛问。
黄朴说,就是茯苓的丈夫。
陶艳一听到茯苓的名字,浑身不禁一颤。随后,她很快低下了头,再不吱声,连饺子也吃不下去了。
4
正月初一早晨,天气突然放晴了。初升的阳光洒满雪地,油菜坡像是在白褂子外面又套了一件红衬衫,显得分外喜庆。
陶艳这天比黄朴起床早。她一起来就拉开窗帘,把目光直直地投向了仓库那里。她在窗前默默地站了许久,然后蓦然过头,对黄朴说,你能不能替我去一趟仓库?黄朴躺在被子里问,去仓库干什么?陶艳说,请茯苓和党生还是来我们院子里上厕所。她说得非常诚恳,显然是认真考虑过的。
你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黄朴连忙从床上坐起来问。
昨晚要不是党生发现我,我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陶艳低声说。
黄朴欣喜地说,看来,我老婆还是有良心的。
陶艳红着脸说,我本来应该自己去的,可我实在没脸见他们。
黄朴起床后立即去了仓库。他到仓库时,党生刚从铁匠铺那里倒了痰盂回来,鞋子上沾满雪泥。茯苓已经起床了,用一条布带将那只骨折的胳膊吊在脖子上,正弓着背在火炉边煮面条。他们见到黄朴都很热情,忙着给他让座。但黄朴没坐。他站在火炉旁,先给茯苓道了歉,又感谢党生救了陶艳,然后说,你们不要再去铁匠铺了,还是去我们院子里上厕所吧。听到后面这句话,茯苓和党生都异常激动,嘴里连声道谢。
黄朴从仓库回来的时候,陶艳正在烤火屋里劝父母和黄豆换羽绒服。她说,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呢,你们都把新衣服穿上,新年要有新气象。这回,父母和黄豆都听了她的,马上就去换上了崭新的羽绒服。羽绒服一穿上身,他们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早饭之后,积雪开始融化了。院子里阳光灿烂,也没有风,气温随即升了起来。十点钟左右,陶艳从烤火屋搬了一把椅子,坐到院子里晒太阳。晒了一会儿,她把黄朴也叫出来了,让他陪着一起晒。可是,陶艳晒得并不专心,不停地扭头朝院子大门那里张望。黄朴看出来了,她在盼望党生和茯苓,盼望他们来院子里上厕所。然而,她盼到中午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陶艳忍不住问黄朴,你去仓库说了没有?黄朴说,说了。她问,说了他们怎么没来?黄朴琢磨了一下说,也许吃了中饭就会来的。
中午的阳光更好,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父母和黄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中饭过后也到院子里晒太阳了。
下午两点多钟,黄朴和陶艳睡午觉起来时,父母和黄豆还坐在院子里。陶艳开口就问母亲,茯苓来上过厕所吗?母亲摇头说,没有。她又问父亲,党生也没来?父亲也摇头说,没有。陶艳感到很失望,垂下头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他们还是去了铁匠铺。
这时,黄豆突然站起来,抬起双手,将十指张开,蒙在了自己脸上。陶艳看不懂黄豆的动作,正感郁闷,母亲说话了。她说,黄豆想说的是,他们想来上厕所,但不好意思。父亲插嘴说,也是,如果换成我,我也会不好意思的。
黄豆站起来后没再坐下,不一会儿便进了房子。再从房子里出来时,她肩上扛了一把锄头。她扛着锄头匆匆忙忙去了菜园。黄朴望着黄豆的背影问,她扛把锄头去干什么?母亲回答说,可能是去挖生姜,她把生姜埋在靠院墙的那块沙地里,吃完了就去挖几块。
这天傍晚,陶艳独自去上了一趟厕所。从厕所那里回来,她显得特别开心,脸上笑容可掬。
碰到了什么喜事,让你开心成这样?黄朴好奇地问。
陶艳乐不可支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茯苓和党生来上厕所了。
不会吧?我一直没看见他们进院子的大门呀。黄朴眨着眼睛说。
陶艳神秘地说,厕所后面的院墙上开了一张小门,他们是从那个小门进来的。
黄朴一下子惊呆了。但他不敢相信,觉得像在做梦,眼前一片模糊。陶艳补充说,她走到厕所门口时,茯苓正从厕所里出来,党生站在菜园边上等她。茯苓没跟陶艳说话,只红着脸对她笑了一下,然后就和党生一道绕到厕所后面去了。当时陶艳很奇怪,不知道他们去厕所后面干什么。上完厕所出来,陶艳走到厕所后面一看,发现院墙上开了一张小门。陶艳讲完停了片刻,又对黄朴说,你若不信,可以自己去看。
黄朴真的去了。在厕所后面的院墙上,他果然看到了一张小门。那门是新挖的,还留着锄头的痕迹。他久久地凝视着那张小门,眼前猛然浮现出了黄豆扛着锄头的样子。

晓苏,男,湖北保康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人民文学》《作家》《收获》《花城》《钟山》《天涯》《芙蓉》《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小说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十三部,散文集一部,学术著作三部。曾获湖北省文艺明星奖、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林斤澜小说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
来源:《芙蓉》
作者:晓苏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