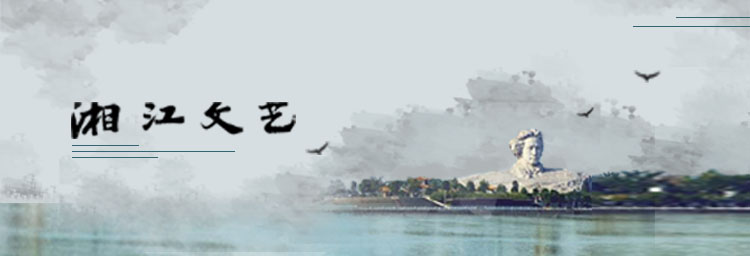

世味煮成茶/摄
观众演员(短篇小说)
文/江月卫(苗族)
1
李婉秋因劳动改造积极被提前释放半年。李婉秋不敢再非法接生直接回家。否则,累教不改是罪上加罪。李婉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离开借母溪才三年多点,村口的大门怎么就破旧到这种程度。去的时候还没有立呢,是不是买了旧的来立在这里呢?可哪有这么适合的门楼,有一边的柱子还立在坎里呢!其实,是专门搞古建的师傅们才修建的,做了旧。
沿着村口的那条小溪往前走就到自己家。没错,这条路看着李婉秋长大,也可以说李婉秋是在这条路上摔跤摔大的,在这条路上闭着眼也能走到家。正当李婉秋怀着喜悦的心情大步向家走的时候,一个手拿大刀,穿着清朝服装背上印有“勇”字的长辫子挡住了他的去路:什么人?
李婉秋吓了一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猛地拍了自己一巴掌觉得痛。发觉不是在做梦。他不停地自我发问:是真的吗?这就是我的家乡么?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那“勇”字说:进入景区要买门票。
李婉秋这下子清楚地感觉到,是在现实之中,愣了愣说,我回家还要买门票?
“勇”字有些惊愕:你是哪个,我怎么不认识你?
李婉秋。
“勇”字说,李婉秋?就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劳改犯!
李婉秋愤怒得讲话都结巴:我,我,你去劳改一下,你还没这本事!
你还蛮有道理,修建公路占你点稻田,你四处告状,小气鬼!
李婉秋很不舒服,心想如果不占我稻田我就不会上访,不上访就不会接生,不接生就不会坐牢。根本原因是村里修公路占了我的稻田引起的。现在把这一切的错,都归到我李婉秋的脑壳上,都是我的错吗?我要我自己的难道有错吗?口气就变得强硬起来:怎么了,我告状怎么了,占我的稻田难道就不应该补我?
“勇”字说,像你这样为了个人利益,阻碍咱们村里发展的,村里不欢迎你,你一个牢改犯,连你儿子李小丑也不欢迎你!
我、我……李婉秋气得脸都通红。
听见这边争吵,又有五六个“勇”字从各个巷子跑来。李婉秋一下子就看到儿子李小丑。李小丑也手持大刀穿清代的“勇”字服。李小丑像不认识一样怯怯地看着李婉秋,李婉秋也静静地看着李小丑。李婉秋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李小丑喘着粗气生气地把头扭向了一边。
沉默几秒钟后,一个“勇”字说,村子里不欢迎不支持借母溪发展的人。李婉秋正要辩驳,有几位客人来了,几个“勇”字撤到了各自的岗位。
李婉秋独自沿着溪水走过石拱桥,再从一排吊脚楼的屋檐下往家里去:吊脚楼板壁用桐油油得贼亮。家家户户屋檐都扳了翘角刷了白瓦口。整个村寨显得庄重大方整洁。自家门口立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挂着的黄色旗子写着“李”字。没有立的人家在屋檐下挂着红灯笼,十分喜庆。
李婉秋放下背包,立马去看那丘“逼”他上访最后进了牢房的稻田。村道已全部硬化成了水泥路。经过他稻田的那一段路面全是硬梆梆的水泥,现在就是同意他开成稻田都不可能。田里的桂花树十分茂盛已有一人多高。好多稻田也与自家的一样全栽了这种桂花树。山比以前更青更茂密了。李婉秋不知道家乡正在兴起一轮叫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全域旅游的大变革。
2
有路不走借母溪的山,有女不嫁借母溪的汉。上世纪三十年代,娶不到老婆的汉子们就去借一个同样穷的女人。借来的女人称之为“狃花女”。由见多识广的“狃子客”与山外的“狃花女”谈妥条件,双方签好契约后,“狃子郎”确定好黄道吉日,把“狃花女”带进借母溪。来的时候“狃花女”的眼睛是用黑布蒙住的,由“狃子客”牵到狃花垭才解开黑布。此时,“狃花女”即便是一千个不愿意也无法反悔,找不着走不出大山的路,只能等到生出一子或一女后才能离开。因为穷,曾有几兄弟凑钱雇一位“狃花女”。走的时候“狃子客”会让“狃花女”蒙着眼睛走另一条路娘娘岗回去。让“狃花女”永远也找不到再来借母溪看望骨肉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在借母溪的人也曾想过许许多多的办法致富,比如种木耳、养猪、木材加工等等,终因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不成气候。修公路——全村人用了五年多时间沿溪沟开挖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一次次被山溪水冲断又一次次被借母溪人修复。
在修建这条公路的过程中占用了李婉秋的半亩稻田。半亩地对于惜地如金的借母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村里作出决定,所有村民承担李婉秋每年上邀的农业税统筹费。李婉秋的上缴远不要半亩稻田的粮食,想着自家也受益,便不再斤斤计较。时间到了2006年元月,国家提出废止《农业税条例》。种田不再上邀农业税,也不再收什么统筹费。还对种粮农民进行粮种补贴。
李婉秋找到村长,说自己亏大了。村长支吾着,今后我们村里给你弥补吧!村里写幅标语买张红纸都没钱,哪有什么钱来补助修公路占田的损失?村长只是顺口安慰李婉秋。在占用李婉秋稻田当年,村里就以“水打沙压”向镇政府报损,农业税在那时就作了减免,如今要粮种补贴已没有由头。
眼看儿子李小丑一天天长大,如果接了媳妇就要添一张嘴,有了孙崽又是一张嘴。想到这,李婉秋坐立不安。这天,他又去找村长,村长正遇上有人告黑状,心里不快活对李婉秋讲了几句气话。李婉秋一气之下,把通村公路经过他稻田里的二十来米强行封断。李婉秋认为他这种做法是维护正当权利,没想到却违反了《刑法》第117条之规定,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
李婉秋争辩说,这是当年村里分给我的地,我让出一条公路,让你们冤枉走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收回来,我还犯法了?
公安说,犯了!你犯了破坏交通设施罪。如果你当初不同意,你没事,你既然已经同意修了路,车也通了这么多年,成了既定事实,由不得你现在不同意了。
我做好事还做拐了场?我的损失哪个来补?
一码归一码,我们只管你破坏公路的事,补你损失的事我们管不了。
…………
李婉秋这个问题镇政府也无法解决。镇政府的钱也是一个钉子管一个眼的,哪里来余钱补李婉秋,也只能是嘴巴哄哄。
李婉秋跑省城上访去了。到了省城才知道和市县不一样。“在家千日好,出门点点难”啊,李婉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听不懂别人讲话,他的话别人也听不懂。借母溪的方言说“马骑骡子马有味,骑了骡子骡死人”,语言学家怎么也猜不到这句话是“没吃辣子没有味,吃了辣子辣死人”。
接待李婉秋的省信访局领导说,你这话领导哪听得懂呢,你向领导汇报得学会普通话。李婉秋不知道什么是普通话,呆呆地看着这位领导。领导和蔼地说,就是电视里讲新闻的那种话,你先得好好学习——哦。那个“哦”字,李婉秋觉得很暖阳,觉得省里的干部素质就是比县里市里的高。李婉秋跟着这位领导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有沙发、厕所,客厅里的电视正播放着新闻。这位领导其实是李婉秋他们县里派到省城负责接访的。之所以把李婉秋哄到屋子里来学普通话,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跑,在这里等县里接访的人赶到后把他接回借母溪。还按时一天三餐给李婉秋送来盒饭。第二天,当李婉秋正一字一句跟着电视里的新闻学普通话时,门被推开了,进来了几个讲借母溪话的人,他们是县信访接待办的人。
李婉秋这次进省城上访虽然无功而返,但至少他省了回来的车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上访的经验。
3
李婉秋老婆离他而去时,儿子李小丑三岁。当初结合时老婆就有些不情愿,李婉秋怕留不住。李木匠劝他“有了孩子拴娘心”,慢慢就会好的。如今老婆走了,李木匠又劝说“三脚蛤蟆无处寻,两脚婆娘何处无”?李木匠那张嘴翻来翻去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吃亏当然是李婉秋,身边拖着个小孩,既当爹又当妈,生活在借母溪这个山坳里,每天差不多累得吐血。好在农村的孩子不娇贵,只要肚子不饿,就能像山坡上的树一样风长。眨眼间,李小丑就十九岁了,高中毕业考上了三本的分数线。看到每年学费要一万五千多,李小丑知道他爹拿不出钱,也懒得讲,直接把录取通知书撕了。
农村人,到了二十岁就开始谈婚论嫁。在借母溪这地方,讨媳妇第一关就是看屋,“出门看衣装,进门看粮仓”吗。毛主席也说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家底子不厚实心是虚的。借母溪处于山区,田土都在山间,基本是些“蓑衣块”“斗笠丘”,不能实行机械化。李婉秋一年到头驮着日头出背着月亮入,早出晚归,田土都要被他种出花了。从插秧后,每天至少要去田里看一次,生虫了不?干旱了不?比当年照顾李小丑还上心。村民们给李婉秋起了个美名——劳模。
李婉秋劳模式的种田,并没有引起李小丑的同感,而是跟他唱反调:你算过成本啵?种子农药化肥活路钱开支后,你还赚几个钱?现在一百斤稻谷卖多少钱?除了锅巴没了饭!
李婉秋不搭理,心想,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借母溪这地方,不老老实实种田去干什么?见李小丑说得多了便举例说道:钱钱钱,开口闭口都讲钱,光有钱有什么用?解放那年,你公不是藏了一坛子钱么?你婆还不是活活饿死。人啊,眼光要看远点,个个都不种谷子,有钱也没地方买!
李小丑瘪着嘴不耐烦地说,你看看旁近的,不种地的过得好,还是种地的过得好?
李婉秋有些生气了,鼓着眼睛说,我比你太阳都要多见几个,还没你晓得?“锄头落地是当家”,种地才是最可靠的!古人比我们看得明白,要相信老祖宗的话。
李婉秋固执地认为,只要给李小丑成了家,他就会安心生产劳动。便托人把附近有姑娘的人家一一访问,但女孩子大都外出打工。有的还带着嘲讽的口气回答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哪还要当父母的操心。
李婉秋这下急了,说崽啊,人家都外出打工,你也去打工吧!
我就不相信呆在借母溪没出息,我偏不出去打工。
你不出去打工就在家好好种田啊!
种田能赚钱吗?
听到这话,李婉秋火冒三丈,大着声音骂道:你又不种田又不出去打工,天上的雀雀屙屎到你嘴巴里来了,你不饿死才怪!见儿子不作声,李婉秋又引导性地说,出门不仅仅是打工,是好找老婆,农村姑娘都外出打工,呆到屋里去哪找老婆!你算过没有?借母溪总人口还不到两千,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单身佬还有四十多个!难道咱们借母溪又要回到借女人的那个年代?现在国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哩!
见李小丑硬是没有外出打工的念头,李婉秋只得四处托媒人给他找对象。访来访去,终于访问到坡背有一个女孩子叫张春芳,高中毕业没有外出打工。这家人与寨上的李木匠关系比较好,而且李木匠与李婉秋又是发小。李婉秋提着双份的香酒和糖果找到李木匠。正在吃早饭的李木匠知道李婉秋是为了他儿子的事,心想上次不是回绝了么,怎么又来了?李木匠放下碗故意问道,你这个劳动模范又有什么事啊?李婉秋捏了捏李木匠的手说,还不是那个事。李木匠一边说一边扯张凳子让李婉秋坐下说,劳模啊,你还是去村头找菊花婶,她是有名的红娘,她可以将稻草说成黄金条!李婉秋沉默了一下说,李师傅啊,如果她行我还来麻烦你吗?这样吧,礼品我都买来了,你去,说成了是你的功劳,说不成也不怪你,谁让她俩没缘分呢?看在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份上,你帮帮忙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李木匠不好再推辞,答应说,那好吧,说不成你可别怪我哦!
李木匠提着李婉秋买来的礼品去了,李木匠曾帮这家人起过房子,和主人家比较熟悉。只有张春芳的母亲在家。当李木匠说明了来意后,张春芳的母亲眨巴了几下眼睛,一方面是看着李木匠提去的礼品,另一方面在想象着李婉秋家里父子俩的情景。张春芳的母亲可能是想起来了吧,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闺女大了留不得,不过如今这个年代,孩子们的事也由不得我们作主。李木匠说,李家孩子是个上进人,李婉秋是个肯干人,只是家里没个女人,你家闺女一去就可当家。张春芳的母亲说,李劳模是远近有名的种田能手,我们哪配得上,如果人家看得起,是我闺女的福气哩!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家收了他提去的礼品,李木匠满以为这桩婚事能成。没想到张春芳回到家听说要去种田劳模家当儿媳,还没分清男方是谁就否定了:这年头在我们山区还死脑筋一根种田,能有出息?我才不嫁到这样的人家去咧!
4
李婉秋,1963年12月出生,男性,短头发,皮肤黝黑,身材高大,留八字须。高中毕业,自学过中医,懂得接生。之所以用这么一个女性的名字,说他八字太过强硬尅父母,名字温文就没事了。
李婉秋第二次到省城上访是在秋收后,秋收后农活没那么紧,打算等有了结果再回借母溪。他在一片拆迁区租了个工棚住下来。看到城里个个用手机,花了一百五十块钱买了台二手机。仅从穿着上看,真还看不出李婉秋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特别是他那两撇八字须给人神秘莫测的感觉。
李婉秋住在工棚区,发现一个商机——接生。一些出门躲生的都租住在工棚里,这些人是超生对象。他们拿不出钱不敢到医院去生,更多的是拿不出准生证。李婉秋便印制了“接生”的小名片四处散发,人行道上、菜市场里见人就发,门缝里、车把上一一插上,每天发出几百张。按照百分之一的成功率来计算,收入也比在借母溪种田强。他准备立足稳了后,再把儿子李小丑叫来,在李婉秋看来,能有接生这门手艺在城里讨生活应该没问题。李婉秋的收费没有具体标准,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根据察言观色确定价格。多的上千,少的几百甚至几十元的都有。
李婉秋在省城一边帮别人非法接生,一边抽时间到省信访局去上访,尽管每次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但他还是要去。用时髦的话说是刷存在感。其实,李婉秋这个问题在他第一次到省信访局上访后,县政府就已拿出专项资金给他解决,按当时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的价格予以补偿。因为李婉秋一直没有到当地政府去找,政府又联系不上他,钱拔到镇政府他一直没有去领取。
每次李婉秋到省信访局上访,都是填写一张表格交上去,接待员每次都很热情。遇到“特殊时期”李婉秋就不去上访,他有经验,此时上访是要被强行送回借母溪的。他目睹过,自己也亲历过。
临近春节,很冷!天空开始飘雪,凛冽的寒风像刀割一样,把路人的脖子都割进了衣领里。一大早,李婉秋发完一盒名片回到工棚,便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李医师,你能治月家病吗?李婉秋完全可以回答不会,其实,他真的不会。但听到这个甜美的声音,他改变了主意问道:你多大了,生孩子多久了?于是他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和电视上看到的难民营差不多,简易的工棚里没有空调,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棉被薄得像一张纸,所有的生活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工棚里四处透风,一个瘦弱的女人在哄着“哇哇”直哭的孩子,怀中的孩子应该还没有一岁。女人与李婉秋是一个县的,出来躲生三孩,三孩又是一个女孩子,她怕回去老公还要她再生,便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城里讨生活。
与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比起来,母女俩显得格格不入。家是什么?首先应该有一个能躲避风雨的房子,之后才能谈奢爱和其他。李婉秋没有这么诗意,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做过父亲的人,一个有着儿女情长的男人,他一个人带着三岁的儿子长大成人,个中的酸甜苦辣他是清楚的。
李婉秋对女人说,你每天给我发一百张名片,我给你开五十块钱的工资。这个自称英子的女人接过名片看了看,发现和她手里那张一模一样。从此以后,清瘦的英子每天清晨拿着印有“接生,李医生,联系电话×××”的名片在街头散发,英子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见人就发,而是凭着自己的眼睛“认”人发。
一晃五个月过去了,英子一次次为李婉秋的关心所感动。那天晚上,李婉秋给英子送去当天的工资和一盒第二天散发的名片,英子留李婉秋坐一会儿。李婉秋坐下后就传出轻微的鼾声,一个人来来回回在城里奔波,他太累了。一个男人身边真少不了一个女人的照顾,从脚上那双通了无数个洞的袜子就能看出。英子给他盖好被子,给他把脚下的火箱温度调好。李婉秋就这样一觉就睡到深夜一点被一个来电吵醒,否则,他要睡到天亮。李婉秋醒来看到英子温情脉脉地坐在身边,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我走了。李婉秋得去给别人接生,是一个临产女人的丈夫打给他的。没想到,李婉秋这一走,英子再也见不到他。
李婉秋从英子那醒来就直接赶去接生。女人生产不算难也不算顺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是一个男婴,可是,右手却只有一个手弯没有指头,应该是先天发育不全。当孩子呱呱坠地时,孩子的父母先是一喜,立马就不高兴了,说是李婉秋接生有问题,不仅不付接生费,还要李婉秋赔偿。李婉秋火气就上来了,忘了自己的身份,抓着对方要到派出所讲理。
李婉秋理是说赢,但因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5
李婉秋一大早起床,发现村民们并没有下地干活,手拿锅盖脸盆作为道具在屋檐下唱唱跳跳癲子样排练节目。这是干什么啊?要不要吃饭?李婉秋心里骂道,以往唱革命样板戏的时候,都是利用晚上排练,都不耽误农活,如今田土都是自家的,都拿来栽树长草,唱戏就能唱饱肚子?
忍不住朝排练人群看了一眼,觉得除了儿子李小丑外,别的人都演得不好。便说道,手到哪眼就应该看到哪,你们那像鸡抱食样,演什么戏啊?人家电视上比你们演得好看多了!
后脑勺用花布捆着长头发的指挥,向李婉秋竖起了大拇指说,这位大叔说得对,眼睛要活起来,表情要跟上去。说完又示范了一下动作。李婉秋也跟着做了一下,引来一阵笑声。李小丑觉得父亲在那丢人现眼,朝父亲刮了一眼说,你去做你的事,少在这啰唆!
李婉秋到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有小型犁田机卖,试了几下,最终还是不敢买,那是一台完完整整的拖拉机,他不会操作。还有一个问题是借母溪的田大都是小丘,犁田机用不了。还是买头牛吧,可整个市场没一头牛卖。
回到家下午四点钟,发现李小丑开始吃晚饭。以往四五点钟才吃午饭,特别是夏天,天断黑得迟,晚上八点还大亮的,还没收工。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已落山,在凉风习习中干活是一件多么爽的事。现在没必要了,整个借母溪人以山为背景以晒谷坪为舞台,演绎他们祖先借妻生崽凄美而动人的爱情故事:《狃子花开》……大山里伐木、放排、拉纤,狃子郎李小丑与狃花女张春芳随着音乐声跳起了双人舞。
李小丑不是专业演员,之前从没有上过舞台,就更莫说演戏。但李小丑经过专业老师的培训后,进步很快。双人舞,李小丑与张春芳配合很默契,一进一退,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共同进退,互相促进。在不断艰难拉扯中,最终走到了一起。每一个动作都很娴熟,上演的却是没有春的浪漫、夏的热情、秋的丰盈,冬的纯洁。全剧以崖上思母、狃花结缘、狃子花开、母子分离、四季寻子和多想你六个篇章,剧情跌宕曲折,情节催人泪下。每一个篇章都有李小丑与张春芳的搂抱表演,肢体语言的表达是含蓄而复杂的。
借母溪人看不懂,觉得李小丑与张春芳这样搂搂抱抱的,只有夫妻才能这样。好在他们都未婚,否则,大逆不道要双双沉塘。李小丑一个大后生,张春芳一个大黄花闺女,两人一起演出,时间久了他们之间真还有点那个意思。但没有挑明,前几天李小丑演出时一个跳跃动作扭伤了右脚,不见张春芳李小丑心里憋得慌,不知张春芳怎么想。他们每演出一场有六七十块钱,也就两个小时,一个月下来有两千元的收入,呆在借母溪吃的不要花钱买啊,年终还有分红,这样算起来没有比外出打工差,如果不买房买车,仅日常开支足够了。其实,张春芳没有看到李小丑,像丢了魂样,更是坐立不安,又不好意思来看望李小丑。
李婉秋对李小丑不种田有些不满,但看到一个姑娘和李小丑在舞台上搂来抱去的,内心深处还是十分高兴。儿子没谈过恋爱,不好意思开口,是不是找个媒人上门去说说。当李婉秋把想法提出来后,立马遭到李小丑的反对:都什么年代了还请媒人上门提亲?李婉秋说,你以为我想请人上门提亲啊,只是我担心你得个穿山甲不会剥。李婉秋四处打听姑娘家的情况,访来访去,才知道这姑娘正是之前他请李木匠上门说媒的那个,想起她对种田的态度,他的心里又打起了鼓——七上八下。
李婉秋犹豫了两天后,还是觉得只能委屈自己去求人。什么叫讨媳妇,就是要上门去讨,象讨米一样讨。可是李婉秋找了几个自认为可靠的媒人都推辞了。都说自己不是做媒的料,没这本事。在这关键时候,有人给李婉秋透了底,说不是没有人愿意去给你说媒,是因为修公路的事你得罪了整个村子里的人,人家不愿意帮你。听到这话李婉秋就火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明明占了我的田,我向村子里要补助难道就错了吗?你们是站着讲话腰不痛,占你们的试试看?
有人回答他说,村子里搞山水实景演出,占了达子的院坝,占了修善家的自留地,占了二狗家半亩多田,还砍了明炳家一山的树苗,人家不要一分钱,人家的风格多高,哪像你这样小气。
李婉秋说,人家是人家,人家的家底子你们是清楚的,我容易吗,又当爹又当娘,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们替我想过没有……听到李婉秋这么说,没有人再说他的不是,但内心里还是鄙视他,不愿意帮他。
见李婉秋又来找自己,李木匠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心想,当年你还是劳模人家张春芳都看不上,如今你是牢改犯人家还会看上?嘴里便推辞说,我不是那个料,好好的姻缘要被我说黄的。见李婉秋死缠着他不放,便直说道,如果要成我四年前就帮你说成了,怕你早就抱孙了,还等到今天。心想,一个牢改犯,谁愿意嫁到他家去啊!说不成不要紧,要是说成了,不是害了人家的黄花大闺女。
李婉秋找来找去找不到帮他去说媒的人,他心一横,决定亲自出马。这天他打扮一新,还打了条红色领带。按规矩提着双份的礼品去了。刚好,张春芳的父母都在家,他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和你女儿天天一起跳舞的那个小伙子的父亲时,张家感到惊愕,觉得眼前这个人没有人们传说得那么可怕。李婉秋鼓着勇气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全说了出来。还特别说到自己一时犯糊糊被政府管制了两年,可孩子李小丑没有错,从小没有母亲……说得声泪俱下,不像是来提亲,像来给人家讲一部血泪史。
张家收下了李婉秋提去的烟酒糖。李婉秋喜出望外地走出张家。没想到,在张家门口碰到李小丑和张春芳手拉着手正朝屋里走来。
6
鲤鱼刀刀那个冈/花轿晃晃那个郎/撒尿线线那个片/娶来爹爹那个娘……
溪水细细那个长/狃花姐姐那个香/白肉嫩嫩那个奶/毛条口口那个糖……
以前藏猫猫和办家家的晒谷坪如今成了舞台。关牛的猪圈,堆柴的茅房成了舞台正背景。灯光从后山那密林中亮起来,如北斗七星在山间行走。电子管控的雨水要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从屋檐上流下来。
大着肚子的狃花女孕妇在采茶。一边采茶一边唱着山歌:郎妹好连久相连/连到百岁不断欠/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歌声在山间回荡,仰头间,那著名的经典诗句直击大脑——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
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孕妇不知往哪去,在奔跑途中摔倒,因为是实景演出,在灯光和雨水的作用下,感觉孕妇的血和羊水沿着腿直流,孕妇霸蛮站起来又倒下。那是多么的痛苦与绝望——李婉秋看到这坐不住了,从凳子上站起来大声叫喊,不要急,我来了,我来了,我虽然没有行医证,但我懂!有人在旁边提醒这是演戏,你干什么?李婉秋跑入雨中向孕妇冲去,那孕妇正是他的儿媳张春芳。李婉秋在雨中被人拉住,但他还站在雨中拼命地喊:是不是胎儿头部偏大,平产难的话就剖腹——没关系的,现在医学发达了,不再是女人生产 “一脚踏进鬼门关里”了,不要相信什么“顺产的孩子更健康”“顺产方便生二胎”——李婉秋被送进医院后一直高烧不醒,一直讲着胡话,医生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终于使李婉秋渡过了危险期。出院后,李婉秋觉得身体一下子差了一大节,他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了,他不分白天黑夜的付出,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大把药单。
不仅李婉秋,整个借母溪人不再种地了,他们都参与《狃子花开》的实景演出。李木匠扮演的是从台湾归来寻找儿子的那位老人。腰也弓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这时,他们需要的就是亲人,需要的就是团聚。每个村民都有着各自的角色,每天都重复演绎着这些角色。其实,生活就是如此。
李婉秋听从儿子李小丑的安排。现在整个借母溪的人都得听李小丑的,李小丑是借母溪的村长又是借母溪艺术团团长。
不再种田的李婉秋觉得无聊,种了几十年地的李婉秋适应不了清闲的生活。他主动承担守门的职责,可大门都安排了背上有“勇”字的清朝人员看管,没人听从他的。有一次,他问游客要门票差点被游客打,游客只服“勇”字管理。李婉秋想着帮助打扫卫生,可是各个区域和地段都有专职的卫生员。看来看去,李婉秋发现演出完成后的道具收检最忙,他便去帮忙。可是经他收捡的道具,演员们在演出时要找好久才能找到,说他帮了倒忙。
李小丑给百无聊赖的李婉秋安排当了一名观众。李婉秋说,不要以权谋私,我看戏也算工作?李小丑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现在,每场演出,李婉秋就坐在观众席上,每当剧情到感人处李婉秋就带头鼓掌,带动着观众的情绪。每当戏演到悲情处,特别是狃花女离开的那一幕,李婉秋差不多会放声大哭。尽管时时提醒自己这是演戏,但他总是控制不住情绪,有一次他控制不住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子砸向狃子客,引起观众席上的混乱。此后,他自觉地在当观众时手里不再拿东西。
这天,当剧情上演到伤心处时,听到身后一女人嘤嘤地哭,李婉秋抹了一把眼泪,循着声音发现是英子。几年不见,英子比以前圆润了很多。英子——这是他在省城时这么叫她的,至今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具体在哪个乡哪个村。女人抬起头怯怯地望了李婉秋一眼又低下头抹眼泪。不是英子,现在的英子应该拥有她幸福的家。
人们都羡慕李婉秋,说他有一个好工作,只要坐在观众席上拍拍手鼓鼓掌就可领工资,轻松快乐。可李婉秋却说,工作开心应该哈哈大笑啊,哪有工作起来泪流满面的。

江月卫,苗族,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大学文化,现为怀化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怀化市作协主席。写小说,偶尔写散文,出版有长篇小说《御用文人》《女大学生村官》《回不去的故乡》及散文集《圈内圈外》《风雅湘西》等,先后在《民族文学》《清明》《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绿洲》等公开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江月卫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