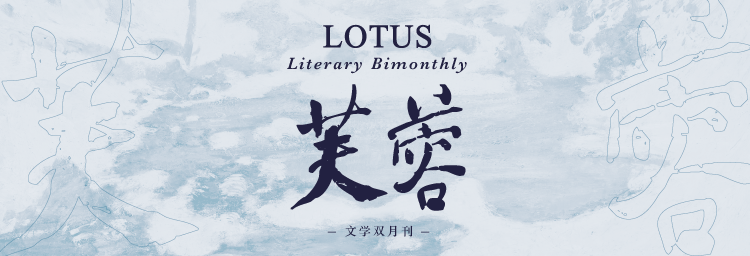

遇见(短篇小说)
文/津子围
比如他就是我——现在我已经上了列车,是靠近车窗的位置。由于上车前的各种紧张,汗液已经偷偷浸淫了内衣的纤维,散发着微酸的气味儿。我拉低了窗帘,遮挡住强烈的夏日阳光,想让自己这个发热的电机冷却下来。
其实,我本来不用那么着急的,真的坐下来才发现,距离开车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没上车之前,希望时间慢一点,上了车之后,又希望时间快一点,最好是屁股刚刚挨上椅子面儿,车身就缓缓启动。
心率恢复到日常的状态,我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我开始盯着陆续上车的乘客,一直到他们在座位上坐下,然后,目光再追寻下一个。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乘客,我希望我身边那个空置的座位是留给她的,我默默祈愿,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还好,今天上车的女乘客挺多,我说的挺多是比较而言的,大概四分之一的比例已经算是挺多了。不知道为什么,旅途上大多是奔忙的男人!
仿佛车厢里亮堂了很多,一位气质和形象俱佳的女士走了过来,她飘逸的长衣后是拉杆箱,女士如我所愿地停留在我的跟前,我的心跳开始偷偷加速。女士抬头瞅了瞅行李架,又低头瞅了瞅樱红色的拉杆箱,我连忙站了起来,帮她把有些分量的箱子托举起来,安全送到行李架上。女士对我简单一笑,算是表达了谢意。她对照着电子客票和座位号。就在我期盼她坐在我身边时,她却将目光转到了另一侧,她坐在了过道另一侧的座位上。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慢慢拉开了车窗帘。
显然,我与这位让我心动的女士擦肩而过。还好,还有乘客连续进来,我的希望还没有破灭。
就这样,我的目光紧紧盯着车厢门口的位置,只要有年轻的女性出现,我都不会放过的。我说的不会放过是指我的眼睛,尽管我的眼睛没有死死地盯着她看,实际上,她的行动都在我的有效视线之内,比如她走路的姿势、查看座位的神态,当然,她衣服的颜色也是很重要的。说了你都不相信,就在她走出六七米的样子,我已经把她和前一位做过比较,也就是与我并排靠另外一侧车窗坐着的长衣女做了比较。是的,她显然不如长衣女漂亮,不过还好、还好吧……长衣女已经指望不上了,她固定在不属于我旁边的位子上,而在没有固定座位的女性中她还是不错的,面孔白皙,眼睛不大,鼻子微微上翘……女孩在过道上谨慎地走着,慢慢向我靠近,我几乎可以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松香味儿。我对松香气味特别敏感,我几乎觉得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种气味。有人喜欢玫瑰香味,有人喜欢檀香味,有人喜欢茉莉花香味,而我尤其喜欢松香的味道,以至于新买的电脑散发出来的松香味儿都令我着迷,我查了一下,知道那些许松香味儿是组装电脑时焊接留下来的。我心里想,来吧,就坐在我身边吧松香女——不好意思,姑且叫你松香女吧。只是……事与愿违。松香女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向我身后走去,我本能地侧过头来看了看,她的确向后面走了过去。难道就这样了吗?不,我还有机会,我认为我一定还有机会。于是,又将目光聚焦到车厢门口,情不情愿我都得将目光搁置在那个旅客上车的入口儿。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可惜来的大多是男性,有青年、中年、老年……终于出现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个子不高,短头发,很干练的样子。也许她对车厢比较熟悉,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没有瞻前顾后,也没有左顾右盼,而是向车厢中间径直走来,难得的是,一瞬间我就感受到她生命的活力。当然,对短发女孩我也做了快速鉴别,我说的鉴别是与前面两个女人比较,我承认,她比不过长衣女,大概也弱于松香女,不过也还好、也还好吧!总归她还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不管怎么说,总比身边坐一个男人强吧!
短发女孩来到了我身边,她抬头看了看行李架下的座位号,又跟自己手机上的信息做了比对,向后看了看,又向前看了看,然后,走到了我前排的座位前,我知道,这个希望又落空了。
车上已经坐了很多人,目测应该超过了八成,而且,离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很显然,实现我的原意的难度更大了。我想,也许我的要求有些不切实际,怎么好事就一定是我的呢?于是,我的标准也开始降低了。说到降低标准,我体会,这个过程不是顿悟而是渐悟来的,就是一点点儿变化而来的,现在我已经不奢望旁边必定是漂亮的女士了,不要说漂亮的女士,不漂亮的女士或者男士也没办法,因为不由我选择。如果是男士,最好是瘦一些、干净一些的,不然狭窄的空间里,我们靠得那么近,我一定会受到拖累。这样说,是不是显得我有些自私,但这确实是我真实的心理。
当然,如果那个座位空置下来最好不过了,空置下来就会有很多想象空间和多种可能性,可以去等待、去唤醒潜藏的内心。问题是,我们这节车厢应该很难有空座位。我想,开车之前一定会坐得满满登登,因为这节车厢既不高也不低,高级车厢的乘客少,大概会有空闲的位子,我们这样的车厢怎么会有空的位子呢?所以我旁边的座位空出来也只能算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吧,就如同我完美地错过了前面的女士一样。好吧,我不再奢望了,男的也行,只要不是臃肿的就行,最好是清爽的、有教养的男人,起码他不会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大家都坐车,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别人会不会也同样在要求你呢!再说,不就是一趟旅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求完美呢,人生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如果凡事都是完美的,就不存在遗憾这个词语了。阻断我胡思乱想的是一个穿着牛仔时装、刀条脸的男孩,他就站在我斜对面,礼貌地问我:请问,您是11排C吗?我说是的,我是C。我的口气带有欢迎的意思。瘦削的男孩子并没有坐下来,他对我笑了笑,温和地叫我师傅,其实我们的年龄也差不了多少,他竟然叫我师傅。他说师傅,可以麻烦您一件事吗?我和母亲一起来的,可座位不在一起,可以跟您调换一下座位吗?我看了看他,他连忙向前面指了指:6排A,靠车窗的位子。我向前面望了望,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既然他说他想跟母亲坐在一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说可以呀。瘦削男致谢的同时连忙带我去前排,那样子怕我反悔似的。于是,我拎着小包裹,跟在瘦削男身后,与上车的乘客逆向而行。
来到6排我才发现,6排B坐着一个体重应该超过250斤的大块头,我心想,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但是既然答应了人家,也不好再反悔了。我和老太太调换好座位,刚刚打理停当,火车就开动了。
伴随着火车运行的节律,我开始观察周边的人,除了我身边的大块头,我把前后左右的乘客扫描了一圈。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张望,还有人在打电话,打电话的声音挺大,大意是我已经安全上车了、火车已经开动了、放心什么的。我身边的大块头,好像是个愿意说话的人,他主动问我,你去哪儿?我说到终点站。他说那你比我远多了,我到山海关。为什么是山海关?本想问他来着,可话到嘴边又溜掉了。本来应该是我先问他的,因为我,真的希望他下一站就下车,换上来一个人,什么人都行……好在山海关还不算太远,大概就是四五站的距离吧。说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乘坐的火车,这趟火车是高速列车,与我之前坐过的绿皮客车不一样,过去到山海关要八九个小时,现在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一方面车速的确加快了,另一方面停车的站点减少了。对于乘客来说,时间短了,就相当于距离压缩了,对不对?我并没有把想的这些与大块头交流,也没有交流的必要,于是我把头转向了窗外,这时太阳还在东边……其实在车上是很难分辨出东南西北的,我之所以判断太阳在东边,是因为时间,现在是上午,太阳自然在东方。有时用时间判断方位,有时用方位判断时间,都是在我们已知的知识里做推断或者认定而已。太阳就在那个位置,无论火车的速度快还是不够快,它还是在那个位置。太阳下面是罗盘一样、一点点旋转的大地,大地上萌动着绿意,还点染着落雪般的花瓣。在淡绿之中,夹着一条蜿蜒的河流,与其说是河流,不如说是一条溪流更准确。溪流波光粼粼,发着明亮的光。我想溪流的流速一定很快,由于有了流速和起伏的落差,所以在阳光照耀下就会抖动着、进而闪耀着。
我扶窗向外眺望时,一股奇怪的味道侵袭过来,萦绕在我嗅觉有效范围之内。我扭过头来——大块头正在啃麻辣鸡脚,喝易拉罐啤酒。见我瞅他,他笑着问我:兄弟来点不?我忙用手示意了一下,我意思是不用了,谢谢。他大概没理解我的意思,拿起一块残肉多一些的骨架递给我,说出门在外千万不要客气。我只好说谢谢,真的不用了。大块头说:别小瞧鸡架,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有熏鸡架、卤鸡架、炸鸡架、拌鸡架……看到我这个了吗?孜然、麻辣、白芝麻,入口满嘴留香。我点了点头,说:别客气,您继续!
大块头继续有滋有味地吃着,还时不时吸一口啤酒,不想,那个场面被后座的声音打断了。后面一位大叔高调地打电话,他大概在谈业务,但他并没有讨价还价,而是讲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事儿,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朋友,这单生意是不可能做成的,你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谁谁是某某的亲戚,连他都出面打招呼了,要知道他非同小可,我们老板要知道他不高兴都得吓尿了。所以呀,你知道我不容易了吧,里里外外反复周旋,容易吗?搭精力、搭人情、搭钱还得搭面子,你自己琢磨吧,干还是不干!给我句痛快话。谈生意的大叔渐入佳境,根本无视身边人的存在,我相信周围的乘客都很反感,不用我说什么,自然有人会站出来。果不其然,我那排过道一侧座位上的乘客站了起来,他扶了一下眼镜,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别影响别人好不好?谈生意的人根本没理会眼镜男,继续大声打电话:还没明白,还让我再说一遍吗?谁谁是某某的亲戚,他出面打招呼,才有了我们这单生意……眼镜男有些恼火,大声说:你这个人素质怎么这么差?能不能讲点公德!谈生意的大叔放下电话,和指责他的眼镜男吵了起来。本来,眼镜男指望大家会站在他那一边,可惜在场的人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说话。两个人越吵越凶,眼看着要动手了。这时,大块头站了起来,他用油乎乎的大手将两人推开:好啦,好啦!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你们大动干戈?大块头出面,随之就有更多的人站了出来,有的对谈生意的大叔说,公共场合你大声嚷嚷就是不对,影响大家休息;也有人劝导眼镜男,算了,别得理不饶人。谈生意的大叔根本就没把眼镜男放在眼里,他说:靠,一副穷酸样儿 ,装什么文明人!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大声指着谈生意的大叔说:你不要无理取闹!就算别人穷酸你富有,真的假的且不论,富有也不代表你有权利,蔑视他人、影响他人……谈生意的大叔白了我一眼,说:我不大声他能听见吗?公共场合,你有权力,我也有权力,我们的权力是平等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动不动拿大道理压人的人!我很恼火,血液直往头顶冲,刚要爆发,被大块头油乎乎的手给摁住了。大块头说:得了得了,理论下去还有头儿?而且没个结果,都少说两句,不就没事儿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双方闭嘴,一场风波就过去了。我也只好自己给自己消气儿,闭上眼睛,平息情绪。说起来,上车前前后后一阵折腾,这一会儿居然还有了疲劳的感觉。书上说,只要闭上双眼深呼吸,心率什么的就会发生改变,人就会慢慢变困。就在我有了困意时,音乐声开始在耳畔环绕,如果那阵音乐是柔和的也就罢了,音乐的节奏激越,特别是那些鼓点,仿佛是专门敲击我的,直至敲击到了耳膜……我睁开眼睛。评定是我前排座位的乘客在放音乐,他一定认为他的音乐是最好的,问题是,他喜欢听的未必别人也喜欢听。我犹豫一下,还是用膝盖顶了顶他的靠背椅子,顶了几下,他没有任何反应,还专心致志地欣赏着他的音乐。大块头大概注意到了,他拉扯一下我的衣角,我看到了他善意的目光。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也许就是放弃理论的后遗症,由于大块头和稀泥,上一场风波是平息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决定去一趟卫生间。去卫生间有两个选择,车厢前面、后面都有卫生间。想的时候我已经向车厢后走去,出于本能而不是判断,往后面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不是想看看先头那两个女孩在干什么?先看到的是长衣女,她大概也注意到了我,我临近她的时候,她竟然抬头看了我一眼,带有幽怨的神情,那眼神令我心动。可惜,我们没缘分坐在一起。隔三个座位就见到了松香女,她大大方方地嗑瓜子,走到她身边我看到,她身前小桌板上放着葵花籽,地下散落着翻白的瓜子壳。我有些失望,我知道那些瓜子壳是最难打扫的,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做,她大概太喜欢嗑瓜子了,可是,她也可以把瓜子壳收集起来,放到口袋里,现在的样子,与她精致的修饰实在不相匹配。她身上散发的松香味儿,不会与瓜子壳有关吧?我继续向后面走去,看到了短头女孩,她正埋头玩手机,除此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注意。
大块头总算下车了,我们彼此礼貌地打个招呼,算是告别。大块头走之后,我就把头转向窗外,我已经不对身边那个座位抱什么期待了,我相信不管来什么人,总比那个大块头要节省空间……太阳升在了当空,我知道现在是正午了。窗外是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在生机盎然的浓绿之中,那条河时隐时现,不过我敢说河流宽了很多,不再是溪流而是正儿八经的小河了,河水映衬着阳光,一闪一闪的,直晃人的眼睛。新上来的乘客是位中年男性,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头顶的头发比较稀少,泛出油亮的光泽——我姑且称他为谢顶先生吧。很显然,谢顶先生是个自来熟,也够诙谐幽默,一见面他就跟我谈起高速列车和普通列车的区别。他说快有快的好处,慢有慢的优点,不过两者不容易调和,就好比是一对夫妻,快车天天担心慢车被撞,慢车呢,时时担心快车出轨,所以,早晚得离婚。讲完,谢顶先生咯咯地笑,他大概觉得很好笑,我倒也没觉得不好笑,只是没有他觉得那么好笑罢了。我之所以判定他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还基于他对邻座的人讲的笑话,不过,遗憾的是,他的诙谐有卡位误差,总有点拧巴的感觉。比如,列车服务员推着餐车兜售中午的盒饭,他就给周围乘客讲了一个奇怪的笑话,他说有个人回老家坐火车,买的上层硬卧。中午听到卖盒饭的声音由远及近,那个人饿了,怕错过了送餐车,一边喊服务员等等,一边匆忙下铺位,忙中出错,一只大汗脚踩进人家送餐车里了……送餐员扯着嗓子喊了一句:9号上铺把盒饭包圆啦……要吃饭的自己去餐车车厢!周围的人笑了起来。谢顶先生讲的笑话不太合时宜,让本来嫌餐车盒饭贵又不好吃的乘客,更不想去买盒饭了。同谢顶先生聊起来,他说他是外省人,从一省——中间隔了两个省——再到另一个省,仅仅是因为一张票。他说我大学毕业那年车票非常紧张,校方问我:你想要的那班火车票如果没有,你服从调剂吗?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没什么社会基础,只能选择服从。过几天,我拿到了票,十分生气地质问:我订的是到江西的票,为什么给我到黑龙江的!校方说:你不是说服从调剂吗?行啊,不都有个江嘛。这回我笑了,笑得还有点苦涩。我问他:现在适应了吧?他笑一笑:快三十年了,已经感受不到适应不适应了。我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我说人生有时候是选择不了的。他说服从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说话都短促且富有哲理,也许火车提速了,时间缩短了,人的交流少了,也简约了。
我不知不觉又有些困,索性再眯一会儿。醒来时,我发现谢顶先生已经不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他在与不在,我并不很上心。我把头转向了窗外,看着窗外的光景……太阳总是摆脱不掉的样子,无论火车开出多远,开得多块,它都在车窗的上方,现在它应该在西方,因为下午时分嘛。离开山区,地势开始平缓,块状的田地呈几何形状,绿色褪去很多,淡绿中熏染着褐黄,还有,那条河又出现了,一副从容舒展的模样,阳光下不再抖动和闪耀,而是一条一条的明亮带子。
事实上,我并没有注意到新的乘客,她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圆脸女孩,我的心随即活跃起来。圆脸女孩在我旁边空出的座位前犹豫了一下,慢慢坐下来,把手提包放在双腿上。我惯常地瞅了她一眼,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头朝车窗外面看。哎!应该是我旁边的圆脸女孩说话。哎……是……阿波吧?没错。是圆脸女孩。我侧过头来:你是?……圆脸女孩笑了,她说还真是你……我是阿玮呀!不记得我了吗?我想了想。圆脸女孩眼睛盯着我说:小学四年、五年级……我说:对对,阿玮,我们小学时是同桌。阿玮笑了起来,她说:真是缘分哪,多年不见,乍一看你根本不像小时候的你。可仔细一看,你怎么都没长出小时候的模样。我说:你可不一样,要不是经你提醒,我还真不敢认你。你是越长越好看了。阿玮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油嘴滑舌了呢。我说:本来的嘛。不管怎么说,阿玮还是满意地接受了我的恭维。阿玮说:现在我们又坐在一起了,你可不许欺负我啊。她这样说,让我联想到课桌上用刀划的分界线,那时候,谁的胳膊过线了,铅笔盒、作业本越线了,就会受到“自卫反击”。我哈哈大笑。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现在我们是大人了,而且我们的空间足够大。阿玮也笑了起来。接下来,我和阿玮聊啊聊,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彼此的现状和处境。我们不仅没有感到拥挤,甚至还觉得座位和座位之间的距离过大。阿玮叹了口气说:唉,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我问她:你说的放弃,是指什么?坚持,又是指的什么呢?她说:很多,你知道的。我想了想,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呢?于是,我也说了一句显得有些哲理的话,我说:很多事,就像手里攥的沙子,越努力漏得越多!阿玮的眼睛盯着我看,脸色红润。
我得承认,我和阿玮聊得很好,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本来是看法一致的问题,交谈起来就变得不那么一致了,也许,关键在于交流的方式,而不是对问题的认知。不过还好,还好没影响我们继续交谈下去。
前面我提到过,我前排座位上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换了乘客,新乘客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我注意到老人时,他已经喝多了,他大概找到了青春燃烧的感觉,光膀子站在座椅上,声音洪亮地嚷着,非要给大家表演一套拳法。旁边有人拉他,尽力劝阻。不劝还好,越劝老人越逞强,仿佛一匹无法驾驭的脱缰野马。这个时候,乘警来到了我们车厢。我以为有人向乘警报案,然而乘警并没有去询问和阻止那个嚷嚷着要表演功夫的人。乘警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仪器,在每位乘客眼前扫描一下。有乘客问乘警:你们在干什么?乘警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们在执行公务。乘警并没有对所有的人进行比对和扫描。当然,我也没找出其中的规律,他检查的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乘警离开了,大家还在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抓小偷,有的说是抓逃犯,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寻找危险分子。阿玮小声问我:危险分子是指什么?我说危险分子是个大概念,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吧!阿玮说:你这样说等于没说嘛。我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努力走进一个套子,再设法走出套子。阿玮说 :你真无聊!
这个时候,天已转暗。阿玮一手拉着我的胳膊一手指着窗外:阿波你看!夕阳真的很好看哦!我把头转向了窗外。夕阳西下,只有远处的天际线上空有燃烧的云彩,大地黯淡了许多,树木隐去色彩,只有迷蒙的轮廓。还好,那条河还在,它已经是一条大河了,宽阔、凝重、平静的大河,仿佛冻住了一般,几乎感觉不到河水在流动,好在它映出了天空的色彩,并且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突然,车厢门口有人喊了起来。我看到,一些乘客向门口聚集。出于好奇,我也走了过去。透过拥挤的人群,我看到一个中年人倒在地上,那人已经晕厥。看得出,围拢的乘客都是热心人,有人提出要掐人中,有人强调给病人中指放血,有人甚至提议做人工呼吸。阿玮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边,她拉了拉了我的衣襟说:别让他们乱来,赶快找医生,这个车上应该有专业医护人员。我立即跑到前头车厢,找到了穿制服的列车员,列车员听明情况,立即用对讲机联系车长和列车广播室。很快,车厢里就响起了寻找医生的广播通知。
火车在一个中等车站停下了,突然发病的患者被送下了车。阿玮也在那个车站下车了。下车前她拥抱了我一下,对我说:我的终点站到了。谢谢你!这一路上,我还是比较充实的。你怎么样?还没等我回答,阿玮说:希望下一趟车还能碰到你!说完她扭头就走,走到门口,转身大声对我说:再次碰到你我们还坐一起,反正,不是你欺负我,就是我欺负你!
也许是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也许是时间太晚了,车厢里的乘客越来越少,我有些疲劳了,闭眼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此刻,火车仿佛向回开去,我也成了一个折返的人。返回的车厢里,我看到了阿玮,阿玮是我的妻子。我也看到了谢顶先生,原来,谢顶先生是我的父亲。而那个大块头,正是我和阿玮唯一的儿子。随着车身的摇晃,我醒来了。我想,刚刚应该是一个梦吧,不然,我怎么会周身大汗淋漓呢?
我在想啊,自己是怎么遇见这趟列车的?早一点晚一点可能都不一样,如果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遇见这趟列车并登上这趟列车吗?缘分是一本密码字典,翻得不认真,就容易错过,可太投入了吧,深陷其中而迷失方向,是不是这样?我们尽可以认为有选择的机会,可事实并不是所想的那样。
凌晨1点,火车进入终点站。
车厢里,年轻漂亮的女列车员正在清理车厢,她走到6排A座、靠车窗一个昏昏欲睡的耄耋老人跟前,轻轻地拍了拍他,对他说:老爷爷,终点站到了,您该下车了!

津子围,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收获季》《童年书》等17部,中篇小说集《大戏》等7部,近百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选载。获《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奖、梁斌小说奖、小小说金麻雀奖、曹雪芹长篇小说提名奖等。参与编剧的电视剧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
来源:《芙蓉》
编辑:陈雅如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