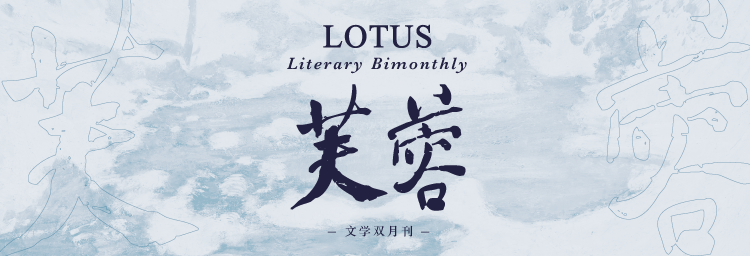

马车(短篇小说)
文/蔡测海
大伢说,我要吃猪。二伢说,我要吃牛。找个名字,当生肉吃,三女伢说,我要吃天。谁吃得多吃得大,算赢。两个哥哥反对:三妹,天不是肉,不算。三女伢说,雷公是玉皇大帝的鸡,吃雷公就是吃天。
童言无忌。童音可动天。雷雨忽然而至,顷刻千条水流奔涌,山为浮舟。又有狂风,揭瓦灭灯,大树折腰,路沉浑流,一线残笔,挂墨雷鸣闪电。
弓子生大伢的时候,就像下了场雷雨,山河变色。弓子生二伢的时候,只像下了场小雨,到生三女伢的时候,只像下场毛毛雨。
大伢会讲话的时候,弓子叫自己的男人,他屋爹。他是孩子,屋是他屋,爹是他爹。屋外头没爹。弓子在火塘边奶孩子,男人看孩子吃奶,弓子说:他屋爹,传一下火,添几根柴,大伢等下就睡着了。男人很听话。大伢学走路,生了二伢。二伢学走路,生了三女伢。三女伢满月,男人要出远门。又远又久。怕是要一年半载,三年五年。那些出远门的伙伴讲,人挪活,树挪死。出门路多,远处菩萨灵。一颗鸡蛋一块腊肉,到集市上才会变钱。带手艺出门,回来盖吊脚楼,到县城买洋房。没手艺,带一身力气,去填海,去扛高楼大厦。回来,不会折手艺,不会折力气。
他屋爹捂着弓子想了一夜,出远门。鸡叫头遍起床,男人一边洗脸一边说:我要把那只铜脸盆找回来。
那只铜脸盆是祖传的。几代人搬迁了几个地方,从一县到另一县,那只铜脸盆从未丢失。来了个过路客进屋讨水喝,见那铜脸盆,三个伢儿当锣敲。过路客拿出一包芝麻饼子,掰开有冰糖。三个伢儿要吃饼,要拿铜盆换。过路客用十块钱加一包饼子,买走了那只铜脸盆。过路客对弓子和他屋爹说:你们什么时候后悔了,就要回去,钱和饼子算送三个伢儿了。有情有义,不让人拿走那只铜脸盆真不好意思。过路客一走,他屋爹就后悔。上哪里去找那过路客?那只铜脸盆从此流落天涯。它在哪里被当锣敲响呢?
弓子拿了双千层底布鞋,让他屋爹试穿,看是不是合脚。给他屋爹做一双千层底布鞋,要费时半个月,先要用魔芋糨糊做棕壳子,布壳子,剪鞋样,用碎布一层一层叠鞋底,用煮过的熟麻绳纳半寸厚的鞋底。鞋面子要选直贡呢或灯草呢。弓子懂他屋爹的脚,像懂自己生下的孩子。他屋爹那双脚爱踩偏,鞋底外侧要加厚一分。树里女人来弓子这里偷样子,就是做不出她那样的鞋,样子不好看,鞋面和鞋底的线缝露针脚,长出龅牙。
鞋要合脚,还要跟脚,才能走长路。
他屋爹燃起杉树皮火把,挑起两只蛇皮袋,一袋衣服,一袋食物。弓子把他屋爹的衣服洗好,缝补被树枝剐破的口子,一件一件叠好,衣裤要勤洗,天凉要添衣。弓子把叮嘱一并叠进蛇皮袋。食物是炒黄豆、煮鸡蛋、腊肉和几样坛子菜。家里能带走的,就是这些。他屋爹挑着两只蛇皮袋,出门上路。他屋爹眼泪没流出来,就开始高兴了,笑嘻嘻的。弓子说:他屋爹,今天当你是新娘,唱一个。
新姑娘
你莫哭
转个弯弯是你屋
屋是大瓦屋
饭是大米饭
菜是肥猪肉
衣是缎子衣
布是绸子布
儿女是龙凤
公婆是金佛
身着新人装
脚踏五彩路
他屋爹接歌:
梦里千条路
一醒一江湖
心记来时路
来去一担谷
命中几粒米
狠劲攒升斗
弓子抱着三女伢,牵上大伢二伢,送他屋爹到山垭口。他屋爹从身上掏出两百元钱,那是卖山货攒下的钱。他屋爹对弓子说:钱留给家里,大伢读书要钱。弓子把那钱先缝在他屋爹衣襟里,要他急用时取出来。人刚出大门,就取出来了,男人就是性急。弓子要他屋爹把钱收好。无钱身不贵。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
下坡。过河。上坡。火把点燃朝霞。他屋爹在那边山上打呵嗬。他还唱了一首歌,他唱什么已经听不清了。
大伢说:爹去赶场了,回来有好吃的。
二伢说:我要吃泡粑粑,油粑粑。
大伢说:我要吃冰糖芝麻夹心饼。
弓子说:你们就知道吃吃吃,回去给你们煮荷包蛋。
二伢问:娘,爹去赶场,逢场天人多,爹怎么认得出爹?爹走丢了怎么办?
大伢说:二伢,你个蠢子,爹又不是小鸡崽,爹是大公鸡,爹还认不出爹?
弓子笑了。这两个伢,真是他屋爹的儿。
他屋爹出远门,日子就像一件衣服撕了个大口子,要细细缝补。做饭喂猪,三女伢抱在怀里。上坡做农活,三女伢背在背上。牛闲着的时候,要大伢二伢把牛赶上坡吃草,放牛回来,要大伢二伢带一捆柴一捆嫩草。二伢不高兴,大伢说:爹不在家,牛不能瘦,柴不能少。没柴火,一家人要吃生饭。
山还是一样绿,炊烟还是一样稠,一切好像未变。在那一个早上,女人和孩子力气变大,成了当家人,个个都是。三女伢也少了些哭闹。
他屋爹从小路走上大路。渴了喝路边泉水,饿了吃几粒炒黄豆。食物要慢吃,路还远。他想起那只跟过路客走失的铜盆,有些字。祖父告诉过他,那些字是人名地名。人名是在路上死去的先祖,地名是那些死去的人经过的地方。他屋爹走过几个地名,在大树下或岩脚宿了几晚。人家的屋檐下是不能睡的,有恶狗,哪怕你是无害通过。
一条缓坡,毛毛雨。他屋爹遇上赶马车的人。上行。马蹄和车轮,往上一尺,倒滑两尺。赶马车的男人在后边推,身子弯成一张弓。他屋爹把两只蛇皮袋和扁担放上马车,帮推马车。比扛木头抬岩轻松多了。马车上了一里多路的长坡。
他屋爹遇上了一个好人。人在路上车,遇上个好人不易。
不远就到了一个货场。马车上是些矿石,在这里装卡车,再运到一个地方,说是炼钨金。比金子贵。金子原来是石头变的,他屋爹很惊奇。
赶马车的人家,是一间铁皮屋。天黑了,雨越下越大。他屋爹没想过自己的鞋和衣服,他担心马车上的东西淋湿了会坏,幸好是矿石。赶马车的人插上电炉子,两个人围着烤雨打湿的衣裤,冒出热气,像两把开水壶。他屋爹脱下千层底布鞋,像泥水里打个滚的小儿,鼻子眼睛找不见了。赶马车的人从坛子里舀出两碗米酒,剥了两颗皮蛋。他屋爹取出炒黄豆,又取出一小坛酸萝卜。赶马车的觉得对不住,又找出一碟小干鱼。一人喝下两碗酒,赶马车的人抹眼泪。兄弟呀,我在那条长坡走了一千遍,你是第一个帮我冲上坡的人。天下啦,好人啦。
打了个炸雷,雨小了。这是一响停雨雷。
赶马车的人讲自己的故事:
我养了一群羊,一百多只呢。有二十几只母羊,再生小羊羔,就是开银行。娶了老婆进门,那个鲜嫩,像剥壳的荔枝。老娘欢喜,添财添喜。欢喜不知愁来。一场大雨,羊淋雨发瘟,一夜全死了。死羊丢了可惜,做成腊羊肉干,不卖,怕害人。自己吃。老婆年轻,壮实像头母牛,吃了没事。我死牛烂马什么没吃过?粪坑淹死的猪也吃过。老娘吃多了死羊肉,病了一场,后来眼瞎了,求仙医也不可复明。
那些羊,是借钱买的,羊死光了,欠债拿什么还?留下瞎子娘和有身孕的老婆,一个人出来了,等我回去,孩子三岁多了,也不知是男是女。中间没回过家,远呢,在十万大山那边。又没挣到多少钱,回去不好见人。
兄弟呀,也就是在那条长坡那里,遇上一个赶马车的人,也是下雨,我帮他冲上坡。后来,他留我,和他一起赶马车,说好管吃管住,一天一百二十块钱,算下来,一年就是三万多块钱。满了一年,那个人要回老家,没结工钱给我,只把马和马车留给我抵工钱。这两年,我攒下十几万块钱了。攒到二十万块钱我就回十万大山那边,这马和马车就给你了。
两个男人挤一张床,两双臭脚,伸到对方的鼻子底下。他屋爹做了一晚梦,吃牛粪,臭啊。
相互闻过臭脚的两个男人,一定会成为好兄弟。你会拥有未来的两双脚印,脚力,千里万里的路。风雨和阳光。两个故乡,你的和他的。你还有歌:朋友一生一起走。
他屋爹留下来赶马车,两个人两股力,冲上坡不难。一只公鸡四两力,两个男人一匹马,力大千斤。赶了几天马车,从矿山到堆场,也就两里多远。他屋爹问赶马车的:把马路修宽些,卡车直接到矿山不好吗?赶马车的告诉他屋爹,路两边全是金丝楠木,还有别的珍贵树种,黄杨木,桫椤树,连一棵草也不好动。只有矿山是一座石头山。天上有卫星看着呢,还有老天看着呢。卫星看人,天看人心。人要是又懒又贪心,就要被惩罚。赶马车的见识多,天上人间的事都知道。
赶马车的人告诉他屋爹,这些石头熬成钨金,钨金炼成卫星,满天飞。马车上运的,是会飞的石头。
他屋爹说:
兄弟,我会唱歌。
你唱吧。
他屋爹就唱:
一块石头飞起来
两块石头飞起来
三块石头飞起来
好多石头飞起来
赶马车的问:还有呢?
他屋爹:还有,唱不出来。兄弟,要一匹好马。力气熬成钨金,炼一匹马。
刚过中秋节,冬天就来了。大雪。好几个冬天没下雪。铁皮屋里,两个男人,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小镇上垃圾场捡回来的。屋外飘雪,电视机也满是雪花。垃圾场捡回来的东西,很贱,打它两拳才会出图像。两拳三拳,打出了新闻联播。又一颗卫星上天了。兄弟兄弟,我们的石头飞上天了!靠火药冲上去的,像放爆竹。
这么大的雪,不知是从来的地方落过来的,还是从这边落过去的。白雪遮了山河,在想象和记忆中,路依然蜿蜒无尽头。
雪是年的信使。过年不差几天,赶马车的人说要回家了。他拆开枕头,一百块一坨的钱,十九坨。二十万差一坨。也够了,按计划是攒够二十万回家。人心要知足啊。还有些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还有几张五十的,也归于零钱。一共一千六百十八块。这些归你了,兄弟。别嫌少,钱就是种子,钱能生钱。马和马车归你了,再过年,你就和我一样,是个有钱人了,高高兴兴回家。回家的事你懂,先和孩子亲热,等孩子睡着了,再和老婆亲热。然后,好好睡一觉。哦,你要用冲上坡的力气和老婆亲热啊。你懂,这个,钱没这个好。你在外边挣多少她不知道,这个她知道。还有,你每次装完石头,再取下一块,这样,你和马都不会太累。要爱惜马。我走了,马就是你的伴。你想说话,你就和它讲,它懂。你想唱,你就和它唱,它爱听。它累了病了,你就给它喝酒,别让它太醉,它只有半碗酒量。你要让它离母马远点,见了母马,它就不和人亲热了。这个畜生,什么都好,就是有这个坏毛病。
他屋爹赶上马车,送好兄弟到小镇上转乘长途汽车,再到省城转火车,再转汽车,下车走半天山路,就到家了。三个人的山村。我给你画个路线图,哪天你想起我就来。
车辙很快被雪盖住了。分手时,他屋爹拆开衣襟线缝,取出弓子留给他的那两百块钱。这是我的心意,给老娘买好吃的,买芝麻冰糖夹心饼吧,好吃。
两个好朋友,在风雪中分手了,没握手那种仪式,也没说再见。说什么呢?
好吃的芝麻冰糖夹心饼,是同那只铜盆连在一起的。铜盆上有地名,人名,路线图,它自己走失了。
他屋爹回到铁皮屋,屋顶厚了一尺,积雪让屋里暖和些,不插电炉子,费电。在那块石头上坐下,冰冰凉。用屁股把石头慢慢焐热。再冷的石头也会被焐热。一块平整光滑的石头,坐上去是凳子,站起来它是一张桌子,摆上饭菜,或者摆上一副象棋。天涯相逢的兄弟俩,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块石头移进屋。他屋爹才把石头焐热,站起来,怔怔看石头,下棋少一个人,吃饭少一双筷子少只碗。石头变成一个伴。那张床,拼了两块板,两个人睡,不太挤。现在一个人睡,把拼的两块板拆了,屋子就不逼仄。铺草要翻一翻,睡板结了,要松一下。像松一下土,庄稼就会舒服。
铺草里翻出一个本子,本子里夹着一支圆珠笔。打开它,会先看到那些阿拉伯数字。那是赶马车的人收支流水账。加号是收入,减号是支出。加的多,减的少。一月一小计,一年一大计。一年开支三千六百块,每天十块钱,早饭三块钱,中饭三块钱,晚饭三块钱。结余一块钱是一个月的酒钱。这些数字记了十几页。再翻,就是几幅画图,一匹马,铁嚼子,笼头,缰绳,没有马鞍,只有牛轭。拉马车的马。铁嚼子是含在马嘴里的铁,和缰绳连在一起,控制马,像控制机器,肉带铁的机器马。两个人一齐用力推马车,冲上坡,其中一个一定是自己,他屋爹笑了。还有一幅图:一个人平躺在床上,旁边放一只碗,一个女的拿勺子喂他。下边有一只鼓,鼓上放一根腿骨。看明白,是一个人病了,女人给他喂汤药。没那女人照顾,那男人的骨头就成打鼓槌了。没看懂,还以为矿山发生了凶杀案。
他屋爹想,兄弟画的那个女的就是她。微胖的小妇人,搭他们的马车回矿山。腿上放一个黑色的大提包,一对奶子摆在那个大提包上。小妇人黑提包拉链拉开,里边全是钱。他屋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黑钨金真值钱啦。小妇人说:这些钱送你们两个,要不要?这话真气人!赶马车的兄弟说:我迟早会把你的钱和人弄到手!小妇人下了马车,在那兄弟脸上拧了一把。说这小妇人出格吧,她那么有钱,不穿金戴银,一身粗布衣,与矿工们没什么不同。说她不出格吧,自己有男人,老是老,不该惹别的男人。赶马车的兄弟告诉他屋爹,小妇人是矿山附近村里人,以前常来矿山卖菜,也拣点好矿石去卖,一次被捉,就成了矿老板的女人。矿老板是外地人,有钱,没钱怎么开矿山?说矿老板以前是盗墓的,还坐过牢。他发财了到这里来,买下一座石头山。他有朋友是搞地质勘探的,给他指了一条财路。他发财了也没忘记朋友,帮朋友买了个地质勘探队长。先前矿山尽是些来路不正的人和智障人,黑矿工,智障黑矿工永远不知道回家,路是黑的。后来,那些来路不正的人合伙抢了矿老板的钱,他去报案,连自己也被警察捉了,再没回来。这矿山就变成小妇人的。她身边的那个老男人,是她的勤杂工。她留下那些黑矿工,又请了些安分守己的本地人。她让警察帮那些黑矿工回家,分给他们一些钱。矿山的黑矿工没几个了,警察找不到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老死在矿山。小妇人打算修一处矿工养老院。
那天也是喝了两碗酒。他屋爹听赶马车的兄弟讲矿山的事,说恶有恶报,恶人很丑。善有善报,心善的女人就是漂亮好看。赶马车的兄弟说,这里连石头都是公的,男人堆里一个女人,一人看一眼就看成仙女。
雪没停。积雪一层层变厚。老家的竹子被压弯。松柏树成一幢一幢银色的雪屋,鸟和松鼠躲在雪屋里。
大伢二伢开年就要上学了。要做新衣,要做书包,三女伢也爱穿花衣服了。弓子请了裁缝进屋。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男孩。裁缝师傅手艺有名,接媳妇嫁女,都请他师徒俩。请手艺人进屋有讲究,好酒好肉招待。手艺也真是手艺,又快又好。三天工夫,两个书包,三套衣服,都做好了。还剩些布料,再给他屋爹做条裤子。人好几年没回来,不知胖了瘦了,等他屋爹回来再做吧。大裁缝说:比着我的做吧。弓子说:就怕他屋爹穿不合身呢。
结裁缝工钱。两个伢儿上学要钱,工钱要差点。弓子对裁缝说:钱有点紧,等卖了猪崽,年后结清,赶场天给你送去。大裁缝连说不要紧不要紧的。
晚上好酒好菜招待那师徒俩,弓子和三个伢儿在一边端着碗吃,没上桌。三个伢儿一人碗里放了片腊肉。
弓子屋里屋外忙了一天,三个伢儿睡了,她收拾好碗筷,也睡了。梦见他屋爹从山垭口那儿回来,敲着铜盆子,打锣一样。
大裁缝等徒弟睡着了,起来,踅到弓子床边,解她的扣子,拿剪刀剪开她的裤子。
弓子模模糊糊的,他屋爹?睁开眼。你?!大裁缝说:顶针不见了,我找顶针。三个伢儿也吵醒了。弓子对三个伢儿说:师傅说顶针不见了,你们拿他的顶针没?
弓子穿好衣服,点上灯,拿了剪破的裤子扔给裁缝:碰上剪刀鬼,把一条好裤子剪破了,给我补好。
天没亮,大裁缝叫醒徒弟,收拾好行头,走路。徒弟说:师傅,工钱还没结呢。大裁缝说:这回手艺没做好,东家骂我们是剪刀鬼,我们快走,还结什么工钱?
下雪天,不闲着,女人扎堆做针线活,做鞋的,来弓子屋里偷个样子。做双好鞋,等男人回来穿。谁家男人,就是谁家他屋爹。
他屋爹,鞋子穿烂了,还不回来?
那双和人一起远行的千层底布鞋,还是半新,回到铁皮屋,冬天暖脚。别的季节,他屋爹把鞋用旧报纸包起来,放在枕头底下。矿山的报纸都是旧报纸,他屋爹也认不得多少字,用它包东西正好。他屋爹用旧轮胎皮做了双鞋,赶马车穿上它不会打滑。结实,他给那位兄弟也做了一双。赶马车的兄弟穿走了那双鞋,留下一个酒坛子和半坛子酒。
少了酒伴,再好的酒也难喝。那天,赶马车多跑了两趟,人和马有些乏。他屋爹舀了一大碗酒,半碗洒在马草上,半碗自己喝。马闻了闻草料,打个响鼻,吃草,舌头像镰刀割稻子。好酒,兄弟,我俩慢慢喝。累了易醉,他屋爹趴在马槽上睡着了,做梦,问弓子,屋里进来什么人了?看不清脸,过路客?
小妇人每天搭他屋爹的马车回矿山,黑提包里装的是钱,不会是别的。矿山没银行,那么多钱,放在枕头里?那得要多少枕头?
每次装马车的,还是那个智障人。他是矿山最后一个黑矿工,他没有来路,像从某地飞来的一只鸟,落在这里,再也飞不回去。他把大块小块的矿石装上马车,装好后,再取下一两块,每次都这样。他屋爹赶马车离开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说一声:哈扎。他屋爹不明白那个人说的是什么?哈扎?是路上小心?一路走好?用力?辛苦?马?马车?他屋爹回一句:哈扎。那个人笑了,白牙,黑眼珠。一点不像智障人。
那天装完最后一趟马车,他屋爹一边用手比画一边问那个人:你,喝酒?他摇摇头,哈扎。哈扎,就是不要?那个人说:哈扎。他指了指胸口。他屋爹问:哈扎是你心爱的姑娘?那人又指了指天空。他屋爹问:云?那个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他屋爹突然像被针刺了一下。哈扎,回家?你说的哈扎,就是回家?哈扎——回家。
他使劲地点头。他屋爹紧紧抱住那个人,那个人像被雨打湿的流浪狗,筛糠一样地发抖。
他屋爹问过小妇人,那个人家在哪里?他想回家。他对我总是说哈扎,回家。小妇人告诉他屋爹,那个人不会说话,问不到他是哪里人。他也许是个孤儿,一直流浪。他在这里,矿山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只能这样了。
每天收工的时候,小妇人会来搭他屋爹的马车,有时是专程送小妇人回矿山。这成了习惯。这一天,小妇人没来。天快黑了,他屋爹没吃饭,等着。等人的时候不饿。
很晚,月亮爬高,小妇人坐一辆小轿车,到堆场那里下来。然后那小轿车像狗追急了的黄鼠狼,跑了。小妇人一嘴酒气,骂王八蛋。女人骂起人来很凶,喝起酒来也很凶。在矿山没人见她凶过,她管钱,就是管生死簿。不凶,像观音菩萨。谁能惹观音菩萨呢?王八蛋才敢惹,王八蛋都是些狠角色。小妇人要他屋爹过来扶她。过来呀,扶我一下,就当我是你兄弟啦。他屋爹扶着小妇人进铁皮屋。她还在骂,骂完王八蛋,就说这铁皮屋里好臭,跟你那兄弟一样臭。自从你进了这铁皮屋,我就没再进来过。你那兄弟是怎么走的?是让我吓走的,我讲要给他生个儿子,他就夹着那条东西跑了。臭。她找出那半坛子米酒,来,兄弟,喝,喝死那些王八蛋!他屋爹抱过酒坛子,一仰脖子,半坛酒倒进肚。
他屋爹醒了,一身精光。小妇人说:你吐了一身,我给你洗了擦了。你想得到的地方擦了,你想不到的地方也擦了。你不是也给马洗身子擦身子吗?人畜一个样。
他屋爹说:洗什么洗?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小妇人说:看你那躺倒的样子,就想你那兄弟。他病倒在床上,我给他洗澡擦身子,喂汤喂药。没我,他骨头棒棒都打得鼓了。跑什么跑?男人再狠,一病一醉,就是一摊稀泥巴。
小妇人不要送,走路回去。
他屋爹对马说:兄弟,今天放一天假。不喝酒了。没酒喝了。马甩了几下尾巴,它懂。除了不会讲话,它什么都懂。
小妇人好几个月未来。他屋爹想,是躲他吧?到一个晴天,小妇人来了,人瘦了些,也白净了些。她抱着的不是那个黑色提包,是一个孩子。她把孩子递给他屋爹。
你看看,像谁?像不像赶马车的?
他屋爹抱着孩子,这么小的人,就会笑。他好生惶惑,不会吧,怎么回事?
一连几天下雨,那一里多的长坡很滑,难走。马上坡不会停,它知道一停马车就往后退。每趟装大半车矿石,冲上坡容易些。到第三个雨天,人和马都有些吃亏。那位装车的智障人兄弟,说声哈扎就跟着马车。他这回说哈扎,是帮忙的意思。他屋爹问:兄弟,你帮马车?冲上坡?他屋爹把一句话拆开,让智障兄弟好懂。智障人兄弟点点头。智障人兄弟要帮忙冲上坡,他才多装了两块大点的矿石,那是诚意,是出力的理由,冲上坡,他必不可少。
一里多的长坡,马车上了大半。雨下大了,淋得人和马睁不开眼。马突然停下来,不到万不得已,它不会停。马车直往后退。智障人兄弟大喊:哈扎!声响如雷。哈扎,这回是挺住的意思。
马突然跪下去,然后倒地,马车翻了。智障人兄弟一掌把他屋爹推出一丈多远。马车和矿石压在智障人身上。两千多斤重砸下来,一头大水牛也受不起。
他屋爹冲回智障人兄弟身边,把他从马车下拖出来,雨水和血水,像是一个人在水里同一条大鱼搏斗过。他屋爹抱着智障人兄弟,他睁开眼说:哈扎。声音微弱。
哈扎。他屋爹呜咽着说。
智障人兄弟只说出一个哈字,人没了。
马嘴里吐着血泡子,闭上眼睛。他屋爹喊了几声兄弟,它没睁开眼。它再也不会站起来。一匹好马,会和马车死在一起,路死路埋。他屋爹先取下轭,又摘下马笼头和铁嚼子,最后脱下缰绳。他屋爹对马说:我把那些东西从你身上脱掉,你去做一匹快乐的马,找一匹好母马,生几匹好马驹,告诉你的孩子,别再拉马车了。
雨停了。
小妇人抱着孩子,赶到铁皮屋,她身边跟着一个男人。小妇人说:兄弟,你看谁来了。
是你?
是我。
那位赶马的兄弟回来了。他要小妇人娘儿俩先回去,我要在铁皮屋里住一晚,兄弟俩说说话。
不插电炉子,那些话把铁皮屋烘得很热。
瞎子老娘死了。那女人,像剥开的荔枝,鲜嫩,跟耍猴子的跑了。屋前屋后长了一人多高的蒿草,大黄狗还在,从蒿草中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不怕你笑话,兄弟,我哭了,我又回来了。兄弟,好马不吃回头草,兄弟,不怕你笑话,那回我得伤寒病,是那个小妇人救了我,后来,她偷我,给我生了个儿子。她做到了,男人狠,女人更狠。她先头那男人,是杀过人的,她不怕,叫我也不要怕。命嘛,真不算什么。那个恶男人 ,后来被抓,毙了。
兄弟,我以后还赶马车。兄弟,我和你坐在马车上,马走到哪里,人就到哪里。兄弟,不要你帮我冲上坡,你只要唱歌。你唱起来真好听。你这样的嗓子,就该上电视。
他屋爹说:兄弟,我想唱歌给你听。
你唱吧。
他屋爹唱:
哈扎,哈扎,哈扎
白云底下
我和兄弟坐上马车
哈扎,哈扎,哈扎
芝麻冰糖夹心饼子
绸子缎子布
腊肉瓦屋苞谷酒
金山银山大太阳
哈扎,哈扎,哈扎
两个男人挤一张床,两双臭脚,伸到对方的鼻底下。脚臭,脚印也会臭呢。日子里也会有臭味。
日子就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好月亮,小妇人在堆场那里放了张桌子,摆上十样菜,一坛酒。各人喝了两碗。小妇人问他屋爹:兄弟,你来矿山多久了?他屋爹想了想说:下雨下雪加上晴天,一共一千三百零九个日子。小妇人点了点头。兄弟,你该回家看看了。你想你的兄弟,再来。这矿山,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你兄弟百分之三十,你小侄子百分之三十,还有百分之十给那些矿工。你嫂子我呢,给你们管钱。
天亮,他屋爹还是两只蛇皮袋上路。一只蛇皮袋是马笼头、马嚼子。另一只蛇皮袋是衣服和一只黑色大提包,小妇人给他的,要他回到家才能看,路上不要打开,要对马车发誓。
赶马车的送他到小镇上,坐长途汽车。没那些告别仪式。
进屋,弓子愣了一会儿说:他屋爹,你?回来了?
三个伢没喊爹,不敢,怕是过路客,怕是请来的裁缝师傅。
弓子对三个伢说:你们的爹回来了。三个伢没叫爹,抢着打开两只蛇皮袋,看有没有好吃的。再去翻那黑提包,打开,一大包钱,一百块一扎,一大堆。
大伢说:好多钱,要吃什么有什么。
二伢说:你又没喊爹。爹,我要好吃的。
三女伢说:钱又不是好吃的,我要睡觉。
三个伢睡了,他屋爹问弓子,这屋里怎么有生人气味呢?
弓子说:你鼻子灵,家里请了裁缝进屋,你都闻出来了。
来了个老叫花子,一身干净,不像个要饭的,托着铜盆子。他屋爹一眼就认出那只铜盆子。是那过路客变成老叫花子,还是老叫花子从过路客那里得到这只铜盆子?
他屋爹问老叫花子:铜盆子卖不卖?多少钱都行。
老叫花子说:不要钱,只要吃的。
弓子留老叫花子吃过饭,给他十个糍粑、十个煮鸡蛋和一大包炒米。炒米里偷偷放了三百块钱,装一只蛇皮袋,打发老叫花子上路。
真是那只铜盆,地名人名在那里,生了些锈。他屋爹用火灰擦,越擦越亮,原来是只金盆子,那些人名地名,亮得像星星。
他屋爹把金盆子和马具拢在一起,锁进一口楠木箱。隔些日子就打开箱子看看,摸一摸,一件一件清点,再锁上。
到家的东西,别飞了。

蔡测海,1952年出生于湘西龙山。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三世界》《套狼》《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地方》,小说集《母船》《今天的太阳》《穿过死亡的黑洞》等多部,累计近千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庄重文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蔡测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