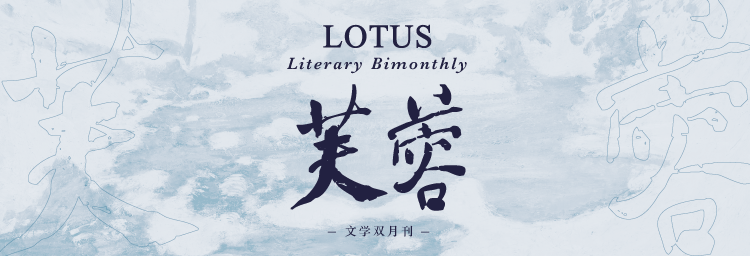

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篇小说)
文/万宁
一
我家小金是在国家宣布开放三胎政策的那个晚上死的。它死得很难看,也很难受。张开的大嘴涎水四溢,全身不停地抽搐,它目光里那些潮湿的眷恋,使我一度崩溃,我哭得稀里哗啦。它躺在它的沙发上,阖上眼睛,又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一下,似乎在等什么人,它这眼神看得我又号啕起来,我知道它在等谁。
我豁出去了,打个电话会死吗?他怎么样也曾自称是小金爸呀。可这个电话真的难打。我发过誓,一辈子不再理他。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离婚五六年了,我从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家里有关他的东西,我全扔了,独独当初他从别人家抱回来的小金没扔。小金奄奄一息的眼神不容我多想,我在电话联系人里翻出白金汉,毫不迟疑地打过去。他显然很意外,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片空白,似乎正走出房间,然后我才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
喂——丁冬青,是你吗?
声音还是那样,厚实里带些嘶哑,只是听上去老了几岁。声音也是跟着人一起老的吗?我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只有小金凄惶的眼神,一开口,哭声就淹没过来,我忍了忍,把哭声吞咽下去。
我站在十六楼的玻璃窗前,吞咽了好几下,才开腔。我居然离题万里地打趣他:
这个时候给你电话,没有影响你弄三胎吧?
忽然镇静的语气还是难以掩饰根深蒂固的戾气,隔着若干路段若干建筑物若干绿化带与人工湖泊,我清楚地看到白金汉脸上的错愕。我没让他的错愕停留下来,很直接告诉他:
小金要死了。
这话一说出,世界出奇地寂静。窗玻璃上的自己,瞪着黑洞洞的眼睛望向我,接着我听见白金汉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问:
小金有十二岁了?
白金汉说得没错。他离开这个家时,小金还是壮年,活蹦乱跳的。家里少了一个人,小金想不明白,它还忧郁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些事我无法跟他起,只说:
小金好作孽,一直强撑着不肯咽气,它在等你。
话说完,我无法不哭。我抱着小金低声抽泣,小金艰难地想伸出它的爪子安抚我。电话里寂静无声。我们的关系让我无法开口,请他来看小金最后一眼。
妈妈在世时,对我不生孩子恨得咬牙切齿。我也记不清,我是从何时起,铁了心不要孩子的。当然,我不养孩子,活在这世上,总要养点什么。我没那么变态,没养蛇、蜥蜴、花猪什么的,我养狗,是只金毛,是那个时候的老公白金汉从朋友家抱回来的。小东西一来,蓬荜生辉,笑声像流水样在屋里荡来荡去。我们自称小金爸小金妈,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妈妈说我们是一对哈宝。对我更是没一句好话,她眼睛横成一条线,还不忘用手戳我的脑门子,说这里边进了水,往后有你苦果子吃。我那个时候目光短浅,根本看不见未来,以为年轻漂亮撞着我了,我就永远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想过老的事,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会老,要老也不会老得很厉害。
在我老得不是很厉害时,我的苦果子来了。白金汉的爸爸病了,是那种不治之症,他躺在医院不积极治疗,而是经常拉起儿子的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见祖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其实,这些话,白金汉听过多次,可是在病房听的效果就不一样,他被触到某根神经,深深自责起来。不要孩子是他提出来的。住在一起时,我接连怀过两次孩子。他说烦,不想要。他三姊妹,上面两姐姐,都早早生了孩子,他嫌孩子吵。他不喜欢,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去医院把孩子流了。一切好像理所当然。与白金汉在一起的头几年,那真是快活,不上班的节假日都可随心所欲地打发,去西藏去青海去云南,去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喊走就走。疯了好几年,日子才稍稍安静,我妈说,你们消停了吧?一起做个正事吧,赶紧生娃!白金汉听我妈这样说时,脸上常常万里无云。还没结婚,他就跟我说,我们做个丁克族吧。丁克族是啥,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可是在他爸爸住院后,他反悔了。我那个时候三十七八了,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刚开始我嘲笑他,说他是个叛徒,可是多走了几趟医院后,我沉默了。他爸对我说,他抱不到孙子,死不瞑目。我去医院取了节育环。喝着各种调理身体的中药,甚至还去了医院的生殖中心,进行人工排卵,准备做试管婴儿。所遭的罪,比我从前的快活要多得多。我心里喊着,太不抵了。在这个时候,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
我的四十岁过得暗淡无光,这个岁数,不知为何成了一个忌讳,没人敢提起。白金汉脸上除了愁云,还游移着纠缠的情愫。我那个时候,一心一意想着怀孩子的事。我好想找个人吐槽,可是我的同龄人都处在陪孩子进入高中阶段,家里的大哥大姐已容不下我的任何吐槽,早在好多年前,他们就把丑话撂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去说,那就是找骂。倒是我妈小心翼翼,与我不再说孩子的事,甚至还说,没孩子没什么,可省好多心。她还打比方,说像她生了仨,累人不说,还操透了心,结果没一个领情,哪个不是白眼狼?我知道我妈的用意,可她说的是大实话。平心而论,子女对父母总是一味索取,而且还以为是天经地义。父母也是人啊,也想按自己的想法来活,问题是很多人一旦做了父母,就没了自己,一代人又一代人都重复着这种生活方式。
我在四十岁这年的末尾离了婚。
我的闺密妮妮与白金汉一个单位,在一个蚂蚁也想恋爱的春日,她约我吃饭。这饭吃得吞吞吐吐,感觉她的表情畏畏缩缩,言语顾左右而言他,弄得我猜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朝她瞪眼睛,说妮妮,你他妈干吗?有屁就放!少废话!妮妮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结巴了好久,突然眼睛一横,说本来是想少管空事,可偏偏是你,我做不到不告诉你。她伸手过来,狠劲地掐了我一把,说你难道没感觉,身边的人出了啥状况?我的心往下落,想过无数次的事,到这个时候真的就出现了。这世上,相信誓言的人,通常是傻子。不等妮妮把事情说出来,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泪过于肆无忌惮。妮妮静静地观赏,不时地递上纸巾。其实,最后她要说的,大家都可以猜到。白金汉外遇了,找了一个看上去土地肥沃的年轻女人。白金汉没看走眼,次年,她就生了俩儿子,双胞胎。至此,尘埃落定,白金汉的老爸满意地去见祖宗了。
二
过了凌晨,门铃终于响了。小金耷拉的耳朵颤了颤,白金汉蹑手蹑脚地走到沙发前,半蹲下来,低声呼唤:小金,小金。小金撑开眼皮,眼珠浸泡在泪水里,它失了一阵神,忽然张开大嘴,呼呼地喘起粗气,很显然,它认出了白金汉。此刻,它一只爪子搭在白金汉肩上,无助地喘气,还呜呜地哭泣,哭泣之时,不忘吐出舌头舔他的手。我眼睛一下就潮湿了,环抱小金的狗头,说好了,好了,爸爸回来了,你放心了,他回来了。我拍抚它,控制住它战栗的躯体。几分钟后,小金呜咽的声音细若游丝,最后就彻底平静了,身体也软塌下来。我知道它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睁着空洞的眼睛,泪水如虫子般在我脸上乱爬,脸花了后,我号啕起来,我完全把小金当家人了。这些年,与小金相依为命,多亏了有它,要不然,人早就抑郁了。我哭得昏天黑地,完全失去自控,白金汉本来也陪着流泪,可是哭着哭着,他发现这场哭泣是有情绪的,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这样一想,泪就干了。而我的哭声仍有些声嘶力竭,他几次伸手过来,没有落下又缩了回去。他环视着这个屋子,家里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窗台上摆满各类多肉植物,看样子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像那么回事。
哭声在白金汉环视房子时细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夜深人静,这哭声会吵到邻居,还会引来很多想象。我抽噎了几声,算是这场哭泣的结尾。见我开始平静,白金汉松了一口气,他的手在小金的尸体上来回抚摸,然后望着我,说你节哀,我先回了。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故障,听错了话。可是白金汉真的往门口走了,我气得朝他飞起一脚,他嗷嗷叫了两声,一个趔趄,往前跄了几步。这两年我的泰拳还真没白学。我气鼓鼓地横在他面前。
小金,怎么办?
埋了呀。
小金七八十斤,我背得起吗?
要你背什么,喊一个人,不就得了。
喊谁?就算喊人背走,他会埋了吗?扔垃圾桶里?万一狗肉店的人捡去煮了给人吃了,不恶心吗?
白金汉显然没想那么多,他移步客厅,坐在小金面前发着呆,我在凉台与房间里来来回回找东西,一把铲子,一大袋小金平常的衣物与玩具。我说,我们把小金埋到江边去吧,只有那里的土松软,好挖洞。
白金汉见我给小金穿了件背背衣,挂上狗牌与铃铛,还郑重其事地给它戴了一顶投胎的帽子,然后把它装进一个超大布袋。他吞咽了一下口水,问,不会是现在就去埋吧?
这事就只能月黑风高去做。白天,能做这件事吗?随便来个部门,都得整死你。我心里有股恶气,朝白金汉扑过去。白金汉还是觉得这事他做不来,又问,这么大的枫城,别人家不死狗吗?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殡仪馆不可以火化吗?
我问遍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电话问过殡仪馆,被他们骂了回来,那是人最后安息的地方,狗怎么可以来?这是对人的侮辱!
这回白金汉咂起嘴来,说这宠物从出生到养,都一条龙了,要什么有什么,还花样搞尽,独独到了死,就断链子了。
感慨归感慨,白金汉还是被我逼着,背起小金出门了。想着白金汉的车平常要坐娃,我让他把小金放到我的车后座,我的车是一辆天蓝色的牧马人,空间比较宽大。我们把车直接开到湘江边,市区灯光亮的地方,显然不方便挖洞。沿着湘江向南,过了资福寺,在江堤大道上飞驰。
六月的夜被江风吹得冰凉如水。
二三十分钟样子,我们就出了城,湘江沿岸黑黢黢的,走了一段后,我把车停在路旁,白金汉把头向外探了探,直接下了车。我以为他会拿铲子,下江堤去挖洞。车停的地方,江堤的斜坡上是一片树林,旁边除了芦苇,便是草地。白金汉对着湘江撒了一泡尿,然后,燃起一支烟,风掀起他头顶上几根稀薄的毛。别人说离了婚的人,虽然陌路了,但某些时候是不晓得避嫌的。就像现在,白金汉居然在车边,堂而皇之地拉尿,一点都不害臊。我气鼓鼓地拉开车门,拿出铁铲,对着还在那儿抽烟的白金汉说,别闲着了,找个地方去挖洞。白金汉铲子倒是接住了,人却站着不动。江风穿过树木呼啦啦地往我们身上吹,这片江滩属于未被开垦的野地,此刻浸在夜色里,无边的诡异风起云涌。
这个季节,蛇出洞了吧?白金汉像是在问,又分明是在自语。
他还是胆小,这些年没变一下。我不得不发出嘿嘿的嘲笑声,自己已经往堤下跳了。只是身体被白金汉的手扯住了,他喊起来,你听我说,小金埋在这儿不好,湘江时不时涨大水,指不定哪天就被水冲跑了。
他说得有道理。这一点,我还真没想到,一根筋地想着沙滩上的洞好挖。我停止了往下跳的动作,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问:那把小金埋哪儿去?一会儿天就亮了。
他把烟蒂往风中一扔,零星的火光在地上虚弱地飘散。这时,他一脚踩上去,还碾了碾,火光沉入夜色不再发亮。也不知他发了什么癫,他坐上了驾驶座,说坐边上,我来开。
去哪儿?我问。
一个开满梨花的山谷。
白金汉打起火,开启高德导航。我系上安全带,说都六月了,梨花早成果实了。没想到白金汉接过话,说总有又开的时候啊。我抿了抿嘴,不再发话。白金汉喜欢梨花、李花,不知是不是与他的姓氏有关,从前没问他,现在问就冒昧了。这样想的时候,瞌睡来了,这一晚的折腾,我根本就没闭过眼。也不知谁给的胆,五六年没见,坐着他开的车,我安心地睡着了。从前自驾游,常常这样,他开车我睡觉,这会儿像是回到从前的某个片段,我什么都不管。
睡梦一直在山里绕,重峦叠嶂的黑影子东摇西晃,一个大拐弯,又一个大拐弯,几乎颠断了我的脖颈。我常常在这个时候,微微睁开眼睛,白金汉在一旁专注地开车,窗外是汽车奔驰的声音,然而无法抵御的瞌睡最终又把我拉了回去。如此重复多次后,我像个失去知觉的废物彻底沦陷。之前在睡梦里,我都不忘伸手放倒了靠座,适应了颠簸后,这种沦陷竟成了一种自由松懈的梦境。梦境里山岚飘在森林、藤蔓之间,梨花漫山遍野,风从山谷旋空而来,我忽然就跑到了一棵梨树下,看空中扬起的花瓣,白茫茫的,如同漫天飞舞的雪。这时,我似乎又有了记忆,能清晰地知道现在是六月,于是心里一惊,飞来一词,六月飞雪。天哪,这是什么预兆。
没由来的一激灵,我睁开了双眼。本想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什么的,却被吓得一弹,什么鬼!我面前瞪着一双人的眼睛,而且是男人的眼睛。我来不及尖叫,这男人不咸不淡地说了声早上好!接着皮笑肉不笑地说,几年不见,睡觉还是这样没心没肺。我坐了起来,尖嘴薄舌地问,有心有肺的觉是啥样子?白金汉哈哈几声,能怎样,睡不着啰。说着打开车门,跳了下去。晨光柔美地浸泡在这片土地上,山谷间几栋农舍点缀在花海中,潺潺的流水在山林间回响。没容我缓过神来,白金汉转身给了我一个回眸,他招了招手,说发什么呆?赶紧下车吧。我刚跳下车,就有一农民装扮的人迎上来,他朝白金汉喊着,稀客,稀客。接着对我作了个揖,叫了一声嫂夫人。我尴尬地别过脸去,听见白金汉叫他老曹。
三
几个屋场错落在林间溪水边,我沿着石板飞奔起来,在一面土墙上,我看见四个字:梨花古道。字是用黑色细石拼起的,旁边堆着劈得规整的柴火,几个风化了的车轱辘,各式陶罐,陶罐里养着铜钱草或是一两朵睡莲,一盆盆兰草摆在墙檐下。我陡然明了,这不是农舍,是深山里的民宿。人间到处有仙境呀,我摸出手机,拍了几组照片,才发现此地没有网络。现如今没网络的地方真是少见,这里四面是山,山峰上滚过一浪一浪的浓雾,东面近处的山坡上长满清脆的竹子,窸窸窣窣地在风里翻浪。白金汉与老曹站在我的背后,似乎也在看山,我没回头,却能猜到他们脸上陶醉的表情。
别磨蹭了,快给小金找个地方。白金汉的声音传过来时,我泄气我猜错了。他才没心思看风景哩,他急着要回枫城。这样想着,我就随他们踩在大石头上跨过溪水。老曹回过头来,告诉我溪水叫梨花溪。我眼里立马有一条淌满梨花的溪水。如此一想似乎就镇住了,这惊艳捆住了我的双脚,我站在那儿,忍不住抬头,看清澈的溪水在各种石头上奔腾,两边水草、青苔绿得深远,只是梨花在这时只是个影子。白金汉在高处的屋场吆喝,我看到一栋废弃的烂屋子,西边的土墙垮了大半边,门窗裸露。老曹扯动着嘴角,说破吧?其实越破越好,梁、瓦、窗、门才好做设计,有足够的空间发挥,这种土坯房最好脱胎换骨了。我疑惑地走进这栋破房子里,厅屋居然躺了两副棺木,一股凉风劈面而来,吓得我连退两步。老曹笑了笑,说空的,空的,是这房子主人的,他们一个九十三了,一个八十九了,都住到山下儿子家去了。我定了定神,抬头看见这家人的神龛上还留着好些东西,敬神的香炉、神位、蒙了灰尘的旧照片,神龛后边是楼梯间。我似乎还想上楼,却被白金汉喝住,上去干吗?不怕垮吗?我灰头土脸地出来了,站在这破房子的前坪,坪里长满野草,黄色的山菊与鼠 草点缀其间,几棵树枝繁叶茂。老曹指着靠东边面溪而立的一棵梨树,说就埋在这儿吧,以后装修整理时,这些树是不会动的。梨树长得气势,树冠如盖,脆玉般的青果挂满了一树,特别不一样的,是在它的树干上,攀缘着深青色的藤蔓,藤上颤颤悠悠地吊着没梨光滑模样像梨的小果果。老曹说,凉粉果咧,昨晚见他们在井边“椤”凉粉,等会儿可吃上。我心头一喜,口水不请自来。我环顾四周,还看到一棵桑树,忽然就叹了一口气,这户人家当年栽树也太随意了,家里有梨树不说,还来棵桑树。我这样感叹,老曹呵呵笑起,上次问了村里老人,都说之前没有,是鸟衔来的。那就是天意,有桑葚吃,也不错。鸟吃一半,人吃一半,蛮好哈。
这样闲聊时,白金汉与这里的村民抬着小金过来,洞眨眼间就挖好,他们把那个袋子放了下去,我也跟着跳到洞里,拉开拉链,摆正小金的头,捋了捋它的毛,双手合十,说希望你能喜欢这里,来世投胎做人。白金汉把我拽了上去,说好了好了,别太作了,人家还有事。他这种语调撞到我的泪腺,我很不舒服,低下头退到一边。我站在另一棵树下,碎碎的小白花正在风里飘,飘荡的还有浓烈的花香。我凝视这青绿色的叶子,片片朝上,油亮油亮的,像一双双绿手正接着光线,那些枝头上一球一球的白花,在这个季节差不多将要散尽。伤感就这样落到我心里,小金已经归于尘土。老曹过来,拍了拍树干,说这是棵老树,叫冬青。
这一刻,不只是我惊到了,我相信白金汉也惊到了。他错愕着一张脸,对着老曹用怪异的口气问,你说什么?
冬青树,又叫蜡树。这个叫梨花古道的山村,家家户户门前喜欢种的一棵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但不管怎样,我要感谢白金汉,是他带我来到这里。冥冥之中,又觉得这是小金的引导,是它的选择,是它的安排,它就想长眠在一棵冬青树与梨树之间。冥想也在这时随着凉粉果的藤蔓攀爬起来,对面沉静的山峦,延绵起伏,沿着梨花溪,若隐若现的青石板已被茅草覆盖,但路基在那儿,一条青色的古道随溪水往山里蜿蜒。
早餐的时候,喝下放了陈醋与红砂糖的凉粉,我半天没回过神来,什么琼浆玉液,太好吃了。软糯糯的,凉飕飕的,只在嘴里停留一下,就滑溜下去,那不能言说的仙气,就一直缭绕在喉头。老曹似乎在等我发出惊叹,我撇了撇嘴,说今天不回枫城了,我要在这儿住两晚。这显然比他等待的惊叹更让人惊叹,他鼓起掌来,说太欢迎了,嫂夫人这是请都请不来的稀客。白金汉嘴里刚放进一个清水鸡蛋,他摆着手,示意他要说话,可是那个蛋还没完全咬碎,开不了口。我横了他一眼,对老曹严肃着表情,说我与姓白的离婚多年,请不要叫我嫂夫人!
餐桌上静默了一秒钟,白金汉也吞下了那枚清水鸡蛋,他说你抽什么风,你不回去,我坐什么车回去?
很不适应别人用这种语气与我说话,心里的火噌噌地冒烟,但我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我管你坐什么车回去。白金汉站了起来,嘿,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讲理了?
我莞尔一笑,脸比刚才更冷了。讲理有什么好?先前与人讲了十来年的理,也没啥好果子吃。
老曹坐在一旁尴尬起来,走开吧,又怕两人干起来,他只得伸出手,拍了拍白金汉,说我这儿正好有车要回枫城,你别急。
(节选自2022年第1期《芙蓉》中篇小说《这个世界会好吗》)

万宁,女,湖南岳阳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株洲市作协主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作品被多家选刊多个选本选载,出版《忙来忙去》《今夜有约》《流逝的花样年华》《走进清华》《麻将》《纸牌》《讲述》等著作。
来源:《芙蓉》
作者:万宁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