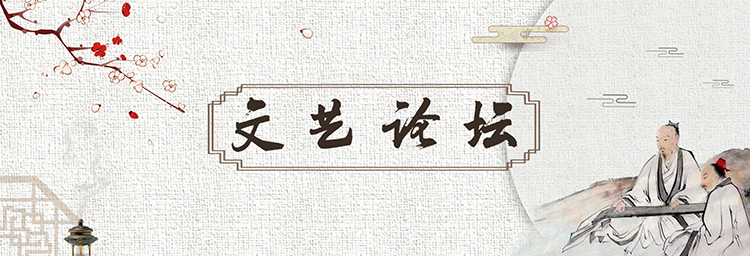

“转业之谜”的阐释潜力:对沈从文研究的反思
文/牛煜
摘 要: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文学史时段,其创作成果也就“顺理成章”地分属于两个学科。文章通过对“沈从文转业之谜”这一极具象征性和症候性的事件的阐释和分析,力图呈现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的路径与历时过程;并以“转业事件”为阐释契机和参照点,反思沈从文研究的范式转型及每一研究阶段的“洞见”与“不见”。
关键词:沈从文研究;“转业之谜”;阐释学价值;研究综述
一
沈从文作为横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大陆主流的文学叙事里是被压抑的。1953年,解放前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中各书均因为内容过时,凡是已经出版和未出版的书稿及纸型,都被代为焚毁。{1}几乎与此同时,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以较大篇幅专章论述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的专章研究,主要借鉴英美“新批评”的阐释方法,细读沈从文的几个短篇代表作;并在与左翼文学的对比中凸显沈从文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怀。夏著视野宏阔,将沈从文与济慈、福克纳、华兹华斯作比来说明沈从文现代性批判背后隐含的道德意识。考虑到夏氏师法利维斯构筑“伟大的传统”的宏愿雄心,被择入史的小说文本均为沈从文小说中“有机性”最强、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基于此逻辑,夏著通过对其精心选取的几个片段的细读,完成了沈从文小说“经典化”的关键步骤,同时也将沈从文锁闭在“成熟的”1930年代前后;19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困境也就自然而然不为夏氏论述所及。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被公认为沈从文小说代表作的《边城》和《长河》在夏著中都被草草处理,一笔带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较之规模较小、有机性更强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的中长篇小说明显有着更多的“裂隙”和无法被整合的“冗余”。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受其成书的时代背景(“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偏见制约而不无某些有失公允的判断。利维斯对有机文本的品鉴背后所附带的精英色彩和意识形态诉求也被夏志清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巧而不巧的是夏著隐含的二元对立的评价形态与1980年代大陆“新启蒙”之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某些取向不谋而合:1980年代以来大陆的沈从文研究大多对其文学活动做“一刀切”的“断裂式”论述,以“压抑——转业”的图式证成某种文化逻辑和政治权力重叠时的粗暴、武断。沈从文的“文字生涯”在这种阐释之下就变成了文学/文物两个判然分明的部分。这种有着鲜明的“新启蒙”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证方式一方面赋予现代文学道义上的崇高性;与此同时也将其锁闭在凝固的“经典领域”。“沈从文转业”的阐释潜力也就随之消耗殆尽: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结构迁移的简单比附无疑是以牺牲沈从文本人的创作实绩的内在丰富性(同时也是歧异性)为代价的;外在宏大结构的框架将个体创作经验吸纳的同时也对其做了必不可少的删削和化约。经此“化约”——突出强调“牧歌小说”和《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短篇小说——沈从文就变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毫无疑义”的、没有任何“瑕疵”的经典作家。简言之,“沈从文转业事件”在此解读之下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则证明历史“怪兽性”的注脚,而不再是关乎作家个人创作本身的“文学”事件{2}——我们原本也可以将其读作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难以为继”的具体显影,也即暴露沈从文文学内在悖谬性的“契机”。
如同夏志清的“小说史”实践可以被“纯文学”研究的批评家拿来做“去政治化”的借鉴,后冷战时代对“历史终结”的玄想,也貌似与沈从文曾经在《时间》(1935)等散文中隐约传达出的对“时间”终将获胜的思考路径内在契合。因此,沈从文创作成熟期(通常认为是1928年到193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小说文本就在“非历史”的、“纯文学”意识形态的通道中成功蜕变为现代文学史上毫无争议的“经典”作品。沈从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去而复返”,“沈从文热”的持续发酵,似乎也证明了经典作品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经典之作也就随之变成了“完美的”沈从文文学的最佳说明——一如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西渭的《边城》论所显示出来的那样。
依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繁杂多样的文学是怎样一步步被推演为“无瑕”的经典之作的:立足于“有机作品”预设的沈从文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极为抽象的语词(如“人性”“文明批判”等),从而逐步证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经典性。但是纵观沈从文小说在民国时期的接受史和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文学从来都不是“不成问题”的。苏雪林、林茨、侍桁等人就沈从文小说的文体、修辞、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过不同程度批评和反思,更不用说后来的左翼文化人对沈从文作品展开的某些不乏洞见的批判。因而,与其说如此“完美”的“人性牧歌”是毫无疑义的“共识”,毋宁说是学院批评的模式(或者不如说以学院为主的话语生产)使“牧歌”逐渐纯洁化和经典化的:学院批评或者研究的基础正是一系列被视作“完满”状态的“有机文本”(学院派倾向于援引刘西渭的说法而忽略其余论者颇有见地的批判观点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沈从文对自己作品的某些评断和阐释,明显要比那些反复称道他文体的完美、思想的深刻的作家和批评家显得公允。在校改1934年10月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边城》时,沈从文写下这样的文字:“看过这书后半部,无聊。我应当写得还好一些。”{3}由此不难看出沈从文本人并不认为《边城》像刘西渭形容的那样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4};他显然明确感受到了《边城》结构上的失衡。在后来写下的一篇自传性文章里,沈从文认为刘西渭关于《边城》的评论“自得其乐较多,而对作者生活作品却无多兴趣”。“自得其乐”再明确不过地点出了刘西渭对《边城》的赏析式评点的非客观性;就像沈从文所暗示的,与其说这种评点是针对作品而发的,不如说更多的是对评鉴者自身 “品味”的自指。{5}
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现在几乎已经习焉不察地接受为“常识”和“公论”的,对《边城》所作的“人性牧歌”式的读解显然也无法解释沈从文多年后对《边城》的创作缘起所做的补充说明:“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6}也就是说,像刘西渭那样将《边城》“有机化”甚至“物化”(“珠玉”)的做法,很难在文本现象学的有机层面之下读出文本本身可能存在的内在的“不完满”,立足“接受效果”的品鉴也难免忽视私人经验在进入文本的体制规约时所可能存在的龃龉和周旋。打破这种凝固的、封闭化的“有机”幻象的切实可行的批评方法是王德威、吴晓东等人着眼于“文本生产”层面的批评策略:王德威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看到的“自然”效果和“自然化”操作之间的分裂,{7}吴晓东在《边城》“所说”和“所示”{8}之间看到的“裂隙”,都有效地回应了沈从文自己暗示出的《边城》结构不圆满的说法。
与对《边城》等牧歌小说的反思可以相提并论的研究成果,是近些年来以钱理群、贺桂梅、姜涛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四十年代”/“转折的时代”的文学进行的细致的重估与阐释,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文本才凭此契机再度引发新的关注,其“转业”也才被看作是某种“创作困境”的自然延伸而不简简单单是历史转轨的“对应”与“牺牲品”。应该说,“四十年代”之所以能够“作为方法”,主要还是得益于“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和对“纯文学意识形态”相关反思的深化。在这种知识视野的启发之下,聚焦于“有机文本”的经典阐释和价值评估活动所掩盖的重重悖谬随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作家文本/作品的凝固形态才被还原为文本形态与社会现实存在之间复杂的“斡旋”与“交涉”。
即便如此,作为方法的“四十年代”视野的“洞见”依然无法掩盖其“短视”。聚焦于“四十年代”的“局部”现实及其相关文本的批评实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放长了“沈从文转业之谜”的观照视野,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割裂作为整体的沈从文的创作实绩的弊病。换句话说,“四十年代”的创作困境的凸显,势必要建立在对1928年至1930年代中期沈从文那些最具“有机性”的文本的“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基础之上 。“四十年代”作家与现实之间焦灼的互动关系只是更清楚、直接地暴露了《芸庐纪事》《雪晴》系列小说的“破碎”形态,而《边城》《贵生》等小说的“牧歌”表象则远远地“逸出”了社会学、历史学所能直接和盘托出的“背景”基底;沈从文小说的整体性还是没有能够获得有效的“统观”。因此不难理解对“转折的时代”加以分析的论者对沈从文身份作的又一次“分割”:从“小说家”到“思想者”;{9}如此一来,好像“小说家”沈从文的创作是成熟的、圆满的,而“思想者”沈从文的困境就在于他没有把“思想”完美地文学化、形式化。
应该说,任何一种对作为整体的沈从文“文字生涯”(不妨策略地借用萨特小说的题名)的分段讨论——无论是从“小说家”到“思想者”,还是从“文学家”到“文物研究专家”——都无法涵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作为一个有着成熟的文体意识的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实践——无论是就小说创作,还是就他的文论来看——有着非常清晰的内在理路。因此,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笔记、日记——凡此种种都应该放到“现代文学”这个装置之中来对它们进行统一分析。正如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所启示我们的那样,“现代文学”作为一套全新的装置/话语体制,内在地就充满了种种悖谬和不圆满。因此无论是被“有机化”为“艺术品”的《边城》,还是“议论”与“叙事”割裂的《芸庐纪事》,乃至完全散碎、不成秩序的《烛虚》集,都是经由“现代文学”的装置生产出来的。《边城》《长河》在阅读现象学层面呈现出的和谐整一的效果,不过是因为那些“裂隙”被很好地“秘藏”在文本的肌理之中罢了;通过对原文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正如王德威、吴晓东、刘洪涛所做的那样——这些“裂隙”还是能够被还原出来的。
因此,作为一个具有认识论价值的事件,“沈从文转业之谜”的意义就在于它以职业转换的方式将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实践整一化了。在1948年致吉六的一封信中,沈从文表示自己因为“情绪凝固”,缺少变通能力,因此“终得把笔搁下”。{10}这里的“凝固”显然不仅仅指的是“情绪”方面,更重要的是该词还指涉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时期通过写作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自洽的“话语秩序”;在进入“当代文学”的时候,这套话语秩序直面了另一套完整、成体系的异质“话语”,竹内好所谓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显然意指的就是这套全新的文学话语。这套话语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与“现代文学”的整套认知模式是极为不同的。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认识“契机”,“沈从文转业之谜”也明显地显现出了沈从文文学的“内在困境”。这个困境同样由“凝固”传达而出。与这个“凝固”具有相近意义的概念大概就是沈从文四十年代以来反复运用的“抽象”一词。如果说沈从文作为小说家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印象主义”式的写法(夏志清、聂华苓均有此观察)所呈现出的纤细的“情绪的散步”,那么四十年代沈从文完全舍弃了他的这项天分而蜕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观念家”。这种“抽象”不仅见诸沈从文的杂记、哲理散文,也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叙事性散文、小说创作之中——他越来越观念化地描写人物和呈述事件而不再“现实主义”地去逼近表现对象。原先那些经由小说叙事“形式化”的“观念”“主题”,在“抽象”的思索之下,全部变成了一些没有生命力的、前后不一的僵硬概念。“现代文学”体制的内在悖谬原本在“小说”形式的经验论的、感性的表层之下隐而不显,到四十年代则全部脱离了“婉曲”的形式直接呈现为概念之间的断裂和矛盾。
二
上文我们回顾了沈从文小说被“经典化”和“有机化”的一系列具体步骤,也进一步释放了“沈从文转业之谜”本应具有的阐释潜力。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沈研”成果。在“沈从文转业事件”的后视视角的启发之下——尤其是该事件的“转折点位置”所带出的“断裂”与“延续”的问题视野——我们将看到这些各各不同的阐释方案具有哪些“洞见”,同时又有哪些“不见”。
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11}在同时期的沈从文研究成果中显得公允而充满洞见。一方面,赵文没有简单地将沈从文从“现代文学”的体制规约中抽离出来,而是意求探索沈从文是如何以其复杂的文本策略达至共同的“现代”处境的。赵园精确地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指认为一套经由复杂曲折的修辞策略建构而成的“话语”。另一方面,沈从文精心构筑的乌托邦话语并非像初看去那样和谐完美,反而是充满着“裂隙”的。沈从文笼统地征用“感性/审美”领域批判现实境况,其简单甚至罗唣的文化主义姿态在赵园看来无疑是“贫困”而非现代的。换言之,沈从文表面上的无功利的审美主义悖谬地变成宣吁另一种善恶观的道德主义。但是,赵园没有将沈从文困囿于“事实”和“价值”层面之间进退维谷的处境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反而简单粗暴地将其悖谬归结为中国作家传统心理的“节制”。这无疑大大削弱了赵文的反思力度。毕竟,是“现代” 发明了“传统”,“传统”在现代的流通本就不是一仍其旧的。
王德威的沈从文研究,是近些年沈从文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12}看来,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是对五四以来“露骨的写实主义”创作潮流的一种反拨,沈以其融写实、抒情于一体的小说质疑了写实和抒情在语义语法上的“拟真性”,并通过隐喻的层面召唤诗意同时启动反讽。但王德威过度强调沈从文文本的“表层构造”,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先验地预设了中心和边缘的空间位置,从而遮蔽了两者之间的动态沟通关系。而且王氏的“抒情”话语因其“解构”意图过于显豁,显得大而无当、漫无所指,难免悖论地滑向他所警惕的本质主义。《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13}同样如此。以其对《抽象的抒情》的解读为例:显然王德威没有将“抽象”这一语词放置到沈从文四十年代以来的创作谱系中加以细致考察,反而以这篇文章中单薄的“古典”一词为中心发微,勾连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论述——以沈从文的表述来看,“抽象”仅仅意指与事实相对的价值层面,而非王德威大加引申的摄物取象;沈所意指的抒情也非准古典抒情根须而毋宁说是厨川白村式的“苦闷的象征”。王德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式的解读无非折射出海外汉学地缘美学的某些征象。而且王德威过于强调沈从文的孤独的、格格不入的位置,忽略了沈从文积极融入彼时话语脉络的良苦用心,沈从文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造性误读”的潜力也并没有被王德威发掘出来。悬浮的“史诗时代”在王德威笔下仿佛自空而降的一股暴力,沈与这一时代的“相遇”非但没有揭示出某些潜藏的危机,反而成了沈从文“超越时代”的“经典化”契机。颇有象征意味的是王德威频频将沈从文与本雅明作比,只不过他并不深究二人对“时间性悖谬”的体悟与书写,反而不断演绎、神秘化沈从文类似于“天启”的“启悟”——异常复杂且难以言尽的“历史境况”被王德威做了超脱的“抽象”。
相较于王德威空泛的“抒情式”解读,史书美{14}的研究显得更加切近实际。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细剖精研对史书美的影响随处可见;史著质疑单一刻板的西方式“现代”话语的一个绝佳例证就是“京派”作家的现代表述。在“京派”作家的书写中,“现代”脱离了本质化和抽象化的刻板背书,“在地化”地展开为目的性表述和批判的现代性之间的无休止的驳诘和协商:现代主体就“镶嵌在” “地方语境”和西方普泛的“文明”话语之间。虽然史书美没有具体论述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但是她对沈所倾心师法的废名的解读对于我们思考沈从文的创作语境/困境来说是极具启发性的。
沈从文本人的具体经验是怎样影响其创作的,沈从文的作品又是怎样“再现”他芜杂的经验世界的?长久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显得过于笼统和浮泛,用丸山昇的话来说就是只注意时代的“大环境”而忽略作家最私我的“小环境”和“大环境”之间的交涉和互动。解志熙的《爱欲书写的“诗与真”》{15}索解沈从文本人的情感轨迹和其作品呈现之间饶有意味的“对应关系”,意图说明沈从文“厨川白村的”力比多升华技术,甚至大胆地推测沈的乡土抒情之作均是对其“被压抑的爱欲”的转喻。就这样,沈从文面貌各异的作品都被统一到这条由欲望驱动的轴线上。这样大胆的归纳法最大限度地将沈从文的创作聚拢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其粗糙的文本发生学只能被看作一种抽象的、无法落实的理论预设。与其细细追索沈从文复杂难解的情感经历并对“女主角”一一指认,还不如用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文本经济学细读沈作的裂隙及其文本策略。而且一言以蔽之的“爱欲”论述难免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从而抽象地擦除了沈从文与“现代文学”的联结及其交涉。
近些年来,张新颖的沈从文研究渐成规模。《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两书分别记述沈从文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主要经历。如何将前半生、后半生统一为一个作家的一生,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中的主要论述似乎给出了答案。张新颖选择《从文自传》作为“精读”沈从文的开端显然有深意存焉。沈从文自《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在张新颖看来,正是这个得到的自我,昭示着沈从文全部文学活动甚至全部生命的“展开”。张新颖用一种后见之明的视角给予了《自传》“创世纪”的地位,于是沈从文的漫长人生在张的论述下只是呈现为不断导向这个“中心”和“伏笔”的复杂奔走。这个被张新颖视为“找到的自我”的“自我”仿佛成为一个本质性的、圆满自足甚至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地点”。但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自我”是一个“地点”,一个本来就存在于某个未知点、一经找到就“圆满”的本真存在,毋宁说“自我”是经由一套复杂的话语发明出的“阐释技术”。关键的问题在于索解为达成这个“自我”,叙事者动用了哪些阐释策略和隐喻,而不是同义反复地说找到自我就是“得其自”。与张氏“自我”同等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透明”,张新颖认为《湘行书简》中沈从文的“看”是没有任何预期的、没有任何目的的“看”,是一种直接的“看”。但是张新颖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看”就意味着“看到”,而“看到”意味着“视角”;现代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看”是直接、透明的,张所谓的“直接”无非说明沈从文找到了一个近似透明的“中介”用以重新观看世界,沈从文之后的创作困境或者说认识论盲区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看似“透明”的自我设定。用张新颖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沈从文的核心方法就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16}但为张所忽视的恰恰是这种“移情式”/认同式论述本身的限度——如果亦步亦趋地跟随沈从文的论述进入他的文学世界,那么最终也只能是同义反复地合理化沈从文自己书写的前提和预设而根本无法发现其中存在的种种悖谬。唯有“距离”才能带出批评视野。
如何在作家论中兼顾作家的“私我”诉求和他身处其中的“外部”环境,是近些年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再好不过地满足了这种理论诉求。可以说,正是凭借着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四十年代”“八十年代”才能作为“问题与方法”源源不断地释放其丰富的阐释潜力;文学文本的历史形态分析才取代了机械的反映论图示,从而更为有效地显示出文学内部、外部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沈从文转业事件以其象征性的过渡形态镶嵌在“四十年代”内部,因而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把它作为个案,以期呈现出“转折的年代”的丰富面向。姜涛的《“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17}和路杨的《“新的综合”:沈从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与实践——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18}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两文都将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本放置到彼时的文化氛围中加以考察,都看出了沈在四十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文体实验——姜涛将其指认为某种“困境”,路杨则从这一系列丰富的文体实验中识别出沈从文的“综合”意图。然而粗粗地将某种所谓的“困境”孤立地限定在四十年代显然是不充分的;仅仅从“失败的尝试”中看出“不足”也显得过于“就事论事”。而且路、姜两位作者在行文的过程中都不免带有一种后见之明式的“叹惋”——如果不是在遥远地平线那一头有“曙光”的征象,那么这种“叹惋”恐怕也不会发生。换言之,历史的事实层面在带来澄明的同时,也埋下了目的论的诱惑——“综合”“有机”“完整”在后世看来总是“更好的”。
总的来说,“四十年代”的“再发现”很大程度上源自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范式”困境——如何对现代文学史的经典文本作“历史化”的还原和重读,同时兼顾研究者自身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显然是“四十年代”的文学视野带给我们的教益。
注释:
{1}{3}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第180页。
{2}这种立论方式在纪念沈从文的文集《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论文题目中的“沈从文转业之谜”的提法就来自收录于该文集中的汪曾祺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详见巴金、黄永玉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5}{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第27页。
{7}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5页。
{8}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67页。
{9}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贺桂梅在《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中对沈从文身份“转变”所作的分析。参见贺桂梅:《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章。
{1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11}{12}该文收入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章。
{14}参见[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章。
{15}参见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17}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18}路杨:《新的综合:沈从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与实践——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2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牛煜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