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空诗歌中的直观生命哲学
文/刘邦朝
如何读诗?理论家可能会给你讲很多学理批评的知识。但是,诗人会告诉你:“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说这句话的是云南诗人子空。在子空老师的这句话启发下,我想到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的“直寻”概念,钟嵘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诗歌创作应该表达真切的审美感受,不假雕饰,堆砌典故,形象生动鲜明,追求质朴无华的自然之美。细读子空老师发表在《诗刊》《边疆文学》《诗潮》《大家》《诗选刊》《汉诗》《诗歌月刊》等文学刊物上的部分诗歌之后,顿感在思想表达、艺术特点上无不显露出“直寻”特点。“直寻”既可以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理想技法,也可以作为读诗的一把钥匙,即可以直接走进诗作而不受外界的干扰。从哲学的维度考量,这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直观”学说似有一些关联之处,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先验感知学”的开头,将直观说明为:“不管一种知识是以何种方式并凭何种手段关联着对象的,它与对象直接关联所依赖的那种东西,以及作为‘关联对象’之手段的那一切思维所集中瞄准的那种东西,就是直观。”此外,子空老师的诗歌似乎还和齐美尔的“生命直观”理论有某些暗合之处,按照德国哲学家齐美尔的看法:“生命不是实体而是“活力”,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在子空的诗中,一定程度上也涌动着这种“永恒的冲动”,它是来自诗人对生活中各种生命对象感性把握和对其本质理性审视的结果,诗人一再告诫我们,应该俯仰审视自我存在的意义,特别是要关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非对立性的关系。可以说,子空以一种“直观”哲学的视野凝视生存和灭亡、肉体与灵魂、个体与他者、空间与时间等等这些命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看来,这组诗歌的意象都隐喻着诗人对生命的直观,其核心主题是对生命、疾病和物我存在关系的剖析批判。
一、生命的隐喻——蚂蚁与大海
直观生命的困难在于,人类总是以固有的知识和历史前见看待肉体的存在,人像是一只掉进知识泥淖和历史前见中的“蚂蚁”倍感挣扎,活在自我制造的“理性”眩晕中。
“小蚂蚁啊/小蚂蚁,我踩死了你/我知道吗”(《偶感》)子空这首小诗可谓是“随手拈来”却又出人意外,按照正常的思维,最后一句应该是“你知道吗?”但诗人摒弃了这种“推己及物”的惯常性思维,而是反求叩问“我知道吗”。诗人善于反观自我,一种“自我意识”立刻显现出来,一般来说,“蚂蚁”与“我”并不是某种必然的联系和映衬,也不构成某种对立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可以自我指认的主体抱着独断的理性意识弃绝了对其他物种的思考与关怀,这类似于细菌和病毒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人只有饱尝疾病的困扰才知道生命健康的重要,可笑之处就在于“人们通过笨拙的推延支持自身的价值意志。”人们总是理性的看待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最为致命的是还死守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愚昧规则。“蚂蚁”隐喻了小写的“人”,“我”则代表了一种大写的“人”,象征着一种能够摧毁“人”和世界的力量。人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状态,无法走出残缺和无知的囹圄,始终被固有的历史前见和有限的知识束缚。在《自以为是》中,子空写到:“有人说,溪流一生向往江河/江河始终向往大海/而我突然发现,溪流不知道江河在哪里/江河也不知道大海的存在/所有的流水,都漫无目的/大海只是守株待兔”。在这首诗中,“大海”的隐喻意义在于它属于一种具有无限性的空间,犹如一张命运的大网,遮蔽了基本的自由,它布满了令人恐惧的气息,人类犹如迷途的“兔子”,惊慌而又软弱无能。从更为深刻的角度说,认识的有限性和知识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例外状态,那是一种反对和撤销意义存在的思维之所在,体现为生命个体直面自我的生与死。在死亡与不朽面前,对肉体长存追求的执拗与狂热反应了“人”作为一个有限生物的基本事实,子空是按照“生命本身所塑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生命直观》),这种塑造是以知识和权力的规训实现的。在诗歌中,诗人告诫我们过于理性的结果是人分不清此在与彼在,正如“鱼,在水里/以为全世界,都是水/鸟在树上,以为全世界/都是森林”,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原则、道德规范来塑造自己的形体,以至于总是容易让“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的苍白对照,陷入“以为”“应该”的命令式的判断之中。
二、生命的状态——疾病与残缺
“认识自我”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样也是一诗学命题,诗人的创作就是在不断地反思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认识自我”伴随的是“反思自我”,在诗作中,通过运用意象来“反思自我”是诗人不断探索生命真谛的自觉,它表征为诗人直面惨淡生活和残缺生命的勇气和执着。子空的诗歌中就充斥着这种精神,他的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是残缺而坚韧的。 《救护车》这首小诗一种讽刺的口吻写出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每次听到声音/我都以为,那是我/那不是我,那是我/那不是我,肯定是我/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这首小诗以截句的形式呈现出来,语言质朴,诗中既有作者情景式的体验,也有一种戏剧式的想象。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人显得弱小无助,生命的神秘性被解除而显露出真实的状态,被语言、物质和精神建构起来的生命意义神话崩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和颤栗。“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种宗教式的祈祷是很具有强反讽意味的结尾,它既是对生命中某些偶然性,诸如命运无常的一种无力的妥协,也是对生命必然性——如生老病死的非理性逃避与调侃式回应。正如西美尔所说:“宗教的教义都只是以一些被强调的、置于生命之外的单个形体——这些形体抽象的固定性最终只能为他们规定单个的生命要素——一些来自灵魂之外的决定。”生命的状态本质上是不完满的,这种不完满在宗教上被渲染和书写为一种逃避和顺从,它用“教义”规诫代替人的自省精神,是从生命外部强行介入生命的一种法则,显然是不能直观生命的,特别是不能回溯到生命现象本质的途径,每一个人的完满性只能在自我同一性中才能得到实现,既要服从道德原则的规训,也要遵从生命规律的制约。子空的诗中就充斥着这种内省精神。
在子空的诗中,诗人“认识自我”的途径,不是一味地诉诸一种哲学式的检视与反思,他的目光从人投射到了一切生命体上,比如“蚂蚁”“鱼”“树”等事物上,以诗人充满悲悯眼光的对待眼前的一切生命。在短诗《动物的眼睛》中,诗人如是写到:“ 看着,看着,/就会和我的眼睛/一起,流出泪来 ”。这首小诗中“眼睛”意象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就在于,从动物眼睛的视角来观照自我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智慧,因为“你必须为你的灵魂操心”,这是人照看自己的重要活动。《庄子·齐物论》中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物质生命的可贵就在于它只在个体身上延续,不存在超越鲜活的个体(身体)而独立存在的不毁灭的生命,同时它也不是抽象的、概念性的存在。人死物灭,情随物迁是自然之理。人不是工具性的存活于世,但是有可能成为工具和手段,只有跳出关于自我认识狭隘的空间,才能解放自我,获得灵魂的解脱。
三、生命的旅程——故土和异乡
在子空的诗歌中显白的展示了诗人关于生命旅程的开端与归宿的思考,可以看出作者徘徊在故土与异乡这两个对其生命形态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中,一端是难以剥离的故土之思,一端是不能割舍的异乡之情。在《修行》中,诗人如是写道:“一只鸟从中国丽江来到了云南普洱/我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它没有/它于 2020 年飞进了寺庙,不知其鸣如何”。显然,在这里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只鸟,从滇西北丽江“迁徙”到了滇南普洱,岁月无情,“我”乡音已改,往事如烟,不堪回首。”“鸟”进入“寺庙”,恰如人进入某些不该进入的场域,我想子空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一定是他生命里遭受一些痛楚的时候,这场生命漫游的归宿,终究还是纠缠在故土和异乡这两个难以割舍空间中。时间、职业、家庭等这些都可以使人的生命从其固有的空间中剥离,被抛入到另一个空间。在《想起一棵树》中,诗人写道:“伐木者问植树的人/一颗东倒西歪的树/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是否继续东倒西歪”,诗人就是那棵被“移植”的身不由己的“树”,谁有权力移植生命?答案是自我,自我的生命的形态是被自我治理的权力欲望塑造同时也束缚,这种作茧自缚的苦厄在诗人的诗中被书写是一种宣泄和无奈。我们可以说,塑造自我生命形态的是来自于自我强大的不可遏制的欲望,改造自己、满足自己最后摧毁自己。从这一点来说,子空的诗歌中有浓郁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是日常化和消解性的。悲剧性在于他的视野和目光迂回在个体直面生命脆弱时的无力感和愤懑,甚至还有些许的恐惧感。消解性则表现为诗人在诗歌中对自身遭遇的种种痛苦,用宗教的说辞转为一种旁观者的同情。正如诗人马雁所说:“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生命不会消失自我的幻觉术”,生命是孱弱的,随波逐流充满悲剧性的,同时也是高贵的,厚重的充满崇高感的,更是荒诞的,说它荒诞是因为无法摆脱西西弗式宿命的折磨。在《复习》一诗中,子空写道:“把泥土撒在她的身上。身上就有了泥土/把泥土撒在她的身上。身上就有了泥土/我把泥土撒在她的身上。身上就有了泥土/把泥土撒在她的身上。身上就有了泥土/请你继续/把泥土撒在她的身上。撒在我的身上/——如果还有泥土”,泥土是大地的产物,它在诗中的存在是诗人确认身份的寄托,“如果还有泥土”其隐语是“如果还有故土”,“她”是谁?泥土为何要撒在她的身上?这首诗以一些重复的话语和段落不断地追问生命归宿的问题,生命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总要惹上一些世俗的尘埃。生命的历程归宿在于坟墓,当生命不得不面临毁灭和死亡的时候,保持静穆的状态不失为一种恰当的决绝。“安静,不是什么声音都没有/恰恰相反——/好像一个人从墓土里走出来”。向死而生是一种直面生命的最高精神挑战,个体生命的存在不可能在肉体上得到永恒,在现实中,只有超越现实束缚才能得到升华的可能。任何个体僭越道德、社会、法则的行为都必将陷入平庸,招致自身毁灭。因为灵魂不朽是过于玄奥的设想,唯有不让生命变得轻薄和孤独才是安放肉体的最好方式。
四、结语
近年来,子空诗歌不断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云南日报》《边疆文学》《名作欣赏》《文学界》《四川诗歌》《大昆仑》《普洱文艺》等纸刊,先后发表了省内外部分评论家对子空诗歌的评论文章,切入点和视角各不相同。而我更偏重诗人的哲学烟火味。子空老师的诗虽然篇幅不长,却能在有限的文字里用准确的意象、词语、形式真诚地抒写自己对于生与死的思考,特别是对“死亡”的思考,具有一种直观生命的哲学艺术。在对个体生命形象进行全面塑造和完整认识时需要对死亡有理性的审视,这是因为死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战胜死亡的生命意志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任何试图违背生命规律延长生命长度的做法都是非人性和徒劳的,只有直面生死的胁迫才能把生命从沉沦麻木中唤醒并超越现实去关注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云南普洱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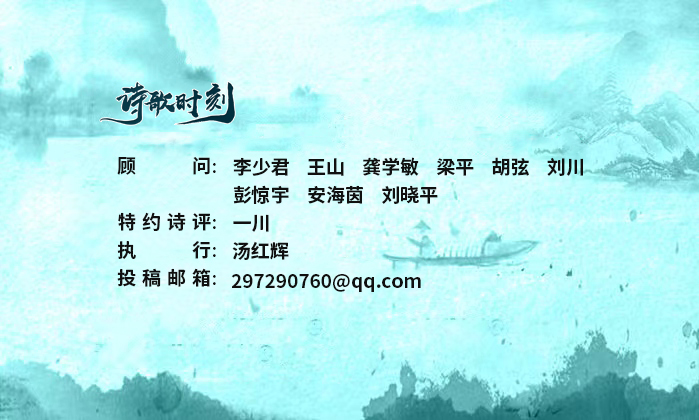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刘邦朝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