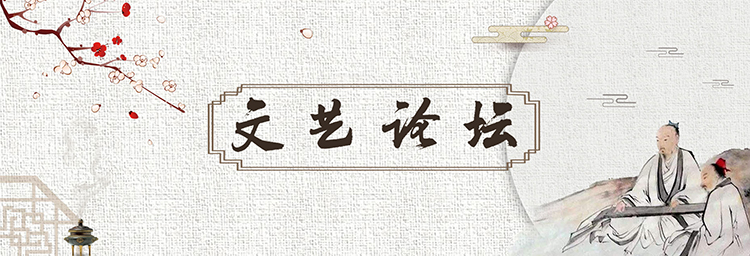

诗歌的岩壁和先锋的回声
——论张清华的诗歌批评实践
文/冯娜
摘 要:与诗人同行的张清华以翔实的史料分析能力、文本细读的能力,强调“生命诗学”以及回归诗歌本体的实践在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独树一帜。在诗歌理论、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的“三栖”写作中,张清华以批评家的勇气与诗人的激情重新发现并指认“先锋”;在与个体诗人的对话中,他以诗人的理解之同情知人论诗、由诗近人,亲证了生命诗学的存在和丰富、多元。张清华的诗歌批评理论丰赡、诗评互证、文辞诗意,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的独特景观。
关键词:张清华;诗学研究;生命诗学;同行者
早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的出版,学者张清华就以极具创造性的史料考证、理论思辨和文本深度阐释能力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以精微、翔实的史料和颇具学术创见的史识意志构建了多重文学对话的路径。张清华作为一个理论丰赡且体量庞大的学者和批评家被人们熟知,无论是文学史、文学理论还是作家、作品论,他都极富耐心地在反复认识和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开掘出独到的思路和洞见。诸如《文学的减法》《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火焰或灰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等著述,不仅彰显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和批评立场,也展示了一个充沛着诗性和激情的创造者在“由语言通向历史”道路上的孜孜不倦。
如此耕耘30余年,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大显身手的同时,张清华还在小说、散文随笔和诗歌等文学创作中蕴养了一片“秘密花园”。《海德堡笔记》(随笔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诗集)等心灵滑翔地是“诗人华清”的生命诗学的现实袒露和亲身力证。张清华始终以与诗人同行的方式,力求精神境界与原著创作者达到“对称”的态度从事着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他的诗歌研究在文学内部的审美上建构起诗学与生命个体、精神分析的文化逻辑链条,在宏观视野中探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连贯性的命题的同时,他也深入文学的时代情境中,真正置身于诗歌的发声现场,去思考“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媒介完全有可能”“中年写作要不要抒情,怎么抒情”等一系列问题。张清华深潜于诗歌内部的诗学建树和诗歌创作,已然成为当代诗歌批评的一种典范。
一、指认与命名:从问题通向本体
在《百年新诗与“师大诗群”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张清华开宗明义地写道:“鲁迅所开辟的诗歌写作传统,或许才是真正‘正宗’的。虽然很久以来,人们将其当作‘散文诗’,而狭隘和矮化了它的意义,但从大的方向看,鲁迅的诗才更接近于一种‘真正的现代诗’,其所包含的思想、思维方式和美学意味,才更能显示出新诗的未来前景。换言之,鲁迅所开创的新诗的写法,对于新文学和新诗的贡献是最重要的。”①这种充满创见和勇气的指认是张清华独特的批评口吻,他的自信来源于对文学史料的精通以及对文学本质的体认。在对百年新诗传统和理论建树做出精准总结后,他回到诗歌本体,以“重提文学性研究”的眼光面对我们自《诗经》始累积了两千多年的“史料”。作为一个具有宏观史识视野、史料功力深厚的批评家,他深刻地体察到一代代诗人(诗潮)被推向历史的前幕,并不完全是诗歌本体的“美学地震”,而往往是诗歌运动带来的“移山效应”。在《第三代以后历史如何延续——关于70后诗歌一个粗略扫描》(与孟繁华合著)中,他不无感慨地说:“回顾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诗歌运动,颇有点像是这种造山的过程。有时过于激烈,对于既存的传统与秩序造成了剧烈的冲击。”②而这种“造山运动”,恰好是诗人们跻身诗歌谱系和诗歌史的重要方式之一。张清华显然对这种脱离诗歌本体的“造山运动”存有疑虑,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第三代”之后的诗人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历史该如何延续?是倚赖一种“运动式”的出场策略还是静水深流般以文本立世、等待着被指认和命名?这是每一代诗人必须回答的命题。张清华似乎期待着一种更贴近诗歌本体的精神崛起来打破过往结构性的存在和局限。通晓中西方诗歌观念史的他所推崇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创作和文学的阐释和概括,那些关于史诗、抒情,涵盖内容、形式、美感、受众等方方面面的指涉,是关于文学本体的求索。那无限接近于一种“纯诗”的文学理想和诗意诉求在一代代创作者那里被实践,有时我们也将其命名为“先锋”。
在为张清华带来学界广泛关注和声名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他以学术整体性观照探讨了中国特定语境中的“先锋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他敏锐地捕捉到先锋思潮最早诞生于诗歌领域,这比小说等文体更加深远的轨迹并非始于浮出地表的“第三代诗人”。“先锋”的风暴眼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黄翔、哑默、食指等诗人那里酝酿并生成,到20世纪70年代“白洋淀诗群”那里已然成型。“谁是先锋?”这被学界反复讨论的话题似乎已形成公论,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朱大可《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等描述之外,张清华重新勘察并发现了遗落在潜流之中的“先锋”。2015年发表的《谁是先锋,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的余论以及张清华对“先锋诗歌”的重新发现和再认识。在文中他详尽地指认了以黄翔、哑默、路茫、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吴若海、李泽华、王刚、王强等诗人为代表的“潜流文学”贵州诗人群;这一诗人群体正是未能进入声势浩荡的先锋“造山运动”中的被忽略的声音。文学批评是一项需要具有考古精神的工作,文学批评家不仅要在史料的主流和分支中通过对具有延续性的宏观命题建构起理论谱系,还要在打捞吉光片羽的同时完成对重要文学实践的指认、祛蔽、命名和重释。张清华的诗歌批评就体现了这种重新发现的自觉和敢于指认的魄力。他在辨认和深入先锋文学内部的同时,意识到“先锋是一大堆重要的或试验的文本”③,而先锋作为一种文化与文学的实践,又该何去何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娱乐化转向“既为文学的表达开辟了新的局面,但也使文学逐渐陷入到了自身主体性的危机之中”④。
面对诗歌实践中的种种“未完成”和“危机”,张清华总是锲而不舍地跟踪着诗歌内部有可能发生的裂变,时常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他的诗歌研究和批评总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未来关切。这在他《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 ——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中尤为凸显。他从“写作资源与外来影响”“象征主义、现代性与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边缘与潜流”“现代性的迂回与承续”“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经典化、边界实验”⑤六个方面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百年新诗道路中的问题和启示。这是诗评家在宏大视域下对新诗实践较为全面而独到的总结,其中包含了历史纵深中的道路抉择、时代横向发展中诗人具体的探索和处境。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诗歌观念和实践经过持续的调整与对峙,在现代性的道路上迂回曲折地向前,诗歌面貌既先锋又多元,但缺乏真正先锋的批评家进行系统的指认、命名并作出客观的评估。张清华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回溯历史、评估当下”,这些问题中所蕴含的诗歌本体建设的历史与现实,无疑为怎样通往“真正的现代诗”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二、生命诗学:从诗歌理解诗人
在所有文学体例中,诗歌是离个体最近的心灵之声,诗歌是诗人用情感、经验、心血所缔造的一种语言生活,是生命最真挚的声音。正如格雷夫斯在《现代派诗歌概论》中所说,“诗是一种极敏感的物质,让它们自己凝结成型比把它们装进预设的模型效果更佳”。因此,在诗歌批评中,很多现成的文学理论、学说也无法批量“盛装”诗歌这一文体。知人论诗,由诗近人,从鲜活的个体感知切入历史的浪潮,是张清华诗歌批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张清华这种回归生命本体的“生命诗学”在充斥着以偏概全、以诗歌流派的群体性描述代替个体特质、以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诗歌思潮忽略诗人个体视角的诗歌评论中如同“一股清流”。
正如他在课堂教学中讲到海子,他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个诗人、一种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事件”,绝不可以敷衍了事。虽然“讨论海子是一个足够危险的话题”,他克服了种种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不确定,抱着这样的初衷:解读海子是“真正涉及从本体和哲学上理解诗歌、理解文学与艺术的宝贵话题。所以,解读海子无异于一次精神的启蒙,从他身上可以衍生出众多属于精神现象学的话题”⑥。于是,《海子六讲》这样针对单个诗人的深度系列解读得以呈现。虽然预设了诸多前提和特定的语境,但张清华认为解读海子的入口就是那被众多文艺青年争相传诵的《祖国(或以梦为马)》。他首先从“语言的返还与穿透力”的角度,来确认海子这一“名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引发了对诗人生命人格实践的思考。虽然在1992年5月《海子诗全编》编竣时,编选者西川已经确认了海子作品“跨时代的价值”,但这一论断还未历经时代的考验。在近20年后,海子诗歌“跨时代的价值”在张清华这里得到了具体而充沛的估量,他将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和李白的《将进酒》、屈原的《离骚》《远游》对照,确认海子作为一个现代汉语的使徒,深知自己的使命,他年轻而苍老的灵魂早早参悟了历史与文明“寒冷的骨骼”,当生命的有限、个体的局限被洞彻之后,他用语言获得的超越和囚禁充满了“毁灭的恐惧与激情”。可以说,张清华对海子的解读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入心入肺、惺惺相惜,常让人生出知音之叹。在《这世界上最残酷的诗意》中,张清华甚至用无比感性而伤怀的笔调描述了他的一个梦境:“梦中我来到位于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园。”这是海子工作过的地方,接下来他在半梦半醒间沿着海子诗中的线索按图索骥,种种场景如同诗人步履所至,荒凉又孤寒。然而海子在生前与张清华从未有过交集,张清华认为这恍然的梦境是诗人留给自己的“想象的剩余”,这何尝不是一种诗人与诗人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应呢?生命的诗学在此获得了最深沉的回响,这恐怕是海子生前无法想象的理解和知惜。缘于这份理解和知惜,张清华在后来真正踏上那被诗人咏唱过的麦地和平原,也见到了那个会背诵儿子诸多诗篇的老母亲。诗歌能否消弭生与死的距离?古老的大地曾怎样启示着远行的诗人?生者世俗的心愿是否能够通过诗歌的永生得以补偿?批评家纵有万般心灵映照的时刻,也难以承受这“残酷的诗意”——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让张清华再次确信,只有用赤诚之心烛照那命运的幽邃,才能亲近诗人,去真正理解那一行一句中埋藏的惊雷和风霜。正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言:“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
这种缺乏、不幸以及不驯服、不妥协的精神,张清华在阅读女性诗歌时应该体会得尤为深刻。无论是翟永明“黑夜的意识”中那巨大而痛楚的灵魂、唐亚平《我举着火把走进溶洞》中“带着血的热情和孤独”,还是伊蕾惊世骇俗的“你不来和我同居”、陆忆敏“谁曾经是我”的诘问……还有舒婷、林子、傅天琳、王小妮、林珂等女诗人都以自己独特的声调唱出了那不仅仅属于自己的悲哀。张清华以一颗体恤之心,从她们那近似锐利的嗓音中听出了这一群体身上所负荷的古老重量。他以一种近似悲悯的语调写道:“只有从女性话语的角度找到女性主义诗歌的意义,才能最终肯定其作为文化反抗的意义。”⑦长期以来,女性写作并没有真正成为“思潮”进入文学的主流视野,“第二性”(波伏娃语)的社会话语结构让女性写作始终处于浓重的暗影之中,张清华在他的诗歌批评中从个体文本到总体思潮,给予了她们公允的位置,同时也理解她们的处境:“女性意识的觉醒,会更加反照出女性话语缺失的困顿,因为某种失语的焦虑便是在事实上更加困扰着女性写作。” ⑧
事实上,困顿和焦虑不只困扰着女性诗人,任何一代诗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顿和焦虑。笔者曾在现场聆听过张清华的讲座,他列举的诗人范围宽泛、直指诗歌现场。比如他分析了沈浩波、巫昂等“70后”诗人的文本,同时也对草根、底层的写作给予客观的评述。他并不以“学院派”的保守和自矜厚古薄今,他仔细辨认和肯定新诗发展序列中那些真切而具体的存在,诗歌就是当下、此刻的心跳,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他们的文本说出人类具有普遍性的体验和冒险,他重视个体的文本实践,也将他们纳入总体性的视野中考察。在深入海子的精神世界时,张清华自称是“‘同时代人’中的未亡者”,在长期的诗歌批评中,他更像一个始终与诗人同行的知音,他是他们真诚的读者、为他们正名的勇士、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同我的论述对象保持‘学术的距离’,而是坚决地与他们站在一起”。⑨
三、华清与清华:互为镜像的诗学
如何坚决地与诗人们站在一起呢?批评家张清华另有蹊径。“诗人 现在你第一个上场/花朵的葬仪已经结束 无须对物/感伤 吟过的主题不可重现/这就是神祇退出后的空旷”(《悲剧在春天的N个展开式》);“听——与二位一样,他以夜枭的方式/剪裁着安详的烛光,拨动低音的马群/用苍白的指尖,将神秘的暗语敲响”(《听贝多芬——致欧阳江河与格非》);“隔着稀薄的空气,隔着命运的/舷窗,都能听到你剧烈的咳嗽”(《中年的假寐》)……这一些充溢着抒情和生命哲思的诗句来自一个叫“华清”的诗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甚至无法将它们与“批评家张清华”联系在一起。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所以,拥有诗人的内心世界是理解其他诗人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单纯依靠阅读、解析、阐释这些外部工作是不够的,让自己成为诗人则是最可信的道路。霍俊明认为,“批评家的诗”已经成为一种极其特殊的“文体”。这种“特殊性”不仅因为批评家对诗歌的界定清晰,对诗学理念也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成熟的体会,这在他们的创作中也会形成重要的影响。而在诗人华清笔下,那种“批评家的口吻”几乎被藏匿了,他的感官变得异常灵敏,“光线弱下来,但也发出奇怪的沙沙声”(《枯坐》)、“时针指向正午,只有咔咔的响声,却一动不动”(《春困》)、“呵 他的耳语和玉米的拔节声/融为了一体 和玉米下蛐蛐的鸣叫声”(《耳语》)……也许这是张清华卸下批评家那些历史责任、文学使命感的重负后最轻松的时候,他与镜中的“华清”对面而坐,四下无人。生命最本真的潮汐涌动着,与之同行的那些诗人一定也有过无数这样的时刻,正如他在诗歌创作谈《我想让过去的一切凝固下来——关于诗歌写作这件事》中引用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句名言:“大约是说,所谓诗歌就是让某个流动的瞬间在语言中凝固下来,变成连续的现在。”这便是时间与存在的奥义所在,无数诗人试图用书写阐述在有限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奥义,诗人华清认为“要设法在自己的诗歌里建立一个‘隐性的他者’,让自己成为与别人一样的人,而不只是自己”⑩。这也许就是批评家的意志使然,他知道自己所写下的一切必将沉入历史的暗道,但只有那些能够被进入、被抵达的公共性、普遍性的经验才能“与历史、与前人,与现实、与他人的共同处境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就好似“华清”与“清华”的互文,是时空深处的镜像,又是面对此身的实在。
美国现代艺术之母乔治亚·欧姬芙也曾说:“当你仔细注视紧握在手里的花时,在那一瞬间,那朵花便成为你的世界。我想把那个世界传递给别人,大城市的人多半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一朵花。”诗人和艺术家就是那停下来看花、同时能够把花朵传递给别人的人。诗歌中那些打动人的瞬间恰好是那些非理性支配的感性元素;逻辑、知识、理论在生命能力迸发的时刻往往是失效的。一个批评家如果拥有了诗人的创作经历,在细读文本时便能将自己的创作经验、思想、感受以及力有不逮的局限性融会其中、言之有物。以诗人之心理解同行的写作,便能理解那些内心的雀跃、暗影或细微末节的颤动。吉狄马加、骆英、蒋三立、朵渔、安琪、寒烟、潘洗尘、桑克、大解等众多活跃于中国诗坛上的诗人,都被张清华认真研读过,他从同行那里一次次听见“黑暗的内部传来了裂帛之声”,也感叹“一切不可言传的都是生命的赞美辞”。诗人的语言背后是他们自己与时代的一次次肉身相搏,他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感受,并以手艺人一般的眼光,欣赏着同行们的技艺;与他们对话,成为他们在场的交谈者。然而,他也冷静地观察着一代代诗人的探索与进展,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论者”{11},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播方式的剧变,诗歌有无数的可能性,需要读者认真阅读和鉴别。长期的批评家工作训练了张清华如何保持敏感和克制,作为一个审慎的读者、一个诗人的同行,他完全懂得区分这其中的界限,也明了不去逾越作者和读者之间心灵的契约。一个诗人的整体气质终归要在诗行中获得精神的回声,一个优秀的诗人也必然要以更丰沛的作品为世人展现多元的精神维度以及多重面影。所以,即使张清华窥探到一首诗的文本局限,他也能从自身出发理解人之为人的局限和诗人的瓶颈和困境,整体的得失和无意识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的写作实践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经验。张清华以前瞻性的视野关注着时代前沿的课题,比如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等问题。当我们身处的时代无可争议地被互联网所联结,诗歌的写作和传播都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剧变。张清华认为“网络新媒体是一种‘文化平权’的实践,无疑会降低门槛,强化娱乐性、大众参与度” {12},面对消费文化、商业文明的冲击,他恪守着“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观念,认为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但没有生命就不存在诗歌。诗人深信不疑的信念感也许正来自他对人类灵魂深处那种饱满真挚的感情体验:“其实生命中大部分的处境都是如此/从未抵达,却比故乡还要亲切/如同一些梦从未梦到,但却有如/旧梦一般。这不,此刻你读到一首/从未读过的诗,你竟然感到它/是你多年前的旧作”(《春梦——兼致张枣》)。就在生命的流逝和回望中,诗人华清与一个个熟悉、陌生的诗人达成了灵魂的共鸣,他触抚着那些写作的细部、参与历史的雄心、幽闭于一隅的想象,一代代人站在新诗的起点或节点上,在现代性复杂的镜像中,寻找着一种失落或还未全然成型的心智。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曾说, “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人华清在他的诗歌花园中洞悉着这一切,而批评家张清华决意将这“无限的少数人”无限地释放出生命的可能,他既为具体的个体“塑像”,也在时间的维度上一遍遍擦拭着诗歌这一文体的尊严。
张清华的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是对话也是创造,是中国文坛另一种先锋的文本和存在。张清华异常珍视那些前仆后继者一次次精神的历险,不然他也不会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的扉页引用骆一禾的诗句:“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注释:
①张清华:《百年新诗与“师大诗群”的前世今生》,《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②张清华、孟繁华:《第三代以后历史如何延续——关于70后诗歌一个粗略扫描》,《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
③张清华:《谁是先锋,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④邱晓丹:《论王朔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转向——兼论当代文学与影视关系之变迁》,《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⑤张清华:《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2期。
⑥张清华:《以梦为马的失败与胜利、远游与还乡:海子诗歌入门》,《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⑦⑧⑨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第293页、第342页。
⑩张清华:《我想让过去的一切凝固下来——关于诗歌写作这件事》,摘自中国作家网,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705/c447005-32466829.html.
{11}张清华:《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12}张清华:《中年写作要不要抒情,怎么抒情?》,《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6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冯娜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