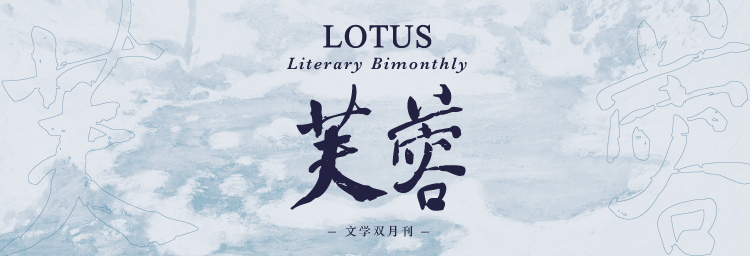

我叔叔的人生片段(短篇小说)
文/李亚
我叔叔李白牙早先是个卖老鼠药的,这一点,无论怎样粉饰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卖老鼠药时的几套顺嘴溜,至今仍在我们那一带久传不衰:“这几天我没来,老鼠逞能上锅台;今儿个,我一来,老鼠吓得夹着尾巴不出来。小老鼠,真讨厌,吃完鸡肉吃鸡蛋;啃完桌子啃椅子,还啃咱的猪蹄子……”然后,他大力夸耀他的老鼠药是按照玉皇大帝家毙鼠秘方配制的,经过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制,所有的老鼠,包括老鼠皇帝、老鼠宰相和三宫六院的老鼠娘们,只要闻到气味,一眨眼就会四肢抽搐,两眨眼已经昏厥于地,要是吃上一粒全窝老鼠就会死光光——我觉得我叔叔李白牙的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了,不免多嘴插了一句:“一只老鼠吃了药,咋能全家死光光呢?俺的好叔,你又吹牛了吧!”我叔叔根本不屑于用他那双白多黑少的三角眼剜我一眼,只听他从牙缝里漏了一丝气似的响了一声:“你吃一粒就知道了。”
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我叔叔的这句话就像一条蛔虫,应该是乘他屁眼不备擅自钻出来的,因为当时我没看到他的嘴唇动弹。即便那时候就有了腹语一说,但是,不管我叔叔有多少妖毛,他都不可能掌握这种有着几分妖气的巫术。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那阵子我叔叔大概是心火上攻,他的双唇都被烤出了吓人的裂纹,就像寒冬腊月在水边的苦工皴裂的手脚。
我叔叔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三五颗麻将牌白板般的大门牙,尤其是姜黄色的脖子悠长美观,好似长颈鹿的脖子……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讲一讲我叔叔那不为人知的真实人生,但担心他的诡秘言行远不是我这种智商的人所能解释得了的。无论何时何地,一想起我叔叔的那些老鼠药,它们就像颗粒状幽灵一样一下子浮现在我面前,似乎也像老鼠一样有着独立的生命,而且如老鼠神秘地穿过各种屏障一样,曲里拐弯穿越幽暗繁杂的岁月,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其实,我叔叔的老鼠药也无甚奇特之处,以我叔叔大约可以盛一汤匙的那点可怜见闻,他研制的老鼠药基本上是粮食的形状,颗粒大小好似小麦黄豆玉米,也有像扁豆豌豆绿豆的,不过在颜色方面我叔叔的大脑小脑还是一起开动了马力——有银灰色的,有乳白色的,有亮黄色的,有樱桃红的,有杏子黄的,有柿子红的,有葡萄紫的,有玫瑰红的,还有像饱满的大豆一样黄澄澄的,当然还有颜色世界里的两棵常青树——红色和黑色,我叔叔把这两种颜色的老鼠药做成了令人厌倦的药片形状。还有很多即便再过一万年我也无法说明的种种颜色。要是单从颜色这方面来评价,那完全可以把我叔叔定性为善于制造老鼠药的世界级工程师。可以说,我叔叔制造的老鼠药五颜六色,斑斓迷人,更不用说像什么颜色的颗粒就发出什么样的香甜气味了。仅仅看着色彩迷人的颗粒,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抓一把像嗑瓜子一样神情休闲频率均匀地一粒一粒吃掉它们——想当年,只要一看见我叔叔的老鼠药,我的榆木脑袋里总是火星乱迸一样迸出偷吃几把的念头。
我叔叔的老鼠药生意兴隆与当年老鼠的生长环境以及繁衍速度有关。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奇怪透顶,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工作人员,哪怕县长也好,公安局局长也好,卫生局局长也罢,家里照样有无穷无尽的大小老鼠出没于梦里和梦外,如同过江之鲫不舍昼夜穿梭于生活之中。无论你是乡下人还是城市里的人,只要你经历过那个年代,请回忆一下,是不是也亲眼看见过老鼠横行的情景。我十余岁的时候,亲眼看到过好大一群老鼠如同列队士兵一样从池塘的北岸游到南岸,然后有条不紊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果实累累的玉米地里。几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让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
那时候,我叔叔不单在柳林铺集市上摆摊子售卖老鼠药,他还像个幽灵一样经常游走四方,往往我眼见他出门时携带的老鼠药十分有限,也就是背着那个在他眼里好似圣器一样的人造革黑皮包出去的——我一说这个,他那个边边角角都被老鼠咬出了大小孔洞的破皮包,就像一顶破破烂烂的黑色毡帽一样出现在我脑海里——但他往往都是过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半月方才返回。有意思的是,我叔叔只要过了半个月不回家,我婶子小白菜就会到我家哭哭啼啼,央求她的好哥哥也就是我爹爹赶紧四下打听一下李白牙那头犟驴死到哪国去了。我婶子是我们李庄东边五里半地白家庄的,名字叫白莲花,要是陌生人在黑夜里听到她的名字,脑子里刹那间就会出现一个手白脸白屁股也白的女性形象,但是,实际上我婶子白莲花手脸颜色都像烧糊锅的死面饼子,至于其他地方白不白,也只有我叔叔这个奸人才能给予准确判断了。但是,善于给人起绰号的我们李庄人单单就叫她小白菜。我婶子是个瓜子脸,还有着一双单眼皮,这应该符合现如今漂亮女性面孔的基本特征,但却一点也不符合那时候的审美标准……那个时候,很多人心目中的漂亮女人必须是银盆大脸杏核大眼,牙似玉蜀黍粒,两耳好比元宝——这样的女人在审美标准千变万化的当前和未来都有可能算作妖怪。我婶子婚前婚后都是直呼我叔叔的大名李白牙。每次她左脚刚刚迈进我家门槛,就会使唤着又糙又胖的一双褐色爪子乱抹着泪汪汪的单眼皮小眼,尖声尖气地嚷一嗓子:“俺的个好大哥呀,你赶紧四下里找找李白牙那头犟驴死哪国去了……”很显然,我婶子刚吃过香喷喷的韭菜煎饼。韭菜煎饼很好吃,但之后呼出的气息却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困扰,也就是说,我婶子嘴里喷出一股股浓烈的难闻气味,就像有毒的浓雾弥漫在我家院子里。
常言说同胞兄弟血浓于水,本来我爹爹就是个二性头,这时刻岂能允许别人诅咒自己的亲弟弟死哪国了,即便是亲弟媳妇也不允许,所以每一回我爹爹都是气急败坏,两根手指夹着又粗又硬的雪茄举得高高的,厉声训斥:“傻女人!净放出溜子屁!一个翻活的好人咋能死了!”即便我爹爹这样当头棒喝,也挡不住我婶子喋喋不休的唠叨。她说李白牙动不动就犯神经病,每次拌好了老鼠药总是捏几粒扔嘴里尝尝,就像她炒黄豆喂牲口,一边炒一边总是不由自主地捏几粒塞嘴里嘎嘎嘣嘣咀嚼一阵子。我婶子言语间还挥动右手做了几次朝嘴里扔黄豆的动作,因此她的话说得更加活灵活现神神道道,好像她两只单眼皮的小老鼠眼真的看到过我叔叔品尝老鼠药一样。
我叔叔不仅制作老鼠药别具特色,唱起琴书来也是惟妙惟肖的。尤其是瘸子坤丁和马利亚来到我们李庄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叔叔彻底展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艺术细胞。虽然说唱琴书时他只是扮演一个应声帮腔的小小角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展露说唱方面的艺术才华。
拄着拐棍的瘸子坤丁和马利亚来到我们李庄时,我们全庄老少都以为他们是从月球上来的。我们这样认为也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从穿着打扮到长相外表都显得有些迥异的异乡人突兀地出现在某个村庄里。多年以来,我一旦想起坤丁和马利亚,马利亚的形象就会立现在我眼前,但是,我总是不能从穿着打扮到脸上表情等方面想起她的高级美丽,唯一可以确凿指出的是,她微微一笑间两粒小虎牙上都镶着闪闪发光的银牙套。马利亚还拖着一个红彤彤的硕大皮箱。那个皮箱大到不仅完全可以把他们二人装进去,还似乎可以装进去一个宇宙般的巨大梦境。
瘸子坤丁的那个样子,唉……事实上,瘸子坤丁的形象根本不需要我绞尽脑汁描绘一番了。
先生们,女士们,请看我手中这张照片。这是当年坤丁给我打磨牙垢时我们李庄的摄影师李金星特意拍摄的。照片上的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脚不挨地地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双手僵硬地撑在两个膝盖上——我少年时代的两个膝盖饱满圆浑,真令人怀念——仰着脸,张着嘴,两眼露出如临深渊般的惊恐和期盼……左右就是让牙科医生看牙时需要摆出的那个贼兮兮的姿势。坤丁穿着只有医护人员才穿的白大褂,白大褂的胸袋上还有一个刺目的红“十”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红“十”字象征着人道、博爱和奉献,我猜测那会儿瘸子坤丁先生也未必知道这些。坤丁上嘴唇留着一道修剪得十分整齐的短髭,在照片上显得像墨油刷过一样,又浓又黑又亮。他左手拿着一把亮晶晶的小镊子,右手执着一把形状活像微型电钻的医疗器具。旁边还有一个用钢筋焊接的有点像放乐谱的架子,架子用亮银漆刷过,可能平时惯于野蛮使用,油漆已经多处脱落,露出生锈的钢筋,显出狰狞的意味,让这个架子看上去有点像柳林铺集市上屠夫范进卖猪肉的铁架子。坤丁的这个充满医疗意味的架子正中间还有一个椭圆形的锡皮盒子。我当时哪里知道这个椭圆盒子就是这台医疗器具的关键部位,就是现在知道了也不敢断定盒子里是不是安装了一个万能转轴。盒子两头分别伸出一根塑料软管,如听诊器的软管那样粗细。这两根管子,上头的这根连接在坤丁手里的钻头把手上,下边的这根连接在架子下边一个铁皮踏板上。简洁地说吧,这个简陋的牙齿理疗器具的工作原理与缝纫机相似,只要坤丁踩踏这个铁皮踏板,他手里活像焊枪或者钻头一样的那个钢笔帽大小的宝贝砂轮就会高速转动……
我现在一说这个,浑身就说不出来地难受,好像大力咀嚼红烧肉浇头的米饭时被一粒石子硌了牙一样。从照片上你看不出坤丁是个瘸子,更看不出他的两条腿患过小儿麻痹症——现在我可以告诉美国总统或者非洲酋长了:坤丁两条腿就像高粱秆一样粗细。在照片的边缘,你仔细看还可以发现坤丁的那根拐棍。说起那根拐棍来,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根司空见惯的荆条棍子——上下一般粗细,两头都有一个黑色的橡皮套。现在我敢肯定,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定制出如此适合那根荆条棍子的橡皮套,肯定是坤丁自己做的。想一下即可知道,他那一双手连有血有肉有无数神经的人牙都能收拾得妥妥的,给一根棍子两头做个橡皮套那还不是等同儿戏?
不要以为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后来要发生什么故事、就知道坤丁的形貌了,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谁也不能把坤丁的形貌描述明白,就像谁也不能原封不动地讲述自己的梦,就像半个世纪以来从没有哪个人能把我叔叔李白牙的形貌描述明白了一样。我唯一能说清楚的是,除了是个瘸子,相貌英俊的坤丁也是单眼皮,和我婶子小白菜的单眼皮一样。言谈间一笑起来,两只眯缝眼里都是淫荡的光芒。先生们,女士们,也不要凭借我这点介绍就武断认为坤丁是个江湖牙医,事实上他还是个琴书艺术家,我叔叔会唱的那几段琴书就是跟他学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想起当年全村老少每天晚上挤在我叔叔家院子里,在一个昏昏欲灭的灯泡下聆听坤丁两口子和我叔叔李白牙演唱琴书的情景,就会觉得那真是一个遥远的太平盛世。我一想起那张扬琴的模样,它发出的声音就会立刻响在耳边。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我叔叔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当时他家就是没有放置这张扬琴的几案,不过,这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能难住我叔叔李白牙!他可是个卖老鼠药的,卖了很多年!他只是站在大门口像麦芒卡在嗓子里一样连连咳嗽了三声,又像雪野里胡狼嗥叫一样吆喝了一嗓子,眨眼工夫就有人把案子抬来了。那是我们李庄每到年底公用的杀猪案子,柳木的,原木粗腿,尺厚大板。这个狼犺物件的高度和宽度恰好适合于搁放扬琴。每天晚上,坤丁居中坐在这张杀猪案子后边,马利亚和我叔叔坐在他两边,三个人一同演唱琴书《再生缘》。坤丁打板击琴开口演唱,马利亚操弦应声,我叔叔捧笙停吹也跟着应声。我叔叔何时学会吹笙的,说起来十分简单,不过,现在已经快要开书了,我叔叔学吹笙的有趣故事就以后再说吧。这会儿,只见坤丁左手打板右手击琴。板就是那种呱嗒板,竹子的。击弦的琴竹自然也是竹子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神奇的乐器叫作琴竹,它还有单音琴竹、双音琴竹以及单音双面琴竹之分;更不知道一个琴竹是由竹头竹身竹柄竹尾构成的。当然了,不知道这些也不影响坤丁唱琴书,不影响我们李庄的人听琴书,就像很多人不知道北京烤鸭是怎样烤制的,但来到北京一定会搞一只尝尝一样。
坤丁敲着扬琴,先是道白:“皇甫夫人身怀六甲,过了十二个月尚未生养,夫妇又添了一番惆怅。这天正是八月十五黄昏时刻,皇甫都督吩咐府中大厨和仆人在庭院摆下一桌精致小菜,与夫人对酒赏月。”坤丁操起琴竹,击打一下琴弦,说道:“夫人请了!”马利亚竖起弦子拉了一响应道:“老爷请了!”我叔叔也装模作样地吹笙一响,跟着说了一声:“二位都请了!”一阵子哄堂大笑。接着,琴弦笙齐奏响乐,坤丁唱道:“满院微风露气团,桂花送香到疏帘。西墙初照娟娟月,万里无云净碧天……”
是的,在说唱琴书时我叔叔不过就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噱角,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瘸子坤丁和戴着银牙套的马利亚不光唱得好,在借助肢体语言来加强故事的形象化和现场感时,一举手一扭腰,凡做动作无不准确生动,更是让听众如同身临其境。尤其是唱到皇甫少华和熊浩跟着那个须眉皆白的黄鹤仙人学艺的情景时,坤丁右手放下琴竹,左手放下呱嗒板,站起来向左边一矬身子,闪开屁股后边的凳子,一跃而起,啪地打了一个响亮的二踢脚,落地时右腿弓左腿蹬,已经摆好了一个犀牛望月的架势……我现在一想起这个细节就怀疑是来自我狭隘的想象,因为一个曾经的小儿麻痹症重症患者,两腿细如高粱秆的人,日常走路都离不开拐棍,怎么可能跳起来打了一式二踢脚呢?还打那么响!可是,好似真有悖论一说:我越是疑惑难解,记忆里坤丁的这一动作就越是活灵活现。我想了又想,即便当时真的发生了,恐怕坤丁冷静下来之后,也不敢相信自己做出了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我不知道马利亚是怎么想的,因为在演出中她一直面带微笑,操琴如旧,应声如旧,好像坤丁这样的奇异动作她早已是司空见惯了的。
不过当时我们李庄的老少就像当时的我一样,谁都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蹊跷之处。老少爷们只是异常感动,在饭场里议论纷纷,说,坤丁这瘸驴不光琴书唱得好,还真是个实在人,为了让咱老少爷们看个真切,一个双腿残疾的人竟然跳那么高打了个那么响的二踢脚!他姥姥个腿的,落下来万一扎不稳步子,那可就直接摔到那边去了。我们李庄人说的摔到那边去了,就是死翘翘了。我们李庄的人都是很容易动感情的,所以,那几天就有很多人家表达了心意,络绎不绝地把礼物送到了我叔叔李白牙家里,因为坤丁和马利亚就住在我叔叔家。白大嫂子送来一海碗大米,这个很神奇,因为当时大米在我们李庄就像珍珠一样稀罕,别说一年,就是三五年也吃不上一顿,遑论我们李庄没有一个喘气的见过白大嫂子家吃过大米饭或者喝过大米粥。柴大婶子从自家菜地里摘了一马篮子黄瓜和番茄,洗得水净给送来了。在我们李庄黄瓜还叫黄瓜,但我们把西红柿叫作番茄,青绿的黄瓜和艳红的番茄都是水淋淋的,新鲜喜人。送鸡蛋、鸭蛋和鹅蛋的人家不可计数……
我叔叔在那段日子里可谓是春风得意。他还把发型梳成两瓣子小分头,就像电影里的汉奸那样。他在人场里叼着自制的雪茄烟,伸着漂亮的长颈鹿脖子,龇着几枚焦黄的大门牙,又说又笑,声音响亮干脆,好像不光天下是他的,整个宇宙也是他的,根本就没顾及牙缝里要么是番茄皮要么是蛋黄渣子,只管一个劲儿地夸赞自己当年游走四方卖老鼠药时结交了坤丁这个好朋友,简直是眼光独到,能掐会算,实在是高过诸葛亮。他一边演讲,一边抽雪茄,还时不时从裤兜里摸出几粒色彩分明的颗粒扔进嘴里。当时人们都沉醉在他的演讲里,他那个动作在大家的意识里就是吃零嘴,谁也没有留意到他吃的是老鼠药。何况,我们李庄老少都有一个习惯,说闲话吹大牛时总得朝嘴里扔点零食……我现在想起来了,彼时我叔叔在人场里讲述他和坤丁的交往时总是笼而统之,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当年游走四方卖老鼠药的传奇见闻。现在我要是复述一下我叔叔当年行走江湖卖老鼠药的见闻,大家肯定认为我是在讲《封神演义》或者《西游记》……
别看我又说唱琴书又说老鼠药,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坤丁镶牙的事情。坤丁和马利亚刚刚出现在我们李庄村头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坤丁是个相貌英俊的瘸子,尤其是马利亚就像王昭君那么漂亮,尤其是面对那个红彤彤的硕大皮箱,我们李庄大人小孩的智商和思维就像一团浑浊的烟雾一样被吸了进去……当天晚上,在我叔叔家院子里听了他们两口子唱琴书,老少爷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唱琴书的。可是,等到了第二天他们带着牙医器具前往柳林铺集市上摆个桌案拔牙镶牙时,我们李庄的人才知道他们还是受人敬重的牙医。
一说起坤丁镶牙的事情,我脑海里与此有关的原本扣在地面上落满灰尘的一帧帧画面就接二连三自动翻转了过来。最先是我叔叔李白牙拉着一辆崭新的架子车,车框散发着微腥又微甜的榆木气味,车轴上也新抹了机油,机油散发着烧蚂蚱的气味。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就像淡淡的炊烟一样,从久远而有点涣散的记忆里飘出来。车上放着那个红彤彤的硕大皮箱,里边装着坤丁和马利亚的全部人生道具。这个是我亲眼所见的:他们演唱琴书的全部家什随用随取用完入箱——这也许是他们那个行当的规矩,或者是他们作为优秀的手艺人养成的良好习惯。自然了,拔牙镶牙的所有器具也放在这个箱子里。后来,我还发现这个红彤彤的硕大皮箱简直就是他们的百宝箱,他们需要什么就能从里边拿出什么,缝补针线、修理收音机手表的工具和仪器表、粘补胶鞋和自行车内胎的胶水和小铁锉,甚至修补铁锅砂锅和陶碗砂缸之类的工具和材料。反正只要我们李庄有人要修什么东西,他们都能从大皮箱里拿出相应的工具和材料——这些,都是坤丁住在我叔叔李白牙家那段日子里发生的神奇事情……
我记得,坤丁双腿如同麻秆行走不便甚至根本无法行走,到柳林铺从事牙医职业他都是坐在架子车上,自然是由我叔叔李白牙拉着。坤丁手里拿着那根上下两头都有黑色橡皮套的魔法拐棍,就像拿着一根独具一格的赶马车鞭子一样。尽管我叔叔媚态十足地再三邀请漂亮的马利亚也坐到架子车上,但她就是不坐上去。她微笑出两粒装了银牙套的小虎牙,就在架子车旁边走着,不疾不徐,身腰挺拔,好像真有几分皇甫夫人的气度。
坤丁的镶牙摊位就挨着我叔叔卖老鼠药的摊位。这一排摊位当年在柳林铺集市上也算是好风水。我叔叔卖老鼠药常站街头子,人面桃花相映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脉广泛,他用一毛八分钱一包的“大铁桥”牌香烟和两包老鼠药贿赂了市场管理员冯小超,才为坤丁弄到了这个好摊位。冯小超这个人,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就同一只大个头的老鼠差不多。当年在柳林铺集市上,好多事都由这个“大老鼠”说了算。这个外形活像老鼠的人,四十多岁,有着老鼠的思维,有着老鼠的言行,总是倒扣着一顶鼠灰色的鸭舌帽,穿着鼠灰色的中山装,把右边的袖口挽得高高的,露出明晃晃的“钟山”牌手表……他妈个婊子养的,每次路过我叔叔的摊位时他总要顺手捏两三包老鼠药装兜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我根本不相信他家里生活着成群结队的老鼠,我怀疑是我叔叔研制的老鼠药让他吃上了瘾,就像嗑药一样,嗑上了瘾。
坤丁拔牙镶牙的手艺娴熟奇妙,简直让我叔叔入了迷。他一下子忘了卖老鼠药,两手抱着膀子站在坤丁的桌案前观看坤丁炫技一样施展手艺。真不知道是水土原因还是饮食结构不合理,那时候我们那一带的牙病患者比老鼠要多,人人都有一嘴坑坑洼洼的黢黑牙齿。因为当时比较穷,几乎没有人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牙医。一旦牙疼发作了,大都是用土法含着几粒花椒或者姜片来欺骗疼痛的牙齿,至多遇到游走乡间的江湖牙医时,一些牙病严重者才会下决心破费几毛钱请人家拔下那颗痛起来让人要死都死不了的糟牙。如今柳林铺集市上来了一个牙医,一个摆摊子的牙医能要几分钱?头一天,坤丁的桌案前就聚集了很多牙病患者,人人都捂着腮帮子吸溜着嘴,好像隐秘的口腔里遭受了重创,自觉排队等待拔掉嘴里那颗害人的坏牙。那张桌子也是从红彤彤的硕大皮箱里拿出来的,原本是几块木板和几根镀银的钢棍,坤丁像变戏法一样将这些在我们看来作用不大的东西组装成一张牢牢实实的桌案……坤丁先用一支像筷子那般细小的注射器朝牙龈上注射麻药,再用一把筷子大小的长柄小锤子奏乐一样敲击牙齿,最后,握着一把筷子大小的尖嘴钳像变戏法一样把一颗牙齿拔下来。那颗坏牙又黑又黄,糟烂状活似遭了虫蛀又霉烂的花生米。坤丁随手当的一声,将这颗丑陋的坏牙扔进了猪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盘里。这个形状新奇的搪瓷盘子也是从那个红彤彤的大皮箱里拿出来的。我叔叔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形状的搪瓷盘子,脸上满是惊讶和迷惑的表情。我就在旁边,看着一团乱麻似的情绪在他大脑里好似激流般地涌动着……头一天,这个搪瓷盘子就装满了又黑又黄烂成奇形怪状的糟牙,就像一盘子缺胳膊断腿的蚂蚱蠢蠢欲动。
自从坤丁在柳林铺集市上开始了拔牙镶牙的营生以后,好像惊动了老天爷,这位无所不能的地球之外的家伙让方圆二三百里的人牙齿都出了问题……每到逢集,坤丁那个摆满各种糟烂牙齿和牙科医具的桌案前总是拥满了牙病患者。尽管那个时候还不富裕,但穷富都不能影响人们追求牙齿完美,像后来我去非洲一趟,看到几乎所有的黑人手里都有一根剥了皮的树枝,刷牙那样捣进嘴里时时刻刻磨蹭牙齿,所以黑人的牙齿分外洁白……可以说,追求牙齿完美是全人类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这些年来,我一想起坤丁拔牙镶牙的情景,就会看到成群结队的牙病患者拥进我们李庄。是的,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他们不光簇拥到柳林铺集市上请坤丁处理坏牙,而且还不分昼夜络绎不绝,拥进我叔叔李白牙家里,央请坤丁给他们拔牙镶牙,或者给他们安装一个银牙套或者金牙套。我记得坤丁开始牙医营生还不到一个月,就不需要再到集市上架桌案摆摊子了,他像个在深山中得道的高明牙医一样直接在家坐诊,搞得我叔叔家如天下闻名的牙科医院一般。县城里经常有人闻名而来我们李庄解决牙齿问题,那都是不足挂齿的。从遥远的省城驱车赶到我们李庄拔牙镶牙,你肯定认为过于夸张了。如果说起京城那十三位中老年足球队员跋涉而来就为在同样位置的一颗牙齿上镶上相同的金牙套,你一定认为这纯粹是天方夜谭放狗屁……你要是真这么认为了,那就可以肯定你对坤丁那高超的牙科技艺一无所知,对我们李庄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我们李庄一尺高的小孩说话做事都是来有来处去有去处,何况我这么一个在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也勉强可以算作有点儿文化的人手握确凿证据言讲正经事情呢!
先生们,女士们,请看我手里的这一摞照片吧。其中这两张大幅合影就是那十三位来自京城的业余足球队员。一张是镶牙前的合影,一张是镶牙后他们和坤丁先生的合影。两张照片都是笑出牙齿的,你一看就明白哪一张是先拍的,哪一张是后拍的。你可以戴上金丝框近视镜或者老花镜,认真看看这张镶牙以后的照片,看看他们的十三颗金牙套是不是都镶在同样位置的那颗牙齿上!你再看看他们黄红相间的运动衣上的一行字:金牙套中老年足球队……这难道是天方夜谭放狗屁吗?如果什么事情只有亲眼见过才能相信,那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可怜虫,在城市里行走会看不见井盖,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在乡村走进高粱地会有人看见,但绝对没有人看见你从高粱地里走出来。也就是说,城里那些揭开井盖的黑洞洞会吞噬你,乡村里青纱帐般的高粱地会分解消弭了你……
(节选自2023年第3期《芙蓉》短篇小说《我叔叔的人生片段》)

李亚,安徽亳州谯城人。著有长篇小说《流芳记》《花好月圆》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万花球》等两部,获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李亚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