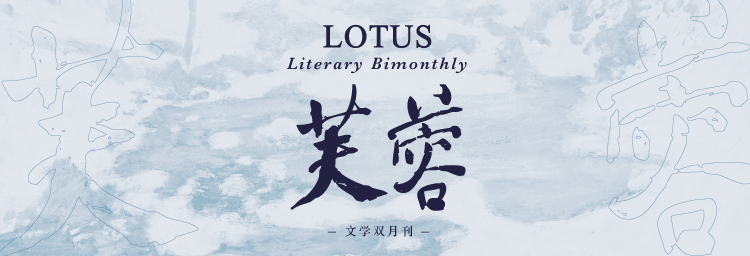

哭嫁歌(中篇小说)
文/蔡测海
格村的女人很漂亮,是猜想。谁见过她们的脸?黑丝帕遮着新娘,像阿拉伯女人被黑纱罩得严实。黑丝帕遮住的新娘,会得到某个男人的证实,麻脸、疤脸、俊俏的脸、天生的脸,在某个男人那里,都灿若桃花。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记得外婆的样子,她戴着做新娘时的黑丝帕,那黑丝帕,有汗和蚕丝的混合香味,岁月的香醇。那时的外婆,脸上有许多皱纹,像蚕丝遮盖了年轻漂亮的脸。她年轻时赶集,用黑丝帕遮脸,防人贩子,防土匪。一怕被卖,二怕被抢,还怕被偷。年轻漂亮很宝贵,凶险。恶人多,漂亮不是好事,有钱也不是好事。钱多的人,家里挖过钱窖,要不做一道假墙。赶集时,一家人穿破衣,打扮成叫花子。漂亮年轻的姑娘,要遮脸,或者脸上抹锅灰。这有什么好?我问。外婆说:你没钱,也不漂亮,不怕。等你长大,哪天有钱,娶个漂亮女人,麻烦就大了。我说我不怕麻烦。外婆笑了,那笑容,几乎要挣断满脸蚕丝,那笑声如裂帛,几颗牙齿,像交错的石头山,一颗上牙摇摇晃晃。外婆的鼻唇沟好看,那是她青春靓丽的痕迹。外婆把挂在身上的铜钥匙交给母亲的时候,把青春靓丽移交给母亲。外婆对母亲说:保管好。
外婆生养七个女儿,七姐妹,七仙女。仙女漂亮,有仙道,下凡来要嫁给打柴的看牛娃,生个孩子,做些家务,再回天庭。夫妻一年里七夕相会,十万只喜鹊搭桥,银河无声,也无岸。
母亲七姊妹,后来都嫁了人,生了孩子,一群表兄弟表姐妹。七姊妹没一个回到天庭。给她们讲银河鹊桥,会挨骂,你哄鬼呢!我有二姨、三姨、四姨、五姨、六姨、七姨,没有大姨。我问我娘,我大姨死了吗?我娘说:大姨就是你娘。你表兄弟表姐妹叫你娘大姨。我娘最大,我在表兄弟表姐妹中算是群主,君临表亲,同一血脉,他们不服不行。
我的几个姨,都嫁给牛郎,使牛耕地犁田,还打柴。她们一开始就嫁对人了,如果后来她们能上天宫,我外婆就是王母娘娘了。外婆生养七个女儿,没生一个儿子,我没舅。外婆对人讲:女婿半边子,我养了三个半儿子,谁说我没儿子?外婆漂亮,她七个女儿都漂亮。外婆会绣花,七个女儿都会绣花。外婆会做坛子菜,七个女儿也会做,就是做不出外婆做的那个味。外婆会讲古,没读书。我娘是老大,读了一年书,二姨、三姨、四姨、五姨、六姨,分别读了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书。大的带小的,年纪大的读书少。七姨读了七年书,会写会画,姊妹中的斯文人。
七女嫁七郎,七郎七艺,万事不求人。在我们那一带,外婆就是人样子,别人拿她作比。你看看,七个女儿七朵花,七个女婿七个能人。你看看,她家做水桶做个洗脚盆都不要请木匠,做衣服不要请裁缝,杀猪杀牛不要请屠夫。你看看,她家过年过节有多热闹,吃饭,屋里摆不下桌子,要院坝搭棚子。
说外婆生养七个仙女,七朵花,大致这样。后来我读几年书,认识几百个字,还爱点儿文学。有人讲,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聪明人,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不太聪明的人,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人。我想,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人贩子,以后把女人比作花的那些人,不是色鬼就是媒婆。没有一个女人会说自己是一朵花,在撒娇时会说自己是乖乖女。没什么比喻会让一个女人更比她本人还完美。我对马六说:你真好看,像一朵花,一朵桃花,马六就哭了。我说她像一朵杏花,她也会哭。
七姨嫁人了,我娘做伴送亲,娘带上我。迎亲送亲都是大人,只我不是大人,算个搭头。搭人一个。努力长大吧,七姨嫁人了。
七姨坐花轿,我和娘跟在花轿后边。一路上坡下坡,还过河,路不好走。七姨唱了一夜哭嫁歌,哭腔歌唱,姊妹姨婶陪哭唱。手帕捂脸,俯仰之间,数少女时光,告别亲人、朋友,也告别做女儿的日子,也歌也哭是哭嫁。手帕上有泪,或者没有。新嫁娘,你哭还是唱,哭嫁歌这个仪式要有。往前往后,不哭不唱,就什么都不会有。
我们在外边闹:新嫁娘,你莫哭,转个弯弯是你屋。吃的桂花糖,穿的绸缎布,睡的鸳鸯枕。床布帐子眼对眼,被子里面肉贴肉。
哭嫁人笑了,手帕落在地上。我娘揪了我的耳朵骂:七姨出嫁你带头闹,羞不羞?
明明是高尔斯华乐带头闹的,我就骂高尔斯华乐:你羞不羞?高尔斯华乐说大家都闹,你们羞不羞?
哑巴在山坡上放牛,哑巴是真哑巴,十六岁。他能唱山歌,唱山歌不哑,说话就哑,一句话说不出,只会用手一边比画,一边呵呵呵。七姨出嫁那些日子,哑巴天天哭,眼睛红肿,他妈给他眼睛涂猪苦胆汁,不见好。哑巴站在半山坡一块石头上唱歌:天上乌云赶乌云,地上灰尘赶灰尘,桌子上面碗重碗,帐子里面人重人。
不管是不是哑巴,在山上唱什么,不会被骂羞不羞。
七姨哭嫁,哭完近亲哭远亲,哭完果树哭近山,哭过猪圈牛栏,最后搭脚岩。
你从山上滚下来
痛不痛
大锤打你
痛不痛
绑你拖你
冤不冤
脚踩手搓
苦不苦
大热天
不出汗
大冷天
不穿棉衣不烤火
天晴不见你渴
下雨见你出汗
喊你不应你不聋
掐你无声你不哑
听的人说,七姨哭搭脚岩是哭哑巴,哑巴在山坡上唱歌。
搭脚岩放在家门口,也放在上坡下坡的路坎里。送亲路上,抬花轿的踩翻一块搭脚岩,我娘一声惊呼,生怕摔着了七姨。两个抬花轿的人,四条腿,稳住了,花轿里的人是摔不起的。
七姨父在成为七姨父之前,我们叫他陈同志。国家干部,都叫同志。他们吃国家粮,管国家事。同志就是干部,干部就是同志。老百姓之间,叫大爷大伯大叔大姨大姐老弟老妹,叫同志会笑死人。老师和医生也不叫同志。七姨父是个干部。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的人。后来读了几句唐诗,知道有个陈子昂,我七姨父叫陈子安。读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七姨父差点就是个大诗人。语文考试题,《登幽州台歌》的作者填空,我不小心写成陈子安,我因此留了一级,这都怪七姨父的名字。
陈子安是省城银行干部,下放住我二姨家。讲武汉话。武汉话和本地口音差不多。二姨家在酉水上游,酉水是长江支流的支流。一河水,下头是武汉,上头是我二姨家。二姨家那个寨子,叫鱼潭。陈子安来了没几天,一寨人开始讲武汉话,把鱼潭讲成武汉大码头,这地方来了一群武汉移民一样,到武汉话讲好了,就去省里当干部,到了省城,不当干部也能吃饱饭,卖黄泥巴也能赚钱。后来,他们有人讲一口武汉话,到武汉过上好日子,后来他们想再回鱼潭,回不来,他们铁了心做武汉人。大码头一带,差不多都是鱼潭人。
陈子安有一本巴掌大的书,他用牛皮纸做封面,毛笔字写的书名——《苏东坡诗词选》,那毛笔字写得比我语文老师的字好看。二姨给七姨说媒,说陈子安是武汉人,又是国家干部,嫁给他就是嫁武汉,嫁国家。我第一个赞成,陈子安的毛笔字和他的人一样好看,他爱读诗。二姨说媒,只是揭开一张纸。七姨和陈子安看露天电影,两人贴在一起。陈子安说七姨的眼睛像电影里李铁梅的眼睛。我在暗处听他俩说话,学舌给七姨听,七姨说:莫乱讲,我给你吃核桃吃桂花糖。我哪会乱讲呢?只是想骗七姨的核桃和桂花糖。有人讲,人心变坏是从吃桂花糖开始的,这话我信。七姨给我吃桂花糖,要我莫乱讲,其实是她和哑巴的事。哑巴和她好,两人躲在石头后边,要我帮他俩望风,有人来了就大咳一声。我让口水呛了,大咳。他俩从石头后边跑出来。七姨骂我:你故意是吧?哑巴是个慢性子,我想他俩什么也没做。这事要让别人知道,就当他俩做什么了。人想人,都会往坏处想。不幸知道人的秘密,守口如瓶,话烂在肚子里。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我好懂事呢。
送亲到文庙。新郎,也就是七姨父,住文庙。禅房做新房。这文庙,先前是陈子安祖上捐建的。陈家祖上是酉水河边大户人家,做桐油生意发家,后来在武汉置业经商,几条桐油船,一路到天津,供天津李氏油号。天津李氏油号,原先也是酉水一带大户,也是做桐油生意。酉水桐油生意有多大?一时可比当年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生意。
文庙百多年历史,不算老建筑,算旧建筑。孔子的石造像断成三截,头、身、下肢散落三处。两根镂雕浮雕的大石柱完好。一座庙做婚房,有些宽阔。庙内有两株古柏,天井里种一圈兰花。有十来间僧房,还有藏经阁和戏台。看来,这寺庙,僧俗皆宜。
陈家钱多。修庙,办学。给辛亥革命捐过钱。给中共地下党捐过钱,给抗日的国民军捐过钱。抗美援朝,陈家捐过飞机。陈家那个家,叫爱国民族资本家。陈子安是爱国人家后代(下放原因不详),他的待遇比一般下放干部要好,政治上受保护,工资级别、生活待遇享受十二级干部待遇,比县团级还高一点。新婚日子,他穿的是凡尼丁裤子,毛哔叽中山装。他娶了七姨,我们表兄弟表姐妹有桂花糖吃。他那一身衣服的钱,能买一头大水牛。嫁这样的男人,不要哭。要是嫁了哑巴,那才要哭一场,苦呢。花轿过黑松林,哑巴拦在路上,我娘让他走开。我娘说:都是好乡亲,莫拦路。哑巴听话,走开了。村长六叔的话哑巴不听,我娘说话他听。让条路是让个人情,这人情留着有用。哑巴虽口不能言,但心里聪明、亮堂。宰相肚里能撑船,哑巴心里能跑马。一个好哑巴,是不是顶得一个陈子安?
新娘三天三夜不出洞房,三天后出来,就是少妇人。七姨在洞房吃了三天桂花糖和月饼,吃甜酒冲鸡蛋,陈子安倒了三天便盆。庙里没抽水马桶,和尚是从庙的后门出去,在庄稼地解溲。庙里要洁净。
我叫马六,她说。七姨给我一块月饼,有芝麻、核桃,还有冰糖。我掰开一半给马六。那年正月,我一个人跑到唐四家,堂屋的板壁上有几张美女画,人脸像格村的姑娘,只是衣服不同。画画的怎么知道格村姑娘?他什么时候见过格村姑娘的脸?美人什么时候画成了美人?格村的姑娘是照着画中人长成的,还是那些画是照着格村姑娘画的?画里有一个人像马六,马六就是其中一张画。是的,我一直记得。马六吃完半块月饼,说好吃,她吮着自己的指头,问我:还有吗?我摊开手,说:没了。她又来舔我的手。我说:我以后有了月饼,给你吃。还有桂花糖。马六说:我长大了就嫁给你七姨父,做你七姨,好不好?我说:我也要长大,自己做月饼,做桂花糖。要吃什么有什么。
人心是从吃桂花糖变坏的。真是。
陈子安算盘打得好,左右手打两台算盘。我的珠算是他教的,他教我珠算口诀,教我打六六六练指法。除了珠算,他还教我念《唐诗三百首》,给我讲宋词、讲苏东坡、讲秦观。都是在文庙,庙里一世界,庙外是天下。和我娘送亲,后来我就成了陪嫁,寄住在七姨家,也就是文庙,方便我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
陈子安当了人民公社会计兼秘书,是大会计。生产队的会计叫小会计。乡村的富裕生活,一天的劳动价值,就是大小会计算出来的。大会计陈子安有多大?供销社的厉同志讲,那个陈子安,是个大人物。厉同志在供销社收购山货,卖盐卖糖卖布卖土茯苓酒,脖子上挂一条蓝布围裙,像旧时读书人穿的长衫。厉同志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与某研究所的吴同志齐名,讲天下钱生钱的道理,然后,一个国家发了大财。厉同志说大会计陈子安是大人物,这个人就真是大人物。
我们倒没看出陈子安是个大人物,就算他待遇高,穿凡尼丁、毛哔叽那么贵重的衣服,就算他衣服上的镀金铜纽扣值钱,他也不像个大人物。他喝土茯苓烧酒,下中国象棋,读中国古诗词。出门在外,有人说:你格村人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像是夸你是个人物,其实当你是饭桶酒桶。对于这样夸我的人,我会回一句:没你厉害,对酒肉表示敬意,也没什么错,我们拿酒肉敬神。神隐藏在神像后边,或者很远,在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大人物像神一样,隐藏更深。集市里人挤人,哪一个人是大人物呢?河里哪一条鱼才是大鱼呢?赶集时,我生怕自己走失,再找不到自己,我紧紧盯着父亲的背影,盯住他蓝衣服上白色的汗渍,我的目光像盐一样画在他的背上,白云边的图形。人多的时候,父亲从不牵着我的手,手会挤脱,目光不会折断。
父亲成了大人物,是中秋节那天。
我在七姨家寄居大半年,逢赶集,我娘来看我,带些鸡蛋,还有一只画眉鸟。七姨父和七姨都喜欢那只画眉鸟,我也喜欢。我要我娘把那只鸟放回去,放回屋后的竹林,它在找别的鸟,别的鸟在找它。那只画眉鸟飞走了,不知会落在哪里。
我娘问我,在七姨家好不好?我说好。七姨给我吃桂花糖。七姨父说我,少吃糖,糖吃多了坏牙齿,坏肠胃,还会长成糖心人,就是傻子。是的,人心是从吃桂花糖变坏的。七姨父要我少吃糖,忘记甜味就好了。他要我多读古诗,喜欢的就抄下来,他给我买了十几支八分钱一支的毛笔,告诉我等那些毛笔写坏了,字就练好了。我没评上五好学生,七姨父没怪我。他对我说:没评上五好学生,就做个最好学生,一样是好。我问最好是几好?七姨父反问我:你说呢?
七姨父喝酒,下中国象棋,用毛笔抄古诗词,不抽烟。我父亲和别的几个姨父都抽烟。有的人抽烟,是为了思考,也有抽烟抽成大人物的。我父亲他们几个抽了半辈子烟,也不见变成大人物。我娘七姊妹嫁人成家,从未聚齐。这年中秋节,我娘约她们带上丈夫到七姨家过团圆节。我爹和那五个姨父自己带烟,七姨家不备烟,酒管够。
七姊妹聚齐,都说大姐最年轻。我娘很开心,那情境,比未嫁时还亲热。七仙女还是七仙女,个个彩霞妆。我娘穿初嫁时绣花满襟衣,二姨穿印花布衣,三姨穿阴丹士林,四姨穿月色竹布,五姨穿棉纺绸,六姨穿夏布,七姨穿云锦。六个抽烟的男人和一个不抽烟的男人,我爹是庄稼好把式,二姨父是鲁班弟子,三姨父是铁匠,四姨父是鹭鸶客,五姨父是酱油客,六姨父是杀猪的。我老爹背了一袋黄豆,二姨父带了一块砧板,三姨父带了一把菜刀,四姨父带了一条鱼,五姨父带了一瓶酱油,六姨父带了一副猪大肠,七姨父摆了一个场子。
那一个中秋夜,月亮是好。七姨父说,难得一聚 ,今晚大家一起演个戏,那戏台一直空着呢。七姨父以前在武汉时,唱过汉戏。他时不时要唱一句:那赵子龙长坂坡杀敌如入无人之境,一匹马一杆枪救阿斗奋不顾身。我爹他们几个没演过戏,只看过戏。心里也想过上戏台演一场,又没外人看,怕什么呢?
几个男人上了戏台,让我父亲站在戏台中央,让他演汉武帝。只要唱一句御驾亲征过黄河,剩下的七姨父帮他唱,父亲一上台就傻了,呆了一会儿,问七姨父:怎么过黄河?七姨父帮腔:御驾亲征过黄河,平定江山——外边大喊:着火了!着火了!
大家跑出去一看,对面的牛肉面馆着火了,喊的人多,救火的人少。父亲和几个姨父忙去救火,把火灭了。回来,七姨父说接着唱戏。我爹说:不演了,怕火。
我爹就这样当了一回大人物,这是值得纪念的事。后来,我问父亲:你知道汉武帝是什么人吗?他说:演戏呢,我哪知道他是什么人?不就是皇帝吗?我们这个姓氏的先祖就是一个王,他有一块领地,种植和放牧,养肥了我们的氏族。父亲不识字,不识字也是会说话的。我娘嫁给我父亲,是因为他老实,不多事,他跟随季节,从不错过。他有自己的谋算,在收获的时候就想到播种。父亲也是有野心的人,他想做这块土地的王。在戏台上演汉武帝的时候,他闭上眼睛,还深吸一口气,那沉醉的样子,真像一位皇帝。他那一刻,真跟七姨父默读诗一个样子。
山河广大,人散落四方。青绿而黄的山岗,时光点染。山与时间互相变化。格村的山,是亿万年前从海底升起的,海底时间,变成山上时间。只有父亲是不变的。土地改革后,单干,合作社,人民公社,不管他穿黑衣还是穿蓝衣,把衣服穿旧再穿个烂,父亲对土地的坚持和庄稼的热情,从未改变。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庄稼地,长得最好的玉米和烟叶,一定是父亲种的。人勤地不懒,讲的是父亲。懒人、闲人、聪明人,三个人发明了风车、水碾、木牛流马和别的省力的东西。乡下有个好懒人,一定会是个好发明家。父亲不是发明家,只是个有耐心的人。
父亲为人,得到七姨父肯定。七姨父不懒,他有闲且聪明。聪明而有闲,不可兼得。聪明必然多事。七姨父做人民公社大会计兼秘书,不嫌事多。他多次观察我父亲的劳作,然后做土地分析。他得出结论的时候,就去给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仁宽同志汇报思想。他去敲仁宽书记的房门,先用指尖叩几下,没应,再用拳头敲门。仁宽书记开了一条门缝,伸出脑壳说:你故意是吧?你嫂子来了,在屋里头。七姨父真没想到,书记也是要有老婆的。平时只见书记一个人进出,穿胶鞋下生产队,挎帆布包上县城开会,没见过书记带个女人到处跑。漂亮的妇女主任英子给他汇报工作,他总要拉七姨父在场。他常给公社干部讲:男同志女同志都是同志关系,这是纪律。年轻人搞恋爱,不影响工作,我支持,乱搞,我没看见,纪律看见了。
仁宽书记穿衣服出来,陈子安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嫂子来了。
仁宽书记问:什么事?
陈子安:就是给书记汇报思想,到办公室慢慢讲。
两个人来到办公室。
陈子安:书记,这两年,我一直观察我家姨姐夫的半亩自留地,他家半亩自留地四季不闲,种菜种粮栽烟叶,庄稼长得好,土地价值高。每亩土地价值比集体土地价值高三倍以上。他半亩自留地比集体两亩地产值还高。
仁宽书记:这是个苗头,一些人把心思都花在自留地里,鸡屎猪屎牛屎及人的大粪,都给自留地吃。集体出工不出力,发展下去问题很严重。我想召开人民公社社员大会,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讲讲你姨姐夫这个问题。
那一天,是一九五七年端午节过后的第二天。
陈子安:书记,开大会我支持,莫点我姨姐夫的名。你一点名,我不就成了举报人吗?我那姨姐夫没文化,人老实,心胸狭窄,还讲面子,你一点名,他想不开,喝了农药呢?书记一言九鼎,他扛不住。再说,我那姨姐夫种集体的地也当自留地一样种,集体也有长得好的庄稼,那是我姨姐夫种的。他的家肥大部分交给集体,他交生产队的人的大粪从不掺水。
是的,七姨父讲得对,我父亲给集体养的那头大黄牛,很健壮,他爱惜公家的牛,不亏它。我受到良好的教育,生产队要像这头黄牛一样健壮,我们一家人才会吃饱穿暖,长大后才会找个好老婆,做个好社员。有个好儿子一定有个好爹。我同父亲,就像时间和大地,我们同时是时间,也是大地。七姨父给仁宽书记汇报思想时,他说大地分三块,属于国家的叫山河,属于集体的叫山坡,属于个人的叫泥巴。泥巴掺进阳光和雨水,就是时间泥巴,从先祖到我,生于泥土,作于山坡,长于山河。我们大爱山河,时有山河故人来的惊喜,时有国破山河在的痛惜。哭嫁歌,歌哭泥土、歌哭山坡、歌哭玉树临风的英雄和诗人、歌哭山河。那些在风中唱过时间的诗人,那些在马背上唱过山河的人,那些在流离呼喊大地的人,古时明月今时光岁月匆匆,他们仍是未来的歌者。
那一年,就是农业八字宪法颁发的那年,山坡上有石灰写在石头上的八个大字: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那年冬天,兴修水利。我们这里,造一座卧龙水库。父亲和几个姨父上了水利工地。我娘她们七姊妹也上了水利工地。
那一年,厉同志同另一名下放干部陈子安告别,他或将去北京教书。他是会计培训班讲课时认识陈子安的。陈子安拿了两篇文章给厉同志看,一篇是《农耕地价值探讨》,另一篇是《农民劳动力价值探讨》。厉同志在煤油灯下一口气读完两篇万字长文,把陈子安从被窝里拉起来说:陈子安,你是个大才,将来是个大人物。
那一年,厉同志正在读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在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一路看南方的稻子和北方的麦田。大地一闪而过,他正在思考中国农民的产权问题。
那一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种出第一代杂交水稻。他在海南岛发现了野生稻种。
那一年,离废除粮票还差二十六年。
那一年,陈子安拿了他的两篇论文给仁宽书记看,陈子安说他的一位同学在农学院,管一本内部科技刊物,他的文章可以在那本刊物上发表。不过,要仁宽书记先审查,然后加盖公章。仁宽书记说:文责自负,公章你自己盖。后来,那两篇文章发表在农学院内刊《农村发现》秋季号。
我娘她们七姊妹组成铁姑娘队,挑土,抬石头。我父亲和几个姨父两人一组,组打夯队。七姨父负责写黑板报,给工地广播站写广播稿,还给工地宣传队写三句半和活报剧脚本。
我从七姨家回到自己家,我家那只大黄狗和黑猫一齐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人都不在,它们看家,等这一家人回来。见我回来,它们又高兴又亲热。竹林的画眉鸟在叫,离猫狗和人不近。几只老鼠在梁上奔跑,麻雀在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米。
这一年,冬天,我在家与黄狗和黑猫相聚,还遇见那个冬天里的一些小动物。那个冬天,我还想遇见一个妖精,她叫马六,我想她,像那冬天的雪花那么多。你知道那个冬天的雪有多大吗?所有想得到的地名都被一场大雪盖住了,再认不出一个地方,叫不出某处的地名。十二岁的爱情,落雪的样子。
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黑姑娘落进天坑,摔死了。黑姑娘是一头刚学会耕地的母牛。村里的几个老人,把它在天坑的尸体剥了皮,再把它分割成几大块弄上来,好牛肉送到水利工地上,我们只吃拆骨碎肉。一口大灶锅,烧旺火,熬牛骨头,大半天,牛骨头上的碎肉就一点一点被撕下来。猫和狗很有耐心地等在一边。
我家那头大黄牛,在天坑边睡了三天,不吃不喝。我给它送一把撒了盐的青草,摇着它的角对它说:别太伤心,该吃还吃,该喝还喝,你是头当家牛呢。它站起来,吃草,像什么也没发生。它恢复了一头牛样。它拉了一堆牛粪,不再伤心。我拍了拍它说:好样的,大个子。
我心里一直爱恋的马六,后来死于难产,又说是死于子宫破裂大出血。她嫁到武汉。出嫁时,也是唱了一夜哭嫁歌。我问过七姨,马六哭嫁歌哭了我的名字没?七姨说,马六出嫁时,手帕捂着脸一直偷偷笑。马六还会是马六,如果她不死,见了她,我会请她吃桂花糖。村子里的姑娘后来都出嫁了,近处是嫁在来凤、漫水、百福司,远处嫁在恩施、宜昌、重庆,只有马六嫁到武汉,一座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马六死了,她的灵魂会走水路或者走旱路回来,好好地做一回新嫁娘,坐一回花轿,花轿里坐一个妖精。
苏东坡有个妹妹,叫苏小妹,人漂亮,诗文做得好,二十一岁就死了。人们没怎么纪念她。苏东坡爱他的妻子,那苏夫人正是绿肥红瘦时,也死了。苏东坡明月夜到短松冈看望苏夫人,那女子已死了十年。到今天,那女子已死去一千多年。那个会算流年八字的刘伯温,说苏东坡命里克妻克妹克女人,苏东坡命里也克父克兄弟克自己。他一辈子没走过大运,除了写诗作词练毛笔字,几乎没什么大出息。他和同事搞不好关系,从顶头上司王安石那里得点好处,就跑到天涯海角去了。比马六嫁到武汉还远。比起下放干部陈子安,苏东坡下放早了一千多年。
其实,我对马六的思念,要少于我对水的思念。一见想到水,我就忘记马六。我喜欢水,多于喜欢马六。那年大旱三个月后,仁宽书记号召修山塘,我发动父亲和几个姨父,修第一口山塘,第二年发春水,山塘贮满水,人畜用水饮水靠它,还养了鱼,种上荷花。那口山塘修在一片树林边,贮雨水,还接上地下几股细泉。这塘耐旱,成了有名的大堰塘,一个新地名。七姨父陈子安拿大堰塘当榜样,找仁宽书记谈想法,山塘加山林,耐旱。我们这喀斯特地貌,无草木无水,会石漠化,旱地变湿地,要趁早。不要等到一片石头山,石漠化,这一块地就废了。仁宽书记竖起大拇指说:厉同志说你是大人物,不假。旱地变湿地,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实现这个理想。
酉水河两岸的山上,修了几十口山塘。山上开过油桐花,桃花也开过了,山上开满荷花,鲤鱼跃出荷叶,惊飞水上蓝鸟。蓝鸟,蓝背白腹,尾巴比鸟身稍长。这蓝白精灵,我们也叫它点水雀,它尾巴点水,然后起飞。有了山塘,这蓝白精灵变得活跃欢快。鱼喜欢水,还有我和蓝雀也喜欢水。
修山塘很忙,七姨父三个月没回家。他找仁宽书记请假:书记,我请几天假。
仁宽书记:请几天假?
陈子安:三天。
仁宽书记:干什么?
陈子安:孩子病了,上吐下泻。
仁宽书记:你是医生?
陈子安嗫嚅:那,我找个老婆就放在家里?做腌菜坛子?
仁宽书记忍不住笑了:你早不说是请假看老婆?回去吧,准你三天假,够不够?不够就五天。
七姨父连忙说:谢谢书记,够了够了。仁宽书记说这些日子,修山塘累了,回家要小心,别太累着。陈子安回来,到仁宽书记那儿销了假。仁宽书记说:你才回家打个转,人就脱形了,给你煨了一瓦罐鸡汤,乌骨鸡,补身子。仁宽书记又说:我调县里去了,任副县长。陈子安一愣,好一阵才说:书记,你怎么就走了呢?我们的理想还没实现呢。仁宽书记说:我走了还有你们在这里。我去县里,也是分管农业,主要工作是抓全县水利工程。
仁宽书记交代,你们有什么困难,要来找我。要大锤要钢钎要炸药要树苗,我给你们开个小灶。还有,你个人要有个造人计划,这是千秋大业。
陈子安想了想说:记住了。
仁宽书记离开的那天晚上,公社篮球场放露天电影,讲城里工人阶级的故事,电影里的人就是武汉一家钢铁厂的人,又像又不像。电影里的武汉也是武汉,有几处景物真是,长江大桥头的龟山和蛇山,黄鹤楼,驳船和大烟囱。电影里那个人像一位中学同学,他不好好上班,偷偷出去打野鸭子,也就是天鹅,卖天鹅攒钱,买了一件料子服。穿上料子服去勾引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技术员。领导狠狠批评了这个人穿料子服。陈子安想,电影里那个人最大的错是杀死那么多天鹅,领导放过他杀天鹅,专批他穿料子服。那年代,还没野生动物保护法,一律蓝工装,穿料子服勾引女青年,性质恶劣。武汉那样的大城市,是有人去过美国又好像很懂美国,他们说,在美国,平常爱穿名牌开豪车的人,差不多是亚洲人和黑人,这样少被歧视。
电影散了,都在看陈子安穿的凡尼丁。
陈子安紧走几步,跟上仁宽书记说:书记,我以后再不穿凡尼丁,穿跟大家一样的衣服。
仁宽书记看了陈子安一眼,大声说:你傻?我们这么辛苦,造林,修水利,提高农业产值,就是为了人人穿好衣服,天天吃肉吃大米饭,过好日子。等好日子来了,干部要带头穿好衣服,穿出个好样子。
仁宽书记出任管农业的副县长,兼全县兴修水利指挥长、卧龙水库工地指挥长。卧龙水库动工比长江葛洲坝电站早几年。葛洲坝水利工程动工时,卧龙水库已竣工,库容量一千四百多万立方米,灌溉十万亩,饮水十万人。
七姨父上卧龙水库工地,找我父亲借一件旧衣服,说等卧龙水库修好了,再还我父亲一件新衣服。我父亲对七姨父说:你不嫌汗臭就拿去穿。七姨父上工地,总把我父亲的旧衣服罩在他的凡尼丁上。几个姨娘笑他,把好腊肉埋在腌菜下面。
七姨父,陈子安,装穷。
我对装穷、装阔、装傻、装学问、卖聪明、讨好卖乖,不以为然,也不深恶痛绝。习以为常的伪装、隐藏,不能说明人的好坏,人性使人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是人性。七姨父给我温暖和爱护,教我学珠算、练毛笔字,教我读古诗,他是个好人。他对我的用心,比父亲对我的用心要多。因为七姨父,我没长成一头黄牛,我长成另外一个生命,除了像黄牛一样劳动,我还会珠算,会写毛笔字,还会读古诗。在古诗里读到大地和山河,一个人就走过万水千山,走到远处。
卧龙水库在武陵山腹地,蓄雨水面积四十多平方公里,它将成为干旱的喀斯特地区的一处永久性湿地。五十多年以后,我带了妻子和女儿,来到卧龙水库,这海蓝色的高山湖泊,一片水色,一湖光影。我对女儿说:这湖里的大鱼,有两百多斤,比湘江里的鱼还大,有洞庭湖里的大鱼那么大。以前,这里没有大湖,也没有大鱼。
站在大坝上,我对女儿说:这大坝,是扁担挑出来的,是独轮车推出来的,一群人,像蚂蚁搬家那样搬来这座大坝。你爷爷奶奶,还有你几位姨奶奶,修过这座大坝。女儿说:我们家的人真了不起。
我们一家人,是开车过来的。离开卧龙水库时,那还是半新的越野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只好找我一位表兄弟开车来接我们,让交警把那辆越野车拖到县城修理厂,修车师傅检查这辆越野车,没一点毛病,车一下就发动了。这真是奇怪。女儿说:爸,去看这样的地方,应该步行。
那个冬天很冷,河风比山风更冷。工地上的人们一刻也不敢停歇,一停下劳作,汗湿的衣服就结冰了。工地上全是胡萝卜样子,手指脚趾都冻成胡萝卜。会劳作的胡萝卜。指挥部分发了一批精纱手套,没一个人戴手套。那手套拆了,给孩子们织成袜子。买一双袜子要多费几毛钱几寸布票。仁宽书记手大手指长,叫他大胡萝卜。
那个冬天的劳作,叫洗胡萝卜。哪一个冬天不是洗胡萝卜呢。
陈子安写了篇广播稿,叫《发扬胡萝卜精神》。他编个舞台短剧,叫《洗胡萝卜》 。有三句台词:一觉醒来洗胡萝卜,再一觉醒来涨大水,再一觉醒来是卧龙。
陈子安一大早起来,写黑板报,用粉笔抄写那篇《发扬胡萝卜精神》 。写几个字,粉笔掉在地上,捡起来再写几个字,粉笔又掉在地上。胡萝卜手指搓揉几下又写,还是拿不住粉笔。拿了支长粉笔,又折断失落。陈子安气恼大骂,我日你粉笔的娘!指挥部干部泽浩同志正好路过,听陈子安骂粉笔的娘,就正色道:陈子安,你发泄不满,你这个外面穿旧衣服里面穿料子服的下放干部,轻点说,是落后分子,重点讲,是思想反动。陈子安正恼火,气头上回话:泽浩同志,我在这里做事,你在那里闲逛。你砍了我的手指好吧。这一句说到泽浩同志痛处。有母子俩饿了,偷了集体地里一根苞谷坨生吃,被泽浩同志看到,他砍了那做娘的一根手指。泽浩同志被撤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降为一般干部。泽浩同志一气之下,跑到仁宽书记那里告状:县长(人家其实是副县长),那个下放干部陈子安,日粉笔的娘,也就是日黑板报的娘,也就是日卧龙水库的娘,也就是日农业八字宪法的娘。仁宽书记舀了一瓢冷水让泽浩同志喝,他对他说:泽浩同志,我要纠正你一下。不要叫我县长,我是副县长,现在是卧龙水库工地指挥长,一个修水库的人。在这里,大家都是修水库的人。下放干部也是干部,是同志。对同志要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讲那么多也就是。吃饭就是吃饭,不要讲人家吃肉。
泽浩同志直到退休,还是泽浩同志,没提拔重用,也没降低待遇。后来,我在县城遇到泽浩同志,他说刚领工资,有一千多块钱,要请我吃饭。他说年轻时不犯错误,待遇比这个好。我说,水涨船高,你以后领的钱比这个多。我说要去看看仁宽书记,请他吃个饭,你一起去?他说不去,要回家浇花,喂猫。也算了一件心事,泽浩同志晚景还好。
十年前,父亲八十岁生日,约上几个姨父、姨妈,还有仁宽书记、哑巴,泽浩同志说有事,没来。人活到八十岁,想约的人总是聚不齐。子孙多了,少时的同伴少了。仁宽书记说:泽浩同志人老事多,总是瞎忙。
父亲八十岁生日,是在卧龙水库过的。吃鱼。水库的鱼肉质好,没泥腥味。
哑巴指着大湖,伸大拇指。又指山坡上的石头,伸小指头。大拇指是指鱼,小指头是指蚯蚓。炎夏,蚯蚓从湿热的泥土里跑出来,在灰尘里打滚,让烈日晒成尸棍,僵如砂砾。
我娘说:哑巴不会说话,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哑巴,你说不出,就唱吧。父亲说。哑巴咧开嘴笑,一口白牙,没少一颗。不说话的人不伤牙,牙齿会一直好下去。脱牙的人,都是说话累的。
哑巴一生未娶,他心里一直想着我七姨。每年夏秋之交的夜晚,他一个人站在山顶上,望天上的银河,他心里有鹊桥的故事。他是个好劳力,做最重的农活儿。两个人抬木头,他会选大的一头。修卧龙水库,哑巴挑断了两根桑木扁担,挑烂了十几副撮箕。陈子安的黑板报写过哑巴。哑巴不识字,听人说是写他,他半夜里偷偷擦掉那些粉笔字。哑巴对人比画,那么多人,都写成黑板报,要多少粉笔字?我娘她们七姊妹铁娘子队也上过黑板报,还有钢钎攻坚队、后勤供给队、水利技术模范小组、红辣椒炊事班。我父亲和几个姨父的打夯队从未上过黑板报,他们的成绩不好估算,他们把填土一层一层夯实,夯成铁板一样,用钢钎测试,插不进钢钎算是质量合格。广播里播放过打夯号子,没提父亲和几个姨父的名字。工地上,夯锤起落,锤锤擂鼓 ,地皮子嘭嘭响。武陵山,彻夜不眠。这大山的腹地,从未这样热闹喧天。
七姨问七姨父陈子安: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七姊妹写成铁娘子?陈子安笑着对七姨说:要把你们写成七仙女、七美人、七朵花,不合适,还以为是编电影呢。七姨说:也是,什么仙女不仙女,美人不美人,要修卧龙水库,人就是铁,饭就是钢。修水库这一练,好多小毛病都没了。我以前不是月月痛经吗?现在好了。我二姐不是不能生育吗?她吃过好多药不见好,现在怀上了。我五姐失眠症,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起床号才能把她唤醒。我们七姊妹,真的变成钢铁身子了。陈子安说:你大姐的斜视也练好了吧?她以前从不正眼看我,说我鼻子是歪的,还少一只耳朵。她当初最反对你嫁给我。
七姨说:我姐说姐妹中大姐最聪明,我最漂亮,姐姐们都嫁了苦命人,要我嫁个好人,人好命好。这是我姐的心愿。我们七姊妹出嫁,哭嫁歌是真哭。大姐出嫁哭七天,不算长。以前大户人家嫁女,要哭上十天半月。哭爹娘疼爱,哭姊妹情分,哭祖上阴德,哭绣楼闺房。小户人家嫁女,也要哭两三天,哭父母,哭兄弟姊妹,哭牛栏猪圈,哭针头线脑,哭搭脚岩,哭背篓,哭水桶。
毕兹卡人的哭嫁歌,女人哭唱,又琐碎,又冗长。琐碎的心思,冗长的歌哭。
毕兹卡人的哭嫁歌,除了歌哭,还夹带了劝。劝,或安慰。嫁一只门闩,摸久了,也会忠实。嫁一坨石头,抱热了也会说话。嫁一根木桩,一生浇灌,也会发芽开花结果。
毕兹卡,汉译本地人。土家族的族名。这个族群,本地人和外来人混杂。在古镇里耶,里耶,毕兹卡语,良土好地方的意思。那地方发现秦简和新石器遗址。秦简是外来人的脚迹,石器是本地人的琐碎。
毕兹卡,是歌哭琐碎和冗长的族群。这里有男人的劳动号子,有女人的哭嫁歌。屈原在这里唱过《桂颂》,刘禹锡在这里吟过《竹枝词》,王昌龄在这里写过流放日记诗。
地质学家说毕兹卡人居住地叫喀斯特。青岩山,干旱之地。毕兹卡人居住地,大武陵山,是一座巨大的青岩山,地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北、重庆。青岩山,亿万年前从海底升起,脱水成山石。这石头称石灰石,烧石灰炼水泥的石头。这石头易溶于水。晋代人记有水泥石,这石头山遇水自溶,成溶洞,阴河。地表不聚水。遇大旱,草木枯死,庄稼颗粒无收。草木死亡,青岩山就成大块石漠。毕兹卡人会再一次迁徙,成为某处的外来人。自己的水井枯了,要赶上牛羊,携老拖幼,去别处喝水。
毕兹卡人渴水,爱水,惜水。一盆水洗过菜,洗脚,洗过脚,喂牛。
毕兹卡人守护了酉水,守护了清江,守护了长江的支流。
毕兹卡人要造大湖,要引阴河成地上河。巨大的青岩山,像一匹找水的骆驼,当它走向石漠的时候,把它勒回来,让它在青山绿水中生生不息。
毕兹卡语的湖,是山坡的意思。车,是河水的意思。毕兹卡人的居住地,没有大湖和轮子。作为毕兹卡人的后人,因为语言流变,一些名词已不知其意。我再也不习惯讲倒装句,不会把吃饭讲成饭吃。到我祖父那一代,已经是改土归流后的保甲乡民。假如有匪患,我们依靠寨堡和梭镖、火铳抵抗,我们还受朝廷保护。在修卧龙水库以前很久,土匪只是故事里的一个名词。我是有一个舅舅的,他十二岁离家进了土匪营,后来被川军的迫击炮弹炸成碎片,他的手挂在一条树枝上,腿挂在另一条树枝上。他还是玩爆竹的年纪,被一颗大爆竹炸死了。
舅舅和土匪,也只是故事里的名词。舅舅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名词。在后人的记忆里,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名字,是一个叫毕兹卡人的名词。这是一定的。在后人的炊烟里,我们不在某一个山寨,不在某一栋木楼,我们只是无处不在的灵魂,像风吹散的稻香和雾岚。我们走过的路会长满荒草。我们吃过的家菜或者早已失传。河里的鱼还是我们吃过的味道吗?鱼可能变得聪明,不会再被人诱捕。鱼可能变得像水母一样透明,变成逃避捕杀的水母,让人失去钓鱼的乐趣,改变人的性情。这是一定的。
山河改样,会让人生忽然在异地。我们游历长江中游的三峡,有谁还记得,李白那个早晨离开白帝城的样子?甚至,三峡有哪三个名字?在哪三处地方?
卧龙水库这一汪水,大湖,不是毕兹卡语的湖,它是今天和往后的湖。
仁宽书记领了几位水利专家来到这里,选定在这里造一处大湖。这里原来的样子,是长满杂树堆满乱石的山沟。选址这里,是因为这里海拔高,水源丰沛,搬迁人户少,只几十户人家。这里是大武陵山腹地,山后有山,山高林密,地面水和地下水在这里汇集。水流潺潺,从未断流。大江大河枯瘦时节,这里水旺。山高水高,细水长流。
要腾出一个地方修水库,几十户原住民要搬迁。这里原住民的记忆,往上记三代,记忆也是肉体,割了很痛。搬迁宣讲队员,有唱三棒鼓的,有哭嫁歌师傅,还有会说书会念报纸的人,一家一户去做宣讲,又说又唱又念,讲农业八字宪法,水是第一位。农业八字宪法不是一部宪法,也不是标语口号,是八件农事。水利,肥料,土壤,种子,合理密植,精工细作,保育保护,管理。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
道理讲通了,举家搬迁,老人抱个腌菜坛子,小的扛一把扫帚,男人挑瓦抬柱,女的赶牛赶猪。毕兹卡人迁徙图,一幅西兰卡普。搬迁在几十里之内,百里之内,都是亲戚。投亲伴友,全是赶集市碰见的人。
还剩姓李的一家人不肯搬,舍不得一园竹林,还有一棵枣树。这李姓人家有来头,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同明朝那个李自成也是族人,搬来这里,八代以上,也算毕兹卡人的混血,亲戚。
李家嫁女,仁宽书记从恩施那边请了个歌师傅,陪哭陪唱三天。那歌师傅是我外婆干女儿和哭嫁歌徒弟。我叫她九姨。
九姨以歌伴哭,从盖头唱到扯眉,哭完《十姊妹》,哭离别,唱前程。这些都是九姨的歌引子,她要哭唱的,是毕兹卡人迁徙歌:
毕兹卡人住在海边
龙王要来
毕兹卡人让了大海
毕兹卡人去找好地方
毕兹卡人住在云梦泽
大鱼要来
毕兹卡人让了云梦泽
去找好地方
毕兹卡人住在大河边
大水要来
毕兹卡人让了大江大河
去找好地方
毕兹卡人住在街市
盐客要来,布客要来,戏子要来,青楼女子要来
毕兹卡人让出街市
去找好地方
毕兹卡人来到猴子攀岩的地方
来到麂子走草的地方
来到虎豹交媾的地方
来到野猪发情的地方
毕兹卡人支木架屋
让虎豹拉犁
把野猪送进猪圈
把麂子送进羊栏
种苞谷红苕
种荞子高粱
天旱,去大河背水
天涝,多挖几条沟
毕兹卡人的好地方
让风让云
不让旱涝
不让人懒
李姓毕兹卡人,嫁了女,专为九姨办了一桌酒饭,然后就搬到女儿那边去住,女婿家那边好田好土,米好,白菜萝卜很甜。
仁宽书记带领水利专家走在乱石滩上,几个人用鹅卵石摆了个阵势,那是卧龙水库最好的奠基。路是野兽踩出来的,一线兽迹。那位年轻的女技术员,衣服上头发上粘满草籽,这种草籽像蚂蟥一样黏人,火烤才能掉下来。这位女技术员后来嫁给一个毕兹卡人,也是位水利技术员。毕兹卡人都是黏人的草籽。
那条小河,卧龙水库的先来之水,岸边有棵很高的枫香树,有只喜鹊正在筑巢,枯枝搭建的巢已成形,再用干草装修一下就好了。那只喜鹊见了仁宽书记几个人,就停下来。到水库大坝建成,离大坝十几丈高的地方有一棵大枫香树,树上有一个喜鹊窝。喜鹊是聪明鸟,登高枝。它原先筑巢那棵枫香树,已在水底,只是筑坝时已移走。那两棵树是不是同一棵树?有人看见那只喜鹊,每天飞来飞去,衔一块石头丢进大湖,像是要做一只精卫鸟。它是学人样,总在垒石头。
那个冬天,卧龙水库竣工。等来年发大水,它就会长成一汪大湖。那个冬天,没听说全世界有什么大事。这要好好庆祝。
水库大坝就是舞台,来一场千人摆手舞,打一回三棒鼓,敲一锣鼓打溜子。仁宽书记要铁娘子队用哭嫁歌演一场《天仙配》 。七姨父陈子安做导演,让我父亲装王母娘娘。父亲男扮女装,染了桃花脸,穿上绣花缀银满襟衣。加上文庙那一回,父亲一生演了一次小戏,一场大戏,都演大人物。演过人间皇帝,又演过天上女王。好运气让给好人,父亲闭上眼睛,云里雾里,多么沉醉的时刻。
七姨演七仙女,抱个绣花枕头当孩子,天兵天将在南天门拦住七仙女,说那孩子是人间秽物,不能入天宫,把那孩子扔回人间,七仙女抱着孩子不放。你抢我夺间,我父亲忽然睁开眼,大吼一声:孩子要吃奶!绣花枕头落地。父亲本来没一句台词,没这声大吼。
满场大笑,喝彩。父亲跟着乐。他演得好,干了一件大事。《天仙配》多了父亲一句台词,就打败了天兵天将。
大坝竣工,工程指挥部没撤,还有些扫尾的事。开挖过的地方要栽树种草,残破的地方要砌石修补。陈子安是指挥部的人,要留下,写卧龙水库的总结报告。胡萝卜精神,蚂蚁搬家,这两个词,在他的总结报告里得到很好的发挥。仁宽书记要他一定要写上一条:修卧龙水库,是苦是累,但没死一个人。
陈子安想,也差点死了两个人吧。那对新婚夫妇,两人一人挑土一人推独轮车,在工地上赛跑,陈子安写过赛跑小夫妻的广播稿。有一天出工,工地上不见了这对小夫妻。仁宽书记派人去宿舍看看。去的人回来报告:那对小夫妻在被窝里赤条条地相拥着,死了。仁宽书记急忙跑到广播室喊:今天休息半天,谁不休息罚谁的工分。人都累死了,谁来修水库?就要准备开追悼会了,那对小夫妻忽然醒来,不好意思地穿上衣服,各人喝了一碗凉水,上工地去了。
仁宽书记批评陈子安,对年轻人的表扬,要适量,多了会死人的。
陈子安留下来,七姨也就留下来。她们七姊妹也一同留下,有伴。她们的丈夫也留下来。
泽浩同志问仁宽书记:我要不要留下来?仁宽书记说:你没个具体职务,去哪里呢?留下来吧。等指挥部撤了,我跟组织讲一下,你留县政府机关做一般干部,你也不年轻了,到乡下腿脚不方便。你这个人,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认的字少,做事,脑子没跟上,就把事办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以后,我要你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工作。看不见你,我不放心。
泽浩同志第一次流泪,老书记真是关心人啊。
哑巴也留下来了。他留下来,水缸天天是满的。他嫌植树种草那些活太轻,早晚挑水,把水缸装满。洗衣洗菜洗澡,用水他一个人包下了。十几口人,两口大水缸。一担水一百斤,哑巴早上挑十担,晚上挑十担,一吨水。这早晚活,不计工分。
那年春雨很猛,水库里的水涨起来,最深的地方有一丈多深,到涨“端午水”,七八月涨了河水,水库就满了。卧龙水库就是一座真的水库了,不是毕兹卡语的那个湖,是一汪大湖。毕兹卡人的语言一直在变化,山河也有变化,名字也会不同。一汪大湖,哑巴要挑多少担水才能装满呢?一个力大无穷的人,一桶一桶把大湖倒满,再一瓢一瓢把大湖舀干,要一万年。一万年,这卧龙水库,卧龙湖,是记忆之水。
哑巴戴一顶斗笠,起早挑水。斗笠被一阵大风吹落,他看见半边山垮下来。哑巴大喊:哇啦、哇啦,垮啦、垮啦。哑巴是看见一条大蟒蛇后变成哑巴的。他见了这半座山崩,突然会说话了。他扔掉水桶,一边喊一边冲进工棚。我娘、几个姨妈、我父亲、几个姨父从工棚里往外冲。哑巴冲进工棚,七姨正在洗澡,哑巴将她拦腰抱起,像捉一条鱼,飞快冲出工棚,一群人冲出几十丈远,半座山把工棚埋了。
仁宽书记、陈子安和泽浩同志从指挥部那边赶过来,看这场面,一句话没说。仁宽书记见人都在,出一口大气,说没死人就好。
哑巴抱了七姨,箭一样射出去。七姨说:抱紧我,跑远点儿。哑巴把七姨放在一堆干稻草上。七姨对哑巴说:把你的衣服裤子脱了,给我穿上,让我怎么见人?
那边半座山垮了,这边大坝完好无损,照仁宽书记的话说,大坝经受住了考验。
我父亲和几个姨父,各人回去做老本行。几个姨妈赶在计划生育以前,给我生养了一群表兄弟表姐妹。我们这一大家的姑娘,各有各的漂亮,唱一场哭嫁歌,都嫁人了。一个人,就成一支亲戚。
卧龙水库的鱼长到两三斤大的时候,最后一名下放干部陈子安走了。厉同志已经离开十几年,袁隆平已种出第二代杂交水稻,七姨和我一个表弟一个表妹跟陈子安走了。我拿了一包桂花糖给七姨,让表弟表妹在路上吃。七姨一边抹眼泪一边笑。七姨说:到了武汉,找到马六,我把桂花糖给她。后来得到消息,马六死了,死于难产。在一座英雄的城市,一个人死于难产,还是我念念不忘的人。我心如刀割。
陈子安走了,从南方走到南方,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从长江的支流走到长江。一个会读古诗会写毛笔字的人,哪里都是山河,都有一口水井和一棵老树。
哑巴不再是哑巴,只是不说话。他一个人站在山顶上,拿竹吹火筒当望远镜,遥望北方,他看见了银河,也看见了武汉。
邮递员给我一封信,七姨父陈子安写给我的。他在武汉做一个参事。几位参事中有一位毕兹卡人,当过土匪,做过国民党的师长,参加过湖南和平起义。这位老毕兹卡,一辈子都在冒险。陈子安写道:我呢,背过古诗,练过毛笔字,在卧龙水库工地写过黑板报。我同那位老毕兹卡一样老,也是个参事。我每天练毛笔字,老毕兹卡每天打太极拳。
七姨父陈子安在信中问我,这些年在做些什么?缺什么告诉他,他能帮我。
我想回信给七姨父。这些年我做过好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做。我当过山村小学老师,修过铁路,当过医生,做过两年记者;还想过到武汉做大生意,买一条大船,通江达海。我缺什么呢?就缺钱,也不是。缺个安心吧?我就缺一根扁担,去当年的卧龙水库工地挑土抬石头。好好练一场,人就实在。实在,是父亲一直教我的。
过大年的时候,父亲快不行了。他叫我:儿子,把你几个姨父都叫来,唱一回戏。我把父亲扶起来,靠在枕头上,我用黑墨水蓝墨水红墨水给父亲画了戏脸,给父亲头帕上插两根野鸡毛。然后让父亲照镜子。父亲笑了,然后闭上眼。没到大年初一,父亲笑着走了。
我把父亲埋在向阳的山坡上,那里看得见酉水。
哑巴的坟挨着父亲的坟。他每天在山顶上,拿竹吹火筒当望远镜,眺望远处,那么健壮的一个人,突然倒下。
在县城的大街上,一位白发老人,一边走路,一边弯下腰去捡地上的果皮、烟头、啃过的鸡骨头,然后丢进垃圾桶。人们说,那老头像仁宽书记,那一定是他,他爱干净。他那件蓝色的中山装,穿了多年,洗得发白,没一点污迹。
给父亲扫墓时,一位白发老妇人给旁边的哑巴扫墓。我认出是我七姨。七姨颤抖着手,纸包着的桂花糖撒落在坟前的乱草里。
七姨拄着根竹棍,她挥舞竹棍,不停地打哑巴的坟:你哑巴啦?

蔡测海,土家族,1952年生,湘西人,小说家,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小说、文论近千万字,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文学大系》。著有小说集《母船》《今天的太阳》《穿过死亡的黑洞》《蔡测海小说选》,长篇小说《地方》《三世界》《套狼》《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外文。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二、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来源:《芙蓉》
作者:蔡测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