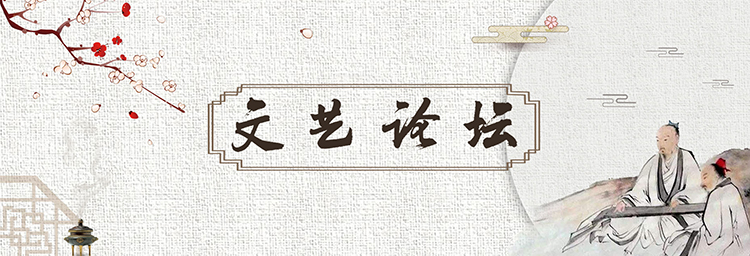

音乐表演者主体建构的接受美学分析
文/赵婧贻
摘 要:取接受美学的研究视角,以音乐表演者为对象,结合音乐表演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从接受美学“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视野融合”等层面揭示音乐表演者审美主体建构问题,并指出接受美学运用于音乐表演过程研究的局限,为深化认知音乐表演者主体建构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接受美学;音乐作品;文本;表演主体
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兴起并发展起来的,风行于欧洲大陆的一种美学思潮。接受美学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与各种社会思潮、哲学思潮、文艺思潮交流融合,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接受美学主张“读者中心论”,即以读者为中心来解读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提高了读者的主体地位,赋予了艺术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音乐表演,作为连接音乐创作与音乐欣赏的桥梁和纽带,是表演者将物态化的乐谱文本通过表演实践来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中介环节。从本质上说,在这一环节中的表演者扮演着接受者、理解者、阐释者、传递者和创造者等多重角色,肩负着发现、创造、充盈、丰富音乐作品及其意蕴内涵,提升民众音乐艺术水准等多重责任,其中蕴含的许多理论命题与接受美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基于此,文章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支撑,从表演者的视角审视音乐表演艺术中“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视野融合”等理论现象,并对接受美学运用于音乐表演环节研究的历史局限展开论述,以获得对音乐表演本质规律和音乐表演者的功能作用有深化认知。
一、理论内核:接受美学的几个核心命题
“接受美学”概念首见于1967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文艺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姚斯发表的演讲——《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姚斯提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他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可见,在姚斯看来,文本不是作品,至多算作半成品,完整意义上的作品离不开读者的参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是历史性的开放系统,其价值的实现渗透着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再创造能力,因此,读者也是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部分。姚斯“借用阐释学‘视野’的概念,以‘期待视野’为中介,以‘视野融合’为途径,将文学史转化为一种阅读者的积淀,在文学与社会、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接通了文学与现实、过去与未来”{2},开拓了从受众群体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研究文学艺术的宏观视野。
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是沃尔夫冈·伊瑟尔,他也是康斯坦茨大学的教授、著名美学家。他与姚斯一样,都主张以读者为中心来阐释文学艺术。但与姚斯注重接受主体宏观广泛的考察不同,伊瑟尔更关注对接受者接受活动及其心理的深层微观探讨。他的著作《文本的召唤结构:散文文学创作中的未定性》在研究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时,认为文本本身具有召唤读者的功能,这种功能源自文本自身的“空白”必须借助读者的想象等心理活动来填充,即“作品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作品自身以外的动因,也就是读者的活动,即通常意义上的解释作品,这个重建的过程就是填补空白的过程,只有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化,才能将其转化成现实的审美价值”{3}。这就是沃尔夫冈·伊瑟尔著名的“召唤结构”理论。
通过对上列观点的分析,反观音乐表演实践,我们不难发现,音乐表演者承担着音乐接受者、理解者、阐释者、传递者和创造者等多种角色,其中蕴含的许多理论命题与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文本召唤”和“视野融合”等观点不谋而合,而将接受美学的上列观点运用与分析音乐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主体身份塑造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先入为主:音乐表演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 )是接受美学理论中最具特色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概念是德国阐释学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基于其师著名现象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前理解”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姚斯直接将伽达默尔的“期待视野”这一概念运用到文学艺术的研究中来揭示其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
“期待视野”指的是“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4}。质言之,“期待视野”就是审美主体在即将接触审美对象前依据自身审美经验对审美对象及其表现内容的心理期盼和诉求。可以说,“期待视野”广泛存在于人类一切艺术审美实践活动中,音乐表演也不例外。在音乐表演艺术中,表演者不仅要忠实于作家的创作意图,还要通过自己的表演创造来补充和丰富原作的意蕴内涵,赋予音乐作品以新的生命,实现其审美价值。音乐作品内涵的填充和丰富、价值的实现在表演环节依赖于表演者的“期待视野”,因为作家将生动的乐思以乐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后,呈现的是一系列乐音符号构成的体系,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音乐。就表演环节而言,表演者正是音乐作品的“第一读者”。正如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的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5}音乐作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其“艺术特性”的彰显离不开不同时代音乐表演者的表演诠释。
音乐表演者的“期待视野”主要表现在表演者对音乐作品文本、音响及其表现内容以及人类生命意蕴层面的期待。换句话说,表演者的期待视野有音乐作品的“形式期待”“内容期待”以及“人生期待”三种主要形态。所谓“形式期待”,指的是表演者依据自身审美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式对音乐作品文本的语言材料、结构方式、音乐音响、旋律发展手法等特征的判断和期待。如要演唱颂歌题材的作品,演唱者自然产生结构紧凑、音响高亢的心理期待;反之亦然,若要诠释低沉哀怨的作品,表演者心中自然涌现深沉浑厚的旋律基调等。“内容期待”主要指表演者对音乐音响表现对象的期待。如快速、跳跃以及低紧张度的旋律很容易使表演者联想到活泼欢快的场景;旋律音高上下来回、高低起伏的线条运动,自然让表演者将它与大海的波涛联系在一块等。“人生期待”则是表演者音乐作品高层次的情感境界、人生态度、思想倾向作出的审美心理反应和价值判断。我们熟知,音乐是人为了满足人类自身听觉感性需要而创作的精神产品,其终极的诉求在于启示人生。这不仅能在古希腊“和谐”“净化”等理论中找到支撑,也能从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教化”中探寻理论渊源。因为,音乐能够通过表现内容的某些感性特征及其动态的变化组合,来激活表演者头脑中的知识、经验、思想观念等多重心理因素,激发多重多样的联想,在表演者脑海中积极地组合、反思和概括,“人生”的抽象概念由此而生。
不难看出,在音乐表演环节,表演者的“期待视野”对于填充和丰富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超出作家的想象,赋予作品以新的色彩。当然,音乐表演者的“期待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表演者个人知识经验、文化修养、生存时空、兴趣爱好、社会阅历、价值取向等的不同而呈现出效果的差异性、形式的多样化、发展的动态化等特点。即便是同一个表演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中面对同一部作品也会产生不同的期待。因此,“期待视野”是音乐作品艺术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同时也是制约音乐表演者自身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切中本体:作品文本中的“召唤结构”
“召唤结构”(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是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吸收借鉴、综合现象学哲学家罗曼·茵伽尔登“作品存在论”与阐释学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核心概念之一。他指出:“空白,是文本中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没有写明的、召唤读者想象的未定性的意蕴空间。作品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6}这里的“空白”“不确定性”是一个多层面、开放性的“召唤结构”系统,而非独立意义的存在,它召唤读者依据自身的“期待视野”、联想加工等心理活动去填补文本的“空白”,使文本“具体化”、完整化。从而达到丰富作品内涵、实现其价值意义的根本目的。
严格意义上说,当作曲家把生动的乐思以音乐音响的结构样式记录在乐谱上的时候,“就已经抽掉了它的灵魂,所剩下的则是一个乐音符号系列”{7}。它有待表演者通过演奏或演唱将其实现为一个具体可感的音响存在。其中所说的“乐音符号系列”,也称“乐谱”“文本”等。离开了表演者的表演,它就是失去“灵魂”的躯壳,也构不成完整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可见,在接受美学看来,音乐作品文本固然也是一个充满着“开放性”的“空白”,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系统,驱使着表演者去填充、去完善,这种内在的机制正是音乐作品文本的“召唤结构”。何以至此?根源之一在于音乐材料的非语义性。所谓非语义性,指的是任何音乐作品中的声音,只作为一种艺术交流的媒介而存在,本身没有明确的含意。如面对一串串的音符,谁都无法说出它的确定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声音的非语义性而否定“指义性音调”的存在,即否定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主体音调使用的可能,如听到《国歌》的旋律立即让人联想到国人抗战救国的英雄形象,当《东方红》的音调在耳边响起,我们自然联想到“领袖”的形象。这些案例不仅说明音乐音响在某种范围内是有约定性的,还表明音乐的声音“能够最准确地体现和传递以情感为主的信息”{8}。那主要是因为音乐的声音具有表情音调和表现的功用。如我们能从歌剧《绣花女》剧终时,铜管乐队沙哑的巨大声响感受到鲁道夫对“咪咪”的真情呼唤;我们还能从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那婉转、静谧的音响中体悟到作者对自由爱情与婚姻的憧憬、向往。
导致音乐作品文本“召唤结构”的成因,还有音乐材料的非对应性。所谓非对应性,主要指音乐音响及其表现对象之间不存在某种确定的、一成不变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音乐音响可以表现对象的可能。人们也许能在音乐中听到各种自然界中的声音如鸟鸣声、雷声、风声、雨声等,但是这些声音与自然界的实际音响不能相提并论。对于自然界的声音,一经入耳就能感知其对象为何物。而这些声音在音乐中的出现,必须借助人们的联觉、联想、想象等多种心理活动才能将其与其对象对应起来。按照罗曼·茵伽尔登的说法就是文本的具体化过程,“在具体化中,读者进行着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他利用从许多可能的或可允许的要素中选择出来的要素(尽管所选择的要素从作品方面来说并不总是可能的),主动地借助于想象‘填补’了许多不定点”{9}。这一过程就是表演者的再创造,即表演者能依靠想象、联想等使得音乐音响及其表现对象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非本质。因为被表现对象与音乐音响构成联觉对应关系的感性特征是有限的,并且这有限的感性特征绝不是某一对象所独有,不能成为一个对象的唯一标识,因此,音乐作品文本开放而不确定的“召唤结构”不断激发着表演者在广泛的空间中凭借自身的审美经验去发现、去创造、去丰富、去增值原作的意义。
四、合理诠释:意义理解中的“视野融合”
“视野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有“视界融合”“视界交融”“视域融合”等多种称谓。这一概念是阐释学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基于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视界”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之一,后来成为接受美学用来解释正确理解历史对象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活动乃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不应把理解设想为某种主观性行为,理解就是使个人置于传统之内,在这传统中过去和现在不断地相互交融。”{10}这说的是“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不应该要求理解者完全放弃自己的视界去追求作品中的那个历史视界,企图用这种方式去克服两个视界之间的差距。相反,应该要求理解者拓宽自己的视界,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11}。理解音乐作品仍不例外。伽达默尔所言不仅为我们理解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具体作品的实践指向。
音乐作品必须依靠表演这一中介环节,才能使其价值最大化,才能使其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作品意义的具体实践者、主动的理解者,实质上就是作品历史视界与演唱者的现实视界融合交流的过程。所谓作品的历史视界,指的是作品的历史时代和音乐风格范畴。任何一部音乐作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催生的“时代产儿”,它总是与作曲家生活的时代背景、文艺思潮,甚至是作曲家的生活阅历、兴趣爱好、思想倾向、价值判断等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必定有其特定的音乐风格特征。这无需我们做过多的说明,反观中外音乐发展的历史,便可对其面貌了如指掌。而表演者的现实视界则是指表演者在表演历史时代的作品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时代的立场、眼光、时代精神、美学观念等去对作品进行阐释和处理。表演者的任务就在于让自己的现实视界与作品内容所包含各种历史视界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界,最终实现对作品的理解。
那么,表演者如何让自己的现实视界与作品的历史视界实现完美融合呢?在接受美学看来,对于作品历史视界的把握,首先要认真研读乐谱。“乐谱是作曲家创作意图的直接记录……许多作曲家倾向于尽可能详尽地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加以标示,因此对于作曲家写下的乐谱进行认真的研读和揣摩。”{12}其次是考察音乐作品所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因为“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与其他方面(相关文化)的对话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创作不是一种封闭的自我行为,其意义是通过作品内涵的传播和对作品的再创造而活动的。换言之,音乐创作和音乐作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具有其价值”{13},意即表演者要设身处地使自己投身于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去体验和熟悉历史时代的人文风貌和音乐风格,因为“音乐,如果割裂其历史渊源,不可避免要丧失其社会的和明确的音乐意义”{14}。而表演者自身现实视界,不仅包括表演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我意识、文化修养、人生体验等内在因素,还包括表演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美学观念、文化思潮等外在条件。毕竟,表演者也都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有自己的立场、眼光,加上所处时代的精神等都会不由自主地体现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因而音乐作品意义的阐释就有了多种可能。人们常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用意大概也在于此。
综上所言,在接受美学的视域下,音乐作品是一个多侧面、多层面、立体化的意义统一体,其价值的实现和意义的彰显在表演环节完全取决于表演者的主体建构,不论是表演者的“期待视野”、作品文本的“召唤结构”,还是意义理解的“视野融合”,都围绕着表演者的主动参与与积极创造,呈现为勾连互动的统一体。这里的主体建构,不是简单对作品进行再现,也绝不意味着表演主体随心所欲的胡编乱造,而是适度、积极的建构和诠释,因为这一过程不仅要求表演者要从乐谱中去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从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了解作品广泛的文化内涵,还要结合其自身所处时代的特征及自我个性去实现作品文本的“具体化”,去融合作品的历史视界。同时,我们也发现,接受美学由于过分强调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对作家自身心路历程缺乏必要的考察,对表演者与作家之间的交流有所忽视,这正是接受美学的一大局限。我们指出来,目的在于使音乐表演者能够更好地去创造、充盈、丰富和传达音乐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1}{5}[德]H·R 姚斯、[美]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第23页。
{2}方建中:《论姚斯的接受美学思想》,《求索》2004年第5期。
{3}林一民:《艺术品的内在魅力来自何方——谈文本的召唤结构》,《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4}朱立元:《西方现代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07 页。
{6}黄敏:《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阅读教学——从确立学生的阅读主体角度谈起》,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第46页。
{7}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8}[苏]莫·卡冈著,凌继尧、金亚娜译:《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9页。
{9}[波]罗曼·英迦登著,陈燕谷、晓未译:《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4页。
{10}[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页。
{11}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
{12}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13}[美]Randall Everett Allsup著,郭声健译:《音乐互助学习与民族行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4}中央音乐学院外国音乐参考资料编辑部:《外国音乐参考资料》(2),1981年版,第42页。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赵婧贻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