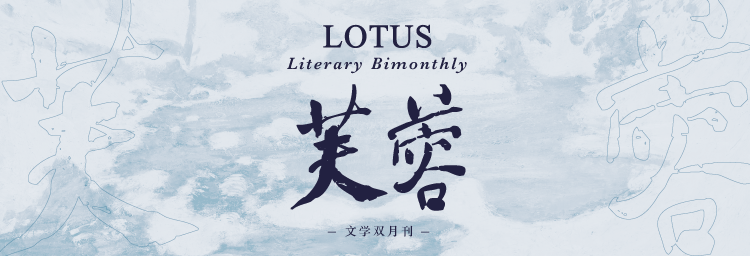

安全屋(中篇小说)
文/杨少衡
工作小组决定接触蔡国宾。我们都知道这个决定相当重大,不同寻常,蔡国宾不是谁想碰就可以碰一下的。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蔡国宾的流言不时流传,听来不免让人胸口止不住“扑通扑通”激动不已,就像在刑场观摩枪决死刑罪犯一般。在类似事项上,看客们总是不嫌热闹,当事者除外。
据我们所知,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是蔡成茂,也就是别名“阿摆”的那家伙。阿摆四十来岁,头是头脸是脸,长得人模狗样,在上涉嫌“黑恶”名单之前,曾经贵为一村之长。阿摆村长任职期间有若干政绩,不外修桥铺路建祠堂等,但是人们大多不认为是他的功劳,其中另有缘故,大有来头。阿摆作为“明星村长”曾经上过市政府表彰名录并获得本地报纸、电视报道。据说当年领荣誉奖牌时,所有受表彰者中唯他最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头发梳得整齐且穿着全套正装,而是因为他在主席台行走时身段显著,晃过来晃过去,幅度极其开阔。他是残疾者,右侧腿脚瘸得厉害。
半年多前,阿摆的老母去世,他为亡母举办了一场阵容豪华的出殡仪式,出席仪式的有死者的画像、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赠送的花圈、铜管乐队、舞蹈队、法术师、俗称“土公”的抬棺者、孝子贤孙和亲朋好友。一如本地重要人家大型送葬,区别只在于以往村人出殡抬的是棺材,而阿摆这一行只能抬一只骨灰盒。这是因为推行殡葬改革,大势所趋,村长自难例外。
那一天,正值铜管乐队齐奏哀乐、出殡仪式隆重之际,忽有巨大的鞭炮声如排子枪般轰然而起,响彻村社上空,与哀乐遥相呼应。鸣炮地点在村长家的小楼西侧,隔着一排民居。几分钟后,阿摆瘸着右腿赶到了鸣炮地点,随同他前来的竟是整个出殡队伍,包括土公、死者画像和骨灰盒。
这里有一片工地,一座即将落成的三层小楼正在浇筑水泥封顶。这一工序相当于早先乡间的新屋上梁,按当地风俗这种时候应鸣炮志喜。本地风俗同时认为出殡时响鞭炮是对死者大不敬,会严重伤害亡灵及其在世家人。
三层新建小楼户主叫陶山水,三十出头,有一张长方脸。
阿摆指着陶山水大骂:“挑日挑时!狗东西!”
陶山水也骂:“阿摆欺人太甚!”
村子里几乎人人都管村长叫阿摆,没有人尊称其大名蔡成茂。但是陶山水属于例外,他不行。他当众这么一吆喝,阿摆整个儿顿时给点着了。
他大喝:“给我吹!”
铜管乐队呜里哇啦卖力吹奏,哀乐对着新楼铺天盖地而来。这在本地风俗里当然不是吉兆。陶山水怒目圆睁,暴跳如雷,顺手抄起身边一把铁锹。有个老头突然从小楼里跑出来,手举一支扁担朝阿摆挥去,啪嗒一下,却不是阿摆挨打,竟是陶山水胳膊挨了扁担一击,手中铁锹“咣当”落地。
老者是陶山水的父亲陶宗。
陶宗把扁担扔在地上,对阿摆拱手赔笑:“村长,别跟后生计较。”
阿摆指了指满地鞭炮屑追问:“这是什么意思?”
陶宗表示绝非故意,他们不知道村长家今天上午出殡,意外冲撞了。
“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你们不知道。”
陶宗咬定不是故意。既然冲撞了,愿意赔礼道歉。
“就一句话?”
陶宗回过身,朝儿子陶山水的小腿用力踢一脚,喝一声:“跪下。”
陶山水在父亲逼迫下,不得不跪在地上,对着出殡行列中的死者画像和骨灰盒连磕三个响头,每一个都在地上敲出结实的“嗵嗵”声响,额头上顿时一片血迹。然后他一抹伤口的血,当众放声大哭,捶胸顿足。
这是哭丧吗?当然不是。
阿摆一甩手转过身,带着送葬队伍离开。所谓死者为大,此刻只能先料理丧事。哀乐渐行渐远,留下遍地阴森森的白纸花在轻风中飘飞,陪伴着尚未完全落成的小楼。
几天后,这段出殡逸事被好事者传到互联网上,有声有色有图有真相,当时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毕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且丧事比较晦气,粉丝和追捧者要稀缺一点。不久后曾有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下来了解过此事,估计是接到上级部门的函询件,需要了解反馈。此后风平浪静,没有更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事件发生,直到工作小组突然到来。这个小组像是很低调,实际不得了,其工作是办案,兵强马壮,人员来自不同方面,出自各强力部门,办的不是普通民间纠纷事项,居然是“黑恶”案。这种案子的厉害在于不仅收拾前台涉黑涉恶人物,还重在挖掘隐身其后的保护伞。一个村长算个啥?芝麻绿豆而已,后边的大瓜才更为重要。于是大家都知道,这回是来真的了。
据说办案组向知情者了解案情时,还有人表示:“阿摆真是不能叫的。”
那意思是,出殡当日陶山水当众叫了一声“阿摆”,那是火上浇油。为什么村长大人的绰号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可以叫,陶山水却不行?因为阿摆蔡成茂的右腿原本好好的,是后来给人弄瘸的。弄瘸它的人是谁?就是陶山水的哥哥陶山林。
这牵涉到一起旧日恩怨。
几年前村民委员会换届,陶山林早早从市区回村,报名参选村长。此前陶山林离村多年,在市区办加工厂,其企业落脚于工业开发区,生产低密度纤维板,同时染指家具行业,生意不错,赚钱不少。陶老板回乡参选村长,阿摆是他的对手。当时阿摆的右腿尚完好,却属籍籍无名,没啥名堂,充其量只当过村治安主任,与陶老板不可同日而语。不料到头来竟是阿摆当了村长,陶山林则因企业偷税漏税被查,被迫退出。随后不久,有一个晚间,阿摆骑摩托车从镇上回村,半道上被人拦截袭击,脑袋给套进一条麻袋,人给拖到路旁小树林,在那里吃了一顿棍棒,打个昏迷不醒。清晨时他被发现浑身血淋淋的,让人用急救车送到市医院,在那里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从此他便成了残疾,再也无法正常走路,因为袭击者打断了他的右腿骨,还挑了他的右脚筋。
这个案子涉及刑事犯罪,由警察办理。警察不含糊,仅十来天就锁定嫌犯,终在工业开发区陶山林的厂子将陶老板抓获。
原来这是一起买凶伤人案,陶山林是该案主谋,出资方。“乙方”则是一流窜作案人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双方通过某中间人达成口头协议及款项交接。据说那个“乙方”藏得很深,专干黑活、脏活,专业范围集中于人的五官和四肢,也就是根据客户需要伤害仇家身体,唯人命不做,因为有偿命风险。陶山林花了一笔大钱买阿摆一条腿,指定为右腿,不需要如宰猪般卸下该腿扛交客户验证,保证弄残,有目共睹即可。为什么只要右腿?因为队列口令从来都是“向右看齐”,右比左显眼。为什么只要腿而不要手?那得怪阿摆自己。阿摆大名蔡成茂,却从小被叫作“阿摆”,据说因为幼时学走路比别人家的小孩慢,走起来总是摇摇晃晃重心不稳,被亲友和邻居戏称之,居然就叫成了别名。本地话里“摆”亦有“瘸腿走路”之意,所以在陶山林看来,让阿摆真的“摆”即使不算替天行道,至少也属帮助他实至名归。陶山林没想到如今警察那般厉害,除了破案功夫不凡,技术手段也极其了得,特别是监控天眼,比孙悟空火眼金睛厉害百倍。阿摆还在医院里“哎呀哎呀”叫唤不止,陶山林自己就被警察铐进了看守所。起初陶山林拒不承认买凶,却不料警察已经将“乙方”和中间人一并抓捕到案,天网恢恢,无可逃避。陶山林只得承认因故与阿摆积怨,报复伤人,案子告破。
他被判了十年,吃牢饭去了,不久其加工厂亦破产倒闭。陶山林的弟弟陶山水原在大哥厂里帮忙,当小老板,买凶案没有牵扯到他,工厂倒闭后他一直在外边游荡,偶尔回村露个面。陶家新楼早在其大哥出事前就埋好地基,因事发停建数年,而后再建,封顶时大放鞭炮,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哀乐和纸花,也属事出有因。阿摆葬母,不能说全世界都知道,芝麻绿豆大的村子里应当人人皆晓,参考两家人之旧怨,陶山水借机大放鞭炮幸灾乐祸的可能性确实不能完全排除,尽管他父亲陶宗坚称不是。当时陶山水给蔡母遗像下跪,表面上是其父陶宗所逼,并非村长阿摆强迫,归根结底还是阿摆以势压人。陶宗怕儿子硬刚吃亏,大的还关在牢里,不想让小的再惹麻烦。
一个大如芝麻绿豆的残疾村长,凭什么如此强势?原因是其背后有人。办案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阿摆“请”进办案地点,查问他几个问题,他或者避而不谈,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最后都归结到一句话:“你们去问他。”
“都是听他的?”
“你们去问。”
“他”是谁?就是蔡国宾。
蔡国宾是本村老村长,执掌本村大权累计近三十年,现已七十大几,奔八十去了。蔡国宾是阿摆的堂叔,当年蔡国宾因年纪大了,身体欠佳,开个会都有困难,不再适合当村长,上级有意找人接班,蔡力推阿摆,还帮助阿摆力克陶山林。阿摆上任后,大事小事都找堂叔拿主意,言听计从,一村大政没有旁落,依然掌握在蔡国宾手中。阿摆被陶山林买凶伤成残疾,伤愈后继续当村长,一瘸一拐地处理村务。由于伤残怨恨,阿摆对陶氏家人及其亲友从来没有好脸色,逮着机会便情不自禁在明里暗里加以收拾,双方矛盾日深,难以化解。几年间关于阿摆村长挟嫌报复仗势欺人的举报屡屡出现,曾有上级领导批示查问,有关部门屡次派员到村了解情况,最终都不了了之,阿摆始终摆来摆去于村部小楼,稳坐钓鱼台,直到打击黑恶办案工作小组悄然抵达。
如果阿摆在村中的种种行为涉嫌黑恶,那谁是他的保护伞?无疑就是阿摆直截了当提到的“他”,蔡国宾。表面上看,把一个卸任多年的前任村长,七八十岁病恹恹的高龄老头摆到现任村长及村中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高度,似乎有点高看了,“德不配位”,勉为其难。但是只要稍微再做一点了解,那就心中了然了。
工作小组组长叫吴霖,他亲自上门,带人到蔡国宾家了解情况。蔡家有一座四层楼房,位于俗称的“村部”近侧,周边民居多为小洋楼,高的五层,矮的三层,蔡家居中。该村位于城乡接合部,山清水秀条件好,是个富村,楼房鳞次栉比,装修比较亮眼。蔡国宾夫妇与儿子一家在小楼里共同生活,二老住顶层,三层是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女的卧室,二层是孩子们的书房和活动室,客厅、饭厅和厨房安排在最下层。
吴霖组长不卑不亢,管主人叫“蔡国宾同志”,声称上门与老村长“聊一聊”,核实一些情况。蔡国宾请对方不必客气,管他叫“老头子”就可以了。他早就什么都不是,就是个乡下病老头。
老头子很放松,胸有成竹。他知道阿摆已经给叫进去了,知道吴霖他们是怎么回事,却没有丝毫胆怯。他拿“乡下病老头”自贬也属话中有话,似暗指被视同“黑恶保护伞”太高看了。在本村,确实人们都管他叫“老头子”“老家伙”,没人称他“蔡国宾同志”。乡里乡亲,叫“老头子”透着亲近,好比管“蔡成茂同志”叫“阿摆”。老头子亲切会见吴组长一行的地点是在自家客厅,这里有一圈红木太师椅,老头子坐在主位请客人喝茶,他自己光着两脚,于会见贵客期间抓紧泡脚,公务保健两不误。
他向客人告罪,称自己患痛风多年,严重时路都走不动。前几年又查出糖尿病且有并发症糖尿病足。这种并发症很厉害,后期病情会恶化,从脚趾头一点一点往上溃烂,医生只能把病腿一段一段锯下来。为了控制病情防止恶化,儿子为他找了名医会诊,其中有个老中医建议他泡脚,泡脚水用几味中药熬制。他试了试,似乎有用,因此每日定时泡脚,每次都泡半小时以上。病老头了,没办法,很抱歉。
吴组长说:“泡吧,没关系。”
老头子指着泡脚盆介绍:“这也是儿子专门给买的。”
那个泡脚盆并非高大上,很普通,就是一个塑料盆加几个按键,接通电源后可加温,可扰动水流做足底按摩并发出“噗噗”声响,从低到高有几个不同挡位。老头子称平时泡脚多在顶层自己的卧室里,省得跑上跑下,毕竟腿脚不好。今天贵客上门,恰好也到了泡脚时间,只好边“噗噗”边谈。儿子对他泡脚很上心,经常亲自给他按摩脚背,检查伤口,泡好后帮他擦脚,还会陪他到外边走一走,说是让脚部“活血”,他们会一直走到镇上,在那里的小吃馆吃一碗咸菜大肠头,老家伙好这一口。这座楼盖早了,当时考虑不周,没装电梯。没料到腿脚活动不便的一天转眼就到。儿子说了,等空下来,他会请人来家里看看,加装个私家电梯。儿子真的很孝顺。
老头子接连提及儿子,吴组长只是听,不表态,未加置评。
双方交谈时,泡脚盆里水声“噗噗”不绝,伴奏很卖力。
吴组长向老头子提了个问题:“村里这些年大的收入和开支情况都了解吧?”
老头子称他并不了解。阿摆有时会来谈些情况,但是他没有兴趣听。不当村长不操那个心,现在他只操心自己泡脚。
“听说过伟达工程集团吧?”
老头子摇头,他不记得这家企业。
“他们老板林金同好像给了一笔钱。”吴组长提示。
老头子笑笑:“他要是给我送一只洗脚盆,我会记住的。”
当天的交谈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个结果在吴霖预料之中。与老头子初步接触,属于“火力侦察”,很有必要,却不能抱太大希望。此刻办案的着力点还在于阿摆,突破口只可能在阿摆那里。
阿摆的素质与其堂叔不在一个档次,无法同日而语。事实上现任村长除了很会记仇、报复心强 ,以及在主席台上行走大幅度摆动令人印象深刻外,确实资质平平。他在任上修桥铺路,村政建设亮眼,被表彰为明星村长,实际尽是堂叔替他操办,从资金到运行,他充其量算个跑腿的。因此时候一到,突破他难度不大。面对经验丰富、志在必得的办案人员,“你们去问他”能抵挡几个时辰?没过多久他的心理防线便被攻破,一点一点开始交代问题。他承认得知自己被工作小组盯住后,心里很紧张,曾求救于堂叔。老头子让他不要怕,“你们去问他”也是老头子教他说的。老头子自认为工作小组轻易不敢动他,阿摆尽管把事情往他身上推,有助于自己脱身,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关于伟达工程集团那笔钱,阿摆提供了一个细节:带该公司老板林金同去见蔡国宾的就是他本人。是一个晚间,林送给老头子一个手提箱,说是一点小意思。老头子没有推辞。走的时候该箱子就留在蔡家。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办案人员追问。
阿摆不清楚,感觉手提箱似乎很沉。
“是钱吗?”
“不知道。没打开。”
不需要他说,里边确实是钱。工作小组已经通过特殊途径查到可靠情况,当时伟达工程集团参加市区内河清理工程某标段招标,林金同分别从几家银行取款,共取出一百万现金,塞满一个手提箱。该手提箱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老头子蔡国宾不记得了,因为手提箱里装的不是洗脚盆。
老头子明摆着是在对抗调查。任何黑恶势力活动的背后,都有经济利益在充当推手。办案组在吴组长的率领下,不动声色地顺藤摸瓜,掌握了更多确凿证据,已经具备把老头子从他那座小楼里“请”出来深入调查的条件。吴组长却还在反复掂量。
“那个泡脚盆怎么办?难道一起请来?”吴组长问。
办案人员认为无妨。老头子可能确有糖尿病足,但是泡脚见客更像是即席表演。据了解,工作小组到来之前,老头子还经常独自在村里四处跑,动作麻利,健步如飞,作为前任村长,其行走状态比现任村长阿摆还强过十倍。
吴组长说:“必须请示一下。”
事关重大,请示是必需的。两天后相关决定下达,工作小组立刻行动,直扑小楼。
他们扑了个空。小楼里只有蔡国宾的妻子在家,她说:“老头子出去了。”
一个小时前,蔡国宾突然离家,骑一辆电动车走人。走之前交代说,他出去办点事,让老太婆不要做他的饭。至于去哪里,要多少时间,都未提及。
蔡国宾就此人间蒸发,居然玩起了失踪。
事后分析,可能是请示环节出了纰漏。由于情况比较特殊,对蔡国宾的组织措施要由比较高的层级来做决定。吴霖的请示会一级一级往上传递,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了一重消息走漏的风险。
蔡国宾充其量也就一前任村长,哪怕比芝麻绿豆大一点,给阿摆当保护伞还有些勉强,何须这般兴师动众?原来这个七老八十之辈之不寻常不在其糖尿病足,却在其儿子。老头子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前妻病亡,娶了后妻,两个妻子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兄弟俩同父异母,相差十几岁。眼下与老头子一起住在村里的是他的后妻及小儿子,该子叫蔡仁业,时为附近乡镇一所初中学校的副校长,儿媳也是该校教员。小儿子无足轻重,老头的大儿子却分量充足,村里修桥铺路建设明星乡村,其实都跟其大儿子有关。老头子与吴霖组长泡脚相会时,曾屡屡提到其子,包括提到其子帮他泡脚擦脚还陪他“活血”,很“有孝”。此时他所说的“儿子”其实特指大儿子,且有所暗示。而吴装作没听见,不加置评,回避那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有所顾忌。
蔡国宾的大儿子叫蔡仁功,时为本市常务副市长。
这把保护伞足够大。
(节选自2023年第4期《芙蓉》中篇小说《安全屋》)

杨少衡,男,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新世界》《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风口浪尖》《铿然有声》《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等,长篇纪实文学《天河之旗》,长篇儿童文学《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你没事吧》等。
来源:《芙蓉》
作者:杨少衡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