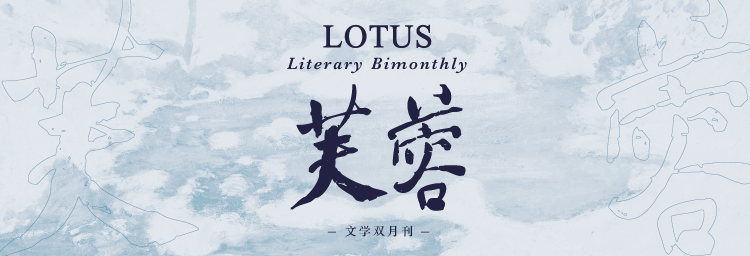

绿色皮卡(短篇小说)
文/阿连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麻七与呼四宝在路上遇到了平平。
起先是他们准备去白云鄂博,呼四宝回家,他家住在白云鄂博。白云鄂博是一个草原小城,以矿产出名。呼四宝原来就是铁矿的一个工人。可麻七却并不是因为矿产而记住了它,而是它的名字——白云。多么白!多么云!单这两个字就可以让麻七飞起来,飞起来,不断飞起来。
麻七是要去白云住店。
麻七住在什玛阿姨家,虽然父母去世好几年,但麻七每年依然会回查干朝鲁。只有回到查干朝鲁,她才会睡得更踏实,仿佛一整年的睡眠,都要在这几天补起。回到村里后,麻七住到什玛阿姨家,什玛阿姨是看着麻七长大的,有着母亲一样的意义。
呼四宝开着他的绿色皮卡经过哈达图。麻七站在什玛阿姨家的阳台上,望着无边无际的原野,东一块西一块的庄稼,并没有让原野显得割裂,反而使它看起来更为疏阔且充满生机。风一阵一阵拂过,麦浪翻滚,菜籽花漾出黄色的光泽。麻七看着呼四宝开着那辆绿色的皮卡,从天边的原野驶来,穿过麦浪,穿过油菜花田,车过处,仿佛前后有千万只金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又经过一片葵花田,车在大路与葵花高大的秆子间,小小的像一只甲壳虫,随着路面的高低不平,颠簸起伏。看着整个原野都在荡漾,麻七的心也跟着荡漾。呼四宝一脚油门把车径直开到什玛阿姨家的院子,嘴里叼着一支油菜花,吊儿郎当地走出卡车时,麻七就想着要跟着他去白云了。
所以,麻七和什玛阿姨说:“我好久没洗澡了,我想去白云洗个澡。”什玛阿姨说白云哪里能洗澡,麻七说酒店。什玛阿姨说:“你说,人家呼四宝是个男的,你跟上像个甚?”麻七笑:“哎呀,姨,你快不要乱操心了,呼四宝是我同学,你也认识。再说,我多大岁数了!”
什玛阿姨白了她一眼,不再说话,只是叮嘱麻七多穿件衣服,草地夜里冷了。
其实洗澡不重要,住店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麻七现在就想坐在呼四宝的皮卡车上,穿过原野,穿过麦田,穿过油菜花,穿过风。这已经足够安抚麻七荡漾的心,何况,麻七去的目的地是白云,这白!这云!
当呼四宝和麻七把漫天的彩霞丢在身后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平平。平平身边跟着一个胖乎乎笑嘻嘻的年轻人,黝黑的脸,在晚霞里泛着阳光的色彩。他们正指着路边的葵花田与远处的牛群,说着什么。原野阔达,这两人站在路上,有着说不出的微小与硕大,仿佛他们不存在,也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
麻七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呼四宝就一脚刹车,将车停下,并探出头:“老平,你这是去哪里个来来?”其实麻七并没有认出他是平平,呼四宝这样一说,麻七就猜着了八九分。平平这几年一直住在包头,据说在包头买了房。麻七也探出头:“平平哥,你好。”平平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立马就和呼四宝打招呼:“哎呀,四宝叔,咋就能碰上个你了?”然后迅速瞟了麻七一眼:“哎呀,是嫂子哇,回白云呀?”平平已经看到麻七,打断小伙子:“贺子,你快不要瞎嚼,这是咱们村的麻七,麻女,你甚会儿回来的?”
麻七和呼四宝都下了车。黄昏时分,风就小了很多,天空渐渐低了下来,回头的刹那,仿佛晚霞就是草地上长出来的。
贺子羞赧地笑笑:“哎呀,我不知道嘛,你就是麻女姑?就知道你在外头上班了,认不出来。”
呼四宝插话:“你连你姑姑都不认识,你还当甚的支书了。快快,回家哄娃娃个哇!”
“叔,你看你说得甚了,我姑姑人家是大城市上班的,我小时候,人家就上大学了,我能认得?”贺子说罢,转向平平和麻七,“对不起,姑,看我,眼笨的!”
麻七还是不解,看向平平,平平说:“贺子是贺大夫的儿子,那会儿小的一点点,你认不得。”
麻七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哎呀,你咋长这么大了,怪不得不认得。”
贺子嘻嘻笑:“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哇!我儿子也已经七岁了。”
呼四宝插不上话,在那儿着急,一把拉过平平:“平平,你这是在哪来吗?多时不见了,你咋还变白了呢?”
平平笑:“白甚了,回来种地,晒得黑洞洞的。你和麻女是咋认识的了吗?”
呼四宝说:“老同学哇,初中同学。”
平平哈哈大笑:“你也只念了个初中,还没毕业,还同学了!”
贺子看看他们:“我看你们有说不完的话,四宝叔也好久不见了,上次去库列点力素办事,还全凭了四宝叔。今儿又见到麻女姑,更是难得。走哇,一起吃个饭吧,吃饭时咱兄弟姐妹好好聊一聊。我请你们。”
呼四宝立马附和:“行了嘛,还没喝酒来了,咋就乱了辈分,我是你叔,她是你姑!”
贺子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麻七疑惑:“呼四宝,你不是回白云吗?”
呼四宝一边让平平和贺子上车,一边走上驾驶座:“回呀哇,回也得先喝酒了哇,见酒不喝有罪了,可是不敢。”
这逻辑让麻七觉得好笑,但也上了车,坐上了副驾驶。
天色已晚,晚霞也已经全部熄灭,天边陆续出现星星,天垂得更低,伸手能摘到星星的近。
平平和贺子也说:“是了哇,咋见也是先吃饭喝酒了哇!”
他们的意见出奇一致。麻七心里想着喝了酒怎么开车,要说出口,但看看外面深蓝色的夜空与广阔无垠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原野,也就作罢。
毕竟这是大草原,草原有草原的特点。
贺子指挥着:“叔,你就顺着去白云的路走,快到库列点力素的时候,路边有一家饭馆,他们家炖的肉挺好,就在那儿吃哇。”
原野上,天高地阔,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呼四宝车稳稳地开着,表情如黄昏一样宁静。夜风很轻,逆着车行的方向,徐徐向后,麻七把手伸出去说:“哎呀,我能握住风了!”
呼四宝瞟了麻七一眼,有些不屑:“能不能不大惊小怪,谁家的风能逮住?把你给日能的!”
麻七继续伸出手,一握一放:“能了,你看手里头满满的,都是。”
呼四宝眼睛看着前方:“唉,你们这些读书人,都读傻了!”然后回答贺子:“知道了,我也吃过几回,那个饭馆叫‘羊换饭店’。”
平平说:“是了,羊换是我们村死了的六四的外甥女婿。”
麻七记得平平家和六四家,很多年前,好像因为几亩地,弄得仇人一般。就回头看他并脱口而出:“哎呀,六四不是你家的仇人吗?”
平平看了麻七一眼:“你看,你这个娃娃,六四也死了好多年了,他儿子也不在村里了,我和他计较甚了。再说,那几年人们种地了,地金贵得不行,你看看现在……”他指了指窗外,“这么多地,唉,人们也是瞎争了,现在你给他地,他瞭也不瞭一眼。”然后又长长叹了口气。
外面其实已经很暗了,虽然有星星,却也只能看到黑魆魆的原野。
呼四宝看了麻七一眼,笑了:“现在已经到了点素的地界。点素是牧区,没地可种,都是草坡。”
麻七这才想起,从查干朝鲁东边的哈达图出去,就成了牧区,牧区是不允许种地的。
远远地就看到,路的左边有一排房子,亮着一片灯光。走近就看到院子里横七竖八停着一些车,大车居多。呼四宝又一脚油门加了速,车就箭一样地射到了院子里,正好落在了两辆大车之间,不偏不倚。麻七从车里下来,不由得赞叹:“你牛了呀,呼四宝,这么完美!”呼四宝把车钥匙套在手指上,不停地绕着圈,并不说话,只轻轻一笑,然后走向其中一间房子。平平也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四宝是汽车兵,那会儿部队比武,人家常是第一。”
房子里,已经坐了两桌客人,一桌是两个人,安静地吃着一盆烩菜,盆边摆着一盘馒头。另一桌上有四五个人,桌上放着一大盆肉,还有几盘炒菜,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
店主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个子矮小,一脸笑容,早就迎了出来:“哎呀,贺子哇,好长时间不见了,咋了,当了支书就忙得不行啦?”又看到了呼四宝:“四宝,你放着支书不当,在哪里发财了?”
呼四宝拍着贺子的肩膀:“唉,快不要说了,我那个破工作,绑住得我甚也做不成!再说,人家贺子有才,我不行,当不了,我这,东跑西颠的,也做不了那种营生。”
店主一边把这行人让回到里间的一个餐桌旁,一边说:“你们都是能人。贺子,你看,吃点甚?”
贺子头也没抬:“姑,你坐里面。吃甚?你说吃甚,把你那最好的肉,给炖上,最好的酒,给拿出来。”
麻七说要去卫生间,呼四宝带她出来,指给他方向:“老七,你敢了不,要不要我等你?”麻七说:“快不用,我又不是外地人,好歹我还是这里长大的。”呼四宝也没多坚持,就回了屋。
麻七从厕所里出来,看着黝蓝的天空,走向路边,朝前后左右张望了好久。已经不太能看得清具体的物事,只感觉这家路边的酒店是凭空出现的,偌大的原野里,就只这么几间低矮的房子,虚无,荒凉,又因为灯光的温热,而真实。
麻七靠在皮卡车的车帮上,看着天空的星星与茫茫的原野,偶尔有车从路上经过,仿佛那车灯光,是虚幻与真实的连接点。除此之外,一切荒诞又神秘。
麻七觉得这次选择和呼四宝去白云,真是个好的决定,要不,怎么能看到如此神奇的景色呢?
呼四宝出来喊:“老七,掉厕所里啦?”
这喊声,把麻七拉回现实,她一边赶紧往回走,一边仿佛恍然大悟,兴奋地大喊:“哎呀,来了,来了。你这里,这整个一龙门客栈嘛!”
进门的时候,店主说:“有好多外地人,过路吃饭,都说,我们这像龙门客栈。我说,我这就是龙门客栈,你们都是过路神仙与各路武林高手。”
酒店里的人,都哈哈大笑。
桌子上已经放了两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盘凉拌沙葱。酒也摆上了桌子,是白酒,商标上贴着“河套王”。贺子一边打开瓶盖,一边吩咐拿上四个杯子来。麻七连忙说:“不要,拿上三个,我不喝。”平平说:“麻女,喝点,喝点,这可不像咱查干朝鲁的闺女,可不能给咱内蒙人丢脸。”贺子也说:“姑,你也要喝点了,这是我请了,你得给我脸了哇!”呼四宝也抬:“快喝哇,老同学,见酒不喝有罪了。再喝也喝不了五十年了,好好喝哇。”
麻七想起上海自己家对面的酒吧,大大的广告牌上有几个字:如果不喝酒,你来这世上干什么!也就不再推辞,况且是这么美丽神奇深邃的夜晚!
当炖肉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喝了一杯,又添上了第二杯。
贺子的话就多了起来:“四宝叔,前年,全凭你跟你弟兄们那几票,要不,我也当不了这个支书。”呼四宝一喝一大口:“快快快,不要这样说,还是你本人有本事嘛。”平平也端着酒杯喝下一大口:“是了,贺子,这是人家四宝不当支书,四宝要当,你就当不上。要说人家四宝的家庭了,还是人四宝的个人能力了,他实在是有那个工作了,不能当。你说是了不,四宝?”呼四宝又喝了一大口:“你要这样说,也是了。不过,我也是不爱当这些东西,有甚用了,一天到晚都是事,麻烦得不行,对的时间,我还想喝酒了。”
贺子说:“是了,四宝叔,过年,给你送只羊。”平平说:“这才是懂事的娃娃了,你老子没白亲你,有出息了。”
贺子把酒端到平平跟前:“叔,咋也得谢谢你了哇,你这两年,不在包头开饭店,回来种地,可是给我帮了天大的忙。你看,你种的那油葵,多好,你收成好,我也有面子。这新农村建设,还得靠你们了。”
呼四宝接过口:“那就把羊送给平平哇,我不要,你给我多拿几瓶酒,就行了。”
贺子连忙说:“来吧,我敬你们,我把杯里的酒都干了。”说着,一口就把大半杯酒喝下肚,然后坐下来,割着盆里的手抓肉。
麻七也端起酒杯:“哎呀,贺子这确实出息了,这人情世故,好娃娃。“
贺子一边吃肉,嘴角已经油腻腻了:“是了,姑,人家都夸我好了。”一边就羞赧地一笑,憨厚又狡猾的样子。
这时候,外面传来喧闹声,平平要出去看怎么回事,店主进来说:“没事,一个人喝多了,出去朝着大路尿,差点被过来的车碰了,怕了一跳,酒醒了一半。”一边说,一边自己就嘻嘻笑起来。
呼四宝也笑:“傻了吧,看不要了他的蛋?”店主把另一瓶酒放下:“要了蛋,不算甚哇,要个命,都有可能了。”
平平说:“哎,你可不说了,前年,还是大前年来,一个喝了酒的人,就是出门尿尿,结果跌倒在路边壕里头,冻死了。”
麻七说:“吃饭少了个人,他们不知道吗?”
平平自己喝了一口酒:“当时不知道,屋里的人都喝得醉麻糊涂,谁也顾不上谁,第二天,才知道出事了。”
呼四宝笑:“哎呀,也好了哇,喝酒喝死,也是幸福了。”
麻七看向呼四宝,呼四宝说:“看甚了,喝酒喝死挺好的,跟你说,你也不懂。”
贺子说:“叔,甚生生死死,咱不说这,给你们说说,我那年。”
“那年,我还没结婚,我妈给了我八百块钱,我把钱装兜里,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他又给其他人添满酒,一一敬过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我坐了车去了包头,哎呀,八百块钱了嘛,真是一笔巨款。我买了一身西装,订了高级酒店。然后联系我的女朋友。”贺子喝了一大口酒,红得有点泛紫的脸上,露出的是得意到有些天真的笑容。
麻七的好奇就上来:“啊,贺子,你女朋友来吗?是你后来的老婆吗?”
贺子嘴里吃着肉,声音就有些含混:“不是我老婆。姑,我老婆是后来介绍的。”
平平和呼四宝也盯着贺子。
贺子笑:“人家不来,说是,把剩下的钱给她,她就来。”
他看着大家都看他,语速就慢下来:“喝酒了哇,叔,喝,喝。”自己就把杯里的酒干了。
平平笑:“看你这个娃娃哇,赶紧说你的故事哇。”
贺子说:“我没给她钱。”
麻七说:“为什么呀?”
贺子说:“我又不傻,我知道她不可能和我结婚,给了她咋呀。不过,当时有些不开心,但第二天,我就又开心了,因为我身上还有四百多块钱。一想起,我还有四百多块钱,就觉得,哎呀,幸好,没给她,要不,我就没钱了。你们可是不知道,身上装了那么多钱,有多快乐。”
接着贺子又说:“我接着又去大饭店吃了一顿,喝了最好的酒。那感觉,真是美极了,像是在天堂上活着。后来,回来,我妈打了我一顿,她一边打,我一边笑,我觉得有钱的感觉,真是打三顿都值得。”
他说完,低头又喝了一大口,大家也低头喝了一大口,接着就蹦出了一阵哈哈哈的笑声。
笑完,大家又一起干了酒,都觉得贺子的快乐,大家都曾经经历过一样,幸福的笑意,弥散在酒桌上。
麻七说:“你的快乐,好简单啊,好快乐啊。”
贺子说:“那你要咋,快乐就是快乐,难道你还要给它添油加醋?”然后对着大家呵呵笑,“现在想想,我都能笑出声来。”
麻七的脸越喝越白,但酒劲儿明显上来了说:“我也给你们说说,我的开心事。大前年,我离婚了,哎呀,可是把我开心得,也是出去旅行了好久,花了不少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自由的女人。”
酒桌子上突然静下来。不知道谁的手机振动的声音,显得格外让人惊心动魄,但谁也不去管。
是贺子的手机,好久,贺子才看了眼手机,没有接,直接摁掉。他打破了在麻七看来的莫名的沉默:“姑,你现在单身?”
仿佛是警报被解除了,麻七哈哈笑:“是呀,单身啊。”
平平说:“你这个娃娃,你看你做甚营生了,婚,还能随便离了?离了,娃娃咋弄?”
麻七说:“娃娃跟他爸呀!”
“唉,跟了爸,没妈,跟了妈,没爸,好好的家,就毁了。”
麻七不解:“咋就没了爸妈呢?爸爸妈妈都活得了呀,他没有失去爸爸妈妈呀!”
平平说:“那能一样了?怪不得每年回来都是你一个人。哎,你说,你这个娃娃,唉!”
平平的叹气,让麻七觉得是自己破坏了刚才欢乐的气氛,有些自责,就自己倒满一杯酒:“各位兄弟,不好意思啊,是我破坏了气氛,我自罚一杯。”就仰头干了下去。
贺子也陪着喝了:“没事,姑,平平叔,是担心你了嘛,没事,离婚,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刚才就是我媳妇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接,不就是个媳妇嘛,不就是个婚姻嘛!”
平平也喝了,说:“你媳妇电话,你要接了嘛,家庭的事,可不要瞎弄。不过,一个人一个生活,没办法。”
贺子说:“知道知道,你看,我不也是安慰麻姑了嘛。”
呼四宝开口了:“你快不用安慰你姑了,你姑不需要你安慰。我看,你姑是没男人,又不是没钱。”
麻七啐了呼四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呼四宝笑,平平笑,贺子也笑。
喝得东倒西歪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多了。呼四宝摇晃着,说要先去送平平和贺子,然后带麻七返回白云。酒店老板死活不放心,说幸好有两间空房,可以让他们住一晚,明天再说。平平和贺子显然喝多了,已经抢先进入一个房间,等麻七和呼四宝去看的时候,都倒在炕上,打起了呼噜。
店主有些不好意思:“四宝,你看,就剩这一个房间了,也还没怎么收拾干净。不过,我专门把这个里外间留给你俩,毕竟你俩一男一女,但也只能这样简单凑合下了。”
呼四宝摇晃着说:“不怕,我们是老同学,睡一起也行。”
麻七问店主:“要不我和你老婆凑合一晚吧?”
店主说:“不好意思,我和另一个男的住。我老婆在村里照应孩子们了,我自己在酒店。”
呼四宝拉了一把麻七:“你快不要矫情了,你住里间,把门插住,我住外间,行了吧?”
看着摇摇晃晃的呼四宝,麻七也只好进了屋子。店主拿来一暖壶水,两个杯子,就走了。
麻七给呼四宝倒了一杯水,叮嘱呼四宝自己喝:“四宝,要不,你睡里间,我睡外间。”
呼四宝坐在凳子上,喝了一口水:“不能哇,你睡里面,我睡外面,你个女人家。”
麻七说:“没事,我想看窗外的星星,里间没有窗户。”
呼四宝有些失落:“你不想看我,你说让我去查干朝鲁接你,我以为你想看我了。”
麻七心里一惊,有被识破的羞耻:“没有,我就是想去白云洗个澡。”然后她赶紧走向里屋,“你喝多了,赶紧睡吧,我也睡呀!”
呼四宝站起来,拦在里间门口,眼睛就看向了麻七的脸:“我早知道你离婚了。”
麻七退后,靠在炕边:“那又怎样?”
呼四宝说:“不咋样,但你不说实话,你就是想见我,并不是要去洗澡,我知道。”
麻七低头不说话,大概酒有后劲儿,她觉得自己晕晕乎乎,脸发烫起来。
呼四宝撵过来:“你看,你看,微信还在了,你说的‘想坐在你车上看白云,看清风,看辽阔的草原’。”呼四宝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把微信内容念出来。他嘴里的酒气,呼到了麻七脸上,使麻七有着不容抗拒的神迷。
麻七依然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是呀,我、我、我就是、就是、就是想看这些了嘛,而你正好会开车了,所以,所以……”
“所以个蛋,会开车的同学多了,和你关系好的也不少,你咋不叫他们?”然后手摸向麻七的头发。
麻七晃着头,躲了一下:“四宝,不要。”
呼四宝不由分说,将麻七的头搂过自己的胸前:“你还记不记得我退伍那年,我托人给你捎过好多次话,结果没有找到你。你好像是消失了,到处没你的消息!”
麻七不再抗拒,把头靠在呼四宝胸前,不说话。
呼四宝说:“我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是捎话,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我又去了大同上班,就完全没有你的消息了。”
麻七终于伸出双臂,抱住了呼四宝的后背:“谢谢你,我当时上大学,我父母不在村里。”
呼四宝抱起麻七,想抱往炕上,但酒劲儿使他胳膊没了力气,麻七就溜到了地上。麻七亲了亲呼四宝的面颊:“你看你,我自己上。”
呼四宝有点尴尬,笑了笑:“老了,不能和以前比了,以前即使喝了多少酒,也影响不了开车。那年我进京,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潇洒威风。”说着脱掉鞋,上炕。
麻七已经解开外衣的扣子,听到这句话,突然停了下来,就那么停着,一动不动。
呼四宝凑近她,看着麻七的眼睛:“怎么了,不好意思了?来,我来。”说着,就动手解麻七的扣子。
麻七有力地摁住呼四宝的手:“这么说,你进京了?”
呼四宝脱口而出:“进了,咋了?”突然意识到什么,“你说的甚了,我不懂。”接着顿了一下,然后才伸出手,要解麻七的扣子。
麻七推开呼四宝的手,一颗一颗地扣上:“你还是去找她了。你可以开车去北京找她,为什么不来上海找我?”
空气里突然是漫长的沉默,像多年的时光凝结而成,硬硬的,浓浓的。
过了好久,麻七脸上浮起一抹笑来,她说:“四宝,我想看外面的星星,要不,我睡到你的皮卡车里吧,反正夏天,也不冷,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天空。”
呼四宝愣着,愣着,愣着。
然后,他从炕边溜下来,坐到桌子边,摸索着点着一支烟,抽了起来。烟雾升起来,笼罩着他的脸,看不出他的表情。
好久,他才说:“好吧,你实在想看星星,那就去吧。”他一只手抱着炕上的被子,一只手搂着麻七的肩膀:“你这个读书读傻了的人,真是个神经病,看甚星星了嘛,唉!”
麻七也伸出手,揽住呼四宝的腰:“谢谢你。”
麻七睡在放平的车座椅上,呼四宝把被子盖到麻七身上,拍了拍麻七的脸:“傻蛋,看妖怪抓走你!”然后,轻轻叹口气,关上车门,走开了。
麻七侧起身子,看天上那条密密麻麻星星的长河,以及异常明亮的北斗七星。这时候,天空反而明亮了许多,有丝丝白云在空中飘浮着,在星星的下面,柔软,轻薄,自由。
是,自由,麻七现在感觉无比自由,仿佛睡在海洋里,是在一条绿色的船上,漂浮着漂浮着。麻七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睡在一辆皮卡车上,更没有觉出生命有时候是如此自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不,她觉得她不是睡到船上,而是阿拉伯的飞毯上,无限地接近天空,无限,无限。
有说不出的平静。
早上醒来的时候,皮卡车两边的大车已经开走了,麻七并没有起来,只是那么躺着。她忘了昨天发生了什么,天哪,喝太多了,她怎么睡在了皮卡车上?
麻七自己就笑起来。
车窗外,天空湛蓝,是黎明的湿润的清凉的蓝。
她想起来,她是要去白云的,那白,那云。
是,一会儿要去白云,白云之上的白云。
这白。
这云。

阿连,原名李春连,生长于内蒙古达茂旗,现居山西方山县。作品散见于《钟山》《黄河》《山西文学》等刊。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哈达图》《寻找田小军》。《一个人的哈达图》获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来源:《芙蓉》
作者:阿连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