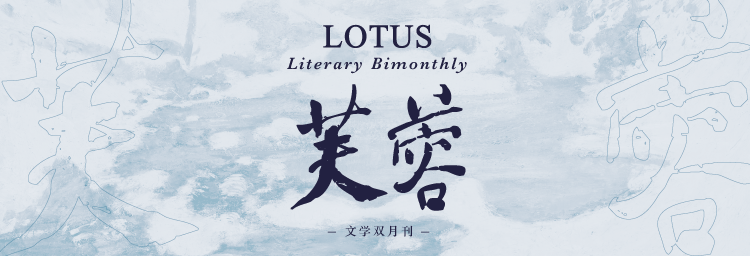

聋人吉小果(中篇小说)
文/薛喜君
从火车上一下来,吉小果就贪婪地深吸一口气,灼热的胸腔瞬间透亮了。随着他移动的脚步,盘旋他眼前的哈气,宛若喷出的烟雾。寒风像一把锋利的刀,把棉军裤打得贴到腿上,他匆匆地走出闸口。接他回来的县武装部干事小许,也紧随其后,他们穿过南广场,又穿过毛子街,一片老旧的楼区就在眼前了。
北镇升级为北镇市后,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但吉小果和父母,还住在头道街老旧的楼区里。当年,这几栋楼可是鸡群里的长脚鹤,招来不少艳羡的眸光。分配楼层,论资排辈,在政府后勤部门做维修工的吉村,只有在六楼和一楼之间选择的资格,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楼。女人聋三拐四,还是住低层方便。
吉小果就是在这间不足50平方米的老楼里,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下汽车,又坐了一夜火车,也没能消耗掉他两天来的离别情绪。相处了三个月的战友,抱头痛哭时,塞给他各种礼物,茶叶、点心、糖果,安徽的战友还拿了一大包石斛。刚到新兵连,战友知道他是来自北方的兵,都好奇地问:“听说你家那儿一出门耳朵就冻僵了,一扒拉就掉下来。”吉小果差点笑喷,他想起老爸像倭瓜似的大脑袋,难道他耳朵在奶奶的肚子里时就被冻掉了?他忍住笑,想了一会儿,才说:“我们那地儿的冷,能听见响儿。”南方兵七嘴八舌地问:“响儿是啥?”南腔北调的声音,仿佛从山对面滚过来的雷,沉闷而又嘈杂,吉小果一脸蒙。
“响儿,就是动静儿。俺们那儿冷,带着嗷嗷的响声,呼出的哈气都能冻上。”南方兵看吴雷,眼神里都是崇拜。从小到大,吴雷就像一把伞,总是在吉小果需要时,砰的一声打开。
吉小果最后看一眼军营,背着身子与战友们挥别。他全身的毛孔,都带着离别的愁绪,但他咬牙没掉一滴眼泪。这就是宿命,他必须承受。他很想与吴雷说说心里话,但这两天,吴雷有意躲着他。他理解发小的心情,他也克制住自己。刚走出军营,他就看见孑然站在山坳口的吴雷。他迎着刮脸的山风跑过去,吴雷双眼红肿。小时候,吴雷他爸用柳条抽他,他也不掉眼泪。“老吴揍人手狠,一根柳条就想让我屈服,吹牛逼。”他咝咝地抽气,甩着被抽出一条条红肿印痕的胳膊。
此刻,吴雷哭得稀里哗啦,吉小果第一次看见发小流泪。他伸出双臂用力地抱住吉小果:“你一个人别去外地打工,我替你当兵,你等我复员。”
吉普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小许催促他上车,说火车不等人。他抽噎着晃了一下脑袋,低头钻进车后座。马达轰鸣了两声,吉普车就走了。他只看见发小拼命地追赶,却听不见他涕泪交零的呼喊。
吉普车很快就甩掉了军营,甩掉了山路上奔跑的吴雷。吉小果的心瞬间就鼓起一个又一个血疱,胀得他胸口闷疼。他双手拢在嘴上,压着嗓子嘶吼一声,血疱砰的一声,又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嗓子眼儿涌上来一股咸腥,他差点吐出来。
“怎么,小果晕车了吗?”小许转过头问。
他摇头。
吉村打开房门,惊恐不安的眼神儿,游离得无处安放。站在他身旁的邱文璐,脸色苍白。小许握住吉村的手,再次说明小果离开部队的原因。吉村哦哦地应着。吉小果把背包放到里屋,看到床,他两腿疲惫得差点瘫软。新兵连训练量那么大,他都没觉得累,坐一夜火车就累得要散架了。
他眯缝着眼睛从里屋出来,小许与他告别。他把小许送出单元门口。
闪着光亮的水撒欢地从花洒下喷出来,像一场急不可待的雨。热水砸到皮肤上,溅起了水花。他抓过一瓶沐浴露,地上又有了一朵朵白花。没一会儿,白花被水冲得七零八落。他盯着落败的花流进下水道,叹了一口气。他清爽地从卫生间出来,却被守候在门口的爸妈吓一跳。
“你俩干啥?”
“要恨,你就恨我。我也不想你来受苦,更不想让你下地狱。”泪水像两条线,从邱文璐的脸颊上扯下来,她紧随儿子的脚步进了里屋。吉小果皱着眉头,拽过被子钻进去。他缓慢地说:“妈,让我睡会儿。”看到蒙头盖脸的吉小果,邱文璐乜斜一眼窗外,阴霾的天,似乎又在酝酿一场雪。“该死的老天爷,就不能施舍点光进来。”
吉小果从繁杂的梦境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雪后的太阳,难得地从玻璃窗射进来,他眯着眼睛,慢慢适应了清冷的光线。“这觉让你睡得,叫了两三次,都不醒。”吉村看着他,“果儿,快起来吃饭,你妈包的牛肉蒸饺,还蒸了鸡蛋糕。”吉村的眼神儿又在他身上游荡,“明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万一要是错了?或者你就那天听力不好。到时候,咱们就拿着检查结果,和部队同志说说,兴许还能回去。”吉村的口气,像是试探刚冰封的水面,能否经住脚似的小心。
吉小果看了吉村一眼,沉默。
邱文璐走路不抬脚,嚓啦嚓啦的摩擦声令人心烦,幸亏她自己听不见。“眼看过年了,乐和不乐和,年都得过。要是留在年那头,你就得给我披麻戴孝。”她的话是说给自己,又是说给儿子。吉小果看她一眼,老妈只要一说话就恶狠狠的,不是地狱,就是天堂。
“别玩游戏了,陪我去买年货。过年,你不吃啊?”邱文璐拔掉电脑电源。
吉小果愣怔地看老妈一眼,嘀咕了一句:“妈,你可真暴力。”
除夕夜,吉小果给老爸老妈倒上啤酒。他知道,爸妈因为自己才心情沉重,但他们都在极力掩饰。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离别军营的苦痛,如细水长流般涓涓不息。他也想让军营像一缕炊烟,风一来就散了,像一道风景,看一眼就过去了。可是军营就像一座耸立的丰碑,在他心头时时地屹立着。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午夜,他责骂自己没出息:“吉小果,被一场离别击倒,你怎么为父母分忧?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他使劲地拧自己的大腿,他想让皮肉的疼痛,把另一种疼痛压住。但疼痛却像藤蔓一样攀爬着蔓延——他举起酒杯:“老爸,给我时间,我会没事儿的。”他又转向邱文璐:“老妈,别老和我生气,我是在游戏里调整,相信我。”三只沉重的杯子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果儿,你总算说话了。”吉村眼眶里有泪光盈动。
在吉村强烈的干预下,吉小果硬着头皮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听阈平均值为>110~120分贝。吉小果仰头望天,这个数值告诉他,声音宛若与他分道扬镳的兄弟,彻底的决裂了。
吉小果从听人世界,走进聋人生活,用了19年。
眼泪掉进油锅里刺啦一声响,滚热的油珠溅到吉村的手上,他激灵地把青菜倒进油锅。青菜与热油碰撞出激烈的争吵后,又散发出袅袅的清香。他抹去眼泪,把饭菜给妻儿端到桌上。“果儿,别难受。有老爸呢,老爸是你的耳朵。”可能觉得自己连耳朵都没长,他又改口,“老爸做你的听人。”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中篇小说《聋人吉小果》)

薛喜君,女,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高研班学员。代表作有《李二的奔走》《迎着太阳走》《永远,其实不远》《2018年的村庄》《后来的村庄》《炊烟像面旗帜》《野水》《白月光》《黑白村庄》《拳心》等。曾获黑龙江省文艺奖小说奖、《朔方》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薛喜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