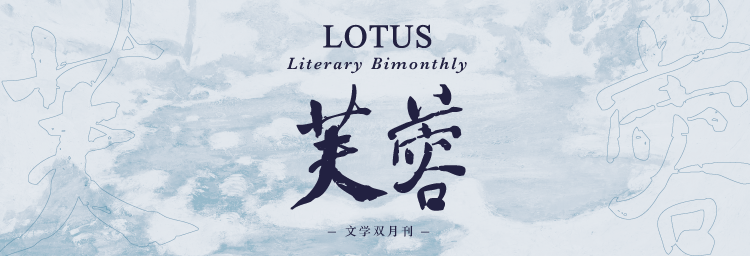

杀树(短篇小说)
文/东紫
秦三婶的拉稀止住后,又在家恹恹了数日。这天早晨,她醒来就觉得有了精神。手指头有劲了。她反复攥攥,伸伸,心里逐渐敞亮,她对空气欢喜地说:看来还没熬到头儿呢。
没熬到头儿的日子,就得干活。她坚定地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才活。有了干活念头的秦三婶,就有了下床的动力,也有了吃饭的动力。她热了头晚的剩粥,在碗里打了个鸡蛋,用滚沸的粥冲了蛋花,就着春节前腌的萝卜豆豉咸菜,吸吸溜溜地喝。一碗蛋花粥喝进去,秦三婶觉得四肢更有了力气,她从东屋里推出电动三轮车。扭头看见东屋窗台上镜片里的自己的脸,秦三婶愣了刹那,揉搓了两把,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哎,怎么老得跟泥瓦碴子似的。
一出门,秦三婶就感觉哪里不对劲,眨巴了两下眼皮,就找出了不对劲的地方。小草家南边的树林子没了,光秃了。遍地残枝断叶,还未干枯的绿色,在垃圾里显得格外俊俏。秦三婶跟空气说:怎么把树杀了,好好地怎么杀起树来了?就那树还遮丑。
那片树林,其实早已不成林,被房屋和垃圾蚕食着,也被那些搞畜牧养殖和花草树木培植的,偷土偷得凹凸不堪。有些根基被动了的,歪斜,倒下,但仍旧有几十棵,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地站着,肯定是去年闹屎灾的原因,所有树叶都油汪汪地绿着。秦三婶看着南树林的狼藉,心里一片茫然:这又刮的哪阵风,怎么把树都杀了?还家家户户商量好了似的,一块儿杀。
秦三婶出村,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她家门口直着往东,然后拐俩弯上大路,另一条就是从小草家南面的路拐弯直接往东。自家门口那条路,秦三婶骑三轮车的时候不愿意走,因为胡同窄,去年通自来水的时候,施工队又在路上垒了水表池。当时垒得高出地面一拃,秦三婶跟施工队为此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嘴角堆白沫,唾沫说干,才小赢下来。施工的气哼哼地拆了水表池,向下挖坑,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自来水,还怪多毛病,真难伺候。最后,还是高出地面三横指,如果不小心,人走着会被绊跤,骑自行车和三轮车的,再怎么注意也难免颠得歪扭两下。毕竟胜利了,秦三婶骄傲了好一阵子,遇到有人埋怨过车颠簸,她就会大声说:要不是我,你这会儿得搬着车走道。
秦三婶现在不愿走小草家南边的路是有原因的。去年芒种那天,小草娘一大早就哆嗦着紫色的嘴唇跑进秦三婶家,声音抖抖地说:我家四千块钱不见啦!家里一点样没变,就钱不见了!你帮着分析分析,是不是招贼了。秦三婶说:这么多的钱你肯定是藏着的,要是招贼屋里不得被翻得乱七八糟?小草娘说:我用袜子装着藏在橱子的一摞衣服里,够严实吧?真是奇了怪了。秦三婶想起前天儿子旭日来家里说:小草怎么趴她家狗窝里扒拉,忽地站起身就跑,差点撞我摩托车上,她忙慌啥啊,我看她家锁着门,问她怎么不等她爹娘回来再走,她说不等了。
小草婚后日子过得紧巴,回娘家从来都是空着手,来了就到处扒拉。小草娘每逢被小草扒拉恼了,就跑到秦三婶家诉苦:唉,我哪辈子欠下她的啊。
秦三婶瞅眼旭日,替小草爹娘叹口气,无言地张了张嘴。一是不想传言拌舌,再就是旭日长到五十,不但没给她买过一个馍半张饼,还把他自己的家伙散了架,让她日夜忧心,又像他幼小时一天三顿地给他做饭。
秦三婶对小草娘说:旭日前天看见小草扒拉你家狗窝,你问问她拿没拿,她要是没拿,你就赶紧去派出所。小草娘愣怔了半日,然后陡然变了脸色说:俺闺女断然做不出偷钱的事来!你和旭日可别睁着眼说瞎话!
秦三婶知道小草娘风一阵雨一阵的性格,嘴跟老棉裤腰似的没有紧头儿,虽然心里不悦,倒也没有怪罪她,就说:确定不是小草拿的就赶紧去派出所。小草娘铁青着脸说:苍蝇都飞不出去,还派出所,派他娘个屁!
过了不足一个时辰,西南邻的小港娘悄着脚来对秦三婶说:小草娘又到处蹿趟子,说她家招了贼,丢了八千块,找人掐算说南北趟里去了,老的和少的合伙,老的平时去她家的时候瞅准了她家钥匙放狗窝里,把藏钱的地方也早瞅准了,让少的去偷。这不分明就是说你吗?她家南边就是树林子,北边就你家。秦三婶的脑袋和肚子里顿时一起急风暴雨,她颤抖地指着阴霾霾的天说:老天!老天在看着!她往厕所跑,还又瞅了眼天。
这次拉稀来势凶猛,仅次于第一次,跟拧开的水龙头似的。
秦三婶第一次拉稀,来势最凶。到了第三天,秦三婶就感觉手指头都快死了,抬不起,攥不上。让旭日用三轮车拉着去村卫生室打针,打了五天针也没好,秦三婶就生起秦三叔的气来:都到那边了,能耐还不长点吗!怎么就不知道去求求阎王小鬼的!你看这一大家子,千头万绪的事,我能撂手就走吗!她让旭日代替她去狠狠批评秦三叔。旭日去批评完秦三叔,刚进家就接到他姐丽云的电话。丽云说:很像神经性腹泻,跟情绪有关系,一是老爹走了,她每逢佳节倍思亲,再就是她要强好面儿,看人家过年都阖家团圆,咱们家,唉,门上连对联都没有。秦三婶也听见了丽云的话,疲乏地一笑说:这么说还批错了人。
这次,秦三婶既不敢把被小草娘诬陷的屈辱告诉旭日也不敢告诉丽云,她怕自从跑了老婆就经常蹿火的旭日去和小草家理论,肯定不出三句就打起来。伤着谁都不好啊!又怕丽云在外地,因为惦记她路途遥远地往回赶,弄不好还被拦在半道上。
秦三婶边推三轮车边天上地下地张望,突见天空里竟然还有一撮油汪汪的绿,地上却看不见树身。原来是小草家的麦秸垛包着的那棵树。她对树说:哎呀,你命好,逃过了一劫。
空中传来老鸹喳喳的聒噪,秦三婶仰头看见树缝里两只鸟合伙啄另一只,不一会儿就明白了它们在争地盘。她对那俩鸟喊:别的树都没了,你们不让它待,让它怎么活?它又不住你窝里。喊了几嗓子,见鸟不听她的,她就蹬着三轮车走至小草家南边的路口,看小草娘从东边路上走来,不想经受碰面的尴尬,她就掉转车头往回走家门口那条路。走至旭日家屋后,看见她病前栽种的五棵芸豆不仅发了芽,还长出了叶片,每个都有小娃娃巴掌那么大。秦三婶喜滋滋地跟芸豆说:哎呀,你们怪能耐呢,我这病恹恹的没顾上你们,你们竟然长这么好。她和芸豆说完话,用眼角瞥见小草娘的身影,赶紧扭动三轮车把,把三轮车发动起来,拐进胡同,颠簸着过了水表池,再转弯,晃悠悠地爬上土陂,来到村里唯一的大路上。
大路早已不是站在那里就能遥望田地的大路,它的另一侧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建了五六排房屋,那是年轻人的家,也有不堪老村的拥挤和破败,希望改善生活的人的家。就在秦三婶琢磨是去路东看树林还是去弹药库南看秦三叔的时候,秦家斌老婆从东面小跑着来到她跟前,气喘吁吁地说:旭日娘,我刚想着要去给你报信,没想到你就来了,秦中华家把你给告了,一群人在你家树行子里转,说要杀你家的树。
电动三轮车发出急促的嗯哼声,秦三婶的胸膛里也发出了同样的声响。一个念头腾空,坚定地盘旋在她的脑子里:那些树无论如何不能杀!老天爷来了我也不答应!
早有人看见了秦三婶,树行子里的人都扭头朝秦三婶看,村委主任秦宝峰摆手叫上驻村干部、村第一书记张得禄,一起从凹地里弓腰上来,等着秦三婶。不等秦三婶从三轮车上下来,就围着她宣讲政策。
树,必须杀,不是村里要求,是上级!国家!
国家有政策,必须杀,不管什么样的树!
上级,秦三婶是知道的,也并不太怕他们,她意识里的上级是那些社区干部或乡政府大院里的人。秦三叔当队长时,因未满足大队书记的弟弟包地干水泥预制而遭到毒打,秦三婶为给秦三叔出冤枉气,曾经找上级理论。那些上级开始躲着她,躲不过就把水杯在桌子上敲得砰砰响,厉声对秦三婶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你家老秦工作方法有问题。秦三婶把手啪啪地拍在他们的水杯旁,拍得他们的水杯颤动,甚至跳动:你堂堂的乡镇干部惹得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嫲嫲拍桌子,你的工作方法不也有问题吗!秦三婶质问他们,秦三叔按照上级规定办事错在哪里?他们凭什么不给秦三叔一个公正的交代。虽然历时两个月,但乡政府的干部最终还是让大队书记带着弟弟,到秦三叔的病床前赔了不是,认了错。
一听国家俩字,秦三婶心里的那份坚定就软了。她从小就知道国家是了不得的,国家政策是谁都必须执行的。秦三婶皱着眉头,嗫嚅道:国家不是一直都号召种树吗,怎么现在让老百姓杀树?她说这话时,脑海里涌出六十五年前她在浮山植树造林的情形。那时,十五岁的她带领着一个哑巴、一个瘸子和一个小脚老太,是浩大的工地上实力最弱的小组,却是植树最多、成活率最高的。她和哑巴挑石头挑土挑水,瘸子垒簸箕形状的坑,老太太运苗扶苗。她和伙伴的名字在大广播里被一遍又一遍地宣扬,那飘荡在空中的赞美让她脚下生风,头发丝里都蓄满了力量。到现在,她每逢去山上,看见那些树,还满心欢喜,觉得它们就像电视开关,一看见它们,自己年轻时的日子就活脱脱地跳出影子来。
秦宝峰和张得禄原本打算应对秦三婶高亢激愤的言语,没想到她的话竟那么无精打采。见她语气绵软,其他人也跟上来,帮着敲边鼓:国家政策呢,要不谁愿意多管事,惹麻烦。
秦三婶四下里瞅了瞅,又仰头望了望树梢,那被秦中华用电锯削过的梢,还没来得及再长出梢该有的形状。她把目光转回秦宝峰的脸上,问:这树咋就碍着国家的事儿了?
说树碍着秦中华家的事,还能扯上一星半点的,因为到太阳转西,树头的阴影落在秦中华家墙外的几棵小杏树上。秦中华因此偷偷地把东边三排的树头给削了。但树的头和人的头一样,凡是被削总能引人注意,何况是拿着那些树当心肝宝贝的秦三婶,她在发现树没头的瞬间就直奔秦中华家,质问他凭什么目中无人,为什么不能和她商量一下。
这块地不让种树能种啥?秦三婶定定地瞅秦宝峰的脸。
这块地差二厘一亩三分,是秦三婶家所有田地里离家最近,也是土质最好的一块,因为离家近就被新的宅子包围了。那第一个造房子的人,生怕地基比路面低了院子里囤水,又深信地基高日子过得好,遂把庭院铺垫得高高的。后者纷纷效仿。没几年就把秦三婶家的地围成了方方正正的凹坑。遇到有人往坑里排污水,秦三婶就变成斗士,她顺着污水流淌过的踪迹,去和人家理论,声嘶力竭地提醒他们做人做事要将心比心,因为头顶有老天在看着。她不知道那被教训的人都有科学知识,知道天就是天,并没有盯着他们的神仙。他们也有委屈,水往低处流,这是地心引力。秦三叔怕得罪人,他阻止不住秦三婶,就只默默地咂巴烟袋,默默地比以往更认真地耕种。小麦、玉米、地瓜、黄豆、绿豆、花生,他都一一试过,大都是开头的一段时光绿意盎然,希望满满,失意基本出在后半程。这也让秦三叔和秦三婶都误以为,庄稼也和人一样。这块地成了老两口的心病,他们疼惜又无可奈何地看它,惦记它,像对待生活能力不足的子孙。
事,没有一成不变的,就像人不可能一生不长皱纹,不长白毛。那场罕见的台风过后,浮村和附近村庄里几乎所有的树都晕厥在地,它们朝同一个方向倒下,如洪水流过后的巨型水草,记录着风的威力和走向。村里村外忙成乱麻,电锯声 、斧凿声把人心里的惊诧和惋惜切割成一声声哀叹。风这样能耐,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那些他们亲手植下的,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高祖父母亲手植下的树,都被杀了。两次。一次全尸。一次碎尸。
秦三婶和秦三叔听旭日说这台风有名字,而且还是个很好听的名,达维。秦三婶说:这起名的人不食人间烟火,这种霸王风,还起上好听的名,咋对得起那些被杀了的树啊。风和人一样,都是霸王才横行霸道,不管别人的死活。霸王横行,小喽啰都噤了声。果真,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闷热无比,一丝风也不见。秦三婶和秦三叔常盯着院墙角处幸存的那棵桃树,瞅得眼晕也未见树叶抖动。秦三婶对慨叹老天要热杀人的秦三叔说:可怜这树,没个一伙的,孤单得叶子都不知道晃荡了。
被杀光了树的村庄,像没戴斗笠的脑袋,被直晒了一段时间后,人们格外怀念起树的好处来,原来种树的地方重新栽上棵小树苗,那些遗憾和悲伤就瞬间得到了缓解,像身上疼的人吃了止痛药片。原来没种树的地方,栽上棵树苗,就像多了个起头编织的斗笠。秦三婶和秦三叔就是这时候在凹地里种树的。
种树的时候,孙女一枝花四岁,负责扶着树苗让爷爷奶奶浇水培土。她扶着那和她差不多高、和她的小辫子差不多粗的树苗,怀疑地问:它们这么小能长成大树吗?秦三叔和秦三婶异口同声地说:能!他们许诺等一枝花长到十八岁,它们就能长成大树,到时候把它们卖了,把所有的钱都给一枝花去读大学。一枝花问:那这些树都是我的了,对吗?秦三叔和秦三婶又异口同声地回答:对!
国家政策,谁也躲不过去!秦宝峰催促秦三婶做决定:杀了吧,正好有来买树的,也不用你自己到处去找买家,你这么大年纪到处走多危险啊,车来车往的。
卖不卖?卖就赶紧的,我们还有别的人家等着呢,四千五全包,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
为啥非让杀树呢?我不明白这树怎么就碍着国家的事了?!秦三婶话音里的执拗,让秦宝峰不得不给她把政策讲透彻些,他低声说:这不全世界种的粮食少了,谁家都先各顾各,不愿再把粮食卖给外国了。咱们国家人多,自己产的不够吃。你这块地是种不了粮,我们也知道,但它在文件上是属于大良田,你家不杀树,别人家就不服。你说,让政策挡在你这里,谁都不愿意杀树种粮,那就会导致全国挨饿!上级来检查,一看登记本,大良田里还种着树,俺们这群人头顶上这顶小乌纱帽都得免。
全国挨饿!秦三婶的眼像被东西扎了,不由得挤了几下眼皮。挨饿的滋味她知道。直到现在,一点点煎饼渣掉地上,她也要舔舔指头,用唾沫把它粘起来,填进嘴里。每当儿女说她这样不讲卫生,她就说:粘上点土就不卫生?你们没挨过饿,饿了土都吃。
现在家家都有存粮,怎么会全国挨饿?秦三婶追问。
那是咱农村,城里人哪有存粮?国家对咱们农民够好了,都十四五年不收公粮了呀,咱们怎么能忘恩负义对不起国家呢?谁都不杀树种粮,城里人不得喝西北风去!
谁不听国家的话,谁就对不起国家!张得禄用他在法院里练就的威严语调缓慢低沉地说:谁就是违法,就是犯罪!
秦三婶的执拗开始动摇,八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她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全国挨饿更大的事,但她还是觉得杀这些树是她自己做不了主的。她长叹口气,妥协道:那你们等我去商量商量吧。
秦三婶倒转三轮车,秦宝峰凑近低声说:你只要肯杀树,这块地我帮你包出去,比你种树还挣钱,正巧他们有人想租块地用,一年两千,一包十年,多合算!
秦三婶说:那我也得商量商量啊。一众人看着她的背影,猜测:她和谁商量去?找旭日?找刘家村那个收木头的打听价格?
秦宝峰瞅了一眼木材贩子,对村委宣传委员秦理说:你跟着看看她找谁商量,催着点,这活别卡在她家推不动了,张书记和我可是给乡领导打了包票,保准一棵不留。
秦理骑上自行车尾随着秦三婶,只见秦三婶一路向南。
秦三叔的坟上长满了荒草,秦三婶爬着把坟上的草都拔完,仔仔细细,就像她曾经用热毛巾给病中的秦三叔擦身擦脸那样。待坟包干干净净地露出来,秦三婶才在坟的南边站直身子,低头看着秦三叔脸的方向,把心里的犹豫和忧虑说给他:你说咋办?咱不杀吧,人人都攀比着不杀,全国粮食就不够吃。咱都挨过饿啊,虽然咱家里还有三缸麦子,可咋能让别人挨饿啊。杀吧,当时咱许诺那些树给孙女了。上回,在法庭上她就不认识我了,我拉她手也不让,抱也不让,问她还记得那些等她上大学的树吗,她才点了点头。这要把树杀了,唉——
秦三婶长长地叹气,哽咽着催促秦三叔给她回答:你说啊,杀还是不杀?
秦理等得不耐烦,就大声招呼着走来:三婶,你怎么跑这里来商量,这能商量出个啥来嘛!
像以往一样,最后的主意还得秦三婶拿。她扭头看看远处的秦理,下定了决心:不能干让国家饿肚子的事,再心疼也得杀。卖的钱我一分也不花,都给孙女存起来,等她上大学的时候,我总能打听到她去了哪里,到时候再远我也给送去。唉,老汉子,我知道你不舍得,我更不舍得啊,看着那些树,就像看着孙女,就觉得心里有盼头。盼她回来的时候,还记得咱仨一块儿种树。平日里,我只要动得了,每天都去那里转悠,看看,想想……唉,这要是杀了树,我再也没东西看了……
秦三叔的坟黄亮亮地在她浑浊的泪眼里被放大,再放大。
秦理看见秦三婶在抹眼泪,他想起秦三叔和秦三婶往日待人的好,心下不忍,想告诉秦三婶,她家的树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是不用杀的,因为那文件上规定只杀八年内种的树,是张得禄怕扯不清,不好执行,才改为所有属于大良田里的树都格杀勿论。转念,秦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事只有张得禄、秦宝峰和他三个人知道,他又想到可以提醒秦三婶反咬秦中华家,因为他家房子连宅基地证都没有,也是占的大良田。可气的是,还搞那么大一个院子。秦理张开嘴,要把话说出口的瞬间,想起秦中华他儿在隔壁县里当官,女婿也在县交通局,自己车撞了人,还托人家走后门处理过。他把话咽下去,蠕动着喉结瞅秦三婶。
秦三婶擦干净泪,知道秦理是来盯她的,就说:怎么还麻烦你跑一趟,还能跑了人?
秦理尴尬地笑笑说:还真怕你跑了,完不成任务,当官的都没法跟上级交代。
秦三婶叹口气说:一个庄户老嫲嫲,能跑哪里去?种一辈子地的人,最终也就是化成把灰儿埋进地里。她转身指着南边的树林,问:这都杀吗?唉,有树还能落鸟,躺在这里的人还能有做伴的,大夏天里也能遮个阴凉。
秦理肯定地说:那当然,国家政策,谁也跑不了。
秦三婶掉转三轮车方向的时候,秦理说:他们给你的价太低了,才一半的价,你奔着八千要,他们肯定会砍价,砍下一千你就咬住牙。秦理说完骑上自行车,又回头叮嘱秦三婶:跟谁也别说是我教你的!
秦三婶感激地点头保证:放心,咱一辈子还没干过出卖人的事。
秦理一到大路,就拨通了秦宝峰的手机:同意了,往回走了。
秦宝峰一行人赶紧走回秦三婶家的凹地。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村里其他的树就都能杀得顺顺当当。等秦三婶一到,秦宝峰亲耳听了秦三婶应承,就对木材贩子说:你们好好谈,我们再执行下一户去。
等秦三婶和木材贩子交涉完毕,木材贩子问还有什么条件,树枝子要不要留。秦三婶摇摇头说:我就一个条件,你们等我走远了,再杀,别让我听见杀树的声。
(节选自2024年第1期《芙蓉》短篇小说《杀树》)

东紫,本名戚慧贞,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2004年始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期刊发表作品,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等期刊及多家年度选本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长篇儿童文学《隐形的父亲》,中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在楼群中歌唱》《红领巾》《穿堂风》《珍珠树上》等。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曾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泰山文艺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山东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东紫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