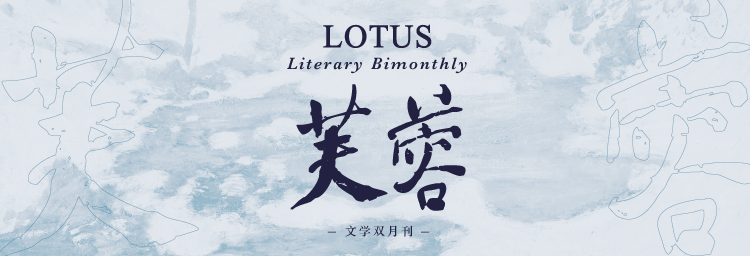

童话城堡(中篇小说)
文/杜阳林
今天,我十八岁了。
不是我想到了自己的生日,是妈妈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奶油蛋糕,上面插了十八根蜡烛。
“儿子,生日快乐。”烛光在妈妈的脸上闪烁跳跃,但她扑哧一口,吹灭烛火,黑暗顿时像铺天盖地的厚绒布,将她团团包裹。
点缀在蛋糕上的草莓,是妈妈亲手种植的。为了在这里创造一个温度适宜的暖棚,从我的十岁生日开始,她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件事。制作奶油的牛奶,来自一头名叫“妞妞”的奶牛,它像是一台机器,每天勤勤恳恳地生产热腾腾的乳汁,爸爸专门写了一首诗来歌颂它,题目就叫“伟大的妞妞”。妈妈清晨从鸡窝里拾捡了刚刚落地的鸡蛋,它还带着母鸡的体温。她总是这样,希望将最好的都留给我,留给她十八岁的儿子。
哪怕我再也无缘品尝一口妈妈制作的蛋糕,也努力想象着蛋糕的扑鼻香味,以及蛋糕的柔滑触感,还有妈妈那一颗爱我不渝的心。
今天是我的冥寿。从五年前离开人间,我已在这座童话城堡里飘荡了整整五年,谁都看不到我,只有妈妈偶尔会忽然转身,暗淡的眼珠朝向身后的虚空:“谁?谁在那儿?”除了穿行无忌的风,没有任何回答她的声音。
妈妈的眼睛晦暗得让我心疼,五年前黑亮的秀发,如今已花白了小半。她眼珠死死盯着半空虚无的某一点,干裂起白皮的嘴唇翕动着:“小希,是你吗?”
一个鬼魂,永远无法回答妈妈的问题,这是令我最心痛的事。
不,我已经没有心了,从它停止跳动的那一刻起,我再也不用为了这颗心脏而患得患失。
一
有的人记事早,有的人记事晚一点,作为一缕鬼魂飘荡了五年的我,多多少少比过去的自己成长了,认清了自己资质之平庸。
我记住的第一件人生大事,是自己动阑尾手术。妈妈、外公、外婆三个人轮番照顾我,我从麻醉中醒来,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躺在床上疲惫不堪,因为麻药的劲头还没完全过去,感受不到刀口的疼痛,只觉得口渴。我喊妈妈,我要喝水。
妈妈扑到我的病床前,右手死死撑着床沿,仿佛稍微松手就会摔下去,身上只剩下这一根咯吱作响的骨头作为支撑了。她看着我,又哭又笑,眼泪从笑容的褶皱里流下来,像是怪异的小溪滚过了山谷。
“小希,你还不能喝水,乖啊。”
医生不准妈妈给我喂水,顶多拿棉签蘸上水,润一润我爆皮的嘴唇。嘴唇成了撒哈拉沙漠,那一点点小水珠润上去,立即就蒸发了,比不蘸水还要让人煎熬和失望。难过的情绪,像泡泡一样越吹越大,我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愤懑,大哭起来:“爸爸呢?我要爸爸啊!”
病床前来来回回都是三个人,他们把我的爸爸藏到哪里去了?
我这一哭,妈妈的眼泪流得更加汹涌了。外婆将她劝到外面,换外公来安抚我。只有外公单独陪我,我慢慢止住了哭泣。更小的时候,我偶尔会将外公和爸爸认混,将外公叫成爸爸,也曾将爸爸喊作外公。他们脸上有相似的皱纹,身上有相似的气息。
这不能怪我,我的爸爸,比外公还要大两岁,比我妈妈大三十岁。在家妈妈叫他“康老师”,与她的姐妹淘聊私密话时,她甜蜜地称他“康先生”。
现在,万恶的白大褂强制我躺在病床上,我连喝水的小小心愿都难以达成,康先生呢?在妈妈眼里万能的、伟大的、魅力无穷的康先生,难道他就不过来看儿子一眼吗?
外公温厚的手掌和爸爸相似,都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儿。他摸了摸我的头顶,我假装是爸爸陪着我,合上眼皮,睡意就来了。
我终于可以下床走动,外婆给了我一只白水煮鸡蛋,让我坐在小椅子上看看窗外。她嫌医院床铺的褥子太薄,怕我睡着不舒服,特意从家带了褥子铺垫。
看着窗外多无聊啊,我要走到窗外去。
趁着病房里的人各忙各的,我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门,顺着走廊,直走了几十步,那儿有道小门,与小花园相通。
花园中间砌着一个水泥花台,台沿十分低矮,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孩,双手按着台沿轻轻一撑,屁股也能稳稳当当地坐上去。
这是我找到的“宝地”,不亚于满镶黄金和钻石的王座。我心满意足地坐在上面,从蓝白条病号服口袋里掏出鸡蛋,轻轻在花台上一磕,原本完整的蛋壳表面立刻变得四分五裂。蛋壳如此脆弱,让我困惑地举起鸡蛋,朝着太阳仔细看了两眼。那时,我太小了,不懂得什么叫“不堪一击”,命运让我先与“不堪一击”相遇,再找恰当的时间和空间,用刻骨的感受反复告诉我这个真理。
从碎裂蛋壳中剥出来的鸡蛋,是另一块完整的白玉,摸上去像爸爸的缎子汗衫,滑滑的,软软的,凉凉的,举高一点,穿过树叶间隙的阳光落在上面,平添一分瓷白与晶莹。我好似面对世上的珍馐美味,它的美丽让我目眩,不敢贸然将它放进嘴里,这是一种莽夫的亵渎。
一只手,像一只不讲道理的鸟儿,翅膀轻轻一扫划过天空,鸟喙准确无误地直奔猎物而来。
我回过头,逆着光,只看到一张胡子中藏着的嘴巴,喉结蠕动几下,鸡蛋就神奇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我刚想咧嘴大哭,嘴的主人蹲下来,我看清原来是爸爸,一下子转悲为喜,一头扎进爸爸怀里。
“爸爸,你怎么不来看我呀?”
“儿子,爸爸这不是来了吗?”
要等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爸爸和妈妈之间,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分歧,妈妈甚至想过离婚的事。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来说,“离婚”是多么可怕的词,即便事后已过去几年,她提起来还会浑身发抖,像风雨中的燕子,满心绝望地在黑夜里乱撞乱飞,每一根羽毛都被淋得透湿沉重。
二
妈妈从结婚那天起,大概就没想过要和爸爸分开,虽然那时的爸爸是康先生,也比她大三十岁,但她有信心与他“白头偕老”。
妈妈身边的小姐妹,奇怪她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老男人”。
“因为,他有才华啊。”妈妈局促不安地用手指反复绞着衣服边儿,有点不自信地小声回答。
那时,妈妈还没看完一本康先生写的书。她只知道,这个叫康明亮的男人,出版过好几十本书,摞起来有半人高,除了写书,他还在大学课堂上讲课。天哪,大学课堂,一辈子都没进过大学校园的妈妈,无法想象在那里面听课的学生有多幸福。
“这有什么要紧呢?你想进大学看看,随时欢迎啊。”康明亮慷慨地发出了邀请,仿佛大学校园是他家的私产,随时都能让她进去看看。
事实上,妈妈第一次鼓足勇气去大学,就差点吃了闭门羹。
原本妈妈和康明亮约好两点在校门等,他自己一点多提早过来了,施施然踱进校门,一直走到教学楼下,坐在紫薇树下喝茶。妈妈打电话给他,他正和两个前来请教学问的学生聊得火热,没有听到电话响。妈妈连打了几个电话后,朝门卫茫然地摇摇头,牙齿咬着嘴唇,一脸恳求的表情:“那个,快到上课时间了,康老师一直没接电话。”
“没接就不能进去。”门卫斜看了母亲一眼,脸上的表情冷冽如万古冰川。
妈妈往后退了半步,她左右看看,仿佛想从陌生环境中找出一点佐证,证明她真的认识大学兼职讲师康明亮,是他邀请她来听课,不是她故意来胡搅蛮缠。
当然,除了周围朝气蓬勃的学生,妈妈什么都没找到。她自惭形秽地往旁边站了站,既想离开又怕误了康明亮的约——人家好心请她来见识未见过的校园,就这么走了,会不会太不识相?
我的妈妈一直都怕给别人添麻烦,她从门卫的神情里读到了不耐烦,这让她局促不安。想走的念头渐渐占了上风,事实上她已经悄悄侧转身,凭着她在体校锻炼十年的肌肉爆发力,她相信自己能在三秒钟以内跑过斑马线,跑到街的那一端,如同隔着一条河似的来看大学校门,也许这能大大稀释她的尴尬。
但妈妈听到了康明亮的声音。
“萍萍,萍萍。”他边跑边喊,后面还跟着他的两个学生。
他的亲密称呼让妈妈脸上有了窘色,伸出去的左腿定了格。妈妈名叫郑玉萍,她不知道康先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她的小名,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才好。她紧张地瞪大眼珠,看他吁吁地大口喘着粗气,离自己越来越近。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来了也不进教室。”康明亮先发制人。
妈妈口吃起来。她来这座城市时间不算短了,以前是体校学生,每天早上起床就没日没夜地练习铅球投掷。体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她又人生地不熟的,很少有机会去外面逛街,也很少和外人打交道。前两年受伤退役,她不愿回老家,留在这里打工,本能的畏惧一切身穿制服的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保安,她都怕自己哪句话不慎,得罪了人家。
郑玉萍嘴上不说,眼神却往门卫脸上瞥了好几次,康明亮当即明白,她是被当作“校外无关人员”遭到了拦阻。
要说门卫拦郑玉萍,也不算冤枉她,其实每天进进出出大学校门的男男女女那么多,门卫也只能选“可疑人士”拦阻。
为了来听课,郑玉萍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前胸后背的衣料上都有在箱子底压久了的折痕,她脸蛋黑红,手关节粗大,竟敢冒充听课的学生,这不是撒谎不打草稿吗?门卫自然要揪着她再三盘问了。
啪!康明亮生气地重重拍了一下门口放登记簿的长条桌,桌上的签字笔受到震动,滚落脚下。他指了指郑玉萍,又冲门卫嚷道:“看清楚,这是专程来听我讲座的,我朋友!”一秒钟后,他又以更响亮的音量补充道:“我女朋友!”
妈妈曾对最要好的小姐妹说,她就是从那一刻起,爱上我爸康先生的。
(节选自2024年第1期《芙蓉》中篇小说《童话城堡》)

杜阳林,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成都女报》总编辑;作品见于《十月》《收获》《中国作家》《作家》《湖南文学》《海燕》《大家》等期刊;著有《惊蛰》《山岗》《长风破浪渡沧海》等长篇小说和散文集。
来源:《芙蓉》
作者:杜阳林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