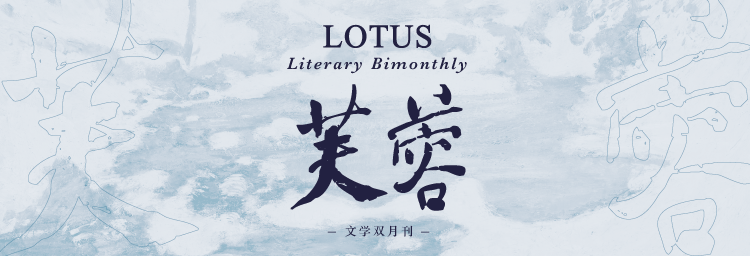

鲸骸(短篇小说)
文/章程
我快要死了。夏多布里昂写过:“在我年轻常犯错误的时候,我常常希望幸福了就死,因为在最初的成功之中有一种至福,使我渴望着毁灭。”如今我相信,我已经无限靠近至福,只要走近,再加上一把火就够了。关于这一生,我谈得够多了。1940年我出生于越南的西贡——后来改称为“胡志明市”。当时的越南属于法国人,被视为“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我在西贡住了十八年,而我父母——他们来自布列塔尼半岛西端的布雷斯特,却在西贡度过大半辈子。1983年,我父亲在那里离世,他去世一年后,母亲也去世了。我成年后去了法国,他们留在西贡。他们给我留有的印象,是由众多重叠不明的记忆组成。这些记忆总是与西贡这个地方相勾连,每当我想起西贡,太阳直射下的光焰就会令我头晕目眩,白色的阳光在我身体上蔓延开,与之而来的喜悦与忧愁都被蒙上一层云雾。我一直不知道西贡岁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很多年后,我才认清自己那些隐秘的情感滥觞于此。回法国后,我在布列塔尼的一所建筑学院学习。在越南,我是白人;回到法国,我是越南出生的法国人。但这种边缘的状态,倒使我保持着理智——人在中心时会怀有幻觉,并总在索取更多的东西。我所有非正统的观念都来自边缘。至于我为何会选择读建筑,则和那个一直侵扰着我的幻影有关—— 一副白惨惨的骸骨。我觉得它构成了建筑,准确说是教堂。它在记忆中庞大得近乎不真实。可事实上,供奉它的寺庙不可能那么大。有时,我会怀疑是否真的见到过它——记忆总在说谎。在讲述它之前,我该说明一下我们一家在西贡的状况。我父母是西贡一所中学的法语老师。与大多数房子类似,中学的教学楼也是平房,瓦屋面,简单却坚固耐用。小学毕业后,我在那所中学就读。白人身份给我带来特权,但并不使我感到开心。那些越南的孩子能察觉到这种权力,所以他们对我总带着畏缩的忸怩不安。同时,我自幼的哮喘病也让我囿于孤独中。真正把我当朋友的是一个叫永吉的少年。永吉总是面容忧郁,站立时像一柄刀子,身形像刀刃一样单薄,脸和脖子留着热带的茶褐色,他笑起来时会露出发黄的牙齿——好似那些吸食鸦片者。他是渔夫的儿子,通水性,熟悉附近水域。他法语说得很好。我十五岁的夏天,他邀请我沿河而下。我对此盼望多年。直到如今,我还深信湄公河是那片土地上柔和、低回的皱褶。后来,西方人来了,在棕褐与暗绿之中加入张扬的银灰、柠檬黄和粉红。古老织毯上的颜色变得斑驳,并且它脱线、走样,被粗糙地缝入不同织物。(整个世界都在褪色、变旧和霉烂。)我在家中听到一声口哨,便知永吉到了。我们先去他家取船。那日,天空清澈明净,天边点缀少许的云,树叶被气浪托起,颜色忽浅忽深。永吉家安在与河流相连的湖泊上,是用木桩支起的房屋。水面银色斑斓,闪烁着白铁皮般的粼粼波光,河两岸泛出银针似的白光。永吉每天出门打鱼,以有限的渔获维持生计。他身上有一股鱼腥味,生活在水上的时间比在地上更长。推开门,吊扇发出并不悦耳的、古怪沉闷的咔嗒咔嗒声。等目光适应并侵入这晦暗,我才看清墙角的竹篾凳上蜷缩着的人——他驼背弓腰,蓬乱的铁灰色发绺下两颊深陷,下巴胡茬黑白错杂,脸上有备受折磨的神情,让人感到他正在承受某种莫可名状的痛苦,或没好好睡过觉。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沮丧阴郁。在这凌乱拥挤、光线昏暗的房里,冷战从我脚底升至头顶,惊恐涌进全身。许久,我才意识到内心恐惧的原因——男人的一条裤管空荡荡,他缺了一条腿。永吉说这是他父亲。我和他打招呼。他抬了下眼皮,打量着我。他的强烈注视让我并不舒服,我莫名想到沙漠里伏击猎物的蜥蜴的眼睛和闪烁开合的眼皮。他收回视线,垂下眼帘,继续埋在黑暗里。永吉走过去和父亲说话,我听不懂(但我能听出男人语调里的疲乏和不快)。他把瘦骨嶙峋的手一摆,像在说“去吧”。他如一团烟雾一样逗留在那里,在我的记忆里成了一个没有形体的梦游者。里头地面烫脚似的,我们没有久待,迅速走出屋子。燠热、明亮的风里,有一股盐分和青草混杂后的味道。
我们跳上船。船上装的老式发动机哧哧发响,噪声很大,排出浓烈的烟气,冒着滚烫的蒸汽。草木蔓生,长得贴近河岸,树根因河水冲刷而外露。有不少地方,河两岸的枝叶快碰到一起,河水费很大气力才将这片密林剪成两半。两个影子待在水里一起一伏。影子碰到了树。影子又离开树。影子始终等待着我们。水面上阳光闪烁不定,像浮着一只只黄蚂蚁。思绪从这些黄蚂蚁中逃逸出来后,我听见这片暗绿的汪洋中雨蛙家族互递潮湿的口信,嗅到泥土散发的腐殖质的气息。这是一片天神尚未雕琢过的荒地,有巨大肥力,倘若撒下种子,抽出的植株会疯狂生枝长叶,而永远不会结果。这里没被香蕉林和芭蕉林攻占,一切热切而明亮。途中,永吉告诉我,他父亲那条腿是在一次捕鲸时发生意外失去的。那次,父亲独自出海。意外的发生多少和母亲离去有关。母亲离开的清早,他和父亲没察觉,但一些例外提醒着他们生活已生出突兀的块茎,比如母亲的衣物从衣柜里消失。那日下午,父亲呆坐在敞开的衣柜前,他本就不爱说话,之后很多天里,他一言未发,一根又一根地抽烟,每餐吃得很少,很快就瘦得脸颊凹陷。等他终于出门,那件灾祸随之降临。(而今,在我七十二岁的年纪,又想起这个画面:一个坐在衣柜前发愣的男人,他的灵魂被嵌入其中的懊恼锈住,记忆像灰白的墙皮般一块块剥落。他一定察觉过更多蛛丝马迹,一个人不可能就这样消失,所有的消失必有马脚。那些细节如此隐蔽,多年后,人才会在某一个瞬间恍然明白,继而山崩地裂。)永吉还说起他父亲是标枪手,离危险最近,发现猎物后得投掷标枪刺向猎物,有时须跳到空中才能瞄准位置。捕获后,他们将其拖到岸边,割鲸脂,鲸脑油(由抹香鲸身上获得)用作药剂,鲸肉被腌制后风干。运气好的时候,能得到鲸的内脏分泌物,制成龙涎香。他说起这些时,低垂着一张通红的、淌着汗的脸,偶尔挺直脊背,遥望远处。对面驶来独木舟,船上的人惯于一只手握桨,不时腾出一只脚往后拨桨。他和渔民们点头致意。相遇的船只愈少,我们就愈接近河下游,直至水上杳无一人。永吉关掉小船的发动机,我们躺在船中,任其漂动。阳光消失,河面如汞液一般沉滞。树上的猴子让树枝颤动,沙沙作响,噪鹃的叫声穿梭于连续蛙声与蝉鸣中,我却感到寂静像涨水一样,在四周涨高了,几乎要漫过我们。天际的云移到头顶,天空被乌云鼓得臃肿。刮起了风。风啸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癫狂的叶子形成一个个暗绿色旋涡。河水起伏,如筋脉张翕搏动。要下雨了。正欲返回,如注暴雨砸下,气势磅礴,海芋的宽大叶子要被摧毁得粉碎。靠岸,系好船,锚链颠簸轰鸣。雨来势汹汹,如无数堵水墙。我们脚踩黏滞的烂泥,奔到树下。雨填塞进树与树的间隙,树干相互击打。在越南,似乎每天傍晚都会来一阵雨。雨停后,灰色水汽从地表分离,袅袅上升,散发淡淡的沼泽味——这是雨后大地的呼吸,凝滞的天空又变得明亮,阳光穿过云层,灰蒙蒙、潮滋滋的林木间落满闪烁的光点。往密林深处走去,地上草叶软烂,一被踩就能渗出水来。荆棘乱树挡住去路,叶子簸动不止。越南的蚊子很多,林间更是蚊虫肆虐,如一团团黑云环绕我们。路愈来愈窄,树冠层层的叶子筛走阳光。我正思量着得用身体勉强挤出路来,却见永吉如认得那些草木般轻轻一拨,出现一小径。小径两旁立着高高低低的木雕,颜色发黑,是一群猴子,很像人——而且的确有着人的凛然神色。它们眼睛的位置被点上黑色,但颜色已经很淡,显得眼神空茫,好似拥有强烈个性的人被时间抚平固执与严厉。我与那眼神相撞时,内心依旧陡然一惊。它们仿若看穿了我的一切——血液、内脏、骨头,以及记忆(甚至是那些在成为我记忆之前就早已存在的记忆)。我的一生不曾被任何人审判过,除了这群猴子。它们在那个时刻掌管了我的心灵。小径固执地通向一座几近一半被藤蔓和杂草包覆的寺庙,它已荒废,但未倾圮。暗绿色的琉璃瓦上长满了草,屋脊兽隐约可见。这并非古寺,基座上缀满马赛克(尽管长满霉斑),挑檐深远,门扇破成大洞。此寺虽为五开间,挑出檐廊那一跨的中间抽去二柱(它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抽柱较之于古建更容易),显得入口气派。步入寺内,屋瓦多处崩落,但水泥浇筑成的骨架仍旧完好。案几上有三尊鲸鱼的泥塑像,香炉、香烛均已倾倒,败落已久。案几前为一副鲸的骸骨,骨头大概经过抛光打磨,色泽偏黄,却将极强烈的亮光打到我眼里,好似有暗藏的刺人荆棘或是钢针扎了我。永吉说,这是虎鲸的骨架。我头一次见到鲸的骸骨。无形之物化为实体,高深莫测的潮汐冲击向心脏,令我无法言语,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充满兴奋与恐惧。永吉说,海在不远处,给鲸建的寺庙一般位于海边,为方便埋葬鲸。穿过林子便是海。沙子洁净。空气黏黏的,如一大群鱼在空中游动。黄昏的海水混杂绛红、蓝紫和灰黑。色彩在海面上燃烧。我说,这个国家很奇怪,一些人崇拜鲸,视之为神,另一些人则以捕鲸为生。黄昏被消磨后,夜晚将万物的色泽和形体逐一吞没。(坚实的形体消融,高耸的林木沉没于薄薄迷雾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在夜晚的洪流中幸存。)我们决定返程,没由原路走,而是沿河找到停泊的木船。发动机重出声响。永吉说起他母亲是和一个白人离开的,据说有人在河内碰见过他们。我看不清他的脸。他嘴里发出一种声音——大概是当地小调。我听不懂,但能察觉出里头有一股幽默而顽强的力量。我们昏沉沉,不再能找出一句话来表达情绪。我们把词语忘了(词语为什么会遁隐而去?),放任沉默自然地横亘在两人之间(我们之间的空隙如此宽阔)。河色变暗。月亮停在树丫间,像银鳞斑斓的鱼。远处点点灯火,起起落落,明灭不定,如无形中神在编织一张悬浮的网,抑或一袭幻影。穿过幽暗的林莽与半流体状的光线,似乎命运登上了这条在水上颠簸的小船,而我们将这样漂去,直至尽头。三年后,我去法国读大学。我最初认识的法国人、受的法文教育,都是在越南,当我抵达法国,仍把法国看作是越南,只不过这个越南没有肆虐生长的热带植物,以及潮闷的季风雨,克服了泥泞、混乱和贫寒罢了。那副鲸的骨架和我最终选择以建筑为志业之间,究竟有多少关联,我不清楚。但我时常想起那个寺庙,它对我而言意味着某种更本质的东西。现代派建筑理念在学院占据上风,偏好几何形的居住规划,认为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将神秘性剔除在外,认为可以找到某种国际化风格。我对其反感并保持怀疑。但这种错误理念中仍包含一半的真理,我相信有某种普遍性的存在,只不过它并非外在的风格,而是在表象深处。我的这种想法恰好和战后法国大学里的结构主义的观念相符,后者以其宽广的空间吸纳我的心灵。我沉醉其中,看待事物的眼光也发生微妙转变,纷繁复杂的表象开始呈现出一致的、可辨认了解的结构,好比地貌景观再复杂,再混乱,底下的地质演变总是有迹可循。来到法国,反倒让我有无根的漂泊感。
(节选自2024年第1期《芙蓉》短篇小说《鲸骸》)

章程,笔名一点儿乌干菜,小说作者,建筑师。生于1993年,浙江金华人。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生。已出版电影随笔集《我还未读懂漫山白雪》。小说作品见于《天涯》《莽原》《特区文学》等文学期刊。曾获第二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铜奖及特别奖。
来源:《芙蓉》
作者:章程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