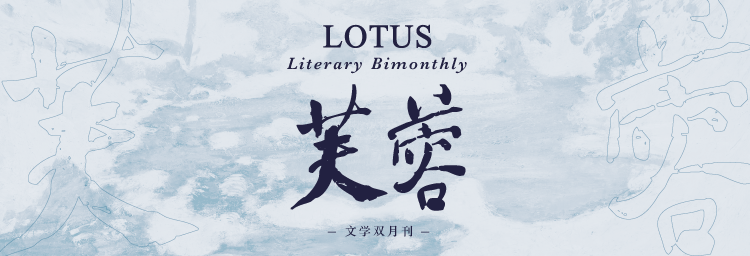

茶韵三叠
文/杨代漳
香韵
春夜月下,沏上一杯明前茶。
月光如水涤我身,茶水如月净我心。恍惚间,只觉得两片肺叶已被翡翠般的茶水染成绿叶,渐渐,连思绪也绿了,绿成一片片关乎茶亦宛若茶的意象。
解构茶字,为草、人、木次第组成。人在草木间,那是天人合一的意蕴,那是人与自然的互相包容亲近。拥有一杯茶,似乎便拥有一份忙里偷闲的洒脱,一份知白守黑的淡定;似乎就能屏蔽红尘,赢得一份融入天然的心情。茶泡杯中,仿佛心也泡在其中,茶香心亦香,茶甜心亦甜,茶苦心亦苦,但无论香甜苦涩,都不乏一种相互品味的陶醉。可不?茶以气息如兰的嘴与人频频亲吻,不正像相知相悦者彼此慰藉温存?“从来佳茗似佳人”,这位不着脂粉的“佳人”则常常伴随夜读。我疑心古代文人津津乐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其香,该是三分之一熏香、三分之一体香、三分之一茶香吧。
茶之香,与生俱来,先前为春雨滋润而绽放新香,随即缘文火烘烤而浓缩清香,而后赖沸水浸泡而徐吐醇香。于雨中可谓前世,于火中可谓涅槃,于水中可谓复活——这就是茶香三部曲,一个简短而精彩的轮回!
四十多年前,身为知青的我,曾在“湖南屋脊”壶瓶山旁的东山峰种过茶。那是一片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地,终年云遮雾绕,最宜茶叶生长。若干年后,每每忆起云雾缥缈的茶山,我便极易联想到朦胧诗。那一行行依次而下郁郁葱葱的茶丛,不就是写在大地上的绿意朦胧的诗行?此刻,茶山的朦胧意蕴和氤氲香气,分明已浓缩在绿叶浮动的茶杯之中了。
月下独饮,兀自怡然,暂无呼朋唤友的念想,倒有举杯邀月的冲动,直欲拿茶当酒饮了。有人说:“雅士饮茶,俗人饮酒。”此言未免失之偏颇。自古以来,香茗与美酒似无轩轾之分,应在伯仲之间。要不,人们怎么会将茶具酒具混用,既当茶壶茶杯茶碗茶盅茶盏亦当酒壶酒杯酒碗酒盅酒盏呢?茶与酒,如同孪生,其状其质,与水皆有血脉之亲;其香其性,与人皆有知己之缘。只不过茶为新芽所制,可谓浓缩的春;酒为五谷所酿,可谓浓缩的秋,于是乎茶酒之香也便有了春秋之分:茶香淡雅,酒香浓烈,类似春兰吐芬与秋桂飘香;茶香宜独处静品,浮动于私密空间;酒香宜朋侣共赏,横溢于喧闹场合;茶香沁于心,酒香爽于口;品茶香不畏其味苦,品酒香则忌讳一个苦字;茶独饮可渐入佳境,酒独饮则易陷入“借酒浇愁愁更愁”的陷阱;尽管茶酒皆可醉人,然茶醉者似仙子,酒醉者似疯子。不妨套改古人的一句话:腹有茶香气自华。而腹有酒香呢?往往酒嗝连连话自多,且酒后之话,真言乱语掺半,大话海话连篇,又多为粗声大嗓,分贝超标。如此比较,饮茶与饮酒分明可鉴雅俗之别了。
也许,茶饮之雅,可让人品悟出茶香有着异于酒香花香而近乎佳人体香的一种韵致。
诗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下饮茶,不能不发思古之情,油然想起颜真卿的月下饮茶诗:“流华净肌骨,疏渝涤心原。”寥寥一语,便写出书圣那千年不退的茶墨俱香的韵味。
步颜公之后写月下饮茶诗的自是不少,晚唐名相李德裕便是其中一位。有回他喜得蜀中名茶,借晓月初上沏茶独品,吟出“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的诗句,似乎满腹茶水,也能化作涌流数朝的诗思之清泉。我想,其宰相肚里,应撑着一叶叶茶的扁舟吧。大约肚皮让茶叶舟撑得豁达,方才应验民间的那句俗话。据说这位相爷还真有“肚里能撑船”的雅量。一次,他托前往京口公干者捎壶金山南零水泡茶。谁知此公健忘,办完公差乘船返至金陵时才想起来,且以为同是长江水,凡人舌尖未必连上下游都分得清,遂就地取水回去敷衍,哪料李德裕以水烹茶一尝即知。但他并未动怒,反倒调侃起来:“怎么南零的水变了?太像石头城下的水了!”足见其品茶功力之深、肚量之大与涵养之好!
无独有偶,宋代名相王安石可谓堪比李德裕的茶中仙,亦有相似的趣闻。他也曾托人汲烹茶之水,只不过是长江上游的西陵峡水。取水人乘舟东下,途中水洒了一半,只得在江陵补添。王安石沏茶一品便道其半是西陵之水半是江陵之水。如此品茗高手,联想到他那“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名句,不能不疑心其中最为传神的“绿”字,亦为绿茶水所染。
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说为王安石“贩假”的那人是苏轼,叫人难以相信,须知苏轼比王安石更嗜茶,品茶功夫更厉害,应该不会干出掺水作弊的蠢事(除非他有意以此试探王安石这位与自己政见相左的文人的品茶功夫)。苏氏与茶结缘终生,即使流放天涯也不弃不离:旅途上,“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入夜后,“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一觉醒来,“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简直是“宁可食无肉”,“不可一日无此君”了。他一生写过近百首颂茶的诗,《汲江煎茶》即为代表作:“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瞧,春瓮贮月,夜瓶取水,煎茶水似乳、泻时声若风,以碗饮茶润枯肠,坐听荒城长短更,好一幅怡然自得的月下品茗图!如果说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那么苏轼润嗓一唱,便有千年茶香。
然而,历代月下品茗诗似乎不如月下饮酒歌响亮,这是否与李白那几首《月下独酌》有关?其实诗仙并非只钟情于酒,亦钟情于茶,曾写下《答族侄僧中孕赠玉泉仙人掌茶》,相传为古人专题咏茶的发轫诗作。遗憾的是未曾见过其月下饮茶诗。我以为他一定写过,只不过失传了。
自唐以降,文人们大多既爱饮茶又爱饮酒,分明双杯并举。大约古代没有诗歌评奖活动,没人发什么奖杯,诗人们便给自己奖励茶杯酒杯吧。也许,文人们徐徐饮之在前,方能源源歌之于后,将茶水酒水化为低吟浅唱或引吭高歌,加之“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茶歌酒歌便更加滔滔如江河了。按风格分类,酒歌豪放,茶歌婉约。试以东坡为例,“大江东去”当是酒后豪唱,“坐听荒城长短更”则属茶余轻吟。
禅韵
纵观历史,文人雅士除了茶酒两大嗜好外,还有一爱,即喜佛好禅。李白早年好道,中年后却倾心于禅,在自己谪仙的名头上加了一个“青莲居士”的雅号。苏轼亦以“东坡居士”自号,更是对禅情有独钟。从教义上讲,佛禅与酒绝缘,却与茶自然而然地结下不解之缘。禅,原本就是西来佛法与本土文化联姻孕育的宁馨儿,文人墨客自然青眼有加。更何况禅宗主张修行不必非出家与读经不可,免却修行之苦,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方式,亦赋予参悟者超越思想信仰、超越尊卑与圣凡对立的空间。基于此,在现实中屡受打压而精神上向往自由的文人士大夫们,遂对禅有了偏好及趋同。他们并非皈依禅门,而是向往禅之意境、陶醉于禅之旨趣。其爱茶亦爱禅,自然将佛理禅意浸淫于茶香之中,将茶的意蕴转化为恬淡空灵的禅意悟境。茶禅结合,可谓唐宋以降中国文人传承的一种文化基因。不过,与其说文人们深爱茶禅,毋宁说这是他们对淡泊宁静的一种向往,对洁身自好的一种咏叹。在其心目中,茶是默咏的天籁,流播着音韵的清纯;茶是微型的画卷,描绘着山水的幽深;茶是绿色的诗行,掩映着意象的空灵;茶是心境的古寺,规避着红尘的纷争。从这一层面上看,茶与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茶,可谓文人雅士的绿颜知己;而禅,则便是文人雅士的梦中之人。
至于凡夫俗子,大多喜欢饭后一杯茶,仿佛茶可解读佳肴美味。宾朋来了奉茶一杯,仿佛茶已约定俗成地定格为人际交往时的见面礼。有人亦喜于笔耕案头备茶一杯,仿佛茶有如水浇地一般能催生灵感;有人亦喜欢于孤寂中以茶排遣寂寞,仿佛茶能营造出“无声胜有声”的情境;还有人在苦恼时偏用苦茶浇苦心,仿佛茶有“以苦治苦”的药用功能……看来,无论雅俗,都把茶当作万能之水。其实,茶哪有这般神奇,它只不过是人们将一种生理需求演绎成生活艺术的成功典范;品茶,亦是品味自我、品味人生。捧上一杯茶,细饮之,静思之,自我的阅历、修养、体验,都随着思绪情感渐渐地与茶融为一体。据此推理,可谓百人百茶味。然而茶究竟何味?香甜苦涩,仅是舌尖味蕾浅尝辄止之味,只有用心去深深地品味,茶才会赋予你独有的几近禅意的况味。如此一来,品茶便真的有点像参禅悟道了。难怪古代高僧云:“茶禅一味。”
寺庙僧人饮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举足轻重。僧侣们可以说是茶文化的传道士。基于茶有醒脑、消食、抑欲“三德”,有利丛林修持,为僧人们参与种茶、制茶、饮茶进而精益求精的实践提供了原动力。因此,天下名山寺占多,亦天下名茶寺出多。西湖龙井、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黄山毛峰、君山银针等名茶,无不出于僧人之手。曾荣膺宋代贡品的夹山牛抵茶,我疑心其十有八九为夹山寺僧所创。当年夹山开山祖善会于品茗中顿悟“茶禅一味”。后有宋代圆悟住持夹山,将“茶禅一味”的理念注入宗门第一书《碧岩录》。此书日后东渡,开启日本茶道的灵光之门。以茶参禅,似是禅宗僧众自创的不二法门。千百年来,茶水不知滋润了多少佛旨禅意、偈语梵音!绿茶、黄卷、青灯,几乎成了涂抹僧侣人生的三原色,从而水到渠成地为“茶禅一味”提供了原生态的文化语境。
“茶禅一味”虽源于佛门,却流芳俗世。生活中几乎处处有禅意。“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潜形于柴米油盐里,隐身于青山绿水间。难怪最早对禅做系统诠释的南朝高僧慧皎说:“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或许,正因为禅“妙万物”且“茶禅一味”,与善会同时代的赵州和尚便用“吃茶去”的三字禅开导众僧徒及善男信女。看来,“吃茶去”不失为“茶禅一味”的一种通晓版本、普度众生的一种便捷途径。
禅是什么?古禅者曰:“不可说,不可说!”当今某昔日神童遁入空门后,以其慧根性悟禅多年,竟得出这样的结论:禅,什么都不是,而又什么都是。
禅究竟是什么?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禅亦千人千禅:高僧有高僧禅,小徒有小徒禅,贵人有贵人禅,平民有平民禅,雅士有雅士禅,俗子有俗子禅。如此推理,一千个饮茶者,即有一千种禅味。
无疑,月下品茶的我,自然也品出了一己之禅味。窃以为:禅是精神茶,茶是物质禅,而月呢,则像一位端坐天庭的参禅者,正以大彻大悟的平静细品“茶禅一味”。
月儿渐渐西沉,依稀沉入半杯绿茶水中。只不过,它沉而不醉,伴随着我慢慢地饮尽了这一杯。茶尽了,然思绪未了。品茗,原本是想求得心境安宁,却反被激活浮想,唱起《茶韵三叠》来!

杨代漳,曾用名章弋,二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湖南省常德市文联原副主席,石门县文联原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眼睛与黄金》《1947上海黄金风潮案》《李自成秘史》,电影剧本《仇中仇》,电视剧《血染金皇后》,戏剧《白喜变奏曲》等作品共计四百万字。曾获田汉戏剧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杨代漳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