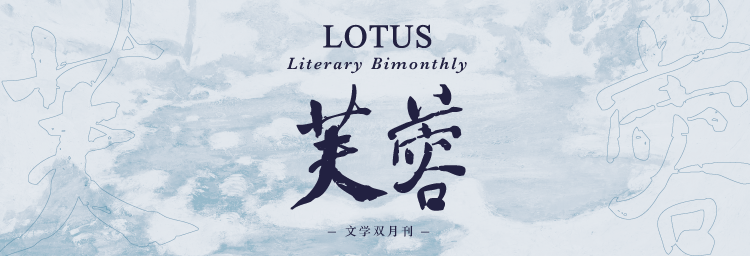

心灵是不需要通行证的(中篇小说)
文/夏天敏
村长在门口喊成志、成志,你去把我圈里的粪起了,挑到村口菜园去,再兑上水,把菜给浇了。成志正在穿衣,忙说要得,我烧点洋芋吃了就来。村长说吃啥洋芋,你不会浇完再吃。成志说要得,我马上就来。成志听见村长脚步声走远,低低说浇个干鸡巴,我成你家长工了,昨天才帮你家挑完谷子,今天又要起圈挑粪,老子连自家的地都还没挖哩。
尽管心里一万个不乐意,他还是挑上撮箕,拿起板锄准备出门,娘在里间说灶上有煮熟的洋芋,你吃两个再去。他进灶屋抓了几个洋芋装在兜里,手里拿着一个边吃边走。到了村长家,村长老婆正提着尿罐出来,说来啦成志,圈里的粪堆拢门槛脚了,两个猪半边都陷在泥粪里了,你快点把粪起了挑出去。说着转身进屋了,也不问他吃过东西没有。
村长家喂着两头肥猪,这在村里是少有的,那年头不许多喂,一家一头喂着自己吃,还要交一半给公家,即使准喂也喂不起,人都不够吃,有多少粮食喂猪?家家的猪都是大人下地回来顺便扯点猪菜,或者是娃娃些背着背篓到田边地脚找些野菜扯点猪草,就这样猪也吃不饱,家家的猪都瘦骨伶仃,眯闭眼倒的,唯独村长家的猪,又白又胖。年关将近,这猪每头都快两百斤了吧,躺在地上哼哼。成志见猪食槽里有没吃尽的苞谷粒,漆黑里像一粒粒金子在闪光,成志想狗日家的猪比人过得好哩,换了别家谁会舍得给猪吃苞谷粒变猪也要在他家才好哩。
费了好大劲才把两头猪弄到院子里,成志开始起粪。村长家的猪圈很长时间没起粪了,厚厚的一层,猪粪猪尿猪食混在一起,泥泞腥臭,脚都下不去,成志估了一下,恐怕有二三十挑,今早都怕挑不完,大半天时间就泡汤了。村里今天放一天假,让大家去赶赶场,做点家里的事。都近一个月了,村里忙着各种事,好不容易放个假,又被村长喊来帮他起粪锄圈。
也罢,既然推脱不掉,就使劲干吧,争取早点干完,去赶一下乡场,成志也有很长时间没去乡场上了。乡场是农村人的聚会之地,乡场上人山人海,有各种各样的摊子,有虽然不算丰富但也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日用品,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是自留地里的,换点零花钱。成志的头发有几个月没剪了,实在太长,他拿剪刀对着镜子剪,剪得狗啃一样,实在太难看。他已经十六岁了,知道爱美了,想去乡场上的理发摊好好地剪一剪。另外,他还想去乡场上的供销社买点书,乡场上只有供销社有个书柜可以买书。他喜欢读书,买上一两本书,又够他看上一阵子。乡场热闹,四乡八里的乡亲都来赶场,赶场对他们来说像过节,总要穿干净点、齐整点,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再怎么拮据,总要把衣服洗净熨平,收拾打扮一番,像去参加什么盛会。十六岁的成志还想看看她们,也不为什么,就是看着舒心。他不像其他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看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眼睛直勾勾的,还追着人家看,厚脸实皮地去搭讪,无话找话地搭白。他会看一眼,赶紧把头扭开,如果人家也看到了他,他会脸热心跳,就像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他还要为娘买药,这些日子娘的哮喘更严重了,喘得不行。
成志狠起劲地挖,狠起劲地挑,但他还是快坚持不住了。他干得太猛,也不会休息一下,只想早点干完能去赶下乡场。出力大肚子饿得快,他在地头掏出怀里的几个冷洋芋,急忙吞下去。出力大,洋芋不扛饿,虽有点饱胀感,但挑了两挑肚子又咕噜咕噜响起来,他的动作慢下来,身子疲软,手脚乏力,挖一下就要停顿下来。他正是吃长饭的年龄,平时几大碗苞谷饭、一钵洋芋酸菜汤,他风卷残云呼呼呼就吃下去,这时他多么渴望能热乎乎地吃上一顿饭呀。
村长家堂屋里传来一阵香味,是面条和鸡蛋的香味,面条他很长时间没吃到了,面条是稀罕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生病时才吃得到,面条那特有的面香味深深地吸引着他,让他的肠胃迅速地搅动起来,他觉得更加饥饿难耐。更要命的是还有煎鸡蛋的香味,那种香味像无以计数的小钩子钻心入肺,钩挠得他清口水直流,饥饿感更加强烈。这时他听见一个女的在说:妈,叫成志来吃吧,干了一早上活,他怕是饿了,我听挖地声音也软了,有一下无一下的。另外一个女的说只有你会说这种话,咋个可能叫他来吃,这是鸡蛋汤面,你以为是洋芋红薯,就是洋芋红薯,也要留着喂猪哩。说的声音低,他还是听到了,他听了像被从头到尾淋了一桶凉水,透心凉。但很快他就平静了,不再为此话伤心难过,只是有种巨大的屈辱感,感觉他在他们眼里连猪都不如。是啊,谁叫他爹是盲流,跑出去几年了,听说是到新疆或是内蒙古了,但从来没和家里联系过,也没寄过一分钱。盲流不是犯人,但盲流是介于犯人和好人之间的一种人,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村盐碱地多,水少不说,还是咸的,地里庄稼永远是半死不活蔫头耷脑的,收成极少,穷得连个地主都有不起,村里开会连个批斗对象都没有。后来有人说爹跑儿子在,把他拿来顶他爹。村长说他爹是他爹,他是他。他又没跑,再说他才十来岁,还是娃娃呢,有啥批的。
村长有些怜惜他,孤儿寡母日子艰难,村长又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个小兔崽子,我不保护你,队里每晚都要开会,不把你斗死。你又是盲流子女,喊你干点活是看得起你,别人巴结都来不及呢。的确如此,村长虽小,但全村人的“生杀大权”都掌握着呢,派人出工,让你去哪块地就得去哪块地,地有好坏、远近,有难挖的有好挖的;活路有轻有重,有脏有臭,都由村长安排。就是记工分,也有猫腻,尤其是粮食分配,更是一件大事,保管室的粮食,村长可以独自支配。就连出趟门,譬如去公社上也就是乡场上,没有村长准假,没有他开的准许证,你是去不了的,更别说县上或其他地方。一张准许证就把你牢牢地拴在原地。
村长的女儿赵琼华说人家干了一早上活,就是牲口也该丢把料,况且人家干得那样实诚,从来到现在汗都没擦过一把。她妈说你这个小蹄子,你怕是看上了他吧。我告诉你,他家是盲流,你莫打错主意。女儿说妈,你说些啥呀,雇个长工也要给吃的,你比他们还抠呢。一个小男孩说我姐脸红了,她准是看上挑粪的那个了。闭嘴,再说我撕烂你的嘴。屋里传来奔跑追逐的声音,小男孩求饶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村长老婆端着一个盛着煮洋芋的小簸箕,里面是刮了皮的黄澄澄、冒着热气的洋芋,还有一碗烧青椒。村长老婆说来吃吧,吃了好干活,这是新洋芋鲜辣椒哩,我们都是第一次吃哩,成志内心一阵反感,嘴上说我吃过了哩,赵婶。村长老婆把装洋芋的簸箕往地上一放,说叫你吃你就吃,还啰唆啥?说着扭身回去了。成志委屈极了,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这不是跟赏赐猪狗一样吗?他还没吃,院里的几只鸡就跑过来了,围着簸箕啄,把洋芋啄得烂翻翻。
赵琼华出来把鸡吆开,说瘟鸡些,这是人吃的,你们倒是不客气哈,连拌青椒都啄了。又说妈你也是,你不会抬个凳凳来把东西放在上面,这不,成鸡食了。她妈说人家不像你讲究,放在地上蹲着吃有啥不好,快些进来把这盆衣服洗了,还要去赶乡场哩。赵琼华反身进屋,左手拎着一张小方桌,右手拎着一个小凳子,又把地上的洋芋和拌青椒拿回去,重新换了拿出来,看着他,说我倒水给你,来洗洗手吃吧。说着又去抬了半盆凉水,还从热水瓶中倒了些热水掺进去,又拿来香胰子。成志呆呆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赵琼华说发啥呆,洗手都不会,还用教你。说着看他一眼,那一眼是热辣辣的。
赵琼华是村长赵顺章的大女儿,中等个儿,胖墩墩的,脸色红润,腿和胳膊都挺粗,就是眼睛是眯眯眼,和她阔大的脸有些不协调,鼻子还可以,虽然不高但圆润,但她的嘴又有些瘪,这样一搭配,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她和成志年龄到底谁大,成志也搞不清楚,他俩小学都在村小读书,从来没讲过话,成志自然不知道她的情况。
成志是真的饿了,他手脚疲软,肚里空空,不吃东西真的干不起了。他也顾不上洗手,抓起洋芋就吃。那洋芋真好,又大又糯又沙,还刮了皮,不像他家的洋芋永远是毛皮洋芋,又小又水,从中间咬一口,两边的顺手丢给猪吃。他吃得又快又狠,一是饿了,二是太好吃了,一会儿就吃去半簸箕,噎得他眼睛翻白,连连打嗝。他有些恨自己的吃相,这不是丢人吗?可他的肚子不争气,一个还没吃完又抓起一个。
赵琼华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瓷杯黑漆漆的,一看就是她爹用的,茶垢老厚。她说慢慢吃,又没得哪个挨你抢。她看着他,说吃嘛,还不好意思。他说真不好意思哩,让你见笑。她说吃东西有啥不好意思,我饿的时候,吃得比你难看。她妈在屋里喊人家吃东西有啥好看的,快来洗衣服。
吃完一堆洋芋,成志感到身上又有了力气,年轻真好,成志虽然只有十六岁,但体格健壮,身材匀称,长年的劳动让他手臂、胸肌、大腿都肌肉饱绽,很有力气。都说吃洋芋长子弟,其实洋芋的营养并不丰富,只是吃到他胃里就丰富了。他看看圈里的粪肥,只有七八挑了,挑完应该不会耽误去赶乡场。
还没挑完,村长回来了,村长背上背着一个长背箩,里面有一堆青绿葱翠的柏树苗。放下背箩,村长说路上遇到林场的杨场长,送我的。他说成志粪锄完了吗?成志说快了。村长见方桌上的簸箕空着,说你吃东西了吗?成志说吃了。村长说吃啥呢?成志说吃煮洋芋。村长说这就对了,吃了才好干活。
村长说吃完你去后山我家坟山把这些树栽了,记得带上水桶把定根水浇足。坑要两尺见方,两尺多深,要栽好保证成活哟。成志看看,树木有二十来棵,村长家祖坟大,有七八座,要栽完这些树苗,恐怕一天都不够。成志说赵叔,我想去赶一下场,我两个来月没去了,你看我这头发……村长说噢,多大个事,下次去吧。成志说我还有其他事哩……村长说啥事?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叫你干啥就干啥。成志说买书的事,想想忍了,说买书不是找骂吗?他说我还要给我妈买药,她的哮喘越来越严重,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村长说多大个事,她这是老毛病了,咳下也就好了,扯把草药熬点水吃就好了。成志无言,默默地担着树苗走了。
天空灰暗,朔风紧逼,四周的山野灰蒙蒙的,成志感到窒息得紧。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他看到队里的那头驴,眼睛被蒙了条布,不停地在磨坊里转圈圈,稍有懈怠,身上马上就被抽几鞭,困倦极了的驴又走了起来。他想他就是这头驴,被局限在小小的磨坊里,永远迈不出磨坊一步,磨坊外的蓝天白云、青山流水,以及更远的地方,是想都不要想的。他的心灰暗到极点,真想把那些树苗倒在地上,抽身就走。可他能吗?那看不见的鞭子,随时在他的灵魂里挥舞,他的脑袋嗡嗡地响,又朝前走去。
村长家的祖坟就在村子后面的山上,这个地方干旱贫瘠,尽是砾石,只有稀稀落落的荆棘,荆棘又瘦弱,一些干硬的枝条僵硬着一动不动。村长是相信他家的风水的,便栽下柏树,以佑他家庭永远兴旺。可这些柏树栽得活吗?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成志心烦意乱,他似乎听到了乡场上熙熙攘攘的声音,似乎看见了五颜六色的各种各样的摊子,听见了人们大声地打着招呼,都是好久不见的乡亲,声音里透着亲切,看见了街边蹲着喝转转酒的汉子,酒是最便宜的散酒,这是他们释放郁闷的最好方法,无论认识不认识,他们都要叫人家去喝酒,那种豪爽,一扫他们的卑微,放大了他们的尊严。他看见苍黄的人流里面有几点红的、绿的颜色,那是大姑娘和小媳妇,她们裹挟在人流里像浊黄的河水里的几瓣桃花、几片绿叶,她们使浊黄里多了鲜丽,使沉闷里多了新鲜。青皮后生眼睛不停地朝她们瞟,小媳妇泼辣,用话骂他们,大姑娘羞涩,虽然矜持,却也受用。
他狠狠地挖起坑来,山坡上的地又干又硬,一锄下去碰撞出一串火星,只挖出浅浅的一点表土。山坡上尽是砾石,俗称羊肝石,很难挖动,好不容易挖了一个二尺见方的坑,他的手臂又麻又疼,板锄也挖卷了口。他把板锄狠狠地丢在地上,想骂人,但又不敢。长期以来他就被压制得不敢随便骂人,有啥只能埋在心头,但他又憋得难受,他就长长地叫了一声,声音像狼嚎,像驴鸣,像马嘶,他想叫总不会犯啥错吧,那就叫,大声地叫,反正也没人听见,他啊啊地大声叫,这一叫一发而不可收,他叫得苍凉,叫得怪异,叫得撕心裂肺,叫得痛快淋漓。叫完,他呆呆地立在原地,心里一下空下去了,空下去后是无尽的迷茫、空虚、惆怅。
他望着迷迷茫茫的山,层层叠叠的大山之外是层层叠叠的云,苍茫的云边是一片虚空,有一抹金色的云,他想这外面是多么阔大,有多少不为他所知的东西,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多么想走出这像磨坊一样的地方,能像风一样轻松,像云一样自由,他不能成为被拴在磨盘上的驴,他要解开眼罩,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可他能吗?他从出生到现在,注定要被拴在生产队这磨盘大的地方了,不要说去外面的世界,就是到乡场上,都要生产队放假。平时出去必须村长批假,批了假还要写证明,否则,你就寸步难行。
板锄挖卷了,必须换成钉耙,钉耙是两个齿的,钢火很好,专门用来挖坚硬的土的。他想今天无论如何是挖不完的,家里就他一个劳动力,母亲走路都喘不匀,不忍心让她来帮,只有硬扛着挖完,哪怕挖到半夜,要不然不好开口向村长请假。
回去吃了饭,他又扛着钉耙拿着风灯来到坟山,寒风瑟瑟,荆棘萧索,坟堆凄迷,让人脊背发凉。成志年轻胆子又大,他想就是鬼也不会纠缠他,他无牵无挂,他怕的是活人,活人是可以决定他的一切的,譬如村长就可以让他在放假时来帮忙出圈、挖坑,村长可以决定他的一切,村长的一张字条,就可以让他出去或者不出去。
憋了一股劲,出了几身汗,人累得蹲在地上像狗一样喘气。终于挖完栽完,他想明天请假是没有问题的了。
第二天他去找村长请假,村长说请什么假,现在活路正紧,大家都去出工,你请假算啥事?他说昨天没去乡场啊。他本想讲是你叫我忙了一整天,但他不敢讲。村长说去乡场要写准行证,上面通知不能乱写,要控制人口流动,这准行证是好写的吗?他说我也没请过假,我不要工分行吗?村长说不行,不要啰唆了,赶紧出工。这时村里的小寡妇王银翠拿着个包袱正往村外走,他看了看。村长说看啥看,她娃娃病了要到乡场上开药。他咽了咽口水,心里那个憋屈、那种屈辱,让他十分难受。村长经常在晚上到王银翠家里去,有时提一袋粮食,有时提一袋瓜果甚至一刀肉,反正都是队里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讲。
今天的活是挖山坡上的地,这些地是最近几年开垦出来的,这是个缓坡,队里花了几年的时间垒了台阶,但尽是砾石,又缺水,庄稼长得稀稀落落的。挖地的时候很热闹,有的东一下西一下地挖,有的在讲荤笑话,有的在拄着板锄歇气,成志是实诚人,他看这样的劳动实在没意义,更谈不上有效益,反正都要出工,都要记工分,谁也没把地当一回事,他看了心里很失落,他卖力地挖,一会儿就把其他人甩下了。这时有人就说风凉话了,积极得很嘛成志,怕要当积极分子了。有人说好好干,村长家姑娘说不定就许给你了,她家缺乏劳力哩。有人说哼,干也白干,也不晓得自己是啥玩意。成志听着五味杂陈,家乡是这种样子,地是盐碱地,土里尽是碎石头,水又缺,吃的水还是咸的,队里出工做活就是这种样子,地不是自己的,做多做少一个样,分配粮食由村长说了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奔头呢?
天气晴朗,远山近水苍黄,山是砂石土,不长树木,有点矮树有些荆棘都被大家砍了,就连茅草也不能幸存,没有烧的,巴不得连树根草根都刨完,苍黄的山苍黄的水,看得成志心灰意冷,更主要的是人几乎没有自由,尤其是自己,村长说干啥就干啥,让你休息就休息,是村长家磨坊里的一头驴了。他好渴望到外面去舒展一下身子,呼吸一下空气,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由近及远,山峦渐行渐远,远处的山的影子模糊了,是清澄透明的天空。虚幻的天空让他心里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澄澈的,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外面的世界是迷幻和不可把握的,就让他更加向往。他太想离开这巴掌大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磨坊,他的行径仅仅是永远走不完的磨道,周而复始地转圈圈。
没有村长批的准许证,他就寸步难行。挨到下工,他匆匆忙忙地吃了饭,心中郁闷,想到河边走一走,尽管这条河几近干涸,水又浊又黄,但毕竟是河。他刚出门,去乡场上回来的王银翠叫住了他,王银翠说成志你去哪?我给你带了一封信。他很惊奇,怎么会有信呢?他和外面几乎没有啥联系,亲戚、朋友都没有,谁会写信呢?王银翠说在乡场上遇到一个人,问她是不是黑石凹的,说请她带封信。这人在膝盖上写了几行字,让她带来。
所谓信其实就是几行字,写信的人叫刘成才,成志的初中同学,邻村的,他们初中毕业就各奔前程了,听说他在家里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小子真有本事,现在到处都要证明,要路条,他居然有本事跑出去,他说明天来乡场上找我,我跟你讲讲外面的事。不要困在这里了,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不来你要后悔一辈子的。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他心旌摇曳,他被困得气都透不过来了,想想自己过的日子,他不免伤感,一头磨道上的驴,尽管没蒙上眼睛,但看得见的就是巴掌大的地方,不停地走,就是走不出这个圈圈。他太想走出磨道,但他不能也不敢,连去乡场上也被村长的一张字条阻挡,到外面去能行吗?他的父亲就是不甘于被困住,不甘于这死水微澜、痛苦不堪的日子而出走的,当盲流是违法的,是耻辱的,至今父亲也不敢回来。但他这个同学的字条,仿佛是阴霾遍布的天空中透出的一抹亮色,让他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不愿意就这样过下去,他要去见这人,了解一下情况。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他就要崩溃了。
他不敢拿那封信说事,只是向村长说他亲孃孃带信来说病重快不行了,让他去见最后一面,请村长写个条子准他去。村长正在吃饭,桌上有一碗炒洋芋片、一碗红豆汤、一钵红烧肉,很丰富了。村长喝着酒,说你的名堂太多了,你也不想想正是大忙季节,人都要死了见什么面,你也不想想你的身份,不准。他呆呆地站在屋里,头脑嗡嗡响。他说村长你家的地还没挖吧,我去挖。村长说不要你挖,巴掌大块地有人挖。成志说雨季要来了,我去翻翻你家的瓦吧。村长说刘木匠会翻,我答应他了。在村长眼里,给谁做是个面子,不是谁都可以去做的。
村长的大女儿觉得不过意,说你给人家一次机会嘛,成志没请过假,没急事他不会开口的。村长奇怪地看着她,说队里的事不要你插嘴,该咋办我有数。赵琼华说你不是批了王银翠的假吗?她能有多大个事?村长的脸一下青了,手里的酒杯猛地按在桌上,酒洒了出来。村长老婆知道话戳到了他痛处,再僵下去,可能要出现不可预料的事。村长老婆忙说你这姑娘也是,你爹他批那个有他的理由,当这个家容易吗?水里按葫芦,这里不起那里起,他有他的难处。赵琼华狠狠地斜了她妈一眼,那里面的意思很明白,她妈急忙扭开脸,但她心里五味杂陈,很是复杂。
成志决定冒一次险,他要在没有假条和准许证的情况下去乡场。为这个决定他折腾了自己半夜,他知道回来后村长会怎样收拾他,他也知道不是赶场天在街上闲逛会有啥结果。他纠结、彷徨、难以排解,最后还是敌不过外面世界的诱惑,他像在缺氧的水里憋了太久的鱼,就算抬起头会被一棍子打晕,他也要去试一下。
(节选自2024年第2期《芙蓉》中篇小说《心灵是不需要通行证的》)

夏天敏,云南省作协原副主席,现任昭通市作协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极地边城》《两个女人的古镇》及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多种,曾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万字,作品被选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及选本。曾获鲁迅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在国外发行。根据其小说《好大一对羊》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法、美、加拿大等国获奖,同名电视剧获飞天奖、金鹰奖。
来源:《芙蓉》
作者:夏天敏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