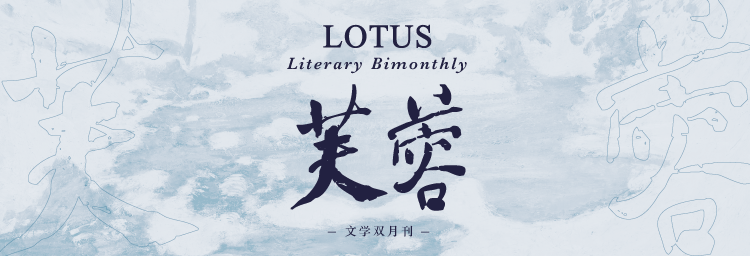

字据(短篇小说)
文/姜贻斌
1
我的堂弟叫张能干。
据我猜测,应该是我满叔特意给他取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干,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住脚。我满叔也许是想到自己这辈子不能干,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我堂弟身上。
先说说我满叔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满叔是乡村教书匠,为人老实、寡言、木讷。由于家庭成分,加上眼睛高度近视,被迫离开讲台,回家种田。
满叔视力太差,出工时频频闹出笑话。菜苗当作杂草锄,稻谷当成稗子拔,甚至连鹅鸭都分不清楚。他手无缚鸡之力,挑五十斤肥料还出气不赢,惹得村里某些人很有牢骚,说他好吃懒做。因此,细把戏们都看不起他,跟在他屁股后面大唱:聋子聋,听不到风;瞎子瞎,不分鸡鸭。村里人看他实在不适合出工,便让他看牛牯,满叔似乎这才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不然。满叔牵着牛牯走在田埂上,自己却经常跌落水田,弄得浑身泥水,狼狈不堪。瓶子盖厚薄的眼镜,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田野上经常响起满叔的求救声,桂珍——我眼镜找不到了嘞。桂珍是我满娘。满娘便像只鹅,急匆匆跑来帮着找眼镜。为此,满叔很有自知之明,叹息说,我没有用——我猜测,这就是给我堂弟取名为能干的由来。
——这些往事,我还是后来听我父亲说的,父亲也是听我姑妈她们说的。
2
这辈子,我仅仅见过满叔一次。
那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父亲去老家,在高沙镇落脚。镇上有我舅母——舅舅早已去世——其家境稍稍宽裕些。我们带来不少旧衣物,包括雨靴、棉帽、雨伞之类。父亲托人带信给我满叔,叫他到镇上来取东西。我老家离镇上仅十五里,父亲居然留在镇上不去老家。我不明白他不去老家的理由何在,是否因为满叔家境不好,父亲就不想给他添麻烦呢,还是满叔不想接纳我们呢?这件事情貌似简单,我却感觉到这里面大有文章。
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我们正在吃早饭——小镇上保留着吃两餐饭的习惯,上午九点左右和下午四点左右各一餐——这时候,舅母家的大门吱呀地被人推开,悄然进来一个男人。此人矮小,个子不足一米六,五十多岁,挑着黢黑的空箩筐,像个收破烂的老者。父亲叫了声国明,又对我说,这是你满叔。我赶紧叫满叔,却没有听到他应答,他也没有叫我父亲。我估猜,应该是回应了的,可能是他声音太小了吧。我打量他们,不由得感到疑惑,这两兄弟怎么相差如此之大?似乎不是一母所生。其一,他们五官不像。我父亲浓眉大眼,印堂光亮,耳朵软厚,一表人才。满叔的五官似乎没有长开,双耳紧贴乳突骨,鼻孔空空朝天,带着几分猥琐。其二,他们身材不像。我父亲高大魁梧,腰身笔直,像军人出身。满叔却极其矮小,手脚枯干,腰背佝偻。
我舅母问,你还没有吃饭吧?快坐下来吃。
满叔小声地说,吃过了。之后便再无言语,拢起双手,卑微地站在原地,低着眼睛望地上。
父亲说,你坐下来歇歇气、喝杯茶吧。我立即倒茶,给满叔递过去。
父亲一边说,一边把旧衣物装在箩筐里,又看一眼满叔,说,你喝茶。
满叔站在边上,摇摇脑壳,把茶杯放回八仙桌。满叔望着箩筐,看见一双长筒雨靴,眼神霍地一亮,脸上的皱纹也随之生动起来,像看见宝物。父亲终于把箩筐装满了,这时候满叔拿起扁担,也不知是对谁说话,我走了,声音像蚊子,竟然没有坐一下,也没有表达谢意,他挑起箩筐便朝门外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和伤痛,它像充气筒,哧哧地把我体内的每个细胞充满了。父亲跟我满叔几十年没有见面了,话也没有说几句,满叔甚至连哥哥也没有叫一声,便这样匆匆分手了,简直是惊鸿一瞥。况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满叔,还没来得及问候,他便悄然消失了。我认为,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意见吧,要不然,亲兄弟怎能如此冷淡呢,我却又不知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隔阂。
舅母说,哎呀,这个国明呀,肯定没有吃早饭。
父亲沉默着,深深地长叹一声,也没有说要去老家看看。作为晚辈,我也不便提及。
其实,我们要去老家真是太方便了。我们是开车从省城来的,父亲说要去哪里,还不是他老人家一句话吗?
——这就是我跟满叔唯一的一次见面。
(节选自2025年第2期《芙蓉》姜贻斌的短篇小说《字据》)

姜贻斌,湖南邵阳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左邻右舍》《火鲤鱼》《酒歌》、小说集《你会不会出事》《窑祭》《孤独的灯光》《漂泊者》等。
来源:《芙蓉》
作者:姜贻斌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