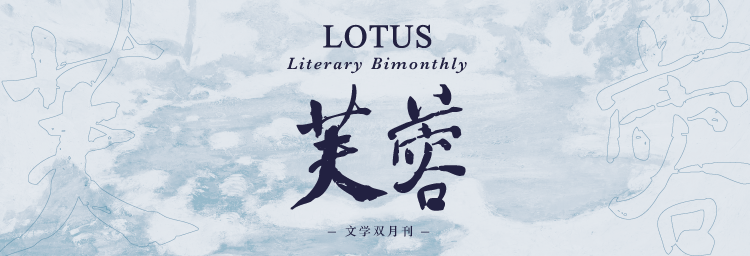

没有人容易死去(中篇小说)
文/朱秀海
暮色苍茫,但远天还残留着一道暗红色河流似的晚霞。车站上的灯亮了,却似乎只照亮了自己,人们凭肉眼还能看清楚车站上的景物。虽然先是动车后是高铁接连呼啸着从这片土地上经过,但是一列大大小小的车站逢站必停的绿皮火车仍旧慢悠悠地开过来,在这个名叫河口镇的小站上停下。车站上一整天都十分悠闲的工作人员忙乎起来,放不多的旅客进站,迎接车门打开后下来的为数同样少的旅客。
在今天所有下车的旅客中,一位老人很快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从看到她的那一刻起,每个人的眼睛都亮了。老人名叫石慧芬,早过了花甲之岁,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或早或晚,她总会来河口镇一趟,乘坐的也总是这趟过去编号1213次现在改为0997次的普客。知道她的故事的人也明白老人每次来这里必乘1213次或0997次的原因是眼下只有这趟车在河口镇这样的四等小站上经停,其他无论什么车都呼啸着开过来又呼啸着离去,火车司机连稍微减缓一下速度的事也不做,仿佛这个小站和小站里的人根本不在他们眼里,或者什么人给了他们权力可以对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视若无睹似的。老人下车的动作也总是一成不变:她会等到其他下车的旅客都走出车厢后才慢慢下车,还要在年久失修的站台上停一会儿。这时急着上车的旅客也全都上了车,下车的旅客大都走散,这时的她仍有可能停在站台上,前后左右地望上一望,像是每次来都格外稀罕这里的风景似的,要仔细观看一番。其实她每年都来,对车站包括河口镇周围的景物都熟悉得紧,没有这么一望也可以,但她还是要习惯性地这么望上一眼,仿佛有了这一眼和没有这一眼是不同的,有了这一眼,她对这座车站、连同车站下方的镇子都更有信心似的。是的,今年和去年没有变化。车站还在,车站下方的河口镇还在。这时老人保不住还会仰起面孔看一看天空,辨别一下她来的日子是阴天还是晴天,如果有雨,是倾盆大雨还是毛毛细雨,但不管什么雨,她都会把手边带的一把旧雨伞撑开,举上自己的头顶。也总是在这个时候,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开走,重新闲下来的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向她走来,和气地和她打一声招呼,表达一句虽普通却仍算亲切的问候:“石大姐,您又来啦?”“又来啦,又来啦。”老人嘴里回答着,眼睛并不看走过来问候的人,仿佛她的眼神儿越发不好,已经不大能看得清他们。当然这并不表明她对他们不客气,不会的,事实上她回答他们的问候时态度和蔼亲切,就像在和一年老也不见的朋友或者亲戚说话似的,这样回答好像有些失礼,其实不过是关系太过于亲近,有些熟不拘礼罢了。一边问候一边走过来的人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的,他们已经看到了,老人回答他们的问候时嘴角轻轻翘起,年老且有着更多皱褶的面颊上也浮现出了熟人见面时那种自然的和放松的微笑。“嗬,真好,你还是那么年轻。”一个调皮的年轻扳道工故意和她说笑。“说什么呢,不行了,老了,再过两年就要跟你们拜拜啦。”老人微笑着回答,目光投射的方向仍然不是和她搭话的人。细心一点的车站工作人员这时就会发现刚刚自己以为她下了车就在这里观察风景是错的,其实她一直都在眯细眼睛眺望车站下方的小镇,像是要在走向它之前给自己的内心一番鼓舞似的。接着他还会发现自己也许真的对了:有了这一番鼓舞,她像是有了勇气,开始挪动两条不灵便的腿,蹒跚着穿过车站不大开阔的出口,顺着一条去年刚刚铺上沥青的斜坡形的乡村公路一直走下去。
镇子离小站不远,半里路的光景,那是顶不住哪怕像这样一位衰弱且明显有病态的老人走的。虽说距离她和张小巧下乡插队到这里的日子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世事沧海桑田,外边的世界都变了几番模样,但在这位老人眼里,河口镇却和她们初次来到时看到的景象没有多大不同。不同当然是有,只是她对镇子太熟了,又年年回来,即便是房屋和街道全都变了样儿,她仍会觉得那不过是这一家或那一家又新修了临街的房子,这条街和那条巷子新铺了水泥路,安了路灯。变了样子的是局部,镇子本身却还是原先那一个,大格局没变,街道没变,东大街还是东大街,衙门口还叫衙门口(河口镇当年曾短时间地拥有过县衙门),马家后还叫马家后,马家后紧临的护城河还叫护城河。居民的成分也在变化,每年到来,她都会听说又有几个熟识的人过世了,但也总会认识几个新嫁过来的年轻媳妇,连同更多在大街上疯跑的孩子——但也不能说他们全是新面孔,从他们脸上她总是能看出他们是哪一家子的,孩子的爷爷或者父亲是谁,十个里头错不了一两个。耸人听闻的事情也有,保不齐她刚走进镇子,遇见第一个熟人,就能听到在过去的一年里,谁谁家的爹上吊了,谁谁家的闺女要上轿了头天夜里却跟一个唱戏的草台班子跑了,谁谁家的媳妇生了个儿子没屁眼儿,去省城医院开刀做了个人工的。要不就是半月前西小街上两条牤牛抵架,闯进赵大脸的酱菜店,把腌咸菜的坛坛罐罐全打碎,赵大脸的儿子抓住牤牛抵账,官司打到县法院,这会儿还没判呢。这些新闻老人听了也就听了,脸上会平静地现出一点笑容,她在河口镇也算是过来人了,知道这些就是镇上的平常世情,每年都会发生,多一件少一件的事儿。真要是哪年她进了镇子没听到这些新闻才了不得呢,那一准是发生了惊天大事。但这样的大事比较少,石慧芬一辈子也就经历过一回。

朱秀海,当代作家、编剧。河南鹿邑人,满族,1972年入伍,先后在武汉军区、第二炮兵和海军服役。两次参加边境作战。曾任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兵临碛口》《远去的白马》,中短篇小说集《在密密的森林中》《出征夜》,电视剧有《百姓》《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地民心》《诚忠堂》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艺术五十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等。《音乐会》入选“百部抗战经典图书”,《乔家大院》第二部入选2017年“中国好书”,《远去的白马》入选2021年“中国好书”。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海军通令嘉奖一次。
来源:《芙蓉》
作者:朱秀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