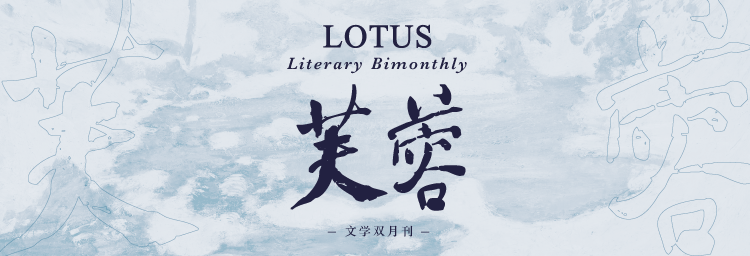

在“江南”的逃逸线上
——略说《古法》之“法”
文/何同彬
一
《古法》有迷惑性,或者说有一种智性的“伪装”,这需要从朱文颖与“古典”和“江南”的关系说起。
在2017年的一篇名为《抒情的逻辑》的文章中,朱文颖提到自己曾经为一个文学沙龙建议了《从古典叛逃》的题目,但被朋友否定了:“从现代叛逃,可以逃往古代,也可以逃往后现代,或者未来,或者不知所以未能命名的所在……叛逆古典太没劲了。因为太容易……”这段曾经启发了朱文颖的话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误区”——事实上,“从古典叛逃”并不容易。
近二十年,多少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从当代“叛逃”到古典,又在“古典”内部留下了更远的“叛逃”的轨迹。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就像艾略特给二十五岁以后还要写诗的人留下的那些重要的建议:“传统”不是继承得到的,“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它含有一种“历史的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中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朱文颖正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意识”——既来源于她生活的“江南”苏州,也来源于她的艺术实践中根深蒂固的“世界性”——才使得她始终凝视着她所栖身的“传统”“古典”“江南”,又坚定不移地建构着它们与“当代”的真实关系。但这种“建构”更像是一次次“逃逸”或“出走”,每每都在呼应着郜元宝对其创作的概括:“她的写作并不想树立一种观念,而在于解构某些观念的固化。”“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这是朱文颖很早就被评论界发现的地方性中永恒的“生长性”,而她在创作长篇小说《深海夜航》前后又培育出了沈杏培所说的“内心的猛虎”:“她近些年的散文和小说流淌着思想上的奔腾和美学上的新的哗变,一种反常规、对抗常识,甚至追求宏阔容量和极致美学的写作意图呼之欲出。”《古法》看似简净、平和,其实内蕴着某种“劲道”,或许就是所谓的“哗变”——一次发生在“江南”逃逸线上的哗变,一次新的“反常规”。
二
在《古法》中铺展着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朱文颖,比如“对情节的放弃和对气息的营造”(林舟),作为情感装置的“空间”(茶室、园子、天井等),充满弥散性的“江南”,男女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感纠缠……但这种“熟悉”只是构成了《古法》的表象,或者我前文强调的“伪装”,这是朱文颖小说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的小说里,人与世界的关系经常不是完全写实的。总有那么一点不太现实的东西在里面。完全写实,就会让我觉得慌乱,并且变得极为笨拙,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感觉。就像一条鱼被扔到了岸上。还有情感度,我发现小说中必须有种让我兴奋起来的东西,奇异的场景。人物之间不那么单纯的、不那么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关系。人物的处境也不是完全现实的。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和我们现实的世界肯定有差距。它是组合了现实的元素和审美元素、寓言元素的一个综合体,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一个领域。”《古法》非常精准地契合了朱文颖对小说的认知和创造,也呼应着她最为认可的一句话:写作不是指向事物的本身,而是指向它的阴影。
《古法》的轮廓是一个“古典”“江南”意味的轮廓(朴素、无相、风、虚空、轻盈等),读者很容易被这样一种氛围感诱惑,误以为这是一个为“古法”“古典”招魂的、指向清楚的小说,但我们一旦真正进入其肌理,就会被文本内部的碎片、褶皱、拐角形成的各种“阴影”导向眩晕、困惑,然而,这并不是终点。朱文颖深谙简·赫斯菲尔德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所提出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伪装”:“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精神世界中,这一课都意义深远:生存依赖一种亲密的、和谐的、相似的舒适感和伪装的艺术。”这种“伪装”“是创造性洞察力的基本姿态,也是我们在为自己打开一个更广阔、更灵巧、更有生命力、更丰盈的世界时常采用的策略”。《古法》有意营造了一种我们与“古典”“江南”及其器物、空间、人的特别亲密、和谐、舒适的氛围,但却在这种“伪装”形成的静水流深中,把我们引向“古法”之外,或者把“古法”放在一条当代的逃逸线上,从而在一个更为广阔、丰盈的小说的世界中“逼迫”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什么是“古法”?我们真的能够拥有“古法”吗?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是“古法”还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真实的世界”?
小说中有两处细节意味深长。一处是女科技人问“我”梦到了什么,“我”说:“小时候,祖父母的小花园。”另一处是老简问我:“你有过一个人穿过黑暗弄堂的经历吗?”这两个问题本身,以及作为听者的女科技人和“我”的那种“沉默”或“冷漠”,已经帮我们回答了很多问题,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回答。正如张莉敏锐发觉的:朱文颖“试图思考的不是人如何活着,而是人如何存在”。
《古法》在“江南”的逃逸线上,而朱文颖则永远在“自我”的逃逸线上,她始终被一种逃离、越过、发现,再逃离、再越过、再发现的渴望吸引。“写作就是绘制逃逸线”“人只能通过长长的、破碎的飞逸才能发现世界”“离开、逃逸,都是在绘制线路。如劳伦斯所言,文学的最高目标就是‘离开、离开、逃逸……越过一道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命……’”
此时我想到了松尾芭蕉的俳句:
即使在京都,
听到布谷的叫声;
我也思念京都。
对“江南”“古典”而言,《古法》就是“布谷的叫声”。而朱文颖的小说,永远在寻找乃至创造这样的“布谷之声”。
三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体会。《古法》的节奏和纹理让人再次想到谢有顺对朱文颖的三个词语的评价:细腻、优雅、节制;也能充分理解王尧对朱文颖写作的整体性的概括:“她基本能做到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氛围状态,把小说的故事、语言、调性和所思考的问题融为一体。”《古法》充满了开放性和自然、温润的对话性,以一种特有的节制性的优雅、从容,唤醒了我们对于风、轻盈、朴素等江南气韵的敬意,并以此为起跳之处,让我们重新认识一种可能已被我们遗忘的、来自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的延展性和广阔性。朱文颖的小说已经越来越趋近于罗兰·巴特所描述的那种理想小说的类型,即“一种非傲慢的话语”“不给他人带来压力的话语实践”;同时也越来越抵达托卡尔丘克所描述的“新型故事的基础”:普遍的、全面的、非排他性的,植根于自然,充满情景,同时易于理解。

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青年评论家,文学创作一级。曾任《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任《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江苏紫金文艺英才、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多种。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丁玲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紫金文艺评论奖等各类文学奖项二十余项。
来源:《芙蓉》
作者:何同彬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