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肥/摄
田庐歌
作者丨寿州高峰
乘飞机坐高铁
骑马或赁驴
我们穿越千山万水
无论路上耗费了多少时间
总算在天黑之前赶到坛头
在一块巨石上凿台阶
过小小门第
老房子斗拱精巧,出檐深广
木头门扉安装的是密码锁
我们的手牵在一起
不约而同按响尘世里剩下的几个数字
今夜没有星月
躺在田里的是即将黄熟的水稻
睡在庐舍里的是刚刚吟诵的诗人
我们不准备班师回朝了
嫁人就嫁田庐郎
娶妻要娶田庐女


寿州高峰,原名高峰,当代诗人,1965年6月生,安徽省肥西县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成员,淮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寿州诗群发起人,现居寿州。
田庐一夜
作者丨冷盈袖
他们都走了
好在留下了风声和清泉
这是最理想的生活
我知道墙边还有几根翠竹
一夜我都睡在流水里
或者说我也是一小截流水
一小段时间。夜晚令我安静
我不关心自己会流向何方
我们的将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记住了半夜黑屋顶上方的星光和风声
这样寂静又空旷的余生
是我们无法轻易描述和拥有的


冷盈袖,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又名骨与朵,偶尔写诗,偶尔获奖。诗作散见《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等刊物及各种选本。 著有个人诗集《暗香》和散文集《闲花抄》。
田庐一夜
作者丨陈星光
骨与朵——冷盈袖藏诗阁
里躺着《暗香》和《闲花抄》。
几本寂静的诗集吸引我来到田庐徐小冰的桃花源。
曲径通幽,鹅卵石的小巷向晚,踢踏着岁月回来又消逝的足音。
坛头湿地飞来飞去的几只白鹭,一只叫闲适,另一只也叫闲适。
鸟鸣在一个个树梢反复跳跃,仿佛替我说出内心的感激。
蚂蚁在松林里忙忙碌碌,花朵在浓得化不开的绿意里唱着自在的歌。
云朵随意闲卧,像弥勒佛的微笑,我醒着就开始做梦了。
时间太快,而万物葱茏。我们的放弃里有不舍的执着。
在一张张诚挚的面孔里发现日子还是诗意和值得过的。
田庐一夜,弹奏温暖的音乐。


陈星光,生于1972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永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月光走动》和《浮生》。诗作散见《诗刊》《青年文学》《草堂诗刊》《诗江南》《中国诗人》《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江南》《扬子江诗刊》《文学报》等,并被收入《当代短诗三百首》《年度最佳诗歌》《中国诗歌年选》等十余种选集。穿行于市声、月光和山野,以梦为马,以诗为寄。
田庐一夜
作者丨方文竹
拿什么修补万物?挂起的红灯笼
惯用古典手法。我独自抚摸老屋斑驳的墙
“对于时间之缝隙的填补一刻也没有停止”
江山如画,用的是心灵的笔墨
蛙鸣,狗吠,见证一个时代的通感
田野成为人类的替身,只有极少数人
沉静如冷僻字或晾在一边落满灰尘的算盘
棋格一样的房舍与此相映成趣
迎面走来的皆熟悉的陌生人,带来一片
意境中的逆光,多了一些内容
无事可做,一起赏月吧,一起修改梦
忽地,高高的夜空脱下它的彩衣
眼前一片漆黑,随它去吧
一小片莫名翅翼拍着我的肩膀
世界就是一只乌鸫,只飞,不叫,有实无名


方文竹,60后诗人、批评家。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等各类著作21部。
田庐送别
作者丨涂国文
“就这么走了美丽、挺拔与骄傲!”
推开田庐溪山雅舍后窗,对面小楼石门中
有离别的身影掀动晨光之帘
脑海忽然浮起高尔基小说
《一个和八个》最后一句
鱼鳞般的黛瓦覆盖着江南
一排排巨浪斜着身子朝向远方奔涌
木质的窗棂泛起木质的感情和美学
一些浪涛试着冲向天空
却被时光凝固成翘檐
我没有看清离去者的背影
也没有呼唤他们的名字
多年以来,我只习惯于迎来而伤情于送往
如同静立在楼底天井中
那几竿单薄的紫竹
但我知道,他们离去时并不孤独
他们随身带着友谊与诗歌
他们的旅行箱
装满了田庐的风声和鸟声
以及潘午潭的一片湖光


涂国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散文学会理事、西湖区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随笔集、文学评论集、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共九部,现供职于某高校杂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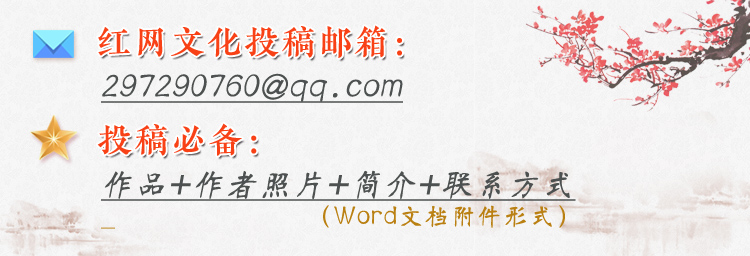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寿州高峰 冷盈袖 陈星光 方文竹 涂国文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