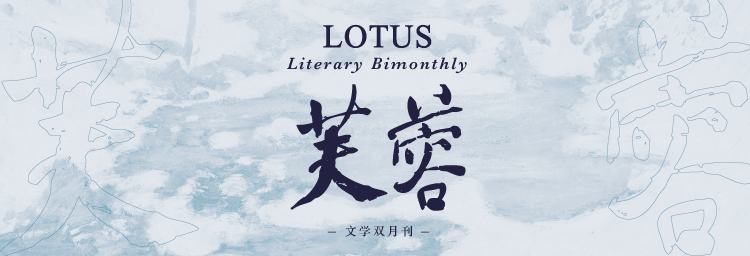

夜苏州(外一篇)
文/阎连科
我这辈子有两处地方去得多,一处是苏州,另一处是我家。我家不说了。苏州去得多,先缘是那儿的朋友情挚厚,再缘是自小都听说“生苏杭,葬北邙”的话。洛阳的邙山宜于死,苏州、杭州宜于生。中国人活着谁不是先思生而不到不得已,谁去思死啊。更何况邙山宜死后之葬也都是皇室贵族之选地,百姓的终选还是离家近的风水处,至少儿孙清明上坟时,可以少走一些路。
说苏杭。
杭州去得少,除了它距离北方远,还因为很早我姐到杭州去旅游,在百货楼上乘电梯,那电梯突然断电停下来,她人在电梯上摔倒了,脚腕扭伤出了血,去和商场的管理人员理论这桩事儿,人家一言道:“你们北方人乘电梯不知道手扶电梯啊!”我姐不光是北方人,而且还是农村的,于是觉得自己与生俱来地理亏了,只好悻悻退回来,一路拄着拐杖旅游了。我是相当记仇的人,杭州把我二姐得罪了,我就把杭州得罪了。能不去杭州坚决不去了。杭州的公园、餐馆和旅店,也挣不到我的分文了。苏州没有得罪我,我经常去苏州。可每次去苏州,又找不到天堂那感觉。往东去,没有“照日深红暖见鱼”;往西去,找不到“桃花流水鳜鱼肥”。十全老人街,是今天苏州最能连通旧往的地方了。正街挤店铺,临街铺河水;抬脚即到拙政园,落脚又到狮子林。可惜那儿人太多,多得路上的脚印比地上的石板还要厚。从你脸上落下一珠儿汗,一定不会落在地面上,而是落在别人的肩或裙子上,弄不好还要因为这汗和人吵一架。再说临街那条河,河水也还清,趴在岸上把头探下去,保证你能看透几寸深。水上也有桥,桥上一般都会扔着一个纸箱或者一只鞋。桥下也许会有船,只是那船都破了三年、五年了,仅剩几块发了乌的船板子。“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那说的都是走不回去的过往了。“谁谓今日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这也都是人家乾隆浩浩荡荡到江南旅游时,其他游人被赶走戒严后的静美处。总之、总之说,我们今天到苏州,见的是和别的城市差不多的城,处的是和别的城市近乎一模一样的市。
这苏州——不去你甚想去,去了会顿生原来尔尔那感觉。
后来和苏州的兄弟说起这感受,他说:“你夜里没事出门走一走。”我便依了他的吩咐夜游苏州城,且还是到了夜里12点,多数人都上床睡觉了,我从十全街的南山饭店走出来,果然多多少少、如期而至地体会到了乾隆说的“谁谓今日非昔日”。大街上行人稀少了,路两边虽然停满私家车,店铺的门窗全都关闭着,可灯光把十全街照得如同白昼样。能看见地上的脚印被洒水车法官判案一样洗了去,留下汪汪片片的水渍,你走着宛若踩在明清时候的雨水里,或像唐宋时候的姑苏水,多多少少浸淫在了大街上。偶尔一段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你和你的影子在,于是影子在前引着你,或者它在后面跟着你。再或者,影子和你并了肩,走着走着你从街的这头到了那头。返回时不走回头路,而是走在临街而住的流岸上。无论是流岸上的住宅门,还是卖苏州特产的流岸窗,这时呈给你的都是一片木黑色,只有流水一条在你脚下清明着。灯光落在水面像玻璃有了软绸在荡动。这时你看到一座桥,想起白居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句子来,虽然知道自己的情绪有些酸,又觉得横竖左右都无人,便小孩要当街撒尿一样快步跑到那桥上,本意是要去桥顶对着天空、流水和苏州城,大念李白的《乌栖曲》,可是一张口,“姑苏台上……”后边的半句丢掉了,如同鱼肉不再,只有鱼刺卡在喉咙里。也就只好干咳咳,想再换一首背出来,比如李商隐《陈后宫》中的“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然你记起了这两句,却又记不起前面两句来,如此也就索性自己对着苏州笑一下,既有自嘲在笑里,也更有年龄和记忆越来越少的感叹在其中。想到年龄和记忆的反比后,瞌睡是越发退去不在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骚泼气,不意间由脚底窜到腿骨上,想到现在平江路上会是什么样?就心血潮涌想去一趟。
打个夜的就去了。
原来平江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河水竟然——竟然可以让人听到流动声,白花花碎银子一样响出来。树影和灯光,在河面上暧昧缠绵得有很浓一股胭脂气。下半夜的寂静把白天汪汪洋洋的脚步淹没了。寂静像皇帝一样统治了平江路。在一家名为“老苏州”的专卖苏绸、苏扇旅游纪念品的店门前,川流不息没有了,店前半静半流的河上泊了载过一天游人的乌篷船。那船和闭关着的“老苏州”的店铺门,彼此的梦呓都借着树虫的鸣叫荡在半空里。整个的水系如同来回交叉的绸缎在舒展。偶尔有星光自河湾的拐角落下来,在水上如钱厂新铸制的银圆样。河水到底载有静谧了。路上到底有了石板味。叫“欧洲分店”的卖咖啡、奶茶的店前有了姑苏月,门前的闲凳上有股月光味。就连路边河岸上的一株青蒿草,这时也终于泛出了一股老姑苏的野草味,如同盐里有了盐味儿、麻油有了香味样。到这时,你觉得苏州似乎被你找到了。平江路成了平江路。你独自携着寂静往前走,朝这儿拐一下,往那儿探探头。拐一下走了一段后,有一堵墙会悄声对你说:“前面路尽了,你往回走吧。”探探头会有一株竹枝拉着你的手,说:“喂——你过来,这儿可以坐下歇一会儿”。也就走进那竹子、花草围起来的一个园子里。几铺席大的木地板,摆了白天供人喝茶的小桌和椅子。现在那桌上摆了月光、星光和屋檐下的昏灯光,还有从河道支流传过来的水声和凉意。你坐在一把凳子上,寂静坐在另外几把凳子上。你说:“要有一碟瓜子、一杯黄酒就好了。”寂静便四处瞅一下,确定这儿只有你一个,又朝天上望了望,悄声问你说 :“瓜子是要民国炒的还是清朝时候的?”你惊了一下,也朝寂静的四周看了看,慌忙拉着寂静的手:“民国茶,清瓜子,明朝时候的小酒行不行?”寂静便点头默去了。很快端来了你要的,还叫了一位评弹女子为你唱曲拨词儿。女子自然是一副好模样,年龄、身段和裙子,都如同夜晚、月光恰对寂静样。她在专心为你弹唱白居易的《琵琶行》,可你在想为什么不弹《长恨歌》,这时你想着,朝那闲椅空凳上看了看,有一把椅子上卧着一只听曲的猫,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只狐狸在边听边看书。你悄声问那狐狸看的什么书,狐狸翻开泛黄的书皮给你看,原来是一册最早的线装《聊斋志异》,想问狐狸这书是哪年刻印的,可有一缕亮光突然从空中静静默默射过来,在大家头顶说了一句“天亮了”。于是唱评弹的女子收了弦,端来了酒和瓜子、糕点的寂静也把盘子、碟子、酒壶收走了。
猫和狐狸也都转眼不在了。
我从平江路的这头入,到了那头出,打上早班的出租回了十全街的南山饭店里。来日苏州的朋友问我昨夜有没有出门到街上走一走。我说去走了,多少有点儿找到苏州了。他会意地笑一笑,建议我以后每次到苏州,都要在夜深人静时去苏州的古巷、老街和旧码头上转一转、坐一坐。我也就遵照他的意思和叮嘱,之后每次去苏州,都打发自己静夜出门去找苏州。通过他的关系之关系,有次在网师园里黄昏没离开,蹲在园里到月牙当顶时,看见园主人王思当年的渔网过了一千多年还挂在一棵河边柳树上,一边晒着一边有人在补网。又一夜,通过另一位朋友的亲戚之关系,在黄昏闭园清园后,逆人进入拙政园。那时正秋季,月亮将要升起时,只有我和拙政园的一个管理员。他领着我走到一段长廊下,看月亮突然正圆悬在头顶上,让我赶快从廊下独自走过一座桥。待我踏上那桥时,他又唤我快朝着水下看。我便低头看见拙政园里湖水莲藕的缝隙间,有一片长长的流光在动着。那流光在水面,仿佛一条弯弯绕绕的银液线,及至水面的晃动静下来,那银液的弯绕不动了,才看见是月光在水里写照出的“筑室种树,逍遥自得”八个字。问为什么月下水里会有这八个字,管理员说每月的十六月圆这一天,月亮升起那一刻,这水里都会有这八个字,但必须是月亮和这湖心垂直对上那一刻。后来我还在夜半独自去过苏州的虎丘、南浔、西塘、七都和寒山寺。在寒山寺的雨夜里看到了一个孤孤苦苦的老钓客,在寺庙的檐下避雨唱着歌。在南浔古镇的一所空宅老院里,有一群村妇在唱歌剥莲蓬,白花花的莲子在院里摊了一大片。待天亮我从南浔打车回到南山饭店后,苏州的朋友在饭店大堂等着我,一见我他就急急抱怨说:“你一早去哪儿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他让我抓紧回房换一套正装快下楼,同他一道去参加一个苏州GDP突破二万亿的庆功会。说会上我只要说几句苏州好的话,每人可得两万元的纪念品,且会后还有与会者抽奖大游戏,运气好也许我能抽到一辆轿车或别墅。
听说一摸一抽可能就得一辆宝马轿车或苏州新区的独院大别墅,我便慌慌忙忙上楼去换正装了。
吴江套肠
中国有个地方叫苏州,苏州有我两个好兄弟,就像天堂我也有两个好友样,每每见着他们,他们都会对我说:“走——我带你去吃些好东西。”我是为着吃饱才出门和人生打架的,这事情颇似筷子断了要去找上帝赔偿样。小时候为吃半碗肉,我曾经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工地上,被父亲藏在一个草屋里,偷吃了大半碗的肥肉还喝了一碗煮肉水。1983年,初读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故事中有个叫留小儿的小姑娘,她和插队的北京知青有这样的一段问和答:“(北京人)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吃。”“你说北京人不爱吃白肉?”那北京知青为此点了头,于是她就为世界上还有人不爱吃白(肥)肉而爱红(素)肉感到奇怪了,感到北京的神秘如同大西北塬梁顶上的银河了。我是为这几句对话爱上这篇小说的。也因为这篇小说就牢不破地认为在中国的知青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为理解农民、最为理解人的存在的那一个。后来因为写作我到北京去,和一个著名诗人兼一家著名刊物的主编在一起,讨论起素肉、白肉和素白兼具的红烧肉哪款好吃时,他过来拍拍我的肩,说肉类中最好吃不是素肉或白肉,而是用大蒜炒的猪大肠。然后他伏在我的耳朵上,绝对机密地认真道:“猪大肠要想好吃不是多放蒜,而是不能洗得太干净。”之后他的脸上放着光,像一首诗中的“诗眼”在对着读者笑一样。还有苏州作家陆文夫,一部温文尔雅的《美食家》,让他成了食客中的仙和道,宛若酒仙倘是举了杯,别人再也不敢说“我手里的酒要比你的酒好”了,因此连许多法国的读者谈起这部小说和作者来,也常常会在嘴角挂着涎水竖起大拇指。而比起《美食家》,我似乎更喜欢他的《围墙》那一篇,缘由是《美食家》中太多写“雅炒”了,而“俗食”被冷落了。世界上区分哲学家大小的不是谁的哲学更雅、更深奥,让研究的后人排成队,而是谁的哲学更为凡俗化,让大众读了脑门洞开可能成为理论家。我以为《美食家》中少涉庸俗大众的煎炒蒸煮是美和艺术之缺欠,这观点让会吃又懂文学的人经常在我身后偷着笑。
无论怎么说,在苏州我有两个好兄弟,宛如在天堂我也有两个挚交样,所以每每一见着,他俩都会对我说:“走——我带你去吃点好东西。”去年10月间,疫情让我的腿短嘴寡了,所以能跑时我从北京一迈腿,落脚到了苏州去——一干人马决定去苏州的吴江吃套肠。先早年少时,为吃半碗肥肉我徒步几十里,这时候坐着兄弟的豪车去吃套肠,说明我和生活打架几十年,是生活败在了我手里。车子在太湖的南岸飞奔着,湖水的光亮从我迎面竖起撞过来,让时间的水珠落在车玻璃上,使所有抒写太湖的唐诗宋词都碎成偏旁和部首,横七竖八地落在大家的欢快和争吵间。我说太湖是美的,苏州人说也就是一大汪的水;我说《圣经》上描写通往天堂的路是一拱彩虹形,苏州人说那彩虹的一端一定起于太湖间。我问他们套肠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多好吃,他们说:“到了你就知道了,见过彩虹你对套肠一定不陌生。”
然后要去的地方就到了。
到的地方是吴江七都镇。镇上到处都是老街老房老流水,码头古船和旧铺子。那时“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的句子人们还没读到,只是觉得码头是石头砌成的,也就果然是石头砌成的。觉得老街口的铺子应该挂有红灯笼,也就果然挂有红灯笼。头顶的阳光是湿的,河面倒显得干爽了,仿佛阳光本是水面被揭去挂在了老街正上方。大家漫步在七都镇的石板小路上,如游客坐在古镇上的老庙里,而庙里的神去街间打肉买菜准备午饭了。时间和物事都是颠倒的,悠闲不停嘴地说着话,念叨到人生若能切成若干段,把其中一段放在七都镇,该是多么美好、天堂的一桩事。可说着说着,主打套肠的“老镇源”餐馆就到了。听说过燕郊、城郊、市郊这样的话,可没听说过哪儿有“镇郊”。郊是一种野,离繁华不太远,如此称老镇源那儿为七都镇的“镇郊”还是贴切些。一面是公路,一面临塘池,另两边是一片树林和菜园。很普通的一幢乡楼屋,门额上“老镇源”三个字也没什么名堂和出处,像“阎连科”三个字给人最大的想象是连长、科长样。踏着楼梯走上去,脚下摊的是河虾和干菜,到了楼上的雅间也没觉得雅静仙界到哪里。墙上挂的书法、字画也确真没有柳公权的字好或比八大山人的笔墨更值钱。冷菜、热菜齐集一堂端将上来了。盘是普通的盘,菜是和姑苏城里同款味的菜。程序、味道也没有《美食家》中写的一二三和宫廷滋味流落民间的那种典故香。然在这失落将要膨胀时,套肠如期而至了——一如全世界的国旗都是在太阳升起那一刻,铁定准时地冉冉升起在大小不一的广场上。一人一个洁白偌大的盘,盘的中央摆着丰肥手镯般的套肠圈,每个套肠圈上都点缀着几丝香菜和葱花。介绍说套肠是鸡肠、鸭肠、鹅肠、羊肠和猪肠一层一层穿套在一起,再根据季节和食材,有时加上人工做的豆皮肠,比如绿豆、黄豆或豇豆皮肠子,不是有什么豆皮配什么,而是需要什么豆皮做什么。之后最少七层肠子配齐了,再由小到大套起来,沉在百年老汤里浸泡和喂养。喂养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然后才可以打捞出来文火蒸。做套肠的方法应该由陆文夫样的美食家们来书写,而我是个野食客,从来只管好吃而不管那味道是如何教养出来的。奇妙的是那彩虹色的套肠环,套环上看不出接口在哪儿,一色的光滑和粗细,只能让人相信套环一生成,就是天然一圈无缝的圆。问那店里的人,套肠的接缝在哪儿,服务员只是笑着说:“得去问厨师和老板,我要说了我就没有工作了。”
有人用筷子挑着套肠寻着窗口的阳光透视着看,想数出套肠里边到底有几层。除了第一层深信不疑是猪的大肠外,里面的羊肠、鸭肠、鸡肠、鹅肠和豆皮等,它们的顺序是谁先谁后怎么组合的,很难看出来。梁遇春二十七岁就死了,他要不死该是怎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哦。在他薄薄少少的散文《黑暗》里,他说 :“没有饿过的人不大晓得食饱之快乐,没有经过性的苦闷的小孩子,很难了解性生活的神秘和意义。”我坚信大家每人吃那套肠时,都在心里预设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庄严和仪式,慢慢徐徐,缓缓轻轻,是让牙齿先去碰套肠,还是让套肠主动上前碰牙齿,如新婚初夜人人都千百次设想构思过的最初和准备,可到真正临着了,也必然还是慌乱和粗莽。无论如何说,套肠的表皮在牙间突然崩破了,油汁和香味在嘴里山呼海啸地跑起来。每一张嘴都在“啊”后张圆着,可又觉得那香味从嘴里到了嘴外太浪费,于是又都急速地在沉默中细细莽莽地品味咀嚼着。世界上没有一人的性生活和另外一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也没有谁的第一次进入和第二次进入感受是相同的。这时候人人都体会了语言的寡弱和瘦薄,说什么都必然丢三落四,而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位著名诗人说的话:“要想好吃就不能洗得太干净。”而不能洗得太干净,是这套肠的一种不能太干净,还是层层都不能洗得太干净?原来所谓的美食总是和堕落和脏联系在一起,仿佛所有的升华都是从堕落开始的,圣洁决然不能把不洁全然否定去。
最初上帝对人类一开口,说的关于食物的定夺是:“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引自《圣经》)奥维德在《变形记》中一开篇,也又说了关于人的食物源 :“四季常春,西风送暖,轻拂着天生自长的花草。土地不需耕种就生出了丰饶的五谷,田亩也不必轮息就长出一片白茫茫、沉甸甸的麦穗来。”由此证明天地初始时,神是圣明的,人是素洁的,仅果蔬、粮食就足为人之美味了。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堕落的美,发现了肉和鱼类比果蔬和粮食更有天香味,于是朝着庸俗的方向势不可当地坠落了。到后来,发现所有的肉类鱼类中,最好吃的竟然是杂碎。再后来,竟然发现是大肠。而在肠类中,套肠才是美味中的珠穆朗玛峰。
套肠吃完了,大家开始怀疑天堂怎么可能在天上。
从“老镇源”的酒店离开时,同行的长江学者说:“美到底还是离不开堕落和庸俗。”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教授很奇怪地问:“为什么不把吴江的套肠献给美欧的国家领导人?”而一直矜持的上海青年女作家,则再三交代我:“以后你再别对人说,没有洗净的大肠才好吃——这太让人浮想联翩了,也太割喉惊天了!”而我妻子从吴江回到北京的一年里,时不时会问我什么时候再到苏州的吴江走走看看去吃套肠。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四书》《炸裂志》《日熄》,散文集《我与父辈》《她们》等。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马来西亚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捷克卡夫卡文学奖,香港红楼梦文学奖等,多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和长名单。作品被译为30多种语言,出版外文作品100余部。
来源:《芙蓉》
作者:阎连科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