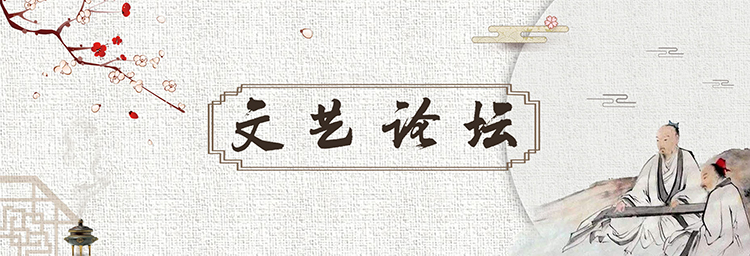

商界小说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学困境
文/杨虹 陶倩
摘 要: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在书写市场经济活动的定位下,商界小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内容建构模式和文学创作机制。与此同时,传播媒介的多元化特性使得商界小说顺应了新时代的文学格局,也相应催生了女性书写模式化问题并由此引发对其文学性的思索。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女性书写模式的基本总结和成因分析,揭示构建商界小说文本固化的书写局限;另一方面,针对创作逐渐商业化、大众审美官能退化、作家媚俗意识的增长等发展痛点,将传统文学的秩序和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并置,为商界小说的未来发展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商界小说;女性书写;模式化;文学困境
以20世纪90年代为端绪,商界小说发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期,并迅速建立以书写商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创作内容,开拓了一片弘扬民族新商业精神的文学园地。自此,这些以反映商业经济活动为主要题材,以塑造商人形象为基本目的,彰显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小说创作{1}便在开放的现代传媒之中不断制造、传输着文学视域下的商战传奇。作为在新时代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一种类型小说,商界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落入模式化和程式化的窠臼,但在形式的审美之外,其女性书写的部分十分引人注目。由于商界小说的叙述背景和创作内容本身就围绕着各项权力的纷争,自然那些深涉其中的性别意识书写就成了我们审视商界小说“精神高塔”不可或缺的内在标准之一。
实际上,直接将商界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和文学性并置而谈并不是明智之举。这个命题过于直白地提供了一种商界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和女性意识表达上与文学性有所疏离的可能性,也或多或少地间接表达了对商界小说整体文学性的否定。商界小说能够在小说创作领域开拓出一方天地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打破自古以来轻商、贱商文化壁垒的一次变革。但在瑕不掩瑜的评析姿态下,清醒地回归到文学创作本身无疑能更好地推动商界小说的发展,也能为它的未来书写提供更多的空间,积聚更深厚的文学审美力量,其中女性书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口。
一、市情商态中女性书写的类型特质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中国自1978年进入社会“商业化”的历史阶段后,消费文化乘势而起,商界小说也在其中展现着市情商态的多变,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关乎经济、人情、伦理等多个向度的故事。观其女性书写,即使商界小说拥有着较为悠久的书写历史,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融入商界小说不可不谓历经了一番波折。直至20世纪末,她们才真正得以用商业主角的身份登上舞台。一拥而起的女性角色背后是作家对她们在商界生存境况的不断探索,也展现了对女性从商的身份认同。其书写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女性书写模式以书写孤雌纯坤的女性掌权商业家族为基本故事架构,以《大宅门》(郭宝昌,2001)、《乔家大院》(朱秀海,2005)、《白银谷》(成一,2005)等作品为首,涌现出白文氏、曹氏等一系列相似的寡母形象,而且这一类的女性较少见于现代。寡母的尊贵源于父权的缺失,她们往往担任着拯救家族于危难的角色,这种书写一来设定符合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二来是为了满足小说文本的书写必要。要想作品受到欢迎,充实的故事和读者的阅读快感就要求其具有独到的差异性。在封建的商业背景之下,女性主角相比于男性有着更吸引人的看点。而商界小说文本之中,动辄几十万字的故事必然要建立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基本叙事背景之下,女性进入商业领域与此种文本架构正好相辅相成,更能呈现出商场尔虞我诈的底色。
第二类女性书写模式以物化了的女性最终沦为商战牺牲品为基本故事走向,以《圈子圈套》(王强,2006)、《资本魔方》(陈一夫,2004)、《输赢》(付遥,2012)、《热屋顶上的猫》(王海玲,2012)等作品为代表。女性的物化蕴含着主动与被动的两层关系。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的进程中,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之间联系愈来愈紧密,但“解放”的根本,借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是一种在“女性与性欲之间的基本意识形态混淆根本尚未廓清的情形下进行的”{2}。我们并不阻挡女性对于支配身体自由行使权利,但从大量的文本中精炼出的却是商场上女性不断成为泄欲对象和消费客体的事实。钱权交易所带来的特权化直接表征于女性沦为消费品的客观写照,既包括男性对女性身体、精神的规训,又包含着女性利用自我身体与男性权力的置换。
第三类女性书写模式则以拥有独立意识、追寻自我成长、挣脱时代束缚的女性为叙述对象,例如《杜拉拉升职记》(李可,2007)、《沉浮》(凌志军,2011)、《奋斗者》(小桥老树,2020)、《暂坐》(贾平凹,2020)等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摆脱物化的标签,追寻自由支配的权力是这一类女性与前两类女性在人物内核上的根本不同,她们或身处商战之中,或挣扎于职场竞争,或渴望在经济社会的桎梏下寻求钱权之外的自由。“小说中的虚构成分,并不在故事,而在于那种由思想发展成外在行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从未发生过。”{3}这类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大量出现在商界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要稍晚于前两类,据福斯特所言,我们可以从作家创作和社会历史两方面溯源:一方面源于作家们文本创作类型化之后的灵感枯竭;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女性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的现实依仗。
那么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以上几种主流的女性书写模式与商界小说的文学性关系的时候,所针对的就不仅仅是单向的女性书写,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其更多地发散到了商界小说的文字价值和社会意义上。一方面,商界小说已经在几十年的创作中形成了鲜明风格,其中以写实为主的叙述内容也增添了更多的历史意义,但对于小说文字的表达技巧、刻画深度乃至背后的话语内涵、表现维度等方面都缺乏较深刻的研究;另一方面,商界小说无法真正得到认可的根源在于公式化的创作模板和低俗化的写作立场,由商场、官场、私人场组成的必备要素与诸多老旧套路让越来越多的商界小说创作陷入固化的创作泥淖。当然,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抛去商界小说通俗化的本质一味地掺入反流行的元素,追求标新立异,但至少通过观其一面,以敲击女性书写这条裂缝,对商界小说文学性问题进行破冰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
二、商业主义背后女性书写的逻辑揭秘
论及商界小说女性书写的模式化写作及其文学性问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其中女性书写模式化的认同。这种认同,一部分来源于我们对于现阶段商界小说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人格建设、思想深度等多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即在肯定商界小说发展的几十年中存在一些创新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女性人物的同时,也要承认剩下的多数小说存在的单一的、空洞的女性人物。另一部分源于商界小说的内驱动力。固然商界小说只是众多小说类别中的小小一脉,但作为文学类型之一,内容和文字的历史价值赋予了它在传统商业题材小说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不禁好奇,这种既古老又新兴的创作题材在民族商业精神塑造的新阶段所呈现的涅槃姿态能否持续发挥价值?在泛娱乐化的时代中会如何进一步去芜存菁?故此,在已形成的女性书写模式化的写作基础之上,我们要穷源朔流,探讨成因。
从近几十年中国小说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商业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通俗文学的热潮席卷了更多的阅读市场,流量至上的运营带来了快餐式的文学表达,这是时代的文学表征,也是文学生产机制不断下沉操纵读者的一种方式。商界小说也没能脱离大环境的束缚:在阅读方式上,便捷的在线连更阅读能更好地迎合大众阅读心理;在书写内容上,大多小说已经不再单纯地注目商战中的经济纠葛或情爱人欲,玄幻、同人、重生、修仙等多个元素的融入使其获得了更加绚丽的布局和架构。综合来看,越是以杂糅的流量元素融入小说创作,越能够觉察到套路式写作的痕迹。这种创新意识的枯竭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书写细节上的公式化,使其与追寻文学性的目标背道而驰。商界小说在整体创作上的模式化已然如此,以此类推,涵盖其中的女性书写在发挥上受限也是一种必然。
其次,从作家层面剖析,创作者本身是受到小说商业机制化影响最直接的人。从《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商界小说经典作品到《大时代之工业王国》《网贷情缘》等一系列高流量、低俗化表达的商界小说之间不过二十余年的间隔,却可以想见其中作者笔力的参差。商界小说的创作,在追随网络小说浪潮的浮沫中传承了独到的定位,写作商业化的运营机制所孵化出的多元产业链让作家由独立创作的个体转变成了模式化创作过程中的“一颗螺丝钉”。作家对大众媚俗意识的迎合,典型地表征于商界小说中对“女性”与“情色”纽带关系的呈现。正如鲍德里亚在讨论女性身体作为符号渗入消费时所说的一样,“身体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符号网,它们可以在抽象化的基础上交换价值……身体与物品的同质进入了指导性消费的深层机制”。{4}在功利主义的写作立场之下,小说中女性身体不仅仅流于裸露的性器官描写,而且成为商业经济领域中与物品等值的软交易对象。
最后,让我们回归到小说文本的原点。从那些被书写的女性出发,不难发现,愈是剔除所谓小说创作产业链、快餐文化、套路化创作的外部因素,愈会抉发出商界小说之中女性的定位多处于一种边缘化的,抑或传统的压制模式之中。以上文所述三种女性书写的基本模式来看,多数女性人物更像是“徒有其名”的工具人,她们的存在多用于表现商场的腥风血雨以及如何成为权力之下的牺牲品。《圈子圈套》中的琳达和菲比就是男性向商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典型,她们明明具有与男性匹敌的经商潜力,却在情爱面前一步步跌入世俗纠葛的鸡毛蒜皮之中,而围绕其中的男主人公洪钧却一副评点的姿态,不断用语言和行动弱化女性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此种“一男对多女”的情爱姿态背后隐藏的是女性之间的竞争,除却能够体现男性强权的实质之外,这种女性书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现实生存而言并无裨益。
当我们展现商界小说女性群像的时候,所谈论的不只是在以经济权力为主要控制力的环境之中女性所展现的边缘化地位,更是当下历史境遇之中两性关系的碰撞。小说不是人类的自白,也不是个人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里的一个总体考察。{5}作家在泛娱乐化时代的文学背景下书写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边缘化的特点,正反映了当下时代之中男性与女性差异的基本事实,即女性身体已经从生理性的实质转变成可供交易的筹码。从这一层面出发,也更好地契合了文本、世界和作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对女性书写模式化之为何的分析闭环。
三、商界小说女性书写的文学困境
历来文学的发展揭橥着这样一个事实:判定一部小说是否能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长久检验,但判定一部小说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则相对容易得多。对商界小说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做判定之前,我们至少要放置两把标尺,一把是衡量传统小说文学的标尺,一把是衡量传媒时代文学的标尺。虽然分离式的评判对于女性书写的文学性衡量乃至整个商界小说的文学创作来说并不绝对准确,这种看似与时俱进的提法,实际上是对商界小说评介的一种降维。但不得不承认,自从进入传媒时代以来,作家群体的下沉,创作环境的相对轻松等都使得许多小说日益非严谨化发展。如此,当我们以传统的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对其中女性书写赋值时,便不可避免地觉察出从人物、情节到叙事上的虚浮之气。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两把标尺各有所长,纯粹的一刀切既不利于传统严肃之文学适应网络媒体,也不利于传媒时代的文学汲取传统文学佳作中的养分。故而,笔者选取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和商界小说的佳作共同对比,从创作差异中为女性书写的文学性找寻更高标准的定位。
钱谷融在谈及文学的最终归属时提到的“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6}。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文学创作的关键在于塑造一个有灵有肉的丰满人物,这种由人及文学,再由文学及人的平衡关系就是打破商界小说书写套路的一把利刃。而论及人物书写出神入化的作品必定离不开《红楼梦》,以当家主母贾母为例,她既是“一番佑启,数代典型”{7},又是中国小说史上孤雌纯坤的女性代表。支撑贾母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的是家族悲剧和人物悲剧的双重性,作为家族的家长,她见证了盛极一时的家庭逐渐衰败;作为封建社会的女性,贾母徒有尊贵,受的只是一份伦理上的虚名。与贾母拥有同质身份的人物在商界小说中也出现过,其中以《大宅门》中白文氏的塑造最为经典。同为主母的身份建构,《大宅门》更多在家族危难、人物纠葛上着墨,以深宅内院的内忧外患为故事主线,杂糅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多层伦理关系,而白文氏身处其中,以掌权人身份在商海中沉稳应付,小说通过对白文氏经商才华的描写,刻画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母神形象。同样是第三人称的视角写家族变化,在塑造主母形象上,《红楼梦》中的贾母是家族至高无上的女性,曹雪芹以入木三分的细节刻画展现了没落家族和封建男权双向维度中女性的悲剧,以丰满有灵的人物个性承载住了真实社会和小说内部的逻辑,内容上隐晦却符合人物命运,这也是贾母这一形象深入人心的原因。而《大宅门》中的白文氏则更像是为了拯救家族而出现的母神,它所聚焦的商海沉浮让白文氏凸显其极强的人物性格的同时,却又显示出单一的苍白感,完美契合了传统大众对于当家主母的形象想象,加之对话流的小说体例容易给读者带来浮于表面的冲击力,很难去进行深刻的思索和探寻。
由此,我们从女性书写的角度试窥商界小说的整体和文本内涵,可以肯定的是它所显露出的弊端远不止在女性书写上的局限性,这只是我们评判和推测商界小说未来创作空间的一部分,而围绕创作主体这一核心,时代的变更和大众的审美欣赏都对商界小说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前期的许多作家企图在现代性和通俗性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用自身深入大众生活的实践经验来展现商场这一社会空间的异彩纷呈,但是在市场化的资本干扰下,商界小说最终呈现的却是“文学性”与“需求性”的偏离。虽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存在向大众化靠拢的艺术个性,但是在这期间,小说的语言一方面在表现大众,一方面又无法代表大众意识。笔者认为,自最终归向于创作者脚踏功利主义沼泽的那一刻起,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已随着传媒时代快速的脚步纷飞离散。
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提高商界小说的整体创作功力,更要重视和找回创作者追逐文学性的内驱力,给自身的作品带来不流于时代快节奏审美的文学赋值。一如陈平原谈柯南·道尔、哈葛德的小说比起雨果、托尔斯泰小说在中国更流行的原因时所说:(中国读者觉其妙的)关键不在小说处理的题材,而在作家的审美眼光及其相应的表现技巧是否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8}这也就证明了大众阅读的审美受到时代阅读的潮流和欣赏的尺度限制。我们不否认商界小说在时代赋予的价值体系中找寻定位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狭隘单一的人物论,固化无趣的模式等问题,但就商界小说的未来发展而言,作者要在时代的局限中壁立千仞,追求经典的文学审美,不受市场和读者左右是必定要选择的道路。一如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终究会比柯南·道尔、哈葛德的作品更经典一般,商界小说在文学审美的塑造上还是需要保持对传统文学性的追求,如此一来,面对时移世易、审美变化,也不会让优秀的商界小说作品湮没不宣。
商界小说的发生和兴起注定会使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分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所映照的社会内容会越来越宏阔和深刻,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刻,诸如打工经济、创业经济等大众化的问题。回顾其发展历程,日益庞大的写作群体、大众阅读的流量支撑都昭示着其独有的创作特点;文学发展所需要的创新意识也正推动着它不断与职场、官场等各个环境相融合;商界小说所形成的创作模式、不断多元的商业元素以及庞大的产出数据一齐奠定了一个准确的阅读定位。但也因此,几十余年间,成百上千位创作者共同探索和提炼出的创作模式造成了类型化书写、两性书写不平衡、性别意识的失落等种种问题,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正是梳理和解构商界小说的第一步。总的来说,商界小说所体现的文学内涵的不足与其取材于社会现实的写作动力之间并不矛盾,前者是流于市场化和迎合大众审美的结果,后者是商界小说创作的天然优势。故此,商界小说完全有改变女性书写模式化的可能以及填补整体架构类型化漏洞的能力,它极强的可塑性似乎也预示着商界小说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变得包罗万象,不断扬长避短,逐渐打破类型化的桎梏。
注释:
{1}杨虹:《叛逆与超越——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②④[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第127页。
③ [英] 爱·莫·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⑤引自[捷克] 米兰·昆德拉:《耶路撒冷文学奖发言》,见https://www.douban.com/note/260105403/,2013年1月27日。
⑥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⑦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红楼梦偶说》,选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⑧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伦理批评视域下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6BZW113)和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性别伦理视域下新世纪商界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项目编号:CX20201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杨虹 陶倩
编辑:陈雅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