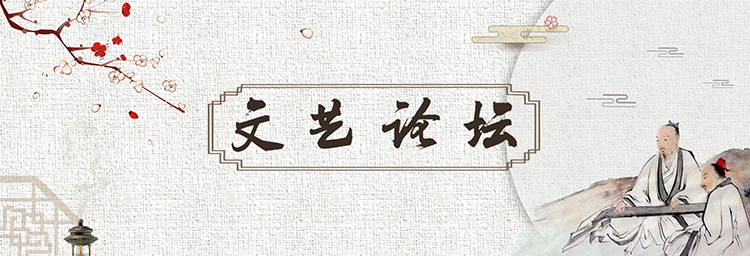

“自我”的厚度与限度:林棹长篇小说论
文/牛煜
摘 要:林棹的长篇小说《流溪》和《潮汐图》是近两年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收获。本文通过对这两篇小说的文本细读,重点分析了林棹小说的美学特质及其具体的文本生成语境。在对两篇小说主题(分别是私人的“感官教育”和对历史的“感性重构”)探讨的基础上,指出原子化的“自恋主义”时代“感性”话语在进入不同的主题领域时的美学洞见与限度。
关键词:林棹;《流溪》;《潮汐图》;美学风格;文本生产
一
在《流溪》中,林棹写到这样一个场景:“我”待在家中的“电脑房”里——一间“从主卧挖走的隔间”——关着灯,静静地靠着墙板和“虚空伙伴”玩耍。小说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类似“虚空伙伴”这样的暗语,只有等读者接受了作者提供的全部基础预设之后,才能将它们翻译成自己能够理解的说法。当然,这种翻译的需要本身就证明,林棹的表达远远胀破了常用词给小说文体设置的基本表达范畴;信息化时代的文学书写发明了它自身的一套词汇。同时也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基本风格,它近似于一个人的私语。
此处,根据“虚空伙伴”一词出现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推断出这个词表达的含义:孤独的小孩创造出的一个跟自己对话的对象。这个长转译本身暴露出了某种矛盾的存在——渴求对话而对象不在,于是这个小孩只能从自己的身体里“凭空”生产出一个对象——如果“对象”这一说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成立的话。于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的已然是一个“自恋的”(泛称)文本世界。
与这个黑漆漆的世界一墙之隔的是另外一个喧哗的、有问有答的“成人世界”,以及更重要的和更具象征意味的,一个父亲的世界。暧昧之处在于传到“我”耳朵里的话是那样的猥亵,因此“我”很本能地感到了“羞耻”——“我”几乎是猝不及防地遭遇了父亲的“出轨”事件。这时“自恋”倒转了它的弗洛伊德式发生机制:不是父之法过于严苛以至于主体产生了“自我内投”的倾向,而是父之尊严—伦理体系的瓦解促成了这个没有“模仿对象”的“我”的长成。与此同时, “我”的女性“榜样”母亲衰颓无力,终日哭天抢地。女性的力量在《流溪》里是孱弱的,但根据小说的结尾来看,却是悖谬性地不断重复的。
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开头获得了它的含义。这几乎是一个预示着“无法开篇”的开头,因为它全然与人、与事件无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混沌模糊、所指不明的色块;色块继而演变成身体;然后又从身体滑向了沉静喑哑的自然物——无生命的身体本身的赤裸形态;身体的每部分各自为政而不再统一为有机的整体。这一身体事件同时预示了小说文本的支离破碎的去中心形态。因此,《流溪》作为小说被书写出来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如何在飘散的碎屑之中“缓慢成形”,也即如何实现从诗到散文的形塑。
只有在读到小说接下来的内容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在开篇读到的那些自然物一样横陈的肉体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被遮掩在鞋盒中的“赤裸身体”原来是父亲私藏的色情录像带。“我”偷看被束之高阁、秘藏的录像带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僭越”——录像带的存在再明确不过地暴露了作为女儿的“我”的生命存在本身的偶然性。与生殖活动无涉的性的自足存在(况且还是遮遮掩掩的)完全抽空了生命/起源的神秘性;与此同时,性的自然存在也瓦解了文化建基于其上并遮掩起源的伦理秩序,因为小说中与色情录像带所掩藏的秘密相对应的事件就是父亲的出轨。
二
伦理关系被还原为赤裸裸的身体存在,形而上层面的本源及其连续性中断了;文本世界本身也就随之变成了无父无母的自体繁殖的空间。由此也可以理解小说开端之艰难。
纵向的坐标因起源的含混暧昧被消解了,横向的坐标也因独生女的身份被抽空。杰姆逊在一篇论述《魔山》的文章中提到了小说史上经典文本常见的结构设置:在经典小说中总是存在着“由两个不完美的个体形成的互补组合”,比如布瓦尔和佩库歇,福尔摩斯和华生,等等。这两个个体互为依存,每一个都不能获得其自足的存在。在杰姆逊看来,这一现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独立个体想要通过叙事建构自我的无能为力”。{1}晚近才产生的个体的独立性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个人主体性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充实的意义和叙事的“可能性”。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发展史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不用说巴金的《家》等家族小说整体地建基于伦理结构的盘根错节之上,就是到了余华写作《兄弟》的时期,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框架也参照了平行并置的兄—弟结构(即使是非亲兄弟)。
只有到了林棹的《流溪》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个体凭借叙事独自获得其内涵的艰难文本操作。当然,这一独生女—叙事者—主人公的三位一体有其发生学的依据;这个结构本身是开始实施于20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美学对应。凭此设置,林棹非常敏锐地把捉到了独属于独生子/女的叙事语法。上文提到的那个“虚空伙伴”其实也就是杰姆逊所说的“互补组合”的象征性补足。只不过组合的另一极是主体(如果还有主体的话)照镜式的虚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人公”杨白马的形象。
作为恋人的杨白马在林棹的笔下,十足像是一个被叙事者“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又一个“虚空伙伴”。我们的相遇具有显而易见的“虚空性质”;“我”和杨白马相识于魔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络世界。
文学史上绝大多数长篇小说的展开依托于主人公不间断的空间位移;小说里每一个新空间的出现都携带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消息并构成了小说本身的时间性。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的长篇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是时间和空间的扭结缠绕。网络世界的实质之所以被林棹浓缩地总结为“空间坍缩,时间获救”,{2}大概是因为发生在网络世界里的相遇轻而易举地跨越了空间的阻隔,时间非常单纯地暴露出了其赤裸均质的本性。大量存在的时间挣脱了空间的重负变得无比轻盈,每一个单纯的时刻即时地被消耗在语词的展开中。
因此,小说中“我”好像得了“表达亢进”{3}病;喋喋不休、繁复缠绕的长句的形态演示了“自我”将自身还原为语词的抽象游戏的全过程;当然,与其把这一游戏的目的看作是截获或澄清自我,还不如说是凭借词语的线性消耗不断延宕“我”与自己的劈面相逢——这也是处理冗余的、单纯空洞的时间的一种策略。如果考虑到这些句子里壅塞的典故和罗唣的自我重复,那么可以说它们几乎就是非指涉、纯消耗性的。
同样地,“我”与杨白马之间的几乎每一次交流也都是孱弱空洞的。如果说人际交往的古典本质在于对陌异的他者的理解和共情,那么依托于网络社交媒体的人际互动则是高度自指和自恋的。爱情作为人际互动形式的一种模式也就相应地变成了自我确证的一个苍白领域。因而“我”反复地、变着花样地在电话里问杨白马自己值不值得被爱。“我”穿越虚拟的字节、电流,膨胀的符码和拟真图像,最终抵达的是一处抽象的、幻影般的自我废墟。
爱欲,或者不如说单纯的性欲只是个人借以躲避外在重负的一块“飞地”。小说第五章的标题《处女》提示我们爱情是如何重复 “自体繁殖”的文本逻辑的。在“我”和杨白马的爱情中,完全不存在关于独一性、始源性的任何困惑。爱情的自体繁殖逻辑体现在它悬置了起源和必然性;此时此刻与杨白马相处的这个“我”只是他之前相处过的“一支姑娘的队列”中的一个“复制品”。像是一种恶性循环,之后发生的每一个爱情故事都只是单纯地证明了“最初的那个”的缺场。最初的丧失作为一种必然性,将此后所有的爱情和相遇降格成没有任何“个人性”的“偶然”。因此爱情最终也表现为“自我”为自己苦心营构的飞地上的一场独舞:舞伴是“虚空伙伴”的不间断的替换和重复。
当然了,叙事者“我”对小说里发生的一切都有着非常清醒的意识。“我”本人常常能够非常快速地从正在描述的事件中分身出来,就眼前的所有行动发表只言片语但却非常精准客观的评论。比如“我”说自己“自知忘我地笑着”(既知又忘)。就这一点而言,“我”是具有高度的自反性的。当一个人能够随时将自己的行动拆解为种种的悖谬和心口不一时,那么这个人就是极具反讽精神的。同时,她通过玩 “自恋”的姿态最终使得自己超越了“自恋者”的狭隘天地。
三
横坐标和纵坐标的缺失,使得“我”像一个在虚空中流荡不定的点。如果不发明出一套参照系来铆住自己,那么小说的主人公随时都有散佚的危险。与此同时,小说必定淹没在恶性的无限性中无法抽身;因为所有的细节和碎片都渴求某种定向的结构力,形塑活动归根结底要将“偶然性”转变为“客观性”。这也是去中心化的小说共有的危机。
好在普鲁斯特已经发明了一套深居斗室的写作者的技艺;一个作家完全可以凭借私人记忆书写自己,继而赎回整个世界。但是历史地平线的不同使普鲁斯特和林棹无法共享同一套记忆语法。普氏的记忆循两条轨道,一条通向“斯万家那边”,另一条通向“盖尔芒特家那边”。因此它的线索是空间—社群式的;一块糕点,一缕经伞面筛下的阳光最终都可以还原成一场场的华宴、舞会、出游。而林棹的记忆则更多借助“植物体系”:它完全是与“共同体”无关的纯私人记忆;这套记忆是非常单纯地凝结于物自身的。
植物体系的语法是:用树来“钉住空间”,“钉住人物”,最终“钉住时间”。{4}还原记忆的操作就是把经压平、干燥处理过的植物标本,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我”重新泡发。普鲁斯特的还原最终要得到的猎物是一个个事件和场景;而林棹所获得的,更多还是一些剔除掉事件脉络遗留下的零散的感官符码。因此,在林棹写下的最好的句子里,我们能依稀看到法国象征派诗歌那些最具纤细感受性的诗行的影子。不过作者显然没有在这些膨胀活跃的感官因子背后,寄寓某种超越性的诉求。植物身上的每条弯流,每道沟壑都不逸出“我”的底纹:患“收藏癖”者的每一个私物都要被自己穷尽。换言之,它们都是自我为防迷路设下的路标。相反,波德莱尔笔下飞逝的感性经验背后总是潜藏着对无限和超验之物的怀想。
文本里周流的感性符号在不停地挣脱线性时间的束缚;它们之间的共时存在秩序几乎要将小说凝固为一个无时间性的晶体。准此逻辑,这部小说就几乎是无法结尾的了——一如其无法“开启”。但是外在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时间显然不具备终结小说的潜力,就像“香港回归”的时刻在小说里最终只呈现为“晚霞和树荫间静垂的国旗、横幅”的静止镜头。{5}林棹非常明显地看出了小说在凝固和运行之间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于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更多的叙事性因素掺杂了进来;更多的人物走马观花一般制造速度之后就迅速退场。直到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她凭空“发明”出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并最终亲手杀死了他。因此,这个弟弟是一个非伦理性的存在;他更多地像是叙事者用来终结小说的“工具”。
林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自己多次阅读《洛丽塔》的经历。{6}《流溪》中满布的感性细节和枝蔓缠绕的句子似乎都是向其文学偶像纳博科夫的致敬。感伤中微带明快的语调也充满了亨伯特(《洛丽塔》的叙事者)精神。当然了,纳博科夫“终结”小说的技艺显然也给了林棹不少教益:纳式为了终结亨伯特繁冗无度的自溺自欺,不也发明了奎尔蒂这个暗影来使亨伯特顺其自然地“获罪”吗?凡此种种,都是纳博科夫留下的丰厚遗产。但是抛开这些表层的细枝末节不论,纳博科夫文学经验里最本质的一点,恐怕还是由普鲁斯特发明而经他本人大加演绎的“重复美学”。布赖恩·博伊德在其《纳博科夫传》中,曾就这一“美学原理”阐释如下:
“正因为时间如此丰富地抽枝分叉,如此开出细节的花朵,回望就能在过去所有的无限大量的生长中发现单个生命频繁重复的花样,它们似乎就是那个人的独特命运的印记。”{7}
解构主义为这类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既然本源性的事件渺无踪迹、亲缘关系崩解无余,那么唯一的“书写”就只能是这样的书写:不断去呈现原型的“拓路”、遗迹,在增补和延异中捕捉那个可被称为原型事件的“力量”和“效能”。
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命运”由此得到了澄清。从来就没有一个原生性的发端,亲缘关系的代际延续无法赋予意义以内在性。只有通过书写、记忆,密织不同的主题层次去增补命运的图案和纹路。在一次又一次重建图样的尝试中,命运好像隐约发出了微光。在小说的结尾,“我”返回了好像具有本源意义的林场,在湖面一圈又一圈荡开的涟漪里,女性的命运,一种近似原型的命运得到了追认。
四
几乎是猝不及防地,林棹从独语的私密世界转向了沸腾澎湃的他人的、历史的大世界。但这种外在的飞跃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毫无预兆的。《流溪》里存在一条致密的、植物织就的廊道;“我”循着这条通道一路掘回了记忆的吉光片羽。到了《潮汐图》,这条廊道急速地膨胀,繁殖为满溢着历史欲望和执拗目光的航道;经由这条航道,不同的时间相遇,不同的欲望缠绕重叠,私我的故事只是其中复数性命运的某种例证和注脚。因此,《流溪》里漫天花雨般的植物的色彩、纹理、气味被分门别类地澄清、归档、化约,最终凝结为一个人庞大的背影:林奈(科学话语与浪漫主义话语的接触点)。虽然在小说中,林奈只被粗粗地提及,但是他却是《潮汐图》呈现的整段历史的肉身化。
《流溪》与《潮汐图》处理的历史时段乍看起来跨度很大,但两个历史景别的内里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如果说《流溪》里“我”深处其中的信息化时代因泛滥的拟像与孱弱罗唣的自恋独语而显得内里贫瘠;那么《潮汐图》中科学的强势“目力”则夷平了所有的凸起而把世界快速收缩为一个扁平的“博物馆”。就此而论,小说之于林棹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能击穿无法忍受的单调性,把每一个总是显得过多的空洞时间单位点化成内涵饱实的璀璨晶体。换句话说,林棹的小说创作是重新赎回感性和更新世界的“及物性”的尝试。
叙事者问题始终是理解林棹小说的核心。《流溪》的叙事者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自我陶醉同时又自我暴露,很自然地切合一个“自恋主义”时代的文化征象。《潮汐图》里的叙事者则更见综合的难度。就像林棹在访谈里提到的,叙事者之所以被设置成一只巨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两栖属性带来的极大的行动便利{8};除此之外,伴随蛙的还有一个幽灵一般的母亲视角的补足,它能帮助蛙跳出局限于“现实”的视野,从而看到在更丰富的时间维度里发生的寓言般的往事。因此《潮汐图》的叙事者是某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它/她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自然”的视点,而是上帝视角与限制性视角之间的拼贴与综合。拼贴的人物视角本身也确证了讲述这个故事的“难度”:它一方面需要叙事者毫不受限地行动——小说的“航行主题”由此传达;另一方面还要尽其所能地吸附各种纷杂的感性信息并将其织成繁缛的文本——蛙再好不过地满足了这一点;跟人类之间存在的生理差别总能使蛙看到那些被我们的注意力化约成习焉不察背景的感性信息的原始状貌;巨蛙像是患了饥渴症一样地,永不停息地“吞噬”眼前的色声香味。两重视点的综合也让我们后见之明地看到了《流溪》中先就已经存在的,“行动”与“感受”之间的基本分裂。这也是“历史主题”之于“小说”的某种馈赠,或者不如说补救:历史总是已经先行搭好了行动的框架。
五
卢卡奇早已经浓缩地概括了“现代”的命运:现代人生来就是先验的无家可归者。如果我们接受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基本预设,那么可以这么说,《潮汐图》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历史“节点”的故事:在这个点上,命运发生了基本的重组,无论是就历史本体,还是历史内部的具体的人而言。蛙的“经历”象征性地浓缩了这种命运重组在话语层面遗留的痕迹。
小说最开始的时候,巨蛙是分不出性别的。相应地,这个部分的面貌也是最为混沌的。我们直面相逢的是一些无法离析出“意义”的,近乎“原生态”的存在状态。世界蒙茸一体,所有裹挟其中的人、事件、景物、动物之间都没有明细的界限;甚至在人与动物、人与物之间都可以发生瞬间的、无过渡的互渗。人与万物共享一些基本的元素,表层界限的渗透最终能够引起本质的溶解、汇合。鸬鹚胜沿袭世代相传的古法捕鱼。捕鱼的过程连贯,崭截;鸬鹚胜像使唤自己的肢体一样诱使鸬鹚捕鱼。捕鱼事毕鸬鹚落回套竿,似老竹的囚徒一样在竹上遗留一代代鸬鹚的魂灵。久而久之,鸬鹚胜有了鸬鹚态,鸬鹚的生命化合进老竹竿的骨节。鸬鹚、鸬鹚胜、老竹最终像是融合成了一个综合的生命体。林棹在描述珠江水上人家的故事时,所使用的语言也跟文本呈现的那个混沌世界浑然一体,无法脱离。岭南方言词汇、表达法在基本的现代汉语、古白话中穿插镶嵌,以其不透明的化石一般的音形意结合态制造顿挫感和表意的丰富性。这种充满物性论色彩的生命互渗、互化状态在小说里的呈现不是偶一为之的,即使到了历史转折时期,我们依然能够在文本里看到不间断的物质交换和词语的隐喻推演。
与珠江水上人家相平行的(也即相遇前)的是上演解剖大象戏剧的异域世界。“条分缕析”地将大象尸体拆解为三百三十七块骨头。拆解后的象骨被重新拼接成标本后送到了博物馆。这个颇具象征性的“分析”事件(这里我们似乎能看到“分析”的本义与引申义的重叠)意味着与蒙茸一体、万汇同一,无区隔的珠江水上世界平行并置的他者的存在。历史发生转折的契机就是小说里的世界旅行。他带着“分析”技术来到中国,从此那个晦涩难名的水上世界成了“象骨”;如同巨蛙“分有”了性别,“海皮”卸下了自然史。
林棹在冯喜这个人物的身上镌刻下了缝合两个世界的针脚。作为画家,冯喜亲身经历了绘画语法的转变带来的两个世界的转换。小说写冯喜刚落地进入的是一个“无影世界”。根据小说的描述来看,这个“无影世界”是中国古代绘画所表征的那个无深度、非写实的世界。其之所以被认为是“无影”的,是因为冯喜后来师从的詹士的画法较之而言,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每个物体在画面的呈现都携带着阴影。阴影所指涉的透视法预示着其背后潜藏的观看与被观看的主客体关系。这一主客关系不仅仅作为一种空间分布关系,更是一种包含实际力量的权力分布关系。观看的目光的强力被很明确地书写在小说之中:“如果你像望向一种远的、辽阔的事物那样,望着一个人,你就会快活起来。哪怕你周身是很挤逼的,或你竟置身牢笼。”{9}
这种极具穿透力的目光预示了《潮汐图》所写故事之后历史展开的基本逻辑(小说的主要部分悬停在鸦片战争时期),帝国主义主体的空间感和纵深性来源于其将其他国家客体化的能力。凭借物质性强力,帝国主义将自己的话语镂刻在了每一个被其影响的、即使只是半殖民地的国家身上。这种目光本身是均质的,目光所到之处差别夷平。就像给巨蛙看病的那个场面描写暗示的:包裹它的是“一种均匀、平静的室内光”;在这种均衡的光的包围下,蛙的每道褶子都被一视同仁。{10}蛙正是在这种逐渐获得命名、性别、学名的过程之中,日益变成一个客体。经历话语重组之后的蛙的具体命运(充满感性丰富性的),也就随之变成了无他异性的、可以被展览和传播的科学话语/标签。
从此之后,像冯喜一样的人就变成了漂泊者、无家可归者。一套新话语(同时伴随的是具体的历史力量)带来“逼真性”的同时,也打散了旧主体与其固有的话语之间的有机关联。历史中的具体的人随之飘散如幽灵。流播不停的就只有关于他们的故事和只言片语。就像小说里写的,只有漫漶无形的事物才散播得最快。那些泛滥无休的意象和感官体验,一如它们的主体那样,中心散失,意义不定;纯粹就是借着文字激发体验之后迅速消解。{11}如同漫漶无形的主体的流散形态,小说本身的语法也和盘托出:就像卢卡奇提示的那样,怀乡意识成了萦绕无家可归时代小说家的集体意念。随着《潮汐图》的展开,开篇部分的珠江水上世界获得了其精神原乡的地位:在那个世界,语言、人、情感、万物扭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充盈的感官信息在小说中自在、无负累地流转;语词也分有了生命本身的具象直观。
作为一部书写历史的小说,《潮汐图》是满溢着创作者的“自我意识”的;它迥异于那些借着历史的冠冕为作者自己建立空洞根基的“历史小说”。就此而言,《潮汐图》同样具有极强的自反性。小说借蛙之口表达了作者某种自我反思:“你认为我们冷血。可能。我们无视眼前受苦受难的生命,投入自我感动的欢愉。那欢愉无关苦难或福祉,生或死,只关乎审美、新知,和别的什么说不上来的东西。”{12}由此可见,网络时代的历史书写,也不过是借着丰饶的历史的原料滋养完全没有自我充实能力的主体的孱弱虚浮。我们借历史之名与历史保持的最切近的关联也仅止于“审美”关系。自恋的逻辑将历史的一切伦理价值倒转为无利害性的感官游戏。历史材料的范围最终也大不过植物的纹章脉络。因此林棹借白鹤之死写下了历史正义对小说文体再现形式的潜在质询:“雪带来一个匀质、阴薄的新世界。鹤羽散落一地,像泼墨,像怨恨的书写。”{13}
注释: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论现代主义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
{2}{3}{4}{5}{9}{10}{11}{12}{13}林棹:《流溪》,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页、第6页、第33页、第86页、第60页、第193页、第180页、第231页、第231页。
{6}参见《澎湃新闻》特约记者Dzolan对林棹作的专访:《林棹:相比童年对个体的影响,我更关心它被理解的可能》,《澎湃新闻》2020年6月29日。
{7}[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1940—195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8}参见《澎湃新闻》罗昕对林棹作的专访《林棹长篇〈潮汐图〉:用魔幻的蛙,讲述生命与尊严的故事》,《澎湃新闻》2021年11月25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牛煜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