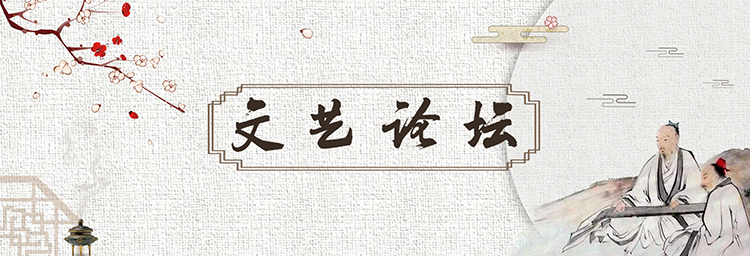

回到“及物”体验本身
——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作家实践经验问题谈
文/简圣宇
摘 要:我国当代文论建设须关注当下作家的实践经验问题,因为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真切具体的审美体验,且基于此种体验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韵味的诗性表述方式和思维习惯。作家擅长以情景化的意象思维去感性把握对象,以细致的切身体验去观察日常生活和以敏锐的个体感受去创造“有我之境”。他们作为实际创作者,更能超越理论语言叙述的局限,用鲜活的感性语言来描述文学创作中种种微妙、生动的创作体验,以“创作本位”的立场将自己的敏锐思考阐述出来。
关键词:体验及物;作家实践经验;意象思维;切身体验;个体感受
我国当代文论建设须关注当下作家的实践经验问题,因为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真切具体的审美体验,且基于此种体验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韵味的诗性表述方式和思维习惯。今日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具体构建,不但需要理性内涵,而且还需要诗性表述,作家的创作经验及其具体阐述为我们的文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精神资源。当下的文艺研究已出现了一种过于倾向于理论本体的“不及物”批评趋势,往往是“理论先行”地去思考和解读文本,而缺少一种与文本密切关联的亲近关系。矫正这种倾向,需要关注作家的实践经验,回到更接地气的“及物”本身。
虽然与文论研究者相比,作家更侧重于具体的创作实践,其叙述语言没有文论研究学科的那种系统性、理论性、规范性,但他们作为实际创作者更能超越理论语言叙述的局限,用鲜活的感性语言来描述文学创作中种种微妙、生动的创作体验,以“创作本位”的立场将自己的敏锐思考阐述出来。故而文论研究者在进行文论探讨时,有必要与作家建立更密切的互动关系,力求实现将理论研究建立在鲜活的创作实践经验之上,两者在积极互动和相对独立之间保持平衡,努力让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保持“及物”状态,更真切、深刻地理解文本内涵,避免凌空建构文论而发生强制阐释等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所谓“当代文艺批评的公共性”。①
一、以情景化的意象思维去感性把握对象
中国学界在参与全球对话和竞争的过程中,愈加意识到我们需要在文学、艺术和设计等领域拿出具有自己的思想、经验和价值观的“中国方案”。其实在文艺批评领域,从作家创作的“及物”体验去寻觅精神资源就是一条极佳的路径。②作为文艺创作者,作家、诗人们格外擅长以形象、生动的诗性方式,运用意象思维去把握对象。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本为一家,有的文艺批评者同时本身也是文艺创作者,所谓左右手交错开弓,也有的文艺批评者尝试将文艺创作的优美和感性融入理论批评过程中。王朝闻先生就曾言:“文艺批评是否可以象文艺创作那样写得美,写得感情充沛,写得引人入胜?许多传统的文论表明,文艺批评自身,是可以当作文艺创作来写作和阅读,甚至值得吟诵的,尽管它不等于文艺创作。……既然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可能是富于个性、创造性和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那就不应当把两者的差别看成是绝对的对立。”③
不过严格说来,文艺批评者和文艺创作者之间的思维习惯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当面对同样的阐述内容时,理论批评者仰赖的乃是抽象的理论思维,力图用概念来把握对象。理论批评所擅长的概念定义和术语描述,往往是将感性经验加以提纯和抽象化之后的结果。这样一来,一方面的确有利于语言描述的精确性和精练性,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原本鲜活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被抽象化,这就像把汁液从柠檬中榨取出来后,虽然所得内容更精粹了,但我们看到的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柠檬。
而文艺创作正好反过来,创作者仰赖的是情景化的意象思维,努力以比喻、类比等通悟手法来把握对象,所以文艺创作者和文艺批评者彼此构成了某种互补互鉴的关系。一般而言,人类面对对象时,其认知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接触对象,在脑海中形成意象,抽象化为语言。所谓文学上的意象思维,就是力图将第二阶段的脑海中的意象尽可能以场景化的文字再造出来,避免将之转换为抽象概念,从而方便读者在阅读时通过这些系列意象进入特定场景,且在场景中真切体会那些难以直接用文字描述出来的微妙情思状态。用陈忠实的话来表述,就是“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也才可能不断触发读者对文字的敏感性,引发他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④读者之所以觉得某些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本特别“有味道”,其关键就在于他们在使用系列文学意象来构造场景方面具有超越一般人的造诣,正所谓“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语),读者得以在阅读时借助着一系列有意味的鲜活形象进入文本世界,以“悟性”而非单纯的理性去把握文本意味。同样由于思维的惯性,作家们在试图以相对学术性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同样带着文艺创作时的意象思维,从而让他们的学术语言带上了某种特别的美感。
这方面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关于如何才能透过时代的喧嚣去把握现象背后最关键的本质,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备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力量?莫言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不是以概念性的学术归纳来回答,而是用比喻来答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里住着,去池塘里捞鱼,看到水面上不断地翻起波浪,以为池塘里有很多的鱼,实际上未必。有时候在水的表面翻起浪花的都是很小的鱼,真正的大鱼在水下是静静的、无声的。也就是说一条小溪可能发出嘹亮的声音,而一条宽阔的大江反而是深水静流。所以对当下这么一个喧嚣的社会,我觉得喧嚣始终是一个表面现象,就像长江、黄河的表面一样,可能有很多的泡沫,裹挟着很多树枝、野草甚至死猫烂狗之类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水下是相对安静的。”⑤莫言在这里没有直接作答,但他的比喻却比分条列项的阐析更具有“可悟性”,在具有相当大的阐释空间的同时,也让人“一触即觉”,印象深刻。
针对创作素材的选择问题,贾平凹认为作家必须“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保持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这样才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把握”。他提出,当作家格外重视某种题材后,他眼前的事物就会自觉分类,这种观察事物的敏感性和分类性甚至是无意识的,正所谓“如果你变成一个磁铁,钉子、螺丝帽、铁丝棍儿都往你身边来。当然,对磁铁来说,木头、石头、土块就没有吸引力”⑥。贾平凹还以踢足球为例描述了他小说的特征,说自己的写法“不讲求故事,也不讲求大致情节”,而是如同踢足球一般,“一只大脚把足球踢来踢去。像是巴萨那种球队吧,就是在门前倒那个小脚,他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看似不经意间,那个球踢进去了。当时我看世界杯时,看到巴萨那种踢法,就像我平常的小说中的那种写法”⑦。贾平凹这淡淡的一段比喻,比学术语言的几段分析都更形象和“入味”,能让人通过这种意象描述来直接观照到他赋予其中的意味。
他之所以要以这种“踢足球”方式来写作,正是为了增加日常事件在小说时空中的厚重度。文本时间与自然时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时间是不为人所控制,与个体生命感受相疏离的。而在文本中,时间被审美化,那些在自然时间中快速流逝的片段,到了文本当中就会流速变慢,乃至被定格在峰值时刻。为了在文本时间中创造感受的长度,贾平凹就采用这种“踢足球”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镇子上的生活尽量写得特别琐碎、特别日常……以琐碎的日常生活来表现重大的事件”,从而借此表现出“更虚的、更荒唐的主题”。⑧
相似的,还有王安忆的“钻石切割面”论,她以钻石的切割面为喻,以具体文本为例,谈道:“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⑨
王安忆此论当中所提“钻石切割”,强调的正是通过将小说中的重要场景加以细致化来增加文本细腻性和生动性的处理方法。该论与贾平凹“踢足球”论虽有差异,但更多的是异曲同工,皆试图从某个细部入手,尽可能地把文本中意象和情境的内在意味以最丰富的样态表现出来。“钻石切割面”论让读者脑海中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一个“钻石意象”,这意象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自足的自我阐释体,它虽然没有具体指向某个具体阐述内容,但提供了一套通用框架,让读者能够通过“感悟”其中意味来实现举一反三的“领悟”“超越”的目的。
二、以细致的切身体验去观察日常生活
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所谓“在场感”,其核心即在于能够直面现场的所见所闻,且由此获得真切的所思所想,实现对现实生存处境的深度介入。⑩文艺创作正是因为其观察的微观和细腻而获得文字的质感,也正是这些文字本身的质感才能触动读者,促使他们将文字构筑的场景和意象在内心当中再现和再创造出来。用自己和他人的切身体验去观察日常生活,特别是将貌似琐碎的细节提升为赋予文本质感的关键节点,乃是文艺创作者最富有自身特点和魅力的地方。
池莉特别从创作的角度强调“生活细节”对文本质感的重要影响,她指出,故事的宏观架构很难逃离“兴衰存亡”“生老病死”这类主题,但细节依旧可以是崭新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拥有绝对不同的细节”。池莉说她由于对生活细节非常敏感,故而喜欢“用密集的细节构成小说”。{11}而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就力图摆脱传统的写作套路:“我不写传奇故事,不写一个人的框架式经历,我尝试的就是用细节来写作长篇。”“阅读这部长篇,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咀嚼语言和细节”,而这样写作的目的就在于试图一窥究竟:“人生中是哪些生活细节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和精神世界。”{12}
贾平凹曾笑谈说:“沈从文讲他是乡下人,我呢是山区人。”他还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一位山区人进城的场景:这位山区人是第一次进城里,结果脚步抬得特别高,原因是平时走山路时经常踢到石头,结果带着这个惯性到城市之后,“他的脚自然还抬得高,他怕石头把脚碰了”。{13}贾平凹这个描述,其实就是一种将个体生命被环境深刻影响的样态以生动的场景片段表现出来。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身边的物质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所规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塑造有时候强大到连个体自己都没法察觉,只有在特定的对比场景中才能以戏剧性的模样显现出来。很多具有意象性的细节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引起注意,但文艺创作者恰恰擅长把这一闪而过的细节瞬间牢牢抓住,固定在文本时间中加以定格、放大和细腻化,使之具备所谓“以心会心”的文学性。
宏大叙事追求的是对具备普遍性、规律性、历史性等重要特征的事件的记录与叙述,那些琐碎、偶然、次要的小细节则往往会在此过程中被忽略,然而对于文学而言,这些细节却恰恰隐藏着诸多来自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是文学需要重点着墨的地方。切身经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其能穿透一般性的宏观叙述和大众认知,关注细节并且在其中发现诸多被忽视的耐人寻味之处。比如,同样是关注服饰,沈从文往往能更细致地观察蕴含在其中的乡土细节,诸如他在谈元代服装时就专门提到,由于彼时平民只能用暗色纻丝制衣,不准僭越使用其他色彩,结果平民反而在此禁令促使下创造出了四五十种命名的褐色服饰,反过来引发流行时尚,影响到帝王也开始采用褐色质材来制衣。{14}同样,由于缺少实际的本土经验,一些学者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时,往往不明白为何本地人要用浸泡米浆和捶打等制作方式将服装制成密实得有些不透风的样式,他们从自己的思维角度出发,提出这是少数民族同胞为了让服装由此变得更笔挺。但其实有本地生活经验的人更清楚,这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项通常不足为外人道的功能:防蚊。西南地区(特别是山区)的蚊虫个头之大,数量之多,是大都市里的专家无法想象的,而浆密实了的衣裤能让蚊虫嘴巴再锋利也无法穿透,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免了被叮咬瘙痒之苦。这些“知识”由于太过细碎和卑微,故而很难从书本上直接获得,而需要自己以具体经验去体会的。这就是贾平凹恳言:“你必须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发生,那个时期树是怎么长的,房子是怎么盖的,那个时期衣服是怎么穿的,人吃的什么饭,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具体是咋回事。”{15}作家必须非常熟悉自己笔下故事,才有可能把这个故事说圆满,把人物塑造得真实入味。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安忆曾在《来自经验的写作》里特别强调:“在我最初的写作里面,经验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吸水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个时候写作就是把吸人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它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罢、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16}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是写作之母,此时正在经历的某些事情,其实就是在为未来的某个时段积累写作的切身体验,为那时的厚积薄发积累充分的素材。
莫言的文本措辞和修辞,被誉为是在“用一种生命来比喻每一种生命”,{17}而这恰恰是因为莫言能够将观察日常生活的细致、真切的体验转化为带着人性温度的具体文字。莫言曾就观察细节的问题谈道:“我记得《红旗插上大门岛》里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真正的渔民,就看她的脚丫子,渔民常年赤脚站在甲板上,小船不断颠簸,渔民要站在船上不停地撒网收网,脚就需要紧紧地扒住船的甲板,所以她的脚趾是张开的,像扇子一样。如果是一个在客厅里长大的小姐,她的脚肯定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我入伍时一件事,当时班长问大家有什么特长,有一个江苏籍战友说自己会开船,然后就伸出两只大手来给我们看,他两只手特别大,手臂特别粗,一看就是把过方向盘的。这两个细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身体特征是和他们的渔民生活、开船的生活密切相关的。”{18}从张开的脚趾到特别粗的手臂,这些都需要作家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去捕捉并且将之化为文本中的具体意象,这样的意象才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感。
三、以敏锐的个体感受去创造“有我之境”
传统的理论研究强调客观性,在文论构建过程中忌讳个人主观意志在文章中直接呈现,因为过多的“我”的色彩会影响研究者作为客观真理代言人的地位。而文艺创作恰恰相反,正所谓“叙述者的视点(与叙述者如何看待和判断事件以及人物相关)直接影响如何叙述”{19},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通常最看重就是作家以个体感受去创造的那种“有我之境”,切忌千人一面、泯然于众人。按照作家的习惯,尽可能深刻地体察和表现个体感受的过程才是写作的核心,至于给出一个具体的客观结论则是次要的范畴。
为了达到“有我之境”,莫言在与军艺学员的对话中谈到过系列观点。一是“深刻体察”论:“任何的虚构都必须建立在作家对生活的丰富体验的积累上,也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上。在写一个人物的语言、行动时,他的语言、行动,言为心声,他这样说是因为心理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他也许说的是虚情假意,也是用好话来讽刺别人,总之一个人的语言里可能带有很丰富的潜台词。”二是“细节捕捉”论:“你的艺术的脉络应该是时刻保持畅通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被别人忽略掉的细节捕捉到,才能把别人认为是很普通、很平常的细节观察到并变成自己的文学积累,将来在写作中,用这样的真实来变成你的虚构。”三是“场景置入”论:为了更好地表现个体生命的内在灵魂,就需要将他/她置入某个特殊的场景之中,让他/她在这个场景中不得不以戏剧化的样态将自己内心以“峰值状态”显现出来。莫言在谈军旅题材时就认为“战争”便是这样一种显现灵魂的场景置入方式。他提出:“人的本性当中和灵魂深处,所包含的最善良的、最丑陋的、最勇敢的和最懦弱的东西,都会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暴露无遗。人的身上最高贵的品质和最卑劣的特性,也都会在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之中得到展示……它会揭示得更加深刻,它会直接触及人类灵魂深处最奥秘的地方。”{20}
莫言这三论散见于他的对话、访谈之中,并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阐释,但这些阐释对于创作论研究而言却颇具价值,与前述的贾平凹“踢足球”论、王安忆的“钻石切割面”论等一样,都颇值得我们在推动当代文论建设时加以关注。
通常说来,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共在”状态,而理论批评更重视的是共性的内容,结果个体本身的特殊体验和微妙感受反而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不警惕这种共性对特殊性的压抑和覆盖,习惯性地按照“共在”状态来书写时代的声音,就很容易滑入概念化、公式化和同质化的陷阱之中,写出一些外观精致却缺少打动灵魂能力的“塑料化”作品。所以王安忆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提法:“艺术要寻找的是特殊性。”{21}王安忆以“缝隙”为喻,提出虽然我们日常所见的生活都是整整齐齐的“一块块”,但其实这貌似铁板一块的生活之中存在着许多“缝隙”,且“这些缝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22}而所谓的“缝隙”,其实就是这种个体生活的“特殊性”。她以“文革”时期自己所目睹的事情为例,谈到在各种后来被固定的概念底下,其实有着各种不被主流书写的生活状态,她从“革命轰轰烈烈”的上海到安徽淮北插队时,看到更多的是农人们在为现实生活而奔忙、焦虑着:“他们关心收成,关心在灾难之间能不能种一些成熟周期快的庄稼,然后把这些奇怪的粮食、很粗糙的粮食做成可以果腹的东西。在他们生活当中,只有一件事情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和革命,就是要非常警惕儿女们和出身不好的,比如地主的孩子结婚。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出路,他们同样警惕着不要和家族势力小的家庭联姻,因为这样也会影响他们的生存。”{23}
在这里,王安忆用自己的阅历阐述了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常识:宏大叙事的类型化框架之下,是失语、隐匿的小人物。农人们在崇高的宣传性书写中被拔高为伟岸的形象,但在现实中却日复一日甚至代复一代地过着田间小动物一般卑微的、担惊受怕的生活。而这就反映了切身体验给观察世界时带来的细腻性和真切性特征。范小青也就“缝隙”问题谈过自己的想法,而她范畴中的“缝隙”,指的是新旧时代交替时,由于两个时代不能完全对榫,故而就会出现“对接不住的缝隙”,她提出,“这种缝隙就是文学的种子”。“个人生活没有太多的惊心动魄,要学会和正常的生活不正常地相处。作家要敏感,才能敏锐。”{24}正如路面上断裂的缝隙容易让驶过的汽车感受到坎坷和磕碰,同样,恰恰是这种生活中的“对接不住的缝隙”,特别能够在鲜明的对比过程中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内心刺激。面对时代之间的缝隙,小人物很难一步跨过去,而往往被阻挡在缝隙造成的断裂前面,甚至掉进缝隙之中,被时代的翻页给压扁了。而表现这种被时代挤压的身体和精神冲突,正是小说能落笔去深刻表现的地方。
对于如何判断一个人物是否为“小人物”,苏童也给出过自己的说法。他认为判断依据并非“社会分工标准”,因为“一个部长一个省长也可能是小人物性格、小人物命运”,“小人物之所以‘小’,是他的存在和命运体与社会变迁结合得特别敏感,而且体现出对强权和外力的弱势”。{25}小说的重要历史使命之一,就是记录和描述这些游离于宏大历史书写之外的“小人物”,透过他们的视域去洞悉这个复杂的社会世界。可以说,小说要写得入味、接地气,就必须将这些在宏大叙事背景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物的生活,通过艺术加工表现出来。这些普通人物看似卑微,但恰恰是这类被历史书写所略去的人物,具体、生动、深刻地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真实复杂的状况。
我们今日构建文论时强调阐述中国经验和发出中国声音,就必须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参与理论建设,符合人民和时代的真切需要,避免出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所谓“失效”问题。{26}而当代作家特别是代表性作家那些独到的思考和表述,正是一种具有时代标识性和较强阐释力的文论资源。故而积极关注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及其具体表达,理解作家是如何用他们的创作经验来思考和从事文艺创作,从而将之提炼为相应的理论成果,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具现场感地理解文艺文本和现象,而且也有利于当代文论建设更具实践性和实效性,是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路径。
注释:
{1}李音:《批评家的任务——刘复生教授访谈录》,《文艺论坛》 2020年第2期。
②柳冠中:《设计是“中国方案”的实践》,《工业工程设计》 2019年第1期。
③王朝闻:《再再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
④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连载四)——〈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
⑤{18}{20}莫言,高博:《莫言与军艺学员对话录》,《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⑥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秘密”》,《群言》2017年第2期。
⑦⑧{13}贾平凹、陈思和、孙周兴:《文学的生成与土壤——贾平凹与陈思和、孙周兴对谈录》,《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⑨王安忆:《丰饶与贫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⑩陈雅琪:《“在场主义”与自由之向——漫谈任东华及其文学批评》,《文艺论坛》 2020年第6期。
{11}池莉:《创作,从生命中来》,《小说评论》 2003年第1期。
{12}赵艳、池莉:《敬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池莉访谈录》,《小说评论》 2003年第1期。
{14}沈从文:《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15}贾平凹、韩鲁华:《天地之间:原本的茫然、自然与本然——关于〈山本〉的对话》,《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16}王安忆:《来自经验的写作》,《光明日报》2015年9月10日。
{17}喻晓薇:《当代文学研究的道与术——张志忠访谈录》,《文艺论坛》 2021年第2期。
{19}刘艳:《余华〈活着〉的叙事嬗变及其文学史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21}王安忆:《艺术要寻找的是“特殊性”》,《博览群书》 2018年5期。
{22}王安忆、张新颖:《文明的缝隙,除不尽的余数,抽象的美学》,《南方文坛》2016年第2期。
{23}王安忆:《王安忆德国谈“启蒙”》,《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20日。
{24}范小青:《泥土一样,种子各不一样》,《扬州晚报》2019年6月30日。
{25}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26}夏可君:《无用的文学批评如何可能?》,《文艺论坛》 2021年第5期。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简圣宇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