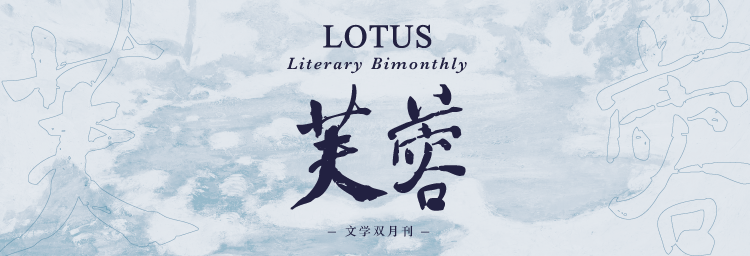

四姥
文/侯严峰
想起四姥,就想起那个叫作王村阎家的村子,想起烙印着一个时代的那些如烟往事。
王村阎家坐落在县城东南约莫九里。村里不光有王姓和阎姓,还有赵、丛、徐、范等姓氏家族。不大的村子,家家毗邻相居,人丁很是兴旺。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每逢寒暑假,母亲总会把我们姊弟几个打发到乡下住上个把月。第一次放寒假到姥姥家,看到南窗外面的猪圈,与茅房一墙之隔的驴棚,还有那口冬天用来储藏红薯的旱井,我感觉很是新奇。冬天寒冷,圈里的粪都冻着,且撒了土,便不似夏天那般臭气熏天。姥爷、姥姥住东屋,我跟四姥住西屋。姥姥家是一处老宅,整棵合抱大树做的横梁,黑黢黢的,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土炕前是一个用几个瓦片围起,再用铁丝缠绕,糊上些泥巴做成的“火炉”,添上些和了黄泥的散煤,烧起来火苗星星点点,还散发着呛人的煤烟味儿。好在堂屋砌有烧麦秸和苞米秸的锅灶,那烟道通过炕洞,就把温暖弥漫了老屋。东西厢房木制的窗户并没有玻璃,窗框里外用白纸糊上,挡风遮阳。快过年了,四姥用一把笨重的剪刀灵巧地剪出好看的窗花,什么鸟兽花草、福禄寿喜的,用糨糊贴在纸窗上,年味就从那窗花上飘荡出来。
四姥那时也就五十岁上下的年纪,却已是满头银发;戴一顶黑毛线编织的帽子,穿一身灰布大襟棉袄,耳朵上坠着一双暗银色的耳环,透着一脸的慈祥。“饥困吗?”四姥问我,操着一口乡间土语。我听不懂,尽管在客车上颠得前仰后合,把早饭吐了个干净,此时饿得肚子咕咕直叫,还是一个劲儿地摇摆着脑袋。后来琢磨,“饥困”的中心词应该是“饥”,也就是“饿”的意思。
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家家户户堂屋正中的桌子上燃起了祭祖的香烛,把平日夜晚幽暗的老宅照得通明;祖上几代先人的排位都写在一张很大的红纸上,按照辈分由上到下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贡品也就那么几样:一碗猪头肉,一盘黄米年糕,再就是腊月蒸的大馒头。时近午夜,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无非是一串串的“小鞭”或二踢脚,家境殷实一些的人家也不过燃放几个震耳的大爆竹,以显示自家的与众不同。村里过年夜不闭户,老少爷们都盘坐在炕上抽旱烟、嗑瓜子、剥花生,唠着家常“守夜”。唯独四姥早早上了炕,倚坐在被子里,手里摩挲着两块磨得锃亮的银圆,不言不语,似乎外面的喧闹与自己并无干系。
年夜饭照例是猪肉白菜饺子,但毕竟是过年了,端上炕的小桌上,还是摆放着几道荤素菜肴,看上去就有些喜庆的样子。外公并不急着下箸,先用锡酒壶给自己斟上一杯温热的烧酒,很滋润地啜上一口,再叮嘱我们:“夹菜时要抬起胳膊,用手扶住袖口,别让袖口落到菜盘里;只能夹自己一边的菜,不能挑拣,更不能用筷子在菜盘里翻弄。”外公早年带舅舅闯京城做小买卖,知晓不少大户人家的俗礼缛节。外公一边耳提面命,一边用手捏住袖口,伸出筷子亲自示范,生怕我这个城里来的毛头小子坏了“规矩”。四姥却不以为然,也不搭理姥爷那套说辞,只是对我笑笑,不停给我碗里夹菜:“过年了,多吃点儿。”
四姥个头高,眉目也清秀,一对大脚竟然躲过了当年女子自幼缠足的厄运,不像姥姥那双小脚,只能满地颠跶着。生活在卫生环境很差的农村,四姥的衣着却总是那么洁净体面,炕上的被褥也归整得一丝不乱。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四姥白天摘下帽子,梳洗头发。有一天到了夜里,四姥以为我睡熟了,便慢慢摘下帽子,卸下发簪,披散下满头白发,口中嗫嚅着:“唉,我的命苦啊!”这时候,我眼前的四姥,瞬间成了一位苍老又令人悲悯的乡村妇人。
四姥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走村串户,与乡邻闲谝家常,整天待在那间不大的西屋里,拾掇拾掇这,打理打理那;唯一的“娱乐”,就是翻翻几本磨掉了封面的小画书,独自把玩那几张发黑的纸牌。
我和弟弟顽皮,不是偷两瓢玉米面喂了猪,就是用木棍敲了驴,要不就是把正在啄食的母鸡赶得满院乱飞。每当闯了祸,我们就会被姥姥斥责一顿,姥爷也会操着带点儿京腔的乡音,喝一声:“淘气!”回到西屋,四姥依然会怜爱地给我们手里塞块地瓜干,或是几粒花生米,从不责怪我们。
姥姥家门前的那口大缸是用来腌菜的,什么大白菜帮、小萝卜头,还有些豆角黄瓜之类的。冬天夜里温度低,早上缸里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把冰砸开,取出几坨腌菜,用水冲洗一下,切上几刀就上了桌。有时四姥会拿来一个不大的瓶子,颤抖着滴上几滴芝麻油,然后对着瓶口舔一舔,我顿时对四姥就有了几分崇敬。
四姥没有子女,也没什么文化,常常念叨的就是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有时还显露出一丝幽默。我们姊弟四人,四姥偏爱大姐,按着我们的名字编了个顺口溜,还合辙押韵:大姐“吃洋梨”,二姐“发大昏”,弟弟“掇尿盆”,轮到我,竟是“拿屁崩”,后面还跟上一句“崩出油来好点灯”。
每次回姥姥家,母亲都会让我们给姥姥和四姥带点儿钱。临行前,母亲总不忘叮嘱我们:“给四姥的钱,别让姥姥看见。”我不明白母亲的用意,只是觉得四姥在姥姥家做不了主,有时甚至像个寄居外姓人家的“客卿”。
姥姥家对面是一户杀猪的人家。屠户阎世达人如其名,长得很是健壮,夏天经常光着膀子,大冷天也穿得单薄。每天早上杀了猪,上午他家院子里支的那口大锅便飘出诱人的清香。猪肉卖光了,锅里煮的都是些“下水”,好像也没放什么佐料,原汤原汁的。抵挡不住那清香的勾引,我时常蹑手蹑脚地踅摸进屠户的小院,盯着锅里喷香的肠肚呆呆地看上半天,大多是吞咽下口水,心有不甘地走开。有时候,四姥会从一块旧手帕里面抠出几个零钱,悄悄塞给我:“去吧,别让你姥爷姥姥看见。”我便趾高气扬地跨进对面的院子,手里排出几分钱:“给!称上一段猪大肠。”阎世达并不因为我们相邻而居出手大方,一双眼睛紧盯着秤杆上的刻度,把那秤杆高高翘起。只要能打上“牙祭”,我才不在乎是不是短斤缺两,还没进姥姥家的门,一小截清炖猪大肠就咽进了肚子。几十年过去了,我竟然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个外姓街坊的名字,一定与他那口细煮慢炖的大锅有着必然联系,当然也多亏了四姥那些毛票和钢镚的成全。
长大后才知道,担心四姥清苦寂寥,母亲幼年时便由长辈做主过继给了四姥做闺女,一直由四姥看护养育。因此,母亲对四姥的感情很深。母亲是抗战后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有一次到县城传递情报,本来已顺利完成任务,可县城的敌伪抓了一个人,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还在胸前一块牌子上写了母亲的名字。消息传到王村阎家,四姥顿时精神崩溃,竟然一夜白头。那时候,四姥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四姥怎么会独身一人?四姥爷在哪儿?这些疑问,年幼时不曾理会,稍稍懂事了又不敢贸然询问。
原来,四姥16岁时就从相隔不远的王村杜家嫁到赵家,夫婿是母亲的四叔。成婚那天晚上,两人还没进东厢的新房,四姥爷就闯了关东,投奔哈尔滨的二姥爷去了。离家时,四姥爷把姥姥给的两块银圆交给四姥,便绝尘而去,不再回头。后来,血气方刚的四姥爷就在东北参加了抗联。1944年春天,有一天四姥爷回到老家,在南邢家住了几天,姥爷得到消息,牵着母亲匆匆赶去。姥爷好说歹说劝四姥爷回家,叙叙家常、看看媳妇,可四姥爷说什么也不肯,接着回部队去了。
就这样,四姥在赵家独守空房,一等就是几十年。
四姥爷在部队做了“大官”。四姥在世的时候,他还托人找过母亲,询问四姥和家里的情形。母亲那时年轻,性情也倔,更对四姥爷的“负心”、四姥的人生遭际愤愤不平,发誓不再认四姥爷这门亲,把四姥爷抛妻不归的事一顿数落后,不客气地把来人打发走了。此后,尽管四姥爷那边不时还有音信传来,但母亲执拗地不再理会。后来还是大姐告诉我,年少时,四姥爷曾在集市上见过四姥,并和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奚落四姥那双不合时宜的大脚。不承想成亲时,洞房里的新娘竟是四姥!
我宁愿相信,是时代的局限,还有少不更事的青涩和战乱频仍的年月错失了他们的姻缘。
四姥虽然没有跟四姥爷过上一天真正的夫妻生活,但她内心深处一定还记挂着那个男人。村里南街有一位妇人,长得矮墩墩的,人称“小老婆”,是四姥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人。“小老婆”的境遇和四姥相似,也是男人婚后不久“失联”,但在“小老婆”病重弥留的时候,她那出走多年的男人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在四姥看来,“小老婆”还是幸福的。
母亲跟四姥亲近,一直称呼“婶妈”。为了孝敬四姥,进城后,母亲时常会把四姥接到家里,让她享受一下城市生活,同时帮忙照看我们姊弟几个。
不知为什么,生长在乡村的四姥却痴迷传统京剧。每当闹市区“新世界”附近的大众剧场上演京剧,父亲就会弄来两张票,让四姥带上我看戏。儿时的我,自然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没有兴趣,进了剧场,看不上几眼,就趴在四姥腿上睡着了。四姥却打熬得住,通场看完,意犹未尽。
1967年我上了初中,又赶上社会上乱糟糟的,寒暑假就再也没有回过姥姥家。
第二年,带着对人生许多无奈和抱憾,时年56岁的四姥走了,走得急促,也安详。四姥慈祥的面容,戛然定格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填满了我对那个时代乡村风习的怀恋。
后来,我到了部队,成为宣传队的一名文艺战士。有一年宣传队到姥姥的家乡慰问,演出结束后我请了假,趁夜赶到王村阎家。那时姥爷、姥姥还都健在,也还像往年那样住在东屋,只是西屋空落落的,了无生气。第二天,住姥姥家隔壁的表嫂带我来到一片荒地,那里孤零零地凸起着一座坟茔,就是四姥的安息之地。听表嫂说,跟四姥一同葬埋的,还有四姥珍藏的那两块银圆。平生第一次,我双膝跪地,给四姥磕了头。
四姥离去已经50多年了。我想念她。

侯严峰,新华社高级记者。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新华社胶东支社社长、黑龙江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总编辑、湖南分社社长。出版有《新闻的律动》、记忆文学《何处归鸿》等作品。
来源:《芙蓉》
作者:侯严峰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