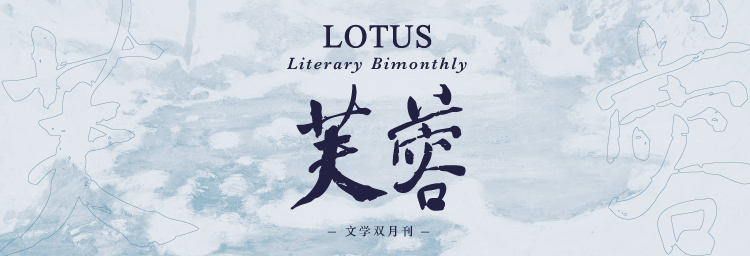

冰雪的家(中篇小说)
文/卢一萍
喜马拉雅,藏语意为“冰雪的家”
——题记
乃堆拉
乃堆拉,海拔4475米,藏语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公路贸易通道,每年4月至10月可以通行。乃堆拉前哨雄踞通道两侧,中印两军哨位仅隔一道不高的铁丝网。两国哨兵面对面挺立,可看清对方的毛孔,听见对方的心跳,感知对方的呼吸。目光、瞭望孔、射击孔、堡垒……一切都是相向的,那道积雪永远难以完全消融的山脊格外森严,加之云遮雾罩,使整个前哨笼罩着铁血而神秘的气氛。
艾札达站在哨位上,俯瞰雪线下郁郁苍苍的亚东河谷。在雪线附近,有茂密的杜鹃林,杜鹃花会在六七月间盛开。但他仍经常感觉缺氧。寒冷也是一个考验。山巅的寒风四季喧嚣,没有阻挡,穿透人体,加之空气潮湿,严寒倍增。刚来不久,他的手脚、耳朵和脸就被冻伤了。
艾札达没有参加高考,高三下学期就报名参军了,那是1990年。他本可到驻疏勒的某步兵团服役,但他自己要求到西藏。路途是遥远漫长的。接兵干部带着新兵,先从叶城乘班车到喀什,再乘班车到库尔勒,从那里坐火车到兰州,从兰州换乘去格尔木的火车,然后坐汽车团的运兵车,一路向上,翻越昆仑,到了拉萨。视野里雪山巍峨,河流封冻,原野沉寂,艾札达心里热血涌动,不时也掠过一丝惧怕。但想到父亲艾喜河已在高原戍边20多年,便舒了一口气,平复了心情。高原冬日的荒凉有万千重,似永远也难以完全跨越。但当车队从拉萨向西南方向继续行驶,南下到江孜后,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河谷,河流竟然开始解冻,一路植被越来越多,最后终于来到了服役地亚东。
在亚东结束新兵训练,河谷已到春色烂漫的时节,艾札达被分配到乃堆拉前哨。乘汽车盘旋而上,他感觉一路向天行。50多公里山路间,春夏秋冬、风雨雷电全都经历。到连部时,春光敛尽,已是风雪弥漫,军车不能再往前行,艾札达只能改成徒步。他很快发现,除了可能爆发的战争中的敌人,在乃堆拉还有三个敌人需要常年与之战斗,那就是大雪、大风和雷电。
雪是常年飘飞,每年10月到来年6月为雪季,3月至6月还常常雷电交加。即使不在雪季,七八月也可能突然大雪弥漫。冬天,哨所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20摄氏度。一夜之间,积雪可厚达四五米,营房被掩埋了,阵地之间需要执勤往来,只能用铁锹从门缝里一点一点把积雪凿开,凿出通道。因此,铁锹变成官兵们最常用的武器,每间营房必备数把。雪厚的地方被凿成雪洞,雪薄的地方开成雪壕。神奇的是,天气好的时候,隔着冰雪,可以望见亚东河谷满谷翠绿,如同翡翠铺就的梦境。
乃堆拉位于雪山之巅,没有任何阻挡,不大的风也会变得格外犀利。而每年10月至次年3月的风速可达每秒12米,风声凄厉,鬼哭狼嚎,地动山摇,大地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人像驾着小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
风来的时间像是定好的:晚上起风,清晨风停。能刮走的东西都被刮走了,甚至让人觉得整个山头都会被风刮到月球上去。哨所的东西都得收进屋里。但屋顶的铁皮会被揭起、刮跑。即使把铁皮钉得再牢,还是抵挡不住风粗暴有力的大手。就这样,白天把铁皮找回,用铁钉钉好,晚上又被掀起、刮跑。如此反复。
所以,连续刮风的日子,大家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铁皮。有时候,风从印度方向吹向我国,印军营房屋顶上的铁皮会被吹入我境;风从我国吹向印度,我军营房屋顶上的铁皮就会被吹到印方。我们找到印军的铁皮会送还,他们找到我们的铁皮也会如此。守在哨所,大家满耳满脑都是尖厉的风声,想着的都是那些随时可能被吹走的铁皮。
乃堆拉下雨下雪前,还常常电闪雷鸣,有时持续好几个小时。炸雷贴着山脊,贴着墙壁、屋顶,甚至贴着头皮隆隆滚过,那巨响令人心惊胆战。闪电从乌云密布的天空直接击中山顶的岩石、积雪、营房、哨楼、掩体,电光闪烁,像电影大片里的特效场景。因此,哨所里的床、桌椅、门窗都是木质的。雷电一来,室外不能背枪,必须迅速将枪放入木制枪柜,并平躺到木床上,一动不动。办公用具在雷电中噼里啪啦直响,即使用的是防雷插座,效果也不佳。通信机房最易遭雷击,通信时常因此中断,其他电器也常被雷电击坏。
打雷时,可以清楚地看见窗外铁栏杆上被雷电击中时冒出的火花,听见刺啦啦的声响。两件连接不紧密的金属器之间,发出的响声则如放鞭炮一般。打雷瞬间,灯泡可能会骤然亮起,墙壁上的插座突然刺的一声,冒出黑烟。最危险的是锅炉,那上头有烟囱,又有铁器,电光直闪,刺人眼目。最惨的是变压器,它经常被雷电击坏导致停电。而进入雪季后,用电情况更为复杂:电线结满厚冰,电线杆上的瓷绝缘子也与冰雪结为一体,输电线路损坏了,电杆也经常被大风吹折,被冰雪压断。所以,雪季停电是常有的事,最长的一次从头年10月停到了次年6月。一旦停电,哨所就只能用汽灯或蜡烛照明。
但即使乃堆拉雨雪这么多,哨所地处山巅,水很难留存,官兵们雨季靠接雨水,雪季则背雪化水,每一滴都非常珍贵。雨雪两季之间,有两个月雨水较少,雪也变薄了,他们只能到离哨所两公里外的冰湖凿冰取水。湖水浑浊发黄,但味道仍比雨水和雪水好了不少,至少没有泥腥味。
哨所的肉食可腌成腊肉,做成风干肉,但新鲜蔬菜很稀缺。这里只有一条狭窄的简易公路通往外界,一下大雪,这里就会与世隔绝。封山后,团里派工兵连来开通道路,常常是刚开通,一场大雪又把路封冻起来了。那是一场绝望的战斗。所谓取胜,只能等风雪自行停止。冰雪封阻后,团部只能把蔬菜送到连部。乃堆拉的战士除了站岗执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到连部背菜。前哨到连部9公里,路上雪厚达2米,不少时候,一脚下去,就骑在雪上了,很难动弹。开路的人最累,所以得轮流来。一般是早饭后出发,到连队吃完午饭后立即返回。下山时,有些地方可以直接往下滑,又没有负重,两小时左右就能到;返回是上坡,每人还要背30公斤蔬菜,最快也得四五个小时,如果下雪,可能要摸黑走到凌晨。
尽管生存条件如此艰苦,但战士们一天24小时站岗执勤、观察巡逻是从不间断的。艾札达与风雪雷电战斗两年之后,担任了前哨班班长。担此重任没多久,也即5月15日,中印双方要在乃堆拉举行边境会晤。这里还没有会晤站,只能清理出一块空地,搭建帐篷。这个任务自然要由前哨班来完成。
亚东河谷即将进入万物葳蕤的夏季,哨卡的积雪仍厚达两三米。由于人手少,从国际劳动节那天开始,艾札达就带领战士们清理场地的积雪,但总是白天清理出来,晚上又堆满了雪,有些是新下的,有些则是大风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的。艾札达只能带领大家连日劳作,到13日下午,场地终于清理出来。搭好帐篷后,每个人都在祈求天老爷保佑不要再有风雪,但老天像故意和他们作对,当晚一场大雪,帐篷塌了,钢架被折断,厚实的帆布被撕裂,平铺在地上,然后被积雪掩埋。
艾札达站在风雪里,看着那一大堆积雪,想哭,却哭不出来,那些战士还需要他这个班长去安慰。他打电话把情况报告给连长,连长又立马报告给团长,团长当即安排在亚东重新购买钢架,尽快运上来。艾札达带着战士们,把雪挖开,把帐篷被积雪撕裂的地方用铁丝固定好,准备等钢架运上来后立即重新搭建。
可道路被积雪封堵了。团里调了两台推土机开路,到晚上10点多,才走到距离哨所12公里的地方。夜黑风大,积雪很厚,路况不清,推土机不能再贸然作业,汽车卸下材料后,只能就地返回。艾札达带着9名战士,徒步下山,去把那些钢架扛上来。
因为季节,白天气温上升,冰雪融化,雪水横流,寸步难行;晚上气温下降,雪水和积雪冻在一起,硬如银甲,一步三滑。加之夜雾弥漫,大家打着手电,即便每走一步都异常小心,仍不时滑倒。走到卸货点,每人要扛40多公斤的钢架,向哨所攀爬。他们直到凌晨4点,才艰难地回到哨所,每个人都累得恨不得立马躺倒在雪地上,呼呼大睡。但当天上午10点就要会晤,大家匆忙填了肚子,又继续干活。上午9点半,帐篷终于搭好,半个小时后,会晤准时举行。
艾札达从新兵训练结束后来到乃堆拉,就一直守在这里。按照部队规定,戍守士兵每年可轮换一次,但他不愿轮换。他说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面官兵的相貌,天上的风雪雷电,脚下的每寸土地、每丛苔藓……
他在前哨班待了两年后,觉得自己应该算一个高原人了。他有了当地人的肤色、疾患、生活习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已把自己从一块昆仑山的羊脂玉变成了一块喜马拉雅山的岩石,没有那么娇贵、易碎,可以随便摔打了。
1993年,艾札达考上了西安陆军学院。8月21日,当他要离开乃堆拉时,竟很是不舍,好像一离开这里,就再也难以归来。他和送行的战友一一拥抱后,望了一眼山顶上的哨楼,又望了一眼正在雪线附近盛开的高山杜鹃,在心里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节选自2025年第5期《芙蓉》卢一萍的中篇小说《冰雪的家》)

卢一萍,四川南江人,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新寓言”四部曲《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少水鱼》,小说集《帕米尔情歌》《父亲的荒原》《名叫月光的骏马》《无名之地》《N种爱情》,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扶贫志》等三十余部。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好书”奖等,作品入选亚洲周刊十大小说、收获文学榜、芙蓉文学双年榜。
来源:《芙蓉》
作者:卢一萍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