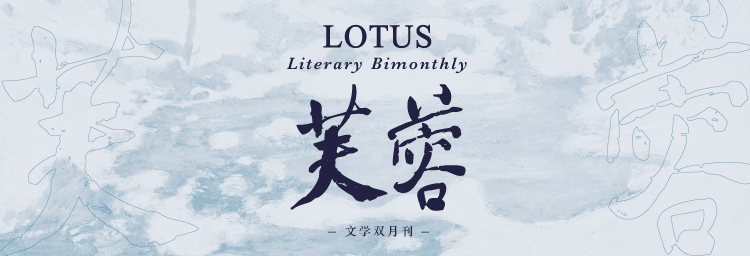

码头上的生灵
文/李颖
父亲在一条大黄狗身上耗费了太多的力气。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除了鱼,他能给家人的最贵重的礼物,便是那条狗了。狗是他捡来的,据说是一条流浪的野狗,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数,能够将那么大一条土狗捕住并顺利押解回家,他疲惫而亢奋,像是刚从荒野里搏斗归来的猎人,押回了一份困顿岁月里难得的体面。事实上,作为一个养家的男人,他学会了很多秘而不宣的绝技,他总能在贫瘠里打捞出奇迹。比如他会用竹篾和尼龙线手工制作一种叫作扳罾的渔具。多年以后,我在《九歌·湘夫人》中读到“罾何为兮木上”,才知道他做的那种渔具可追溯到先秦以前。20世纪70年代的雾霭里,他像远古的渔猎者般,用古老的生存秘术,试图填满我们姊妹的欲壑。
他捉住狗的那天艳阳高照,春风十里,为他得胜归来做好了铺垫。大黄狗被绑在家里养了两个月,父亲觉得它已经足够老了,便决定将它绳之以法,吊死在门口那棵苦楝树下,弄给我们吃,他兴奋地想象了很多种吃法,甚至包括腌制腊狗肉。
可是一条狗犯了什么天条要被处以极刑呢?父亲说,猪猪狗狗就是用来吃的。父亲特别亢奋,大张旗鼓地做着准备工作,带着表演性质,希望城陵矶全部的街坊邻居都来看他打狗。城陵矶是我出生的地方,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城陵山”早已被浪涛啃得只剩嶙峋骨节。长江和洞庭湖在此交汇,我们住在离水最近的堤街上。这是一条无比脆弱的街,每年夏秋江湖水涨,广播里播报着城陵矶水文站的水位监测数值,当收音机里面说城陵矶三十四点几几米时,第一个被淹掉的就是我们家了。
父亲用粗麻绳将大黄狗悬在苦楝树下的那个正午,整条街的蝉鸣都在沸腾。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树皮簌簌剥落,狗的眼珠凸得几乎要挣脱眼眶。年幼的我空洞地和那条即将失去生命的老狗对视,内心波澜不惊。我至今记得它后腿在空中画出的弧线,记得它的瞳孔里映着整个颠倒的世界。但父亲干活总是毛毛躁躁,母亲每天都会说他“圆手板,十个指头没开叉”。当他转身去拿工具的刹那,那条被命运选中又抛弃的狗,竟在生死间隙爆发出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狂奔逃离。背着手、伸长脖子围观的邻居们发出惋惜的惊呼,父亲追出了几里地,终未寻到。
那天父亲追到江堤尽头,甚至对着码头边货轮远去的帆影骂了半个下午。母亲倚着门框择菜,菜根丢进盆里的声响格外清脆。“畜生通人性呢。”她像是在说狗,又像是在说人。她似乎并不赞成父亲杀掉那条狗,但她也并没有过多阻止。对于狗逃跑了这个结局,她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绪。
这次失败的行刑仪式成为父亲毕生的隐痛。此后大半年,他出门必定要带一根粗木棒,双手背在身后,等着找到那条狗,给它致命一击。
于是,当年父亲拿根木棒四处转悠寻狗,成了城陵矶码头、河街上惯见的场景。街坊邻居见他背着手持着木棍到处转悠,都会问上一句:“李师傅,又去寻狗?”他们的语气里藏着整个城陵矶街坊对失败者的怜悯。
我的母亲说,寻不到的,不要寻了,说不定早就进了人家的肚子。
“它跑不了。它跑不了……”有大半年,父亲都在念叨这句话,他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世界听。父亲负气地拎着棒子逡巡,一遍一遍搜寻城陵矶所有的街道、码头、货仓,甚至伸长脖子探向别人家的窗口。他觉得所有人都在暗地嘲笑他,包括藏在暗处的那条狗。
父亲追到吴聋子家。他疑心吴聋子把他的狗藏起来了。吴聋子并不是真的聋,只是有些耳背,然而他力大无穷,父亲不敢真的找他理论,只好站在他家门口指桑骂槐。父亲低声咒他:“吃了狗肉去死!”吴聋子说:“李师傅吃了没?当中班去啊?”——“吃了没?”在那个年代相当于现在打招呼说“你好”。父亲便背着手讪笑着走了。
后来父亲晚上也出门寻狗,在一个白露沾衣的黎明,我趴在窗户上看见父亲在屋后的江边站成一块黑礁石,我忽而疑心父亲的黑影才是真正的木棍,我疑心他想对着这个世界当头一棒——他被那条不知所终的黄狗折磨成了会走动的木棍,会喘气的木棍,会在深夜里负气出门的木棍。
那些天,他都回来得很晚。后来,我一度认为是城陵矶的码头吞噬了那条狗,由此我对那些码头总是怀着莫名的戒心,码头吃掉了那么多时辰,吃掉了那么多月光,却永远喂不饱自己。
月光洗白了所有归途,父亲的脚印长出青苔。或许,当年那个晚归的父亲,他从未真正离开过码头,他早已是码头的一部分,他困于那个码头现场,他的工作是在那里装卸沥青,余下来的时间便是追逐那条逃亡的狗,而这也从来不是一起简单的狩猎事件,更像是一头困兽对另一头困兽的穷追不舍。
(节选自2025年第6期《芙蓉》李颖的散文《码头上的生灵》)

李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天涯》《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芙蓉》《湖南文学》《文艺报》等报刊。获2015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首届湘江散文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李颖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