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川静美无恙,世间有爱堪怜
——读起伦《山川与尘世中的热爱》
文/凌之鹤
你回你的村子去吧
你祝福故乡的悬崖吧
那赤裸的泥土是你的黎明
——佚名
虽从未谋面,但我一直关注诗人起伦的创作。最近偶然读到这组像在旷野中呼吸般的自然而清新、具有传统汉诗气象的短诗,激起我无限美学想象,亦激起我多重牵挂与无边忧思。被一波又一波狂热城镇化与工业化浪潮频繁侵扰的大地,被高门票围困的极美山川,那些被迫人为搁荒、失去稻香蛙鸣的土地如今是否安好?那些仅仅只为改变人生命运投奔都市闯天下的兄弟姐妹,如今是否还愿意回到面目全非的乡村?那些飘零江湖多年的游子,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世事如何激荡,人心如何纷乱,行走于红尘世间,放眼天下,极目山水,我们仍需要从伟大的“诗教”中获取精神营养、思想力量和至爱大美的源泉。观天象,听风声,察世道,炼人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人以爱美之心,诗人以悲悯之魂。诚如谢有顺所说,文学创作要“从尘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置身世俗红尘仍然记得追究高洁的灵魂何在,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获得诗意的人生并活出人之为人的体面与尊严。
1
余世存曾感叹:多少文人一脸浊相,多少官员望之不似人君。化用余先生的话说,今日诗界,多少诗人浑似流氓、疯子,多少诗歌读来只是一堆鬼话、废话。君不见,这些年来,诗坛山头主义横行,荒唐的诗歌事件此起彼伏,真正的大诗人和优秀的诗歌被喧嚣的山头主义与诗霸们排挤、遮蔽。诗坛呼唤清新的大雅之风,期待恢复纯粹雅正的汉诗传统,尤其需要清醒睿智的大诗人。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起伦的《山川与尘世中的热爱》,就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好诗。说起伦的这组诗歌好,主要是因为这些诗里弥漫着我们熟悉的中国诗歌的气息,它们鲜有从西方诗歌那里舶来的生硬的洋调子,不晦涩,语气平和,义理贯通,造境讲究,譬如碧空云里看鹤出没,又似月夜空山恍闻花落鸟鸣,诗意昭然:一般读者能清晰地读出诗歌表层的意思,也或多或少能感受得到诗歌深层内蕴的力量与美。此即传统诗论所主张的“妇孺可解”是也。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早已厌倦了那些故作高深,梦呓似的、不着边际的、索然无味的分行句子,它们含义混沌,语法乖张,了无生气。而从起伦的这组诗中,我们不仅能看见山川独特的气象与风度,还看得到烟火红尘中的唯美风景,感受到诗人的性情和胸襟,听得到诗人平静的心跳和自然的呼吸,体会得到人生命运的颇多奥妙。这些都是中国文脉或汉语诗歌里至为宝贵的文化元素。
2
《山川与尘世》共28首,分为上部和下部。
上部:《山川静美,我在其中》,写的是“我”眼前熟知的名山大川。诗人抒写的对象是自己故乡湖南的部分风景名胜,也是他的游历修行感悟。面对巍峨的南岳、神奇的张家界、浩瀚的洞庭湖、滔滔北去的湘江和蜿蜒的浏阳河,还有诗魂涌动的汩罗江,面对故里祁东,甚至桃花源这样传奇般绚丽的山川景致,就算用千言万语来描述它们的景色之美,也不过分,也难穷尽。但诗人没有用华丽的言辞来赞美,而是避实就虚,采取大写意水墨笔法,单刀直取诗核,语言干净,用词精准,只用寥寥数行,就简洁明快地勾画出这些奇山佳水在自己眼中、心里的生动形象;尤为难能可贵者,是诗人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现场感,以及为山川代言立传的真诚与自信。面对这些雄奇的山川,诗人并没有兴起“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历史感慨,也没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种“相看两不厌”的多情自白;在诗人眼里,千山万水行来,那山还是山,那水还是水,他仍然只想坦然地在静美山川中独自徜徉。
下部:《尘世中的热爱》,诗人书写的仍然是我们目光所及的寻常物事,比如黄河、老树、天空、杯盏、猫、疾病、秋风、风筝和铁轨之类的器物与症候。诗人借俗世风物,写尘世风情,写天地人生,写实景幻象,写俗丽和惊艳,写内心历险,写精神长成,归根结蒂,是写我们对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唯一的人生滚烫的原初大爱,写人生孤独、缓慢而执著的自我圆满。下部中一些诗显得过于通俗,表象过于严峻而几近僵硬,没有上部的灵动与通透,也许,这是诗人太过于热爱这有且仅有一次的人生吧?
钱穆说:“摩诘诗若是写物,然正贵其有我之存在;子美诗若是写我,然亦正贵其有物之存在。”起伦的诗,吾亦贵其写山川“我在其中”,写红尘中人情世态,亦有山川风物在焉。
3
仁者乐水,智者乐山。山川仁德,非常人所能体会或言其妙。起伦对故乡山水的诗意诠释,可谓情真意切,山高水长:那些山,一直在他胸中起伏;那些水,一直在他心间流淌。因此,那青山碧水便有了淋漓可见的精气神,有了生命体温,有了鲜明个性,有了天下知音。
帕斯警告过:解释一首诗是一种罪孽。但我还是想痛快地冒“罪孽”之险解读起伦的诗。
试读《南岳》:
山在坐禅。每一块石头谦逊之外表
藏有深刻的奥义。四季不散的
雾,是慢性子的领悟;欲盖弥彰地提示
有一颗未知的、但确凿存在的心
期待我,倾听我。我出发,坚定而沉默
——我在此,而终点只是你!
人云“衡山如飞”,可见其气象非凡。面对“变应玑衡”“铨德钧物”的南岳“飞山”,诗人只用短短六行,便巧妙地勾勒出这座名山的仙风道骨、气势与象征。堪称经典。危崖怪石高耸、云雾弥漫的“山在坐禅”,人在参悟——行吟至此的诗人,倾听到谁的心跳?他的终点,又岂止衡山耶?对于一个敏感多情的修行者来说,作为终点的这个“你”能指何其丰富!同样写山,传说有神仙居住的张家界,群峰林立,云横雾绕,险象环生恍如仙境。但雨天前来探访张家界真容的诗人,面对“仿佛这无中生有的巨石沟壑”,当守得云开雾散之时:
我所看见的,乃更大的奥秘
我无言,那是沉默的真相
大象无形。大美无言。大音希声。张家界之诡谲梦幻之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置身此境,诗人俨然哲学家,发出了“其实世界/从不为意义而存在,或者说,世界本无意义”。美,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余秋雨所说:艺术世界的至高部位总是充满神秘。(《断裂的爱》)写到《回雁峰》,感喟“将流浪当作家园”的诗人感觉那从眼前一晃而过的山只是“视域里一个遁点”,而岁月流逝,光阴似箭——诗人直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说的必须沉默”,委婉地表达了对神秘自然的热爱与敬畏,欲说还休,格外节制。
“山水犹人待知己”。如果高山提升了诗人的精神海拔和峻峭之美,那么,浩荡的江湖则滋养了诗人思想的深邃和辽阔。在起伦看来,月光照耀下的八百里洞庭湖,仿佛可以把玩于掌中的千年青花瓶;而当他再次注目“蓝焰熄灭”的汤汤大湖时,他竟惊异于“时光的深不可测里/思想者的粮食,至今填不饱星空的饥饿”。起伦为何会有如此奇幻而清醒的观感呢?原来,他一直希望在众声喧哗里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超越先贤,“继续我那毫不动听的呐喊。因为/我必须为渴死在半路上的向往招魂”。(《洞庭湖》)读此诗我心为之一颤:夸父追日的传说依然令人动容,但我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何在?江河的训诫值得玩味。在《湘江》一诗中,起伦对湘江北去的宇宙法则欣然认可,对自身命运的铁律也有了自觉确认。逶迤龙行的济阳河,其强大而隐忍的生命力,则让生活在它身边近三十年的起伦对生命天问于瞬间获得了顿悟;这条河(也许一切的河流)作为一种生命的象征,已经不能再困扰或束缚诗人:
从一把门锁,到一条开启我思想更为澄明的路
星辰驻足苍穹,俯瞰它汇入湘江走向大海
这是怎样的启示拉直我头脑中的问号——
生命来自无,亦走向无:那无比充盈的无
如此深沉、壮阔的生命体验,无中生有,大有大无,虚实相生,颇具老庄之风。屈原投身的汩罗江,绝对是中国江河中的一首悲情长诗。我们看到,太多的骚人墨客,面对浩荡的汩罗江,只能发出兔死狐悲的凄凉哀鸣,只会作千篇一律的矫情挽歌,但起伦却别开生面,化悲剧为喜剧,以讽喻诗笔颠覆屈子投江的意义与后人所谓的“端午节名义”之可疑;他不相信诗情汪洋的“蓝墨水的上游”可以掩盖半部战国史的荒唐,质问“那时楚国之天,哪有蓝色的抒写?”相反,是三闾大夫如悲愤之石的自沉,才成就了汩罗江的千古诗名。巫风也许难止,牢骚与毒草仍然滋生蔓延,幸好——“石破天惊!让我看见一个灵魂分娩的风”。这浩荡的正义“天风”,起自“楚辞”,迄今仍在中国诗歌的旷野中激荡着沁人心脾的王者之香!
再读《惊艳》:
慵懒的大地何时理会过光阴的紧迫?
紧迫的光阴又何曾理会一个人生命的短长?
在她那里,所有人不过一眨眼的呈现。
但她,那一刻呈现的美丽如此安静与清晰
我敢打赌,大地也为之惊讶,时光也为之驻足。
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足够温柔的双手
用漫长的一生,从容不迫,细细描绘……
《惊艳》这首短诗诚然令我们惊艳,如果不潜心阅读,它其实也令人深感困惑。它甚至会让诗评家绝望而无语。这七行诗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诗人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大地,光阴,人生,“我”,——这几个关键词,能否揭示这首小诗的真谛?大地苍茫,紧迫的光阴是相对刹那间的人生而言的,显然,时间与大地同构而且永恒,人不过其间过客耳。李白早就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在她那里”的她,实则指时间也;紧随其后的“但她”这个她,已然指向身为过客的凡人,这个她,尽管眨眼间就会消失,但因其“那一刻呈现的美丽如此安静与清晰”,以至永恒的大地为之惊讶,时光也为之停留。从这个意义上考察,生如夏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的“她”是何等惊艳?她,由女神(具有化育之德的母性)而转化为生命的隐喻,而生命因爱得以繁衍并生生不息,与天地光阴共存,难怪大地会为之惊讶、时光会为之驻足。感动如是,难怪诗人愿意用漫长的一生,以温柔的双手来从容不迫地描绘生命之大美、人生之可爱……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粗浅解读;诗无达诂,《惊艳》丰盈的旨趣,取决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理解能力。
4
乐于“盘踞内心”的起伦具有极强的自省能力,稳得住“内心的江山”。这是决定一个诗人能走多远、飞多高的关键素养。空洞的抒情出不了好诗歌。睿智与冷静的异秉,理性和情感的超常平衡,这些品性在起伦的诗歌中浑如繁星闪烁,分外引人瞩目。但这些都显得波澜不惊,不着痕迹,显示出颇为高妙的世术——不动声色,不是炫技,是胸有成竹的从容自若,亦是深思熟虑的自然表达。起伦像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一样,拥有一种“废话少说”的觉悟。他的诗,删繁就简,用语朴素简洁,结句结实有力,乍读可能稍嫌言语朴白,再读却别有韵味,端的是真水无香、菜根有味!从精神家园的《桃花源》到物质世界的《岳阳楼》这两首小诗,庶几可以验证我对起伦其人其诗的气质和品味判断。
陶渊明虚构的世外“桃花源”,是后来一代代文人向往的精神净地。然而,我们知道,所谓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纯属子虚乌有,即或有吧,这浪漫的乌托邦也绝对不在权力可控范畴内。即使每个人心里都有“虚构之权杖”,但面对人造的“桃花源”,回眸喧嚣的现实世界,天真烂漫的年轻诗人彼时只能“得出无关痛痒的诗句”;到了五十岁后,深秋再去时,诗人已获得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我想再去,眼里必无游人。世事纷繁啊
那么多人面对权力始终保持立正姿势
我学着陶令给自己下道口令:稍息
——《桃花源》
这是起伦的冷幽默,更是他的铮铮傲骨写照。辛家轩词曰:世事从头减,秋怀澈底清。是啊,世事尽管纷繁,但我们可以试着放下,像诗人那样“用最痛快的减法,把一切都减去”。人生苦短,何妨活得洒脱些,敢于对权势说不,不为五斗米摧眉折腰——不是主动向权贵献媚,想方设法去无耻地攀附特权生活,夫如是,我们定会领悟到,所谓桃花源,仍在我们心灵深处。
与当代都市中高耸的摩天大楼相比,层高三重的岳阳楼谈不上巍峨,但它代表和彰显的人文历史观与道德伦理价值的高度,却是当下任何一座豪华高楼都无法比拟的。这也许就是后人为何要不断仿制重修岳阳楼的缘故。自滕子京重修斯楼、范仲淹倾心作《岳阳楼记》以降,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无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以生于忧患为荣,死于安乐为耻,毕生追寻忠君报国、造福黎民百姓之道。今日的岳阳楼,俨然中国政治文化伦理之荣耀地标矣。然而,起伦并不陶醉于这座天下名楼的神话,更不轻信那些言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台上满口道德文章,台下却奉行丛林法则的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的肉食者。
你看,登临岳阳楼,起伦并没有故作高深发浩然忧思之叹,更不无病呻吟强作忧欢论;反之,他只是警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铭文已成为“某个行道之标签”。他发现“声名与崇高被谬误的砖石/堆砌得越来越高。显而易见的道理/往往被视而不见”。集体假装无意识甚至集体故意失语,这确实是我们习焉不察或熟视无睹的时代通病。起伦以四两拔千斤的内功,轻轻一笔荡过,便有力地洞穿了官与民、帝王和江山的理想关系,大家都有饭吃,各安其道,没有欺诈盘剥,“此生则是欣逢太平盛世”也:
我站在江边
千年不变的姿势只是告诉你,累了渴了
三千弱水,只取一瓢饮
——《岳阳楼》
诗人不经意间将斯楼祛魅,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人不必非要随时随地紧绷着一副忧乐参半的阴阳脸,在伟大的岳阳楼上,面对八百里洞庭烟波,我们要抖落满身的浮华,还要以清洁精神的姿态,擦去历史的谎言与时代的空话。
5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什么时候,我们已忽略了身边的山水草木甚至高天厚地,忽视了风花雪月和鸡鸣犬吠?(其实是丧失了发现和命名事物的热情与能力。)慢下来,且容身心稍息片刻,让灵魂跟得上我们仓促的脚步,仔细看一看我们行过的风景,也许才会实现我们一直渴求的理想与幸福的人生。而诗人与诗歌承载的,恰是如此神圣的责任与使命。我们今天读唐诗宋词为什么仍然倍感亲切,百读不厌,就因为古人那些诗词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节奏、唯美风物和人情趣味。起伦的诗里有天地,有灵性的山水,更有人在天地山水中且行且驻的身影,有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影像,仿佛孤舟随水飘过千山,看起来虽然缓慢,却能引人入胜,其情其景,令人神远。
阅读起伦的诗歌时,我想到沈亮《为了逃避自我而旅行》一文中的一句话:“或许真正的壮美并不存在于外部世界,而在认识自己的勇气之中。我们站在原地,就可以有更深刻的生活”。起伦的诗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游记体,亦非简单描摹赞美山川的山水诗。作为湖南人,他写身边熟知的山水,写这方山水养育的人,通过故乡山水和其中人物的所观所感所思所想,未尝不是试图以诗笔精炼地总结楚地湘人的精神史和文化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起伦得湘楚山水灵气,才有如是缠绵诗思。起伦的创作足资那些倡导地方性写作的诗人镜鉴:立足当下,扎根故里,脚踏实地,满怀赤子之心与真诚之爱,才能写出元气淋漓,既接地气又独具地方标识的好作品。而对于那些迷信“风景在远方”的好游者亦富启迪:故乡并不缺乏独特的山水和绮丽的风景,缺乏的只是我们深情投注的目光。
浅薄有浅薄的美,深刻有深刻的痛。在这个物欲横流、思想尘土飞扬的小时代,不能像长江黄河那样快意奔腾咆哮,那就做秋日山野里的一条小溪吧,虽然清浅,但那澄清的秋水可以接纳蓝天白云的影像。是的,在这个喧嚣纷扰的浮华尘世中,唯有诗人,原本可谓最为深刻而神秘的诗人,能够坦率地拒绝暧昧、深刻与浮华,做一个纯粹、简单甚至透明的人。行走于滚滚红尘,晓得如何将自己清清爽爽地安放其中,不夺天地造化之功,不与山川争雄,知道人生真正之所求,懂得世间大爱之要义,这不仅需要勇气,尤其需要智慧,舍得放弃,方能得到心灵的自由和灵魂的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起伦的这组小诗,其实并不小,尽管其形制简短,但他关切的山川与尘世,省思的人生和心灵,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举重若轻的“大题小作”。
6
是真诗人无畏,唯大诗人能本色。诗人当有狮虎气质。但我们所处的社会不欢迎特立独行者。没有人关心我们从孩提时代受到的集体规训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希望活出个性,活出真正的自我。这想法不错。但经历过严酷的人生磨砺之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棱角早已消磨殆尽;更糟糕的是,因为我们自身丧失了锐气、勇气和正气,我们自然也见不得那些历尽挫折依然不肯向极权和势利妥协的人,我们因为厌恶“先锋”、畏惧“自由”而无端排斥他们,视其为另类。潜意识里,为了活得比别人更幸福,我们不愿也不能独善其身,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人事,还要经受无处不在的诱惑,不要说来自上司或下属的非正常干扰,即或防不胜防的骚扰电话和诈骗信息,都会扰乱我们的既定方向,影响我们的内心生活——从清晨到深夜,从公共空间到私密时间,吾侪似乎已无处可遁矣!
读到《猫》这首诗时,我不禁为一只野性尚存而有王者风范的猫击节叫好,同时亦颇感羞愧难堪。诗人发现的这只猫,能惬意地在自己的王国享受私有时间,“它枕着午间的阳光,飬养自己的野性”,“这没有常性的小东西”,“它高贵的、自由的灵魂只属于自己的梦想和骄傲的身躯”;它警惕外人擅闯领地,敢于对自己所憎恶的造访和打扰说不,当诗人无意间靠近它时:
突然,它发出一声尖叫,是庄严的警告:先生,您必须止步!
闻此尖叫,犹如当头棒喝,我们难免惊骇,亦不免悲催:更多时候,我们其实连一只猫都不如。不是吗?为了所谓生计或事业,我们每天戴着面具,在外面精彩却无奈的世界小心地倾情表演,晚上回家固然有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惬意,但早已忘却了理想信念的人只会抱着手机刷微信玩游戏,或不停地换电视频道或守着肥皂剧看到天昏地暗满脸浊相,哪里还顾得上“修身养性”呢?而昔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亦成了酒后茶余的笑谈也!
起伦提醒我们,不仅野性难驯的猫拒绝我们靠近,就连我们所爱的一切,包括大自然,也不允许我们“假借爱的名义”靠得太近:
不要靠得太近。它孤绝卓越的身姿
拒绝一切外在的阴影和光芒
它谢绝任何他人的在场与共感
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专注于自我成长,“不要让自己粗重的呼吸,干扰它神圣的怀想与独白”:
你应屏住呼吸,剔除妄念,俯下身子
像一棵果树那样,俯身于自身果实的重量
——《不要靠得太近》
7
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幻象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威廉·布莱克曾对旁人说,他走到苍茫大地的尽头,用手指触碰到了天空。这固然是这位“总是在天堂里”生活的诗人的幻觉,但诗人仰望长天与星空并为之纵情放歌,当然不只是为了欣赏天上的白云和灿烂的星光,而是对人类追求的崇高道德律和伟大信仰的现实礼赞。起伦也热爱湛蓝高远的天空,在《老苦楝树》中,他甚至用诗笔拉近了自己与“天空”的距离:
他在孤独之中发出的隐忍光芒
已不知不觉把天空拉得靠近了自己
在我们看来,这棵独立于旷野秋风中,仿佛入定的玄衣老僧的老苦楝树,就是诗人的自画像:掏空怀里珍藏的那点苦,(那点致命的自负),彻悟的诗人连带着万物逍遥事外的心思也没有了,他只想静静地享受悠闲的时光。“年轻时倒着看世界/如今即使掉进深渊,也要努力仰望天空”的诗人,他用淡泊与孤独之苦修获得的温柔的光芒,不仅要将天空拉近自己,还要用秋水“洗尽矿石的孤愤,带走坚硬”,相信“蔚蓝将重返天空,看护光明”。《写到天空》,——起伦实则在写历经世事淘洗过的人心的深邃,写人无形的灵魂大于宇宙。显然,如此形而上的精神体操,是每个人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必修课。
如今,不再与莽撞的青春斗智斗勇
如今,爱上了黄昏与静静的飘雪
因为沧桑之手,已积聚足够温柔的力量
捧住的不再是虚幻的理想,而是降落
——《雪中的黄河》
车前子断言:诗人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鸟。会飞翔的诗人当然还要学会降落。而降落是一门艺术。降落,意味着平安抵达或凯旋。未经历过漫长而惊险刺激的高空飞翔的人,不能领会降落的深意,更不能想象降落的快感。起伦以平稳降落的姿态,以脚踏实地的形象,诠释了精神飞翔(凌空蹈虚)的最终目的,无论飞翔或降落,我们最终要“成为自己的天空”:
他说,已看清了内心那道裂缝
看清了,就无须再远远地绕开
经历了独自哀诉到永恒的欢乐
他已成为自己的天空
——《深秋的河流》
——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发现了“内心裂缝”的诗人需要“沉入自身,在回忆里发掘生之意义”。
8
孤独是诗人必备的坚硬品质,也是其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更是其才华的磨刀石。读起伦的诗时,德国大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的名作《孤独者》不时会浮现在我的脑海:
谁孤寂,谁就能掌握奥秘,
孤独者置身于意象之河,
熟悉意象的萌生和缘起,
了解影子也蕴涵着炽热。
他擅长建设,具有创造力
充满思想的力量,
有益的人性不断地增值
他能阻止人性的灭亡。
死亡和变异开始消失
他冷眼旁观,发现
地球已变成另一种星体:
他赢得了完美静默的青眼。
起伦确实是一位富于建设、具有创造力和充满思想力量的孤独者。但他不冷漠,而是满怀热忱地探索人性的秘密。他在《等待在诗中下一场雪》中写道:
我一直认为,只有诗歌
能让万物沉潜在伟大的静息中
也认为,只有灵魂
能掀起月亮隐秘的潮汐。
因此,他想抛弃一切,以浪迹天涯的激情和决绝、涵养推倒重来的力量:
它能驱赶老虎背负黄金的落日,浪迹天涯
又能让词语闪烁激情的光芒
孤独者至敏,寂寞者至警。只有习惯于孤独和寂寞的人,才能真正地掌控自我意识,永远不会在茫茫人海中失去自我,更不可能在泥沙俱下的话语长河中无声地沉沦。爱因斯坦自承:“我愿意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人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孤独感和寂寞感或曰存在感,是起伦诗歌中的晴雪,它们闪烁着冷艳而迷人的光芒。在病榻上,“我无法阻止看不见的幽灵对我误解/那些以某些规范的执行者面目出现/在窗玻璃上的/使我反感”;当诗人自己独处时,他发现自己与身体之间,“存在一个笨拙的解释者”,他们不能和睦相处,“我必须将其中一个我/从病的牵缠中解放出来”:
我在极力寻找那个敞开又敞亮的自己
他驱除了内心的矛盾与惶惑
能够接纳一个流浪者
我要让我的不安消解在他无边的宁静中
是的,我必须让自己与灵魂和谐统一
——《病中之愿》
诗人渴望而迫切解放的,当然不只是疾病缠绕的身体,还有灵魂:
疏通河道,搬走命里的荒年
让爱情找到顺风顺水的方向
其实,命运有其无法窥透的纷繁性
不在现实的重压下臣服,就得让灵魂解放
——《九嶷山》
9
“诗坛顽童”W.H.奥登素来在艺术上倡导“游戏”精神。关于诗歌,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诗歌是知识的游戏,——却是一场严肃、有序、意味深长的游戏。他强调,但这游戏必须坚持规则。起伦似乎也接受这一论断,并醉心于这种讲求规则的智力游戏:
相信词与词的搭配融合,如一次绝妙的拥抱
这是诗的游戏,也是鸽子的游戏
——《一对鸽子》
所谓人生如戏,作为演员,我们岂能不用心演好这场人生的大戏呢?
黑格尔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句话十分赞赏,但他犹嫌不足,进而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834年,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在读到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并为其写评论时,他在开篇写道:“我们处在一个匆忙、繁杂的时代,言语在其中从不停留。昨天发生的事已经是历史,成为诗歌或故事,而未来的作品却已经不耐烦地开始预演,人们的好奇心催促着,好像要吞了它。早上我们听了一段故事,晚上之前就要叙述出来,歌颂它。”他继而惋叹并质疑:“对那些美好、伟大和绝对不朽的事物,我们为什么不一遇到它们就观察它们,对它们喝彩呢?在这个以速度、无聊、胎死腹中的努力和襁褓中的希望而著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为当下的愉悦和已然确定的胜利而沉醉呢?一定要等到它与我们渐行渐远,被尘埃和人群阻碍才开始欣赏它吗?”时隔近两个世纪,我们今日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又有多少令人欣悦的改观呢?我们将如何解脱“悲剧←→喜剧”的无穷轮回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坦言不想与秋风攀亲且害怕真相的诗人,当然不会就此放弃思索。而作为读者的我们,目睹长河落日,飞鸟投林,自然会想起被誉为“活着的经典”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德克在其四部曲《缓慢的归乡》中演绎的宏大主题:你们听我说吧。我不愿走向毁灭。在这一巨大的损失来临之时,我的反应是归乡,不仅仅是回到一个国家,不仅仅是回到一个确切的地方,而是回到我出生的故居。
是的,无论诗人,还是我们,都渴望回家。
10
“人到中年时/夜间远望蜜桃熟”。西东三鬼的这首俳句,窃以为正合起伦之诗境。而窪田空穗的俳句:“当我心灵充实的时候/天空向我靠拢/我伸手可及”,恰是起伦目前在人生和创作上正在接近的理想状态。这既是他诗歌里可堪珍重怜爱的红尘人生,也是他矢志不渝脚踏实地的诗意追求。大美山川,在起伦这里,遂成为壮丽的背景,他安静而悠然地行过,带着尘世温暖的大爱与赤诚之恋,“轻盈在幸福与忧伤之上”。如我们所知,诗人明白:
看惯繁花似锦,就得习惯黄叶纷飞
瘦削的树干写满铁打证词
——《黄昏江边断想》
在《尘世的热爱》中,我们注意到,起伦的诗里起了秋风,飘了白雪,呈现出黄昏,发现了疾病,看到了起落的风筝、温顺的鸽子、野性的猫和废弃的钢轨——他以这些或冷或灰的色调和具有流亡气息的意象表达了一个中年诗人温情脉脉动的精神世界和秋水般澄明的思想。起伦以风筝隐喻自己跌跌撞撞、起起落落的人生际遇。人到中年,他已深切地发现那条将自己的灵魂与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的线,并且懂得小心翼翼地将这根线一寸寸地收拢;虽然离天空还那么远,但敬畏之心明亮如月,毕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现自己始终还在这里/这多么好!”知足常乐,平安是福,山川静美无恙,世间有爱堪怜!玩过致命游戏,到最后仍知道保持平衡的艺术,在回望峥嵘岁月的时候依然努力为未来加持智慧,这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心?诗人在《一截废弃的钢轨》中平静写下:
一截废弃的钢轨,静静生锈
在黄昏的夕照里
它无所事事,只为死亡开心
如此安谧如梦,“死亡”岂能不开心呢?死亡即还乡,如雨水落入大海,以有形之身无物之魂,干净彻底地融入万物。起伦最后以一首悼亡诗——《诗人还乡——兼致韩作荣先生》一诗作为组诗的收尾,与开篇《南岳》遥相呼应,平心静气地完成了山川巡礼与人生圆满的诗意探索:
是的,他交出所有本质的特定储蓄
更无重负。更能与树木、花草和故土亲近
他还乡。在这个最纯粹意义的所属的尘世
他用一生画了一个广大的圆圈


凌之鹤,本名张凌,回族,1971年10月生于云南嵩明。诗人,评论家。云南省作协会员、昆明市作协会员,昆明市作协理事,昆明市网络文学作家协会会员、理事,曾任嵩明作家协会主席。创办纯文学民刊《滇中文学》并任主编。16岁发表处女作。常用笔名有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作品散见于《中国艺术报》《滇池》《云南日报》《休斯敦诗苑》《小说林》《诗歌月刊》《散文诗》《星河》《山西青年》《文艺评论》《大家》《边疆文学》《江西散文诗》《译林书评》《湖南文学》《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等刊物。著有《醉千年:与古人对饮》《独鹤与飞》等。在《昆明青年》《女性大世界》发过诗歌专辑。曾获首届滇云网络文学大赛提名奖、第二届滇云网络文学最佳评论奖、第四届滇云网络文学大赛佳作奖及2017年、2019年《滇池》文学年会奖等。有诗作入选中国2003、2009年度优秀诗歌选集,有散文作品入选云南作家精品文库《散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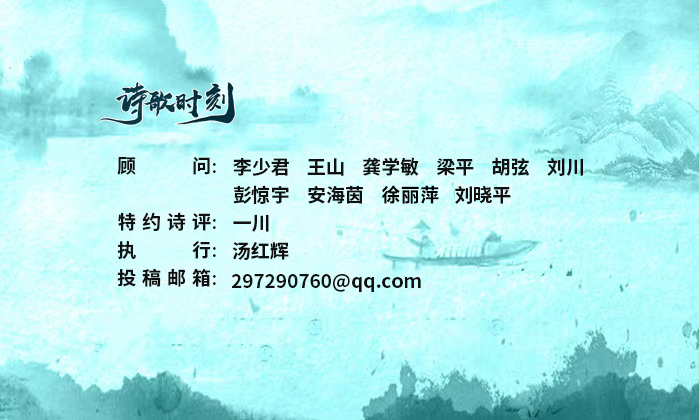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凌之鹤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