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物之眼与人间之诗
——读梦天岚诗集《屋顶上的藤萝》
文/康怀宇
先读一首诗,以此进入梦天岚诗集《屋顶上的藤萝》:
风的怒发和它砖头一样暗红的脸,
在夜的黑暗中归于梦境。
不堪仰首,那星月的英灵,
如同消散的云烟见证着,
摇晃的大地。
令人晕眩的意志的根,
在另一种黑暗里,
寻找那不属于它的,
晨光和露水。
我们共同的命运莫过如此,
那向着天空的赤焰和歌喉,
在各自的小路上,
似乎都走到了尽头。
——此诗题为《屋顶上的藤萝》,和诗集同名,也可见诗人对该诗的重视。我亦可将其视为开启诗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风的怒发和它砖头一样暗红的脸/在夜的黑暗中归于梦境”,诗篇开篇便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诗性空间。风的“怒发”与“砖头一样暗红的脸”这两个异质意象的碰撞,暗示着生命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不堪仰首,那星月的英灵,/如同消散的云烟见证着,/摇晃的大地。”则进一步强化了向上仰望的艰难与精神高度的不可企及。诗人以藤萝自况,那“令人晕眩的意志的根,/在另一种黑暗里,/寻找那不属于它的,/晨光和露水”,正是诗人自身精神追求的写照——在存在的困境中依然执着地追寻超越性的光明。但梦天岚的诗学视野从不固于个体的一己悲欢。他清醒地写道:“我们共同的命运莫过如此,/那向着天空的赤焰和歌喉,/在各自的小路上,/似乎都走到了尽头。”这种从个体经验向人类普遍命运的诗性跃升,构成了梦天岚诗歌最为动人的精神特质。
他不是在书写私密的情绪波动,而是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精神境遇作证。且其间隐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动人心弦。这种特质同样体现在诗集的第一首诗《白鹭》中。白鹭作为诗歌的中心意象,它的种种姿态——“埋下头”“雪的扮演者”“在滩涂上漫步”“突然飞起,又落下”,都不是诗人最核心的关切。诗人真正在意的是白鹭能够促使雪,或者说能够促使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个体“回溯”到“原初时”“那不顾一切扑向人间的样子”。也即是说,“白鹭”在这里成为一个诗学媒介,通过它,诗人表达了对人间的深切眷恋与无限关怀。诗人的心志所在并不是什么“白鹭”,也不是什么“雪”,而是“人间”。这种“寓大于小”“寓无限于有形”的能力,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屋顶上的藤萝》一诗,如出一辙。
再拿《马齿苋》一诗来说,诗人要写的也并非是什么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吃起来略带苦涩味的“马齿苋”,而寄托着他的一些关怀。在他看来,“大地似病得不轻”,而马齿苋就是可以治愈大地之病的“药水”或“药物”。如果说,“马齿苋”是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细小生命,那么“大地”当然是更辽阔、更宏大的存在。
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那就是诗人并非一个单纯的观察者,只会站在岸边对河水和河里的游鱼指指点点。在《鸟叫》中,他惊呼“遇到了什么?”,而牵挂“一只鸟在夜半振翅惊飞”后,“在这个无风的夜晚,/哪里才是它的落脚之处?”这种关怀超越了物种的界限,成为一种普世的生命共情。更令人动容的是,诗人从不将自己置于冷眼旁观的安全距离,而是坦诚地分享着与这些微小生命相通的情感体验:“而我,一次次在大脑中演练——/那属于我的后怕和惊慌”。这种深切的共情能力,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
这是一个注定被遗忘的清晨,
众鸟欢送一条河流的仪仗队从身下经过,
只有它,比人类更懂得沉默和隐忍。
——《渡鸦》
此时的大地尚未苏醒,
疼痛也是。
——《细雨》
那是一条从天堂划向地狱的弧线。
只是一个瞬间,
带着擦伤,划过夜的黑,
划过你,和这个亮着灯光的人间。
——《窗外》
此时的大地,尚处在昏迷之中。
——《马齿苋》
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我举出这些,是为了方便那些没有读过诗集的人,能够更为迅速地看到一个诗人写的诗,究竟哪些才是其心迹与心魂所在,才是其精神向度、思想深度、语言锐度所在。上述引用的诗句中,诗人写到了微弱的事物,比如渡鸦、细雨、流星、马齿苋,但诗人心之所系却是“人类”“大地”“人间”。
纵观整部诗集,梦天岚的目光总是温柔地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存在:蚂蚁、渡鸦、藤萝、白鹭、火苗、细雨、小飞虫、蚊子、马齿苋、萤火虫、车前草、草垛、果核、露珠……这些在世俗眼光中无足轻重的生命,并非没有被其他的诗人书写过、描绘过。只不过,在梦天岚这里,它们获得了存在的尊严与光辉。他不是在进行简单的咏物练习,而是在这些微小生命中窥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境况。
讲明这一点,也是为了继续表明梦天岚的心志与心迹。他是一个有大关怀的诗人,而绝非把生命耗损在那些微小生命上以求得修辞上的快感、姿态上的虚荣。
当下诗歌,已经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胸襟和气度,还一味地退缩,甚至坚执地退回到“唯我”。很多诗人虽说也在写身边周遭那些微弱之物,但是仅仅停留在“物的描绘”,像一个笨拙的绘画者。他们的作品既没有“物之心灵”,也没有“人之心志”。而梦天岚的诗歌美学最为宝贵之处,在于一种平衡,或者说在于一种尺度。有限生命个体的经验、体悟,从来不是宣泄情绪的理由,也从来不是自我暴露的借口,而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最真实的生存图景。它们不是诗歌的归宿,而只是诗歌的出发地。经由有限生命个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领悟,而最终抵达一个更为广阔的存在。
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代,甚至也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还在坚持写诗的人,不说多么崇高,也是相当地不易。我无意于夸大一部诗集的作用,也不想贬抑一部诗集的价值。梦天岚的这部诗集《屋顶上的藤萝》,为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微小生命、微弱事物、微弱记忆构筑了一片诗意的栖息地,也恰如一株“屋顶上的藤萝”,不事张扬,却顽强生长。让我们多了一个从方寸之地腾挪到更高境地的机缘,甚至渴盼“不顾一切扑向人间”。

康怀宇,90后,永州人,有作品见于《诗林》《湖南文学》《文学天地》等刊。


梦天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数百篇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星星》《天涯》《芙蓉》《山花》《长江文艺》等期刊。著有历史人物传记《老子》《周敦颐》《王夫之》《蔡伦》,其中《老子》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周敦颐》(繁体中文版)在中国香港印行。另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单边楼》,散文集《屋檐三境》,散文诗集《比月色更美》,短诗集《屋顶上的藤萝》《莫须有镇》,长诗《神秘园》等。现供职于湖南省诗歌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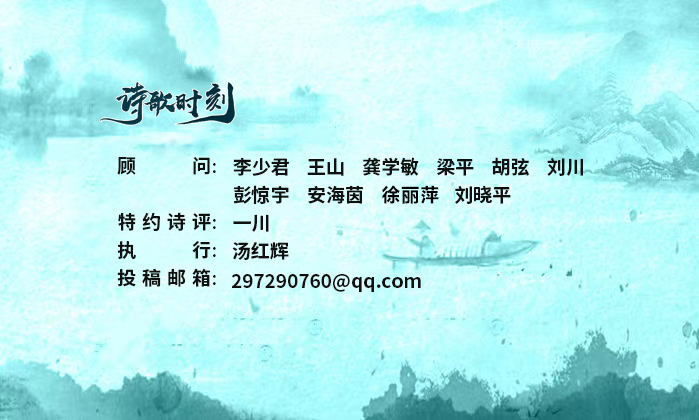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康怀宇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