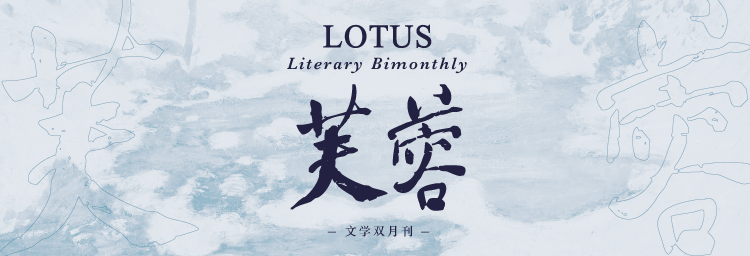

星星索(中篇小说)
文/潘灵
0
迟暮的美人终究还是美人。百无聊赖酒足饭饱的我,黄昏散步到广场时,看见那个领舞的头发胜雪的老太太,心中就生发出了感慨。平生最讨厌广场舞的我,竟然顿足观望起来。一群臃肿的广场舞大妈,被一个身段甚好舞姿绰约的老太太领着,越发像一群营养过剩的老母鸡。她们笨拙而僵硬的仪态,让我觉得既滑稽又为她们心痛。我甚至认为这老太太是故意的,她存心要表演残忍给我看。她皱纹密布的脸上有鹤的骄傲。是的,鹤!一只立在鸡群里的鹤。皱纹不仅没有绞杀掉她姣好的面容,还给她增添了历尽沧桑却又超凡脱俗的气质。一个拥有气质的老太太,那种美仿佛是从骨子里渗出的,惊心动魄又咄咄逼人。她的表情安然沉静,但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潜藏着阴险。要不,她为何要与这群广场舞大妈为伍?在我心里,混在鸡群里的鹤都是居心叵测的,像美女找陪衬人一样不人道。老太太并不关心我不怀好意的目光,她沉浸在广场舞欢快得近乎浅薄的旋律里,与大妈们一样,享受着她们律动的幸福。
我知道我这个过客既扫兴又多余,决定拔腿离开,但走了几步我却停住了。我脑海里涌起四个字:似曾相识。对,似曾相识,老太太身上弥漫的美,我非常确认在过去是见识过的,但什么时候,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于是又折回头去,想再做一次看客。但等我回头,一曲广场舞正好结束,我与老太太来了个四目相对。我看到她一脸的惊异。
是阿水吗?你真的是阿水?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才会有的那种克制——再兴奋和吃惊也不大声嚷嚷。我还从这声音里听到一种遥远的熟悉,那种低低的轻轻的声音,跟她叫出的我的小名一样亲切。
您是……她的声音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我脱口而出,是庹阿姨呀。
阿水!不,该叫你林作家。
庹阿姨!
我们激动地伸出的手紧握在了一起。
她认真地打量着我,说一点都没变。
我说,老了,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
跟你庹阿姨说老?她松开握我的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又看看我说,你鬓上才染霜,你庹阿姨可是头上堆雪了。在庹阿姨这里,你永远是少年。
她边说边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看出我有些犹豫,她说,不远的,就在附近。
我知道拒绝一个老人的热情会不礼貌,就点头应允了。她带着我走,步履轻快得不像一个年迈的老人。
我庹素已经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看她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我跟着她走出广场,穿过一条马路,来到一座有些年代的法式老楼前。
她转身用抱歉的目光看我一眼说,老房子,没装电梯,要劳驾你爬楼了。
我抬头看了看这幢黄颜色的法式老房子,也就六层楼高,夹在这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群中,显得既矮小又孤独,一种格格不入的孤独。
我跟着她爬楼梯,一直爬到四楼,腿脚依然灵便的她看不出有啥吃力,倒是我有些气喘吁吁。她用钥匙边开门边说,实在有些寒酸简陋,阿水可不要见笑啊。
房门敞开,我有一种穿越感,恍若进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个城市居民家。整个屋子的陈设都彰显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电视机是那个时代的,沙发是那个时代的,洗衣机和冰箱也是那个时代的,唯一不同的是,在那个时代的书桌上,放着一台比那个时代还要遥远的像一朵喇叭花的留声机。
屋子的陈设虽然老旧,但屋子却异常干净整洁,各种东西也摆放得井然有序。她给我泡了一杯茶,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说,听点音乐?还没等我点头说好,她就自顾转身去,抽出了一张老唱片,放在老式留声机上。
旋律从留声机的喇叭花口流淌出来,我听出来了,是《星星索》。
她坐在留声机前看着我,我也看着她,相顾无言。这样过了很久很久,这样一遍遍地放《星星索》 。
那张老唱片上,就只有这首曲。
是我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
庹阿姨,你们家的人呢?
不就在这里吗?
她边说边用手指指自己,随即关掉了留声机。她进到卧室,过一会儿抱出来厚厚一摞书和杂志说,阿水,不,林若水作家,我是你的粉丝呀。
我这时看清了,那些都是我出版的书和发表我作品的刊物。她竟然收集了那么多,让我心里不知是感激还是吃惊。
你好像从不写你的故乡,她说,作家怎能不写自己的故乡呢?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我沉思了一下说,我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我每每想到故乡,就会想起你。我想写你,但又……
写我?她摇摇头说,我有啥好写的?对于你的故乡白鹤镇,我只是一个过客,过客而已。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她的话。
我告诉她,故乡修建白鹤滩巨型电站,白鹤镇已经埋在水下了。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也许你是对的。有些东西,它就该像白鹤镇埋在水里那样,埋在心里。
我知道话不宜再讲下去,便想起身告辞。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阿水,再坐一会儿好吗?
我从她话里不仅听出了诚恳,甚至还听出了央求。
我抬起的屁股重新回到座位上。屋内,《星星索》的旋律环绕。
阿水,你三叔现在还好吗?我扭转头,惊讶地发现她那张苍老的脸上,有少女般羞涩的红晕。
三叔?我长叹一口气说,他离世都二十年了。
1
白鹤镇有一段岁月里不叫白鹤镇,叫白鹤公社,但乡亲们还是叫它白鹤镇,习惯成自然,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白鹤镇没有白鹤,白鹤镇到处都是乌鸦。这些黑夜之子,在白鹤镇上空纷纷扬扬,它们的鸣叫让人心烦意乱。在金沙江边撑船的我的父亲,今天说啥也拒绝干他摆渡的活,他对央求他的顾客们铁青着脸说,没听见乌鸦叫吗?这是号丧,风浪那么大,不去对岸会死吗?
这时人们才关注起了肆无忌惮的江风,风确实太大了,浪涛把停靠在岸边的木船都抛到岸上了。
历经太多风浪的船夫父亲,他并不是被今天的风浪给吓住了,比这样风高浪急的江面,他见多了。他今天罢工,有另一个隐情,那就是在镇上教书的三叔回来了。父亲想说服三叔,把我带去镇上的学校念书。而三叔显然把我当成了累赘,任父亲磨破嘴皮,都没点头。
你真忍心看着阿水像我,一辈子在江上提条命讨生活?
二哥,像你有啥不好呢?船老大比我这教书匠强。
强?父亲吹胡子瞪眼,说林江平呀林江平,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吃公家粮拿公家钱,做享清福的公家人,还说我比你强,屁话!你看那些在江岸木棉树上的乌鸦,个个双双鸟眼都瞪着我,巴不得我成水打棒,成它们的牙祭。
二哥,你做的是摆渡活,积德事,上天保佑着你,再说,你那么好的水性,水鬼奈何不了你。
江平,古话怎么说,会刀刀上死,会水水中亡,这是宿命。
二哥,我帮不了阿水,我学的是吹拉弹唱,可阿水身上没一丁点音乐细胞。
听三叔这么说,父亲就带三叔去江边河滩上。那是我信手涂鸦的地方,沙滩上,是我写的一些在村小语文课上学的课文。
这字写得堂堂正正,兴许能成我林家光宗耀祖的文化人。
也许是父亲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也许是我在沙滩上那些在我父亲眼里堂堂正正的字打动了三叔,他犹豫了一下,极勉强地应承了下来。
于是,我就这样跟着三叔从江边的村子去镇上。一路上,我心中都笼罩着强烈的自卑,我跟着三叔,那场景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后面跟了一只自惭形秽的丑小鸭。三叔人长得标致、帅气,这是白鹤镇地方公认的,我后来接触到成语玉树临风,眼中就出现三叔的样子。我一路上都在听三叔嘀咕,说文化人有啥好,公家人有啥好。我没接话,任他的话被江风吹远。我发现,三叔这次回村来,跟以往不同。他眉头紧锁,一张英俊的脸紧绷着,像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白鹤镇上正在赶集,人多得就像白鹤镇的乌鸦,一个镇子仿佛随时有撑炸的危险。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太阳既热且毒,它伸出金晃晃的爪子,轻易就挤出了我一头油汗。尽管这样,我的心中依旧一片冰凉。我想,三叔一定把我当成了累赘,他的郁郁寡欢和闷闷不乐让我忐忑不安,跟这样的长辈一起生活,定是我少年时光的至暗时刻。白鹤镇才不会关心一个少年的心事,它就像一口翻炒着豆子的热气腾腾的铁锅,充斥着人声鼎沸的嘈杂和欢乐。三叔偶尔回头,铁板一样的脸上,目光冰冷地刺我一下,随即就又回过头去。就在他第四次回头看我时,黄桷树上那个大喇叭响了,那是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它一响,喧嚣的镇子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这不是广播时间,大家知道,这喇叭在广播时间之外响起,镇上一定有事情发生。
广播里播放的是一个夹杂了白鹤方言的说普通话的女声,内容竟然是一份检举书。
被检举的是一个女人,她叫庹素。我认识她,她原来是镇上新华书店的售书员,我过去从村子里来镇上买连环画书,经常能见到她。她只要每天打开新华书店的售书窗,窗前就会挤满镇上流里流气不三不四的小镇男青年,他们不是来买书,只是来看她。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种乞丐看到食物的饥饿眼神。个别过分的,还会吹响轻浮而下流的口哨。但庹素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是安静地卖她的书。她对我尤其好,我叫她庹阿姨,她夸我有礼貌。遇到畅销的连环画,她会偷偷为我留下一本,等我赶街的时候卖给我。
我也喜欢睁大眼睛看她, 她就像连环画上那些女的一样好看,不!她比她们还好看。她脸上身上有画中人没有的东西,我长大后才知那叫气质。据镇上的人八卦,说她是印尼归国华侨,她是跟随父母回的祖国。在我心里,庹阿姨的模样,就是仙女的样子。她冰清玉洁,温文尔雅,超凡脱俗,光彩照人。她,配得上任何美好的形容词。但后来她调去了供销社,成了一个卖白糖大饼的售货员。这样的人,也会被检举,这镇上套路之深,使我年少的心,只剩下惊愕的份了。
让我更惊愕得差点掉了下巴的是检举人。
他竟然跟我的三叔有着共同的名字:林江平。
我紧走两步,对三叔说,三叔,那个检举庹阿姨的人,不能跟你叫一样的名字。
面如死灰的三叔冷冷地小声警告我,这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子别掺和。
架在黄桷树上的大喇叭不仅义正词严,而且带着愤怒的情绪扩散出对庹素的检举。这检举信里有些语句我要么不懂,要么似懂非懂,我唯一听明白的是,深受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腐蚀的庹素,妄图用靡靡之音和爱情的糖衣炮弹,拉拢并腐蚀我镇的进步青年。她的狼子野心,是无法得逞的。庹素是一条美女蛇,我们大家尤其是男青年要擦亮眼睛,看清认准她的毒素, 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有街上混混听广播里这么讲,就耸耸肩自嘲,我想沾,我想被腐蚀,但沾不上啊!林江平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欠揍!
他周遭的人就笑,有人说,汤二毛,林江平得了啥便宜,难道他把美女蛇睡了?
那倒没,被叫作汤二毛的人说,据内部可靠消息,那叫庹素的美女蛇,在林江平的额上亲了一口。
不可能!一个用手摸了摸自己额头的长一张刀脸的小镇青年说,汤二毛,你别听林江平吹牛逼,庹美女吻她?他这种软蛋,人家看得上他?
这时汤二毛看见了三叔,他手一指对小镇刀脸青年说,林江平就在那里,你问他去。
小镇刀脸青年迈着方步朝三叔走来,他一脸坏笑说,林江平林老师,美女蛇如何亲你的,说给大家听听嘛。
众人一阵哄笑,三叔又急又气,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我这下终于明白,检举庹阿姨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三叔林江平。这个让我无法接受的事实,残忍得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捅入了我的内心。当气急败坏的三叔转身伸手拉我离开这是非之地是非之人群时,我拼命地挣开他的手,厌恶而羞耻地跑开了。
2
我发疯地在镇上攒动的人群中奔跑,样子像一个偷了别人钱夹被发现的小偷。我一直跑,跑到了镇上的供销社的柜台,我知道庹素阿姨在那里卖白糖大饼。过去,这里从来都是门庭若市的,都会挤满乌鸦一样黑压压的人群。今天这里却门可罗雀,难道那乌合之众,真的把庹阿姨当成了美女蛇?气喘吁吁的我看着木偶一样面无表情的庹阿姨,她站在柜台前的样子,依旧楚楚动人。
庹阿姨!
阿水!
我们几乎是同时招呼了对方。
庹阿姨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脸上生硬的表情柔和了许多,她拉开面前的抽屉,拿出一本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阿水,这本书,是新华书店前两天刚到的,我替你买了一本,我今天不要你的钱,送给你。
她说着从柜台上面伸出手来,我没去接她的书,却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庹阿姨,我一脸歉意地叫了她一声,眼泪就夺眶而出了,我哽咽着说,对不起!
阿水,说啥傻话?庹阿姨说,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呀!
我是替我三叔给你赔不是。
已经柔和的庹阿姨的脸,又恢复了先前的生硬,她把书塞我手里说,阿水,那是大人的事。
你要好好看这本书,下次我可要听你说心得哦。
我说,三叔他……
别说你三叔,庹阿姨轻轻打断我的话说,如果你见了他,就告诉他,我不怪罪他。
那天下午,我在街边用我临走时母亲塞我口袋里的零钞,买了一碗伤心凉粉吃后,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我没心思看连环画,也不想回三叔所在的中心学校的住处。街上都是关于三叔和庹阿姨的流言蜚语,那些贩夫走卒,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关于他们的风流韵事。我从那些人的谈论中逐渐弄清了故事的棱角。
不久前,公社让镇上的各单位凑节目,搞中秋晚会。供销社主任有些为难,他们社里找不出几个有文艺细胞的,就去找他的好友中心学校校长。校长说,你们庹素,大美人一个,这不派上用场,岂不资源浪费?你让她往台上一站,唱个歌,保准一片哗啦啦掌声。主任觉得校长的话在理,就说,这唱歌得有人伴奏。校长说,那好办,我支援你。我们的音乐老师林江平,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全镇一流。
三叔就这样被校长派去与庹阿姨合作节目,两个相貌出众的年轻人,一来二去心里都对对方生出了好感,配合也日趋默契。但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挑到彼此满意的歌曲。
一天,二人又凑一起,聊天时,三叔说自己祖上就是在金沙江上撑船摆渡的。这话提醒了庹阿姨,她说,我们唱首船歌吧。三叔说,金沙江上没有船歌,恶浪滔天的江上摆渡人,一撑船心就提到嗓子眼,还唱什么歌?庹阿姨就说,我说的船歌,是印尼歌。我大伯当年讨生活下南洋,一家人生活在苏门答腊群岛上,经常听巴达克人唱。他回国后,教我唱,可好听了。庹阿姨就哼了几句,三叔要她放开唱。庹阿姨听了三叔的,就站起身,星星索啊星星索地唱开了。庹阿姨唱完,三叔却呆住了,愣了好一会儿才把掌鼓得脆脆响,三叔说,太好听啦!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庹素,我喜欢你这种唱法,每句前紧后松,柔和而松弛,缓慢而悠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仿佛在表达思念之情。三叔的话,让庹素也兴奋得鼓起掌来,她激动地说,不愧是白鹤镇的音乐才子,江平,你解读得太到位了!听我大伯说,巴达克人唱的就是思念,他们歌唱的是爱情。
爱情这两个字一出口,庹素脸上泛起了红晕,三叔也弄了一张大红脸。
三叔结结巴巴地说, 爱……爱情?中秋晚会上唱这歌合适吗?
庹阿姨说,怎么不合适?我听大伯说,在苏门答腊群岛上,巴达克人的歌大多是歌唱爱情的呀!他们大大方方唱,男女老少都唱,那场面美好得很。
可……三叔迟疑了一下说,这是白鹤镇呀。
庹阿姨撒娇似的说,我不管,我就只想唱它,我要和你一起唱它。
唱它?三叔说,我连这首歌的歌名都不知道。
庹阿姨说,它就叫《星星索》。
《星星索》?三叔搔了搔头发说,好怪的歌名。
庹阿姨说,我当年也跟你一样觉得怪,大伯就解释,说那是巴达克人的船桨有节奏起落在水面上发出的声音,星星索,星星索。
好吧,三叔说,就随你的意,反正大家都不知道印尼话,不会懂它的意思的。
三叔一应允,庹阿姨就激动得蹦了起来,她在三叔额头亲了一口,就像一只欢快又害羞的羚羊跑出了屋子……
中秋晚会上,三叔和庹阿姨的男女对唱《星星索》,在白鹤镇引起了轰动。
3
一首《星星索》,仿佛是一粒石子投进一片静寂的湖面一般,在白鹤镇人心中荡起了涟漪。人们虽然听不懂这对金童玉女唱的是什么,但旋律还是从耳膜钻进了他们荒芜而干涸的内心。很舒服,很好听,僵硬的时光似乎都变得柔软起来——白鹤镇的人们,心中有了直接而异样的感受。
镇上的年轻人,被这首来自异域的歌给迷住了。中心学校的年轻教师,自是不会放过近水楼台的机会,他们围着我的三叔林江平,要他教他们唱。有年轻教师还提了酒,上门去找林江平,企图从他嘴里套出些关于这首歌的内容和信息。但三叔却总是笑而不答。终于有一天,三叔在他的年轻同事别有用心的频频劝酒下,道出了这首歌的“机密”。
三叔借着酒劲挥舞着手说,这首歌唱的是爱情!
三叔的话,说它是石破天惊也不为过,那些三叔的年轻同事面面相觑,脸热心跳,统统选择了缄默不言,然后自顾散去了。
在不谈爱的年代,爱情是一个禁词,三叔没有把它关在牙齿的牢笼里,他吐出了它,等于吐出了祸水。
匿名的告状信就到了公社主任的手上。中秋晚会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唱爱情歌曲,这还了得!
两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让公社主任很是恼火,他觉得事态分外严重,于是就叫人请来了中心学校的校长。校长也觉得事态严重,但他认为林江平是被蒙蔽了。
我保证他不懂印尼语,校长当着主任的面拍着胸脯说,始作俑者定是庹素。
主任说,但唱的是爱情可是你的教师林江平说的。
那也是庹素教的,校长说,据说她有海外关系。她明知歌词内容关于爱情,却还要在中秋晚会上唱,这动机可疑呀。
主任点头,说庹素确有海外关系,难免受腐朽思想影响,唱靡靡之音,事出有因,但林江平跟着瞎起哄干啥?知道是男欢女爱,还唱?
校长想了想说,他中了庹素的毒,据青年教师反映,他俩现在打得火热,私下里约会。这都怪我,客观上起了撮合的作用,好端端一个青年教师,中了无孔不入的资产阶级的毒。
要挽救他,主任挥挥手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该替他打扫一下思想卫生了。
那天的黄昏,白鹤镇上没有其他的话题,连江风的呢喃,仿佛都是在窃窃私语林江平和庹素这对男女。我听见镇东口白鹤饭店里靠窗的一个喝酒的男人用高亢的嗓子对他的酒友讲,林江平不是东西,软蛋一个,他还不如黄廷波。黄廷波虽然坏,但人家有担当。我们都知道那庹美女给黄廷波看的是《简·爱》,还是繁体字的,有人举报后,公社主任带着审查组,找黄廷波谈了三天三夜,人家黄廷波就是咬死,说庹美女借给他的是《水浒传》。
酒友们都点头称是。其中一个用筷子敲击着酒碗一脸暧昧地说,这黄廷波要是一无是处,会吸引庹美女,他成天往庹美女的屋子跑,一去一两个小时。
嗓子高亢的男人说,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不说也罢。
用筷子敲酒碗的那位继续懒洋洋敲了几下说,过去以为黄廷波是牛粪,现在看来,林江平更是,他空长了一身好皮囊,没点男人气。
我听这群酒徒八卦三叔,恨不得冲进店去揍他们。但我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他们会像提一只鸡仔一样把我从酒馆里扔出来。我知道,我像自己的三叔一样懦弱。这让我少年的内心羞耻极了。
我现在知道,庹阿姨为何会从镇上的新华书店调去供销社了,原来是她借书给黄廷波。那个人我认识,长得魁梧强壮。他是公社的一名干部,做什么都出手重下手狠。镇上的人背地里说,这黄廷波的心不是肉长的,而是铁铸的。有人还传,说他从出生就得了一种病,不知道疼痛是什么。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如果有魔鬼,那一定是黄廷波的样子。庹阿姨会借书给黄廷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那叫《简·爱》的书,到底是本怎样的书?我的心中,一下子多了好多问题。
我那天在街上,替三叔感受了太多的羞耻,直到夜色浓郁,才极不情愿地回到三叔所在的中心学校教职工宿舍。我推门进屋,闻到了刺鼻的酒味。三叔一个人喝闷酒,他喝高了,像一摊烂泥龟缩在床角,手中握着一个空酒瓶,衣服上,沾着令人恶心的呕吐物。他见我进来,想爬起来,但还没等站起来,就像大风中摇晃的树又倒下了。他醉眼蒙眬地看着我,抬了抬他有气无力的右手,口齿不清地冲我嚷开了。我惊恐地看着一个醉汉愤怒的样子,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在叫嚣什么。
三叔在问——我不知他在问谁——不是给我保证过,只要我说出实情,就饶了我们吗?啊?
我想,那个“我们”,该是他和庹阿姨。
我走到床角,吃力地把他扶起来,摇摇晃晃的他把难闻的酒气喷了我一头一脸,他还在口齿不清地问,不是保证过吗?为啥说话不算数呢?
我把他扶到床上,给他脱衣,盖好被子,然后去清理呕吐物。天天盼望长成大人的我,第一次对成人世界充满了恐惧。
(原载于2023年第3期《芙蓉》潘灵的中篇小说《星星索》)

潘灵,男,布依族,1966年7月生于云南巧家,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泥太阳》《翡暖翠寒》《血恋》《情逝》《红风筝》,小说集《风吹雪》《奔跑的木头》《太平有象》等。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文学奖一等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民族文学》年度大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潘灵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