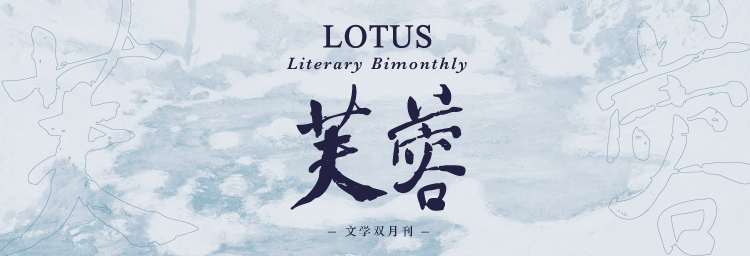

秋日巷谭(中篇小说)
文/张学东
天气一凉,我总爱缩着脖子,摇摇晃晃蹬着老爷子那辆旧自行车回家。这破烂玩意儿除了铃铛(丢了)永不再响,车身各个部位感觉也快完蛋,一动窝就吱吱嘎嘎的,驮着我怨声载道,那动静听来委实恼人。
意志巷就在前头不远,穿过两三条灰头土脸的小街,绕过玉皇阁老城楼,再拐个弯子,就能看到一条细长的巷道了,它的左右两侧,都是极矮又旧的砖木结构瓦房,通常最靠里面正中央居住一户人家,这家人的下首左右两旁相对居住着八家,九户人家便圈围在臃肿不堪的杂院里,我家当然也在其中,这样的杂院正如蜈蚣的毛爪,参差排列开来。狭窄幽长的巷道,只能容纳一人谨慎地推一辆自行车单独行走,倘若遇到迎面来人,客气的一方只得闪到巷道两侧的某个小院里回避。人一旦钻进巷口,立刻有种井底之蛙的感觉,头顶仅一方或蓝或灰的天空,像块条布高高地蒙着,偶尔,有一两只鸟雀掠过,人的心好像也随之飞走了。
回家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多迫切的事,我甚至觉得,回去不回去就那么回事。这个家除了能让我吃上饭睡上觉外,没啥值得归心似箭的东西。我一个二十好几的人,整天穿一身脏乎乎的劳动布电工服,在冷冰冰的电线杆子上爬上爬下,简直跟马戏团小丑似的,拼死拼活也就挣那么点儿可怜的工资。所以,我打骨子里厌恶这烂地方。我更讨厌现在这份工作,这还是老爷子病退后,厂子照顾家属,才给解决的,顶替老爷子干了电工行当,说不准哪天,我让电老虎直接从电线杆子上给撂趴下,想想都晦气。
其实,我打一开始就后悔,真不该回到这鬼地方来。意志巷里没一样事情让人觉得舒心畅意,唯一还算好点儿的记忆,是那次跟母亲坐了三天两夜的长途火车——这是我生平头一回乘那长蛇似的庞大怪物,那种汽笛的嘶鸣声和铁轨发出的咔嗒声很长时间也忘不掉。后来,就连这点儿新奇感,也变成了我后悔时常常咒骂的理由,我老在想,如果世上没有该死的火车,这辈子恐怕真就回不到意志巷了,那样的话父母一直两地生活,我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苦恼了。
立 秋
等看到巷口的白杨树,婆婆娑娑坠下第一片金黄色的落叶时,便是意志巷的秋天了。
今早,我又跟往常一样,睡眼惺忪地从门台上扛起那辆破自行车,一步一晃走下台阶,然后骑上车去干我不喜欢的电工活。不知为什么,这时节我总能记起十多年前,我随母亲千里迢迢回到意志巷的那个秋天。可以说,从我跨进巷口,走进家门的一刻起,我就饱尝了这个家里的男主人——也就是被我后来生硬地喊作“爸”的男人的不近人情的管教,在此之前,我一直随母亲在外地野蛮生长无拘无束,早就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可生活总爱跟人开玩笑,突然间就凭空多出这么一个狠角色,大人不用两地分开过了,我的苦日子可来了。
那天,男人狠狠瞪着我,像鄙视一条癞皮狗,发出了他的第一道命令:给,这是五毛钱,你急忙拿上,去巷子口剃头馆,把你的头剃了!看看你这头发,疯长成一堆乱草,不男不女的,成个啥样!我并没立即去接他手里的钱,只是傻站在原地,很为难地摸了摸那头引以为豪的头发,面对陌生男人的无端斥责,我一时半会儿还揣摸不透,只好无可奈何地瞅了我妈一眼。
我叫你急忙去,耳朵塞猪毛了听不见啊?愣在那儿不动窝,脚底生根啦!男人继续高声大嗓发号施令。
娃娃这不才进门吗,就算头发长了些,吃罢饭再理不迟,看把娃娃吓唬的!我妈怯生生地替我来圆场。
一个男娃子家,你咋给他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个二流子,急忙让他去……我看着咽不下饭。
就依你爸的话,快去理理,完了赶忙回来吃饭!
随着“砰”的一记门响,我一百万个不乐意冲出了家门。正如那个阴郁的男人所说,巷口果然有一家小理发馆,我迟疑了一下,便掀开门帘踅进去。脑袋顿时轰的一声,完蛋,一瞅理发馆老头儿,他那颗剃得锃明发亮的光脑壳,我立刻明白了,我爸为何管理发的叫剃头了。我本打算退出去,可一看天快黑了,况且,自己才跟母亲下车没多大工夫,人生地不熟的,干脆将就一回。师傅,麻烦给少剪掉点儿……我几乎央求着说。不用交代,现在的小年轻儿,我算看出来了,裤腿越穿越宽了,头发越留越长啦,我像你这么大,还留过大辫呢,后来不是也剪了嘛,嘿,还是剪了清爽呀……我可没有那份好的心情听老头唠叨,就闭着双眼等他打理,眼前却又浮现出那张凶神恶煞的脸,越想越觉得硌硬。
那天我理完发进家,一屋人围着桌子吃晚饭。我妈忙起身盛好饭,递给我。男人马上又鸡蛋里挑骨头,嚷道,往后别惯这毛病,咱又不是员外家,自己吃,自己盛。我没好气地坐下来往嘴里扒饭,我妈给我夹过两回菜,我连头也懒得抬。喂,这就是你刚剃的头?白花了老子的钱,跟没剃有啥两样,你留这么长的头发,明儿咋去报名上学,啊?都是让你妈惯的,吃过饭,你再给我出去剃一遍,小小的年纪,学啥不好,我顶看不上不男不女的样子。
我记得自己撂下饭碗的同时,眼泪也亮亮地掉在了饭桌上。理就理,有啥了不起!我一边自言自语赌气,一边扭头往屋外冲。唉,你也是,总得让娃娃把饭吃完再说。我妈在身后喃喃着。唯独我那个刚逢面的姐,连头也没抬,仅从鼻孔里发出轻蔑的一声哼,继续埋头吃她的饭。我们一家情况特殊,大人长期生活在两地,姐姐从小是爷爷奶奶领大的,等老人们相继过世后,她才无可奈何地搬回来跟父亲住。所以,她对待爷爷奶奶之外的任何家庭成员,总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也包括我这个后来者。
我像一头小倔牛,再次怒冲冲地闯进理发店。
小伙子,你又来弄啥?
剃——头!!
不才剃了没多大工夫,咋的又长长了?
这回给我刮个光头,一根头发茬也别剩!
噢?老头儿一怔。看吧,早就说过,剃了干净,剃了干净。
这种极端的做法果然奏效,再进家门马上惹得男人发起了飙。喂,谁叫你剃成秃瓢?你真格是个现世宝,这个家养不下你了,干脆蹲大牢去!他简直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狮,大声斥责着,竟没忘记随手再赐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长到十来岁,才回到这意志巷,这可是他送给我的见面礼。许多年以来,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天,因为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被最亲的人打骂,在这之前,我一直和我妈在外地相依为命,她可是从不肯轻易动我一指头的,我真恨这个地方!
还有,我刚转到这里的学校念书,也是最难堪的时光。就因为我这颗赌气剃成的光头,被全体同学当作怪物,每个人都拿我当笑料。有人说,我不讲卫生,头顶生了虱子,所以才剃了个精光;更有人疑心,我来之前是个小阿飞,没少被人家管过。于是,女生们都提出不愿和我做同桌。本来当时我就是个插班生,那颗大光头让我扎眼极了。我见天只好戴一顶旧绿军帽,躲在教室的旮旯里,尽量远离那些好奇而又不友善的目光。幸好,头发是很容易长出来的东西,否则,我真不知道要在那种尴尬的境地中痛苦地煎熬多久。
总之在这个家里,我和我爸从来都是冤家路窄,他说东,我就说西,他让我捉鸡,我偏要去撵狗 。父子俩就好比一只耀武扬威的大公鸡,和一条总试图前来偷吃的野狗,水火永不相容,家里往往会因为我们俩,闹腾得鸡犬不宁,也每每使得我妈夹在中间哭鼻子抹泪。那件事过了很久,有一回,我趁那男人上班不在家时,悄悄问过我妈一次。
他,真是我亲爸?
傻瓜,不是亲爸,你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咋看都不像,他见我跟见了仇人似的,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你爸就那么个牛脾气,他年轻的时候,和你现在一个样,死犟,一条道能走到黑,九匹骡马也拉不回来,你倒是随了他的性格。
我不以为然,宁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反正从出生到现在,他没给过我一丝好处,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抱过我一次。我不过是十几年前,他在跟我妈分别那晚的激情产物,除此之外,“爸”这个概念对于我近乎陌生,在头脑里没留下一丝好印记。所以,我有一千个理由讨厌这鬼地方。
都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说说眼下的糗事吧。
我刚要越过院里最后一户人家的门口,却迷迷糊糊同正从房里走出来倒马桶的阿桂撞在一处。耳畔听到一阵很响亮的稀里哗啦乱响,一股腥臊的恶臭刺人鼻子。低头看时,裤脚上早已沾溅上湿乎乎的秽物,几团带着血污的卫生纸横在脚下的青砖地面上。没等我发作,对方早已先发制人,出门也不看路,又不是急着去投胎!我知道是院子里的寡妇阿桂,一腔的怒火不知怎么被抑制住了,眼前倏地闪现出她家丫头的娇嗔的小脸和微蹙的眸子。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我或许会动些肝火,可倒霉的偏偏是这个女人。我很木讷地双脚叉稳车身,一时竟不知所措。当目光落到阿桂的身体上时,我顿时有些眩晕和窒息,阿桂只穿一件低胸的睡衣,料子看起来很柔也很垂,大抵是丝绸一类的。阿桂的乳房透过睡衣隐约可见,丰盈浑圆的曲线在秋日晨曦中正散发着某种暧昧的光。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喉咙间发出一声干咳,仿佛突然折断的干树枝那样响亮刺耳。
恰好院子里的几个去晨练的人拎着木剑、端着盛满鲜奶的铝锅,陆陆续续走了进来,小院立刻显得危险而又拥挤不堪。我乘机推起自行车夺路而逃,隐约听到阿桂在炫耀她的真丝睡衣,可我眼前一直浮现着那摊秽物,这便让我突然萌生了一种猥亵的念头,我在想那卫生纸究竟是阿桂的还是她家丫头的。这样一想,胃里竟然一阵翻江倒海,我慌忙跳下车子,蹲在马路旁边的白杨树下干呕起来,我的窘态在路人看来一定和孕妇一样滑稽。
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阿桂的名字一直像王致和臭豆腐一样令人津津乐道。当然这并非完全是寡妇门前是非多的缘故。早在阿桂的丈夫死之前,院子里的老少就喜欢捕风捉影,经常谈及她的是非长短。阿桂说来也算不幸,串联的那阵子,她也风风火火地打起背包,搭火车,睡露天地,可等她重返故里时,却无可奈何地怀上了,而那个曾在她耳边信誓旦旦的人,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悔恨之余,阿桂只得先堕胎,随后又稀里糊涂嫁了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
后来阿桂的这个男人染病死后,意志巷的老少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来审视已然是丫头母亲的阿桂了。阿桂的皮肤白皙光洁,四十好几的女人,胸脯和臀部依然挺拔高凸,尤其她的眉目之间,还不时地闪烁着少女一般的情愫。阿桂穿衣十分讲究,该紧的地方绝对曲线突出不拘不束,而宽松的时候又裙衫飘舞摇曳生风。我知道丫头是不敢同她妈一道上街的,丫头很不习惯熟人阴阳怪气地和她们打趣。哟,是阿桂呀!打扮得这么时髦,和你家丫头简直像孪生姐妹啦。这个时候,阿桂往往会得意得飘起来,咯咯的笑声落了一路。丫头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意志巷里的老年人是顶瞧不上阿桂的,他们暗地里像煞有介事地议论不休。年逾古稀的莫老太,算是这群人的杰出代表,她虽已弓背塌腰,走路双腿打战,但对院子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却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让人觉得居委会没有返聘她,真是工作上的一大失误。
意志巷没一个好人!
莫老太总是从她那被浓痰堵塞得发音异常困难的喉咙间,咳出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老话,她对阿桂常常是冷眼相觑,撇着干瘪的嘴唇。阿桂是天生的妖精相,哪个男人跟了她,准不会有好日子过。这种预言在丫头她爸死后,委实让莫老太引以为豪。
事实上,丫头打懂事以后,就有一种难言的羞耻感时常萦绕着她。那时,我们院里的孩子在空旷的巷口藏蒙蒙、丢沙包、跳皮筋或玩打仗,她总是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即便走在巷里,也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仿佛谁会吃了她似的,远远躲开每个人的目光。我知道丫头打心底里厌恶她妈,就像我一直讨厌我爸一样。尤其是,在她爸过世以后,丫头最讨厌看到她妈站在穿衣镜前,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样子。
(节选自2023年第4期《芙蓉》中篇小说《秋日巷谭》)

张学东,1972年生于宁夏,现居银川。宁夏文坛“新三棵树”之一。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宁夏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发表作品,入选各种国内优秀小说选本及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
来源:《芙蓉》
作者:张学东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