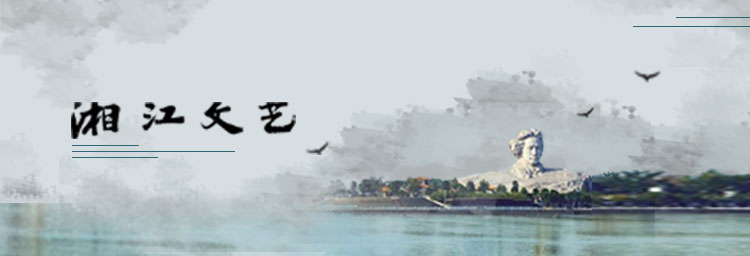

斑竹笛(中篇小说)
文/胡小平
一
那天是谷雨,雨没下,太阳也斯文,却是莫名地闷热,热得让人有点心烦意乱。
摆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我忙拿过一看,是母亲打来的。她开口就问我还记得那个文化癫子不。我一愣,问哪个文化癫子。母亲说还有几个文化癫子,就老鹰冲里那个杨半仙啊!我“哦”了一声,说那记得。母亲一声叹息,说可惜他死了。我一惊,说清明节回家扫墓时,还看到他给人做法事,吹笛子、拉二胡也好,念经文、唱祭歌也好,都还有板有眼、中气十足的,怎么一下就死了。母亲说是啊,谁也没想到的,一个时辰前还在给人做法事,也不知道他是给什么恶鬼捉着了,好当当地就一声怪叫,将锣钹往地上一扔,捧起桌上那碗酒几口喝了,将碗往地上一砸,取下挂在胸前那根斑竹笛,吹着就走了,结果掉进了路边的鱼塘里。
我走进卧室,从抽屉里取出那根用绸子包着的斑竹笛,走到阳台上,望着家乡的方向,轻轻吹了两下,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想起文化癫子原本的名字,只好问母亲。母亲说她也一下想不起来了,得问问。过了十来分钟,母亲回电话过来,说总算问到了,他叫杨双喜,早前大多叫他文化癫子,后来有喊他文化人的,近些年叫他杨半仙的人又多了。
二
那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吃过饭,我赶紧写完作业,从书包里取出用纸板做的扑克,刚准备跟弟弟玩两把,给牛添完草料的母亲回来了。她边说天寒地冻的,快点上床,边将散在桌上的课本和纸笔往蓝布书包里捡。我边应答边洗着牌。她一把从我手上抢过扑克,探一眼桌下的火盆,稍一犹豫,将扑克往书包里一塞,说别磨蹭了,快睡觉去。我脖子一缩,拎了书包,拉着弟弟就往卧室跑,边跑边想,真是谢天谢地,母亲总算没有将扑克扔进火盆。
缩在被窝里,我先是默背课文,然后在手心里默写生字。弟弟起了鼾声,含混不清地说着梦话,不时地还哈哈笑着。
刚要蒙眬睡去,就听到院子东头的石板路上传来了笛声,我一下瞌睡全跑了,跟着笛声哼了起来。那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我才跟着哼了几下,就听到隔壁有了拍床沿的声响,有了母亲问我怎么还不睡,还在哼什么,有了母亲说这杨双喜,也真是,天寒地冻的,都这么晚了,还在外边吹什么鬼笛子,真是个文化癫子。
深浅快慢不一的脚步声伴着悠扬清亮的笛声从窗外飘过。我正听得入神,猛地传来“咕咚”一声闷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母亲已“吱呀”一声开了门,说准是文化癫子掉鱼塘里了。
进了屋,哆嗦着的杨双喜一数挂在胸前的笛子,说怎么只有五根,少了一根,转身要去塘边找。我说他手上还拿着一根。他一看,嘻嘻笑了。母亲给他找来衣服,又给他用老姜和干红辣椒煮了姜辣汤。
杨双喜后退一步,说请母亲受他一拜。母亲忙扶着他,说不敢当。他说母亲救他一命,还给他找衣服,煮姜辣汤,比他亲娘还好,又说他也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这点礼数他懂,说着又要拜。母亲一笑,说知道他是个有文化的人,知道他懂礼数,可她受不起。他挠挠头,笛子一横,说那给母亲吹个歌。母亲摆摆手,说深更半夜的,别吓着邻里,快早点回去。他偏着头一想,看了看那几根笛子,取下中间那根短的斑竹笛,双手托着,说送给我。我看一眼母亲,满心欢喜地双手接了过来。
杨双喜刚要出门,院子东头的吴小娥跑来了。她看一眼杨双喜,脸一红,说外边又加寒了,也起青水冰了,地上滑溜溜的。杨双喜说知道,他刚才就是一不留神,滑到塘里了。
母亲给杨双喜点燃了一把竹篾,催着他快点走,晚了路上就更走不稳了。吴小娥要他等一下,她马上回来。她转身就跑,转眼又来了,边说外面冷,下刀子似的,边将一件补丁打补丁的夹衣往杨双喜手上塞。杨双喜边看着夹衣边往后退。吴小娥红着脸,说没事,她娘没看见。母亲接过夹衣,边看边说没关系,面子是有点花花绿绿,但里子是蓝的,翻一面穿就行了,穿着总比挨冻好。杨双喜犹豫着接过夹衣,抖了抖,往身上一披,看一眼吴小娥,嘿嘿一笑说嗯,这就是下刀也不怕了。吴小娥脸又一红,瞟一眼杨双喜,跑回家去了。母亲飞快地搓了两根稻草绳,绑在杨双喜的鞋底上。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醒了,摸出放在枕头下的斑竹笛,放到胸口上,边透过窗户上的薄膜数着屋檐上垂挂下来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冰凌,边等着杨双喜的歌声或笛声从屋前的地坪飘过。
这两年来,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阴晴雨雪,杨双喜都是天刚大亮,就会唱着歌或吹着笛子,从我家屋前地坪走过。他的歌声或笛声已然成了我的时钟、我的号角。每每一听到他的歌声或笛声,我准会被子一掀,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可是这天早上我等呀等呀,等到的是已忙碌了好一阵的母亲走来被子一掀,说你怎么还在床上,还不快去上学?我连忙穿好衣服,挎上书包就跑。
那天晚上,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饭,碗一搁,问母亲怎么叫杨双喜文化癫子。母亲一愣,说这可不是她叫出来的,早就有人这么叫了,又说杨双喜是像个有点文化的样子,会唱歌,会吹笛子,说话又讨人喜欢,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但他不分早晚、不分场合,想唱就唱,想吹就吹,跟癫子一样,叫他文化癫子也没错。我点了点头,却还是没怎么弄明白。母亲放下碗,看着我和弟弟,说杨双喜虽然会唱歌、会吹笛子,可那些都换不来油盐、换不来柴米,没半点用处,千万别学他,上学就得有个上学的样子,要不就回来帮家里挣工分。我小鸡啄米一般点着头,心里却有点羡慕杨双喜。羡慕他会歌唱,又会吹笛子,还讨吴小娥的喜欢。吴小娥那小酒窝,那大眼睛着实让人着迷。
早上起来一看,地上全白了。母亲要我快去一趟杨双喜家,把衣服换回来,也看看他怎么样了,都两天没听他唱歌,没听他吹笛子了。我高兴坏了,拿了那斑竹笛就跑,可才走到塘堤上,吴小娥就追了上来,说她也去讨衣服。我知道她这是借口,就故意逗她,说我给她顺便带回来,免得她跑一趟。她说反正没事,走一走还暖和些,也正好给我做个伴。我指了指她,哈哈大笑,笑得她脸一红,映红了路边坎上的雪。
那是一栋老旧木房子,上一层四面敞开着,堆放着稻草、晒簟之类的东西,还晾着几件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房子西头是一片小竹林,竹林里最抢眼的是那一丛斑竹,东边是一片小树林,树林中最显眼的是那棵梨树。房子的前边是地坪,地坪前边是梯田,一条石板路蜿蜒下去,连着田垄那边的机耕道。
进了门,一听我们是找杨双喜的,易美秀将手上的潲桶往地上一搁,一指里边卧室,说还在床上躺尸呢,没淹死好了。
杨双喜有气无力地说,前天晚上从我家出来后,半路上滑到水田里,火把熄了,脚上的草绳脱了,几乎是爬回来的,烧得差点把床铺都点燃了。吴小娥抹了抹湿润的眼睛,说他怎么不早点回家,非要来遭这个罪。他说跟街上的贾秀才学吹笛子,学拉二胡,忘了时辰。吴小娥说那也得有个早晚,今后不能再这样了。易美秀刮一眼吴小娥,嘟哝了一句骂人的话。我听得有点含糊,也不知道吴小娥听见没有。
母亲见我怏怏不乐地回了家,问是怎么了。我说没什么。闷坐了一会儿,我问在剁干红薯藤的母亲,都说天下爹娘疼崽女,怎么易美秀就一点也不疼杨双喜,还巴不得他淹死。母亲瞟我一眼,边剁红薯藤边说那是怄气话,哪有爹娘巴不得儿子淹死的。我说看易美秀那样子,凶巴巴的,可不像是说的怄气话。母亲放下刀,看着我,说杨双喜也是太不争气,既不好好上学,也不好好帮家里干活,要我是这个样,那她也不会喜欢的。我忙把手背到身后,手上紧攥着那斑竹笛。
三
杨双喜说的贾秀才叫贾梦生,说是他母亲多年未孕,一日坐在堂前小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不久就怀上了。他出生时科举考试已废止十来年了,只因他是村上少有的能识文断字的人,加上长得斯斯文文,说话也细声细气,又长年蓄着胡须,还一年四季一身长衫,真就一个秀才似的。
贾秀才年少时家中有上百担谷的田地,街上还有一家铺子,是村上有名的殷实大户。他父亲贾善人先是请了先生教他,后来又送他去了县里的学堂,正准备送他出国留洋,不知怎么惹恼了山上的土匪头子陈大麻子。那天晚上,陈大麻子本来只想吓唬一下贾善人,让他有所畏惧,多孝敬山上,没想到火一点,刚好起了风,结果风助火势,把一个大院子差点烧个精光,烧得贾善人大口吐血,昏倒在地。陈大麻子见祸闯大了,也怕了起来,但走时又扬言过几天再来,到时候把贾秀才这根独苗给掳上山去,吓得贾秀才他娘只好连夜让他去省城投奔亲戚,还一再叮嘱他,陈大麻子没死就别回来。他走后没多久,贾善人就归西了。两个多月后,贾秀才他娘也跟着走了。
贾秀才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发誓要灭了土匪、杀了陈大麻子,还起誓不灭土匪,不杀了陈大麻子,就不剃胡须、不娶妻成家。
投奔亲戚没几天,看到街上招兵,贾秀才一想,自己去当兵,等当上了连长什么的,到时候就带兵回去剿灭了陈大麻子,为地方除害,为家中报仇。第二天,他给亲戚留了张纸条就跟着队伍走了。
到了部队,贾秀才做的是文书,可他不想拿笔,就想扛枪。一年后,连长给他机会,让他当副排长,可上任没几天,在转移途中,碰到日寇飞机轰炸,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把他炸到山崖下去了。他昏迷一天后给村民救了下来,身上伤了几处,一条腿残了。
一能下地,贾秀才就去找队伍,可队伍不知去向,便去找招兵的地方,可招兵的一看他瘸着的腿就直摇头。兵是当不成了,又不敢回村上,怎么办?他思来想去,只好回到亲戚那里。于是他穿上长衫,在街上摆了个小摊子,干点代人写信写春联之类的事,后来又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亲戚几次让他剃掉胡子,给他张罗亲事,他都摇头,说还没到时候。
等贾秀才回到村上,土匪被消灭干净了,陈大麻子也被枪毙了。有人说这下他可以剃胡子了,可以娶亲了。他说土匪不是他灭的,陈大麻子更不是他杀的。就这样,他到死都没剃过胡子,只是太长了就修剪一下,也没成家,虽然有女人想着他,还在他那住过一夜,但他说什么都没发生。
乡亲们知道他是打鬼子伤残了腿,家里又遭了那么大的变故,贾善人在村上也不是恶人,没做过恶事,土改时便没打贾秀才的地主,一样给他分了田地,分了房子,见他腿残了,又没下地干过活,就让他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于是,他长衫一穿,在铺子里一站,又干起了给人写信写春联的活儿来,同时卖点日杂南货,闲暇时学着刻印章,学着吹笛子拉二胡,后来又喜欢上了《易经》,琢磨起了看相看风水。
这天,贾秀才放下刻刀,吹了吹桌上的木屑,用刷子刷了刷章子,在印泥盒里摁了摁,在纸上一盖,满意地点了点头,将章子放进抽屉的铁盒里,等人明天来取。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两口水,一抹嘴,取下挂在墙上的竹笛,望一眼远处快下山的太阳,转身倚着桌子,对着墙上的杨子荣画像吹了起来,吹着吹着笛声就呜咽了,眼泪掉在了笛子上。《打虎上山》是他最喜欢吹的,每每吹着就把敬佩杨子荣的英勇机智,恨座山雕的凶狠狡诈,恨自己没能亲手灭了土匪,没能亲手杀了陈大麻子的情感融入了笛声里。
贾秀才一声叹息,一转身看到一个小脑袋倏地缩到柜台下边去了,便用竹笛轻轻敲了敲柜台,说你又在偷听,还躲什么,快出来吧!杨双喜腼腆地笑着,露出大半个头来。贾秀才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听。他说好喜欢,比听老师上课还喜欢。贾秀才冲他一笑,指了一下柜台里边。他挠挠头,嘿嘿笑了笑,从柜台一侧下边的小门钻了进去。
才听杨双喜吹了几口,贾秀才就点了点头,拿过他手上的笛子,要他快唱个歌来听听。他一段还没唱完,贾秀才就把他拉到跟前,看了看他的五官、摸了摸他的后颈、捏了捏他的手骨,捋了捋胡须,说好一个文曲星的料,却只怕没这个命。他眨眨眼睛,问贾秀才说的什么。贾秀才浅浅一笑,说,没什么,没什么。贾秀才虽然声音小,也有点含糊,但“文曲星”三个字他是听到了的。见他还要问,贾秀才拍拍他的后背,说往后放了学只管来,进铺子里边,别老在外面躲躲藏藏,做贼似的。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贾秀才却脸一板,说来可以,但不能耽误了上学,在家也不能偷懒,别到时候他爹娘来怪罪。他略一迟疑,点了点头。贾秀才望一眼铺子前边夕阳里金波闪跳的河湾,吸一口清风捎来的田塅里的稻花香,催着杨双喜出了铺子。杨双喜三步一回头地往街的南端走去。贾秀才见杨双喜消失在桥亭前的人流中才收了目光,出神地望着田塅,望着河湾。
这田塅叫黄金塅,那河叫流金河。流金河从田塅东北边的崇山峻岭间奔腾而下,从田塅中央蜿蜒而来,将田塅一分为二,在田塅西南边的蛇形山前一拐,拐出一个大河湾后,滚滚涛涛地向东南去了。
一座廊桥飞架在河湾的尾巴上,把南北古老的青石板官道连接起来。这官道林则徐和魏源曾结伴走过,还一起在廊桥当头的茶亭歇息喝茶。这些贾秀才都考证过,常津津乐道,特别是每每一说起林则徐和魏源的交往,说起魏源醮墨吃粽子的故事,那准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这我都他听说过,听得津津有味。
在蛇形山下,河湾岸边,店铺鳞次栉比,绵延三四里。这就是杨双喜说的街上。贾秀才的铺子依山面河,站在柜台里边,远处那层层叠叠的山色、蜿蜒而来的流金河,近处廊桥上的景致、街上的热闹,可尽在眼底、尽在胸中。
(节选自2023年第4期《湘江文艺》胡小平的中篇小说《斑竹笛》)

胡小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主席,已发表、出版作品400万字,获中国第二、第三届金融文学奖、中国金融作协征文一等奖、《湖南日报》和湖南省作协联合征文一等奖,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征文二等奖、湖南省“青山碧水新湖南”征文三等奖,长沙市“五个一工程”奖等。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胡小平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