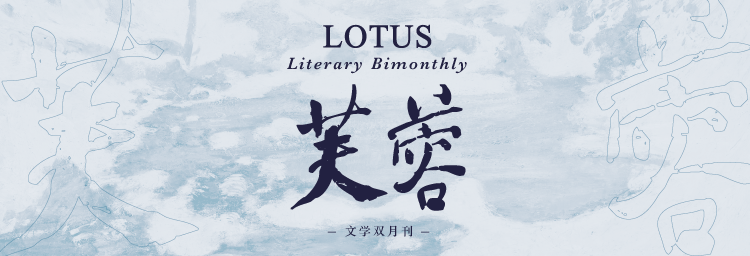

干净(短篇小说)
文/刘庆邦
天黑了下来,越来越黑。该睡觉了,爷爷还没回来。我们家的灶屋里支了一张小床,我和爷爷睡在那张小床上。爷爷很喜欢我,对我持的是欢迎的态度,一直。可我不怎么喜欢跟爷爷睡,更愿意和娘、大姐、二姐、妹妹和两个弟弟一起,挤在堂屋西间屋的那张大床上,像一群雏鸟依偎在亲鸟的翅膀下面一样。把我单独摘出来,让我跟爷爷一块儿睡,是娘分派给我的一项任务,说是给爷爷暖脚。我的脚还是凉的呢,怎么给爷爷暖脚!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娘不由分说,坚持派我去给爷爷暖脚。娘说出的理由是:谁让你爷爷最喜欢你呢!娘对我说过,爷爷没抱过我大姐,没抱过我二姐,更没抱过我妹妹,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老是把我抱在怀里。不管是到镇上赶集、听小戏儿,还是下雨下雪天,去听村里的一位老先生给他念书,他都会带上我。我饿了,他买白蒸馍给我吃。我想玩点什么,他就让我捋他长长的花白胡子。爷爷有一件棉袍子,在天冷的时候,爷爷就把我揣进他的棉袍子里,外面再系上一根布带,只让我的头在棉袍子里露出来。现在想来,爷爷那样把我揣在他贴胸的怀里,很像一只老袋鼠揣着一只小袋鼠。有人从对面走过来,爷爷往往不等人家问,就主动把“小袋鼠”推荐给人家看,说这是他孙子。爷爷的做法,显然有些显摆。暮年有了孙子,仿佛孙子是他一辈子的全部骄傲所在。
对于能不能起到给爷爷暖脚的作用,我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因为我有尿床的毛病,三天两头把尿水撒在床上。我们姐弟六人,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娘的别的孩子都不尿床,只有我一个人尿床。也就是说,他们在被窝里睡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被窝还是热气腾腾的干被窝,只有我的被窝,常常成了臊气烘烘的湿被窝。被子和褥子被尿湿了,在晴天有太阳的时候,娘难免会把湿成一块块深色的被褥拿到院子里晾晒。院子里的叔叔婶子们看见了,把我尿湿的地方,说成是我画的地图,还说每一幅地图都不重样。这样一来,娘晾晒被褥,等于公开晾晒我的丑,把我丑得眉头紧皱,头都不敢抬。还有人把尿床的事编成了顺口溜儿:尿床精,踩床牚,半夜里来数星星;老天爷,咋还不明,把我的屁股渍得一片红。我相信,这个顺口溜儿不是专门针对我编的,它应该是把天下所有的尿床精都包括在内了。不想承认也不行,这个顺口溜儿还真的道出了尿床精尿床后的难堪细节和悲苦心情。我有时发觉自己尿床后,就压在尿湿的地方不挪窝,企图用自己的热身子把湿处暖干。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对自己说:谁让你尿床呢,你把床尿湿了,就得自己暖干。可恼的是,我身上释放的暖气总是有限,虽然带碱的尿水把我身体渍得又红又痒,可每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开始上学并当上班长以后,我渐渐地有了自尊心,知道了树要皮,人要脸。树没有皮就不能成活,人不要脸面呢,就会被人看不起。兔子撒尿,可以撒在窝里;羊撒尿,可以撒在圈里。人既然变成了人,不是别的动物,怎么能尿在床上呢!都当上学生了还在尿床,肯定是丢脸的事。有时刚躺下睡觉时,我大睁着两只眼,不允许自己睡着。只要还醒着,总不会尿床吧。然而,把眼睁一会儿不难做到,倘若睁着眼一夜不睡,我无论如何都办不到。在不知不觉间,我关上眼皮,睡着了。同样在不知不觉间,我又尿了床。真恼人哪,真可恨哪,人干吗非要撒尿呢,难道不撒尿就不行吗!
长大成人后,听大姐、二姐回忆往事,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养成了尿床的毛病,与娘对我的娇生惯养不无关系。我一两岁之前,都是娘搂着我睡。我夜里撒尿时,有时会滋在娘身上。娘明明醒了,却一动不动,一点儿都不惊慌。娘不叫醒我,也不中断我的撒尿,任凭我把尿水一直滋在她身上,直到把一泡尿撒完。娘对我大姐、二姐说,半道打断我撒尿,她担心我会憋出毛病来。娘还说,我撒的尿热乎乎的,一点儿都不凉。这就是娘,娘对我的宠爱达到了溺爱的程度。我见过溺爱这个词,以前对这个词不是很理解,不懂溺和爱怎么就联系到了一起。听了大姐、二姐讲的我小时候的故事,才真正懂得了溺爱的含义,得知娘对我的爱是典型的溺爱。
不见爷爷回来,娘让我去喊一下爷爷。二姐见我迟疑着不想去,主动要求跟我一块儿去。是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但是,我们不是去喊爷爷回家吃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家不再做晚饭,无晚饭可吃。不做晚饭,是因为没粮食下锅,做不起晚饭。当时,我们家仅有的可以哄哄嘴巴的东西,就是半瓢棉籽,半筐长着黑色霉点儿的红薯片子,还有半盆用霉红薯片子磨成的粉。这些东西要留给做早饭和做午饭的时候用。人在上午和下午都要干活儿,不吃点儿饭干不动。晚上不干活儿,天一落黑就可以上床睡觉,不吃晚饭也可以吧。多次听娘说过,人的肚子是盘磨,躺着不动就不饿。在没什么东西可吃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向不动的石磨学习,向不动的石磨看齐。我和二姐都知道,爷爷有可能还在饲养室前墙的墙根那里靠墙坐着。只要是晴天,爷爷就去那里晒太阳。牛要从饲养室里牵出来,拴在门前的木桩子上晒太阳。驴也要牵出来,拴在木桩子上晒太阳。爷爷跟它们一起晒太阳。在晒太阳时,牛和驴都眯着眼不说话。爷爷也不说话。爷爷晒太阳的能力很强,一晒一上午,一晒一下午。到了下午,牛和驴都被饲养员牵进饲养室里去了,爷爷还在原地坐着不动。太阳都落到地底下去了,早春二月的夜晚还很凉,爷爷不回家睡觉,还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以前,是我们的爹,在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当饲养员。在爹当饲养员期间,爷爷就习惯了靠坐在墙根晒太阳。我爹在回家的时候,会喊他一块儿回家。爹在去年六月去世了,老年丧子,爷爷伤心是难免的。爷爷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是不是在这里守着他儿子的魂呢?是不是等着他儿子的魂喊他回家呢?
离饲养室还有好几步远,透过饲养室的门缝里透出的微弱煤油灯光,我们就看到门口左侧的墙根有一团黑影,不用说,那团黑影就是我们的爷爷。二姐拉了我一下,把我拉得停了下来。二姐小声对我说:咱爷不会没气儿了吧!二姐的话把我吓住了,吓得我禁不住直往后退。在我们那里,说人没气儿了,就是人死了。说得好听一些,是没气儿了;说得直接一些,就是死了。我和二姐知道,因为长期吃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爷爷得了浮肿病。爷爷的浮肿,是从脚面子那里开始肿起,肿得脚面像遇到危险就虚张声势的气蛤蟆一样。爷爷肿起的双脚,跟气蛤蟆又不大一样:气蛤蟆是灰白色,爷爷的肿脚是蜡黄色;鼓胀起肚皮的气蛤蟆富有弹性,越按越硬,爷爷浮肿的脚面是软的,用大拇指一摁就是一个深坑,深坑迟迟不能弹平。村里所有因饥饿得浮肿病的人症状都差不多,都是先从脚面子那里肿起,然后是脚踝、脚脖子、小腿等,自下而上逐渐蔓延,等蔓延到大腿、胳膊、脖子,甚至面部,离没气儿就不远了。我不知道爷爷的浮肿到了哪个阶段,至少还没肿到脸上,难道这么快就没气儿了吗?
二姐让我不要害怕,她说,她要对爷爷喊三声,如果喊过三声,爷爷不答应,我们就赶紧回家告诉娘。二姐第一声喊的是爷,第二声喊的是爷爷。二姐喊第一声的时候,没听见爷爷答应,我扎好了架势,准备往回跑。还好,二姐喊第二声的时候,爷爷有了回应,爷爷嗯了一下,像是在睡着的状态下被喊醒了一样。打二姐一出生,爷爷就不喜欢二姐。同样,二姐也不喜欢爷爷。二姐的口气像是有些生气,问爷爷:天都黑了,你为啥还不回家?
爷爷说,他站不起来,站了几次都站不起来。爷爷没有把站不起来的原因归结到双脚的浮肿上,他说看来他真的老了,不中用了。爷爷让我们两个把他拉起来。
我和二姐确认爷爷还活着,还会说话,这才敢走到他身旁。爷爷还穿着那件粗布棉袍子,棉袍子已经很破旧,老得像爷爷一样。爷爷很瘦,瘦得皮包骨头。棉袍子把爷爷的瘦包住了。夜影中,在地上坐成一堆的爷爷,不但不显瘦,似乎还有些臃肿,全身都浮肿了一样。爷爷向我们伸出了手,爷爷的双手有些发抖。爷爷说,他疼孙子,真是疼值了,孙子现在中用了。他只说孙子中用了,没说孙女中用了,这让二姐有些生气。好在二姐对爷爷没有甩手不管,我们姐弟二人分别抱住爷爷的一只胳膊,使劲往上拉。是的,爷爷递给我们的是他的手,我们不敢接触他的手,他的瘦骨嶙峋的黑手让我们有些害怕,我们只能隔着棉袍子的袍袖子,抱住爷爷的胳膊奋力拉拽。我们刚把爷爷拉起来,爷爷站立不稳,身子有些摇晃,差点儿跌倒。爷爷把后背靠在后面用土坯垒成的墙上,以墙壁为依托,才没有跌倒。村子里很静,听不到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狗叫声。大概每户人家都不做晚饭,村子里闻不到一点儿烟火味。没有风,树梢一动不动。不见月亮,天上只有一些星星。每一颗星星看上去都很寒,像是用冰凌做成的。爷爷仰脸看了看天上的星星,捋了一下胡子说,走吧,回家吧。
回到家,二姐去堂屋跟娘交差,我和爷爷直接回到灶屋的小床上睡觉。别看我们家的灶屋只有一间屋,几年间先后住过两户人家呢。在“大跃进”时村里成立大食堂那年,当队长的堂叔家的房子被挪作生产队的磨坊,堂叔一家四口只好搬到我们家的灶屋里住。接着,人民公社搞集体农庄,邻村的小李庄有一半人口要搬到我们村居住,住房重新调整,堂叔家搬出去,小灶屋里住进了外村来的一家六口。后来,集体农庄垮掉了,大食堂断顿了,解散了,各家各户的人重新回到原来的房子里住,我们家的灶屋才得以物归原主。灶屋里没有煤油灯,我和爷爷只能摸黑进屋,摸黑脱衣服,摸黑往小床上爬。我们那里不管大床小床,床上都不封床板,只在床上横着钉几根牚子,再在床牚子上铺上秫秸箔和席子,就可以在床上睡觉了。小床上铺的褥子很薄,虽说褥子的正反面都打了不少补丁,薄得还是跟没套棉花差不多。别管如何,床上能铺一块褥子,热身子不用直接贴在冰凉的席片子上,已让我们感到不错。更让我们感到不错的是,床上还有一床被子,爷爷每晚把他的棉袍子敞开覆盖在被子上面,等于我们爷孙俩身上又盖了一层被子,构成了加倍的满足。
我和爷爷打通腿,各睡在床的一头。北为上,南为下,爷爷睡北头,我睡南头。既然娘派给我的任务是给爷爷暖脚,睡觉时我应该把爷爷的脚抱在怀里才对,可爷爷总是把他的脚跟我拉开一段距离,从来不让我抱他的脚。这样正好,爷爷的脚是臭脚,不值得我抱。爷爷也知道我有尿床的毛病,他大概不愿意让我尿在他的脚上吧。不管抱不抱爷爷的脚,尿床是难免的。每当发觉他的孙子尿了床,爷爷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从没有用脚踹过我的屁股,连大声吵我都没有,顶多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说:又尿床了,真没办法!爷爷的脚浮肿之后,我更不愿意抱他的脚。听大人说,人的脚一旦浮肿,表面看像是脚发胖了,其实里面包的都是水分。这么说来,爷爷浮肿的双脚里等于也包了不少水,说不定爷爷的脚也会尿床呢,我还是离他的脚远一点为好。
我和爷爷分两头在小床上躺下,爷爷不说话,我也无话可说。我们像是两个哑巴,一个老哑巴,一个小哑巴。说话也是需要费力气的,我和爷爷的气力都有限。能省一点气力就省一点吧。睡觉前,我把灶屋的单扇桐木门关上了,灶屋顿时陷入与世隔绝般的黑暗。灶屋因常年烟熏,四壁和房顶本来就很黑,黑夜里把门一关,黑上加黑又加黑,小屋里显得更黑。我呢,好像嫌黑得还不够,拉被头把脸蒙上了。我眨眨眼皮,除了从眼底冒出的朵朵金花,什么都看不见了。
(节选自2023年第5期《芙蓉》短篇小说《干净》)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家长》《断层》《远方诗意》《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文字。
来源:《芙蓉》
作者:刘庆邦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