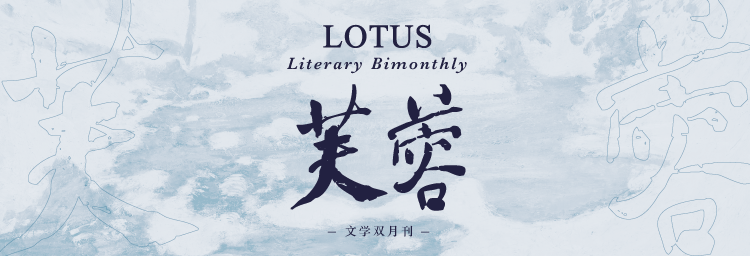

黑山牧铺
文/阿尼苏
我已经记不清那是7月末还是8月初了,在牧铺待久了,时间就像静止的山峦,没有什么变化。那天夜里下着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的雨。雨势时大时小,毡房外一片漆黑,栅栏里的羊群躁动一阵后安静下来了。我在铁炉内生起牛粪火,驱赶阴冷的湿气。小黑狗蜷缩在哈那下,雨声一变大,它就抬头看向紧闭的木门。我把收音机塞到枕头底下,然后找出一瓶白酒,就着奶豆腐和芥菜疙瘩喝起来。不知不觉间大半瓶酒进肚,肉皮挤出一身汗,我感到浑身畅快,就光着膀子小声哼唱没有歌词的乌尔汀哆来。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寂寞难熬的漫漫长夜里,除了听收音机、喝酒、唱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从三十岁那年夏天离开家乡到如今,已经在山地草原上的多个牧铺间游走了二十年。我的雇主换了一个又一个。现在的雇主去年被他侄子接到镇上,舍不得转让牧场,也舍不得卖掉羊群,便找到了我。他预付了一个夏季的工钱,还留下了两匹苍灰色的马。这种马越来越罕见,他叮嘱我要好好照料。我居无定所,孤身一人,除了两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外,只剩一个亚麻布行李包。好多人曾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但我没什么可悲叹的,于我而言,人生不过是个过场,尤其年龄大了,这种体会更深。
临近半夜,雨势减弱。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小黑狗突然叫起来,随即传来一阵沉闷的敲门声。这样的天气,偶尔会有走夜路的牧民进来避雨,并不奇怪。可那天进来的人不像牧民。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等个子,很瘦,皮肤白嫩,尖脸上戴一副黑边眼镜。他明显在路上摔倒过,手背有刮伤,西裤和格子衬衫还破了几处,不过他看起来像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他没有穿雨衣,浑身湿透,鞋子上沾满泥浆。我赶紧让他坐到铁炉边烤火。小黑狗停止了叫唤。我拿给他消炎药,又煮了一锅奶茶,里面放了一大勺黄油和足够多的炒米、奶豆腐、肉干,又给他倒了一杯白酒。他没有喝酒。他吃完时,身上的衣服也干了大半。蓬松起来的头发和乱长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有些落魄。我问他的情况,他低头不语。蜡烛快要烧到底部时,我擅自做主,拿出雇主家的一张毛毯,递给他,说:“年轻人,先睡一觉吧。”盖上毛毯,他很快就睡着了。
我穿上衣服走出毡房,去看了看羊群和两匹马。小黑狗跟着我。毡房、羊圈和马棚搭建的位置地势稍高,雨水已经顺着斜坡流进不远处的河道。此时的天空布满了星星,从西北边的山谷里吹来凉爽的风。草原的夜格外宁静,清透的空气令我神清气爽。我回到毡房时,小伙子睡得死死的,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小伙子说:“我想再住些天,帮您牧羊。”我说:“孩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做事?像昨晚的情况,谁都会帮你的,不用放在心上。”他先是向远处的土路望了望,然后收回目光,说:“我叫……敖其尔,在市里做文职工作。”
他轻咬着嘴唇,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三十岁时的自己。那时的我,因为一场意外,陷入绝望不能自拔。那天刚下过一场暴雨,地上满是黑泥和积水,我去快建完的砖房做检查时,怀胎四个月的妻子也跟着来了。她说想活动活动,顺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没有制止。我们正在砖房内有说有笑时,一根横梁突然掉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她的脑袋上……
妻子和未来得及出生的孩子,两个生命在我眼前没了。我就是凶手。我所有的欢乐、幸福和憧憬瞬间化为乌有。后来,我卖掉房子和牲畜,开始四处游荡。妻子半睁的眼睛和搭在肚子上的手,在我日渐麻木的记忆中显得格外突兀,仿佛发生在昨天,我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我常常从噩梦中醒来,然后茫然地对着黑夜叹息。
我赶紧从回忆中拽出自己。我问敖其尔:“你会骑马吗?”他一下子振作精神,用力点点头。我给两匹马架上了鞍桥,又给他找了顶草帽。他微微撑开双臂,像是给自己打气似的摆出一副英雄好汉的架势,脸上浮出不自然的笑容。百余只羊在山地草原上缓缓前行。雨后的阳光更加毒辣,被雨水浸润过的青草,干透后泛着白光。适应一阵后,敖其尔很快摸透了灰马的脾气,他那一声声“驾”“吁”,弄得有模有样。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的话题,我对他市里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也对眼前的景色只感慨不多言。
走了一段路。敖其尔眯着眼指着远处,问:“那座山怎么是黑色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原因,总之那座山远远望去像一块乌云,但走近了就会看到最绿的草,这里的牧民称之为黑山。”他问:“这座山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吗?”我说:“这是一座圣山,牧民不让畜群吃黑山上的草,山顶有一个敖包,像一块白云。”他没再说什么。
当我们穿过两座山后,就到了黑山脚下。我的雇主走前祭拜过山顶的敖包。我因为时刻盯着羊群,还未曾上去过。敖其尔下马将马绳递给我,说:“我上去看看。”这座山不高,他很快就爬上去了。羊群在山脚吃草。我把他的马绳钉在山脚,两匹马一起望向山顶,它们的眼睛清澈明亮。我骑上自己的马,领着小黑狗继续向前方牧羊。天上没有云。等我走到另一座山的半山腰上时,远远看见敖其尔像拴马桩似的戳在敖包前,一动不动。写满经文的彩带在风中翻飞,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他站了很久,直到我折向另一个方向时,他才骑马赶来。这里的山布局疏朗,从山顶能望向很远的地方。回来后的敖其尔连连叹气,不过比之前似乎少了点愁绪。虽然我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但是能理解他的心境。成长中的年轻人需要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需要面对各种压力。我希望辽阔的草原能消解他心头的苦闷。于是,我再次唱起没有歌词的乌尔汀哆。他也跟着唱起来。我们自编自唱,悠长的旋律逐渐融到一起。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声音很好听,带着磁性的中音诉说着某种隐秘的哀愁。但他就是放不开,处处拘谨。我大声说:“小伙子,啥也别在乎,放开唱吧。”他受到鼓励,握紧马绳,仰脖唱。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股没有解开的心结和一丝愤怒。
敖其尔在牧铺住下,没说什么时候走。白天每次路过黑山时,他都会爬上山顶,然后面朝敖包伫立良久,看不出是在忏悔,还是在希冀着什么。他晒黑了,也结实了。我拍着他的臂膀,笑着说:“你越来越像牧民了。”他说:“如果真能成为牧民就好了。”他这话说得很干脆,也很硬,我听来不是滋味。我越来越欣赏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了。在我的指导和鼓励下,他放牧、唱歌、喝酒都与牧民别无两样。牧羊时,我总是勒住马缰,让他先骑过去。看着他的背影,我产生一种幻觉,如果没有那场意外,无论我的孩子是男是女,肯定会像他这样在我前方骑着马,时不时回头叫我一声“阿爸”,而身边的妻子则会向我投来温柔的目光。我的心被无形而奇怪的东西戳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我真觉得敖其尔就是我的儿子,直到眼睛被烈日灼疼,才回到现实,仿佛刚才做了场短暂的梦,或是走进了另一个空间。
夜里,敖其尔跟我听收音机,当乌力格尔里的英雄倒下时,他会随着哀婉、沉静的低音四胡声发出长长的叹息。他虽然很迷恋眼前的生活,但他终究不是牧人,他有他的生活。当他的脸上展露出某种坚定的笑容时,也就意味着他将要离开。那天,他没有跟着我放牧,留在毡房洗衣服。他说衣服干了就回去。我有些难过,但更多是替他高兴。我下午在河边饮羊群时,故意磨蹭。我不想尝到面对面离别的滋味,那很不好受。这时,我看见一只半个身子陷进河边泥地里的野兔。它不断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我牵马走过去,蹲下身,一只手握紧马绳,一只手伸过去抓住野兔的耳朵向外拽。野兔被我成功救下,它蹦跶几下,便消失在草丛中。而我的一只脚被泥底的几块石头夹住,无法抽回。灰马着急地向后拉我,这不仅无济于事,还让我更加疼痛难忍。我也没法叫人。这片牧区,只有爬到山顶手机才有信号。我的脚脖被夹得动弹不得。小黑狗狂吠一阵后,突然向远处奔去。羊群在河边散开,灰马不断点头跺脚……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阿尼苏《黑山牧铺》)

阿尼苏,本名赵文,80后,蒙古族。写作、翻译。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文汇报》《作品》《草原》《绿洲》等报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散文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已出版散文集《寻根草》、短篇小说集《西日嘎》。
来源:《芙蓉》
作者:阿尼苏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