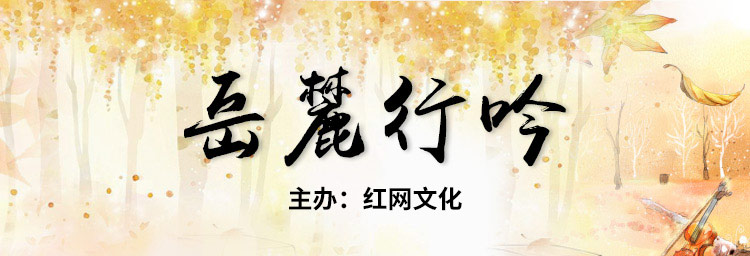

月光皎白惟清辉
——品读戴志刚《月光皎白》
文/李先平
一
亥时连子时,我看完《徐霞客游记》第二册之“粤西游日记”,虽说满脑子“是夜月明如昼”“是夜月色甚皎”,但略有倦意,正待休息。忽然微信一闪,打开一看,志刚发来两幅高清图片。一张是新书封面《月光皎白》,一张是扉页。
但见扉页上写道:
李先平先生雅正,
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
戴志刚
2025年6月18日于弄月斋
诚惶诚恐!不消说,志刚又放了一颗“原子弹”,我于是困意顿消,浮想联翩。这本新书《月光皎白》定是志刚挑灯夜战之结晶。昔日谪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今有志刚“奋笔伴明月,对影成三人”。皆神人也!
志刚有几本散文集的书名都与“月”相关,昔者《凉月微弄》,今次《月光皎白》,想必都是在弄月斋“两句三年得”熬出来的。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地处湘西北,原名安福,是块被澧水滋润千年的福地。这里丘陵不大,起伏如先辈的脊梁,稻田与山林交织,绘就四季调色盘。志刚生于斯,长于斯,他那支如椽巨笔始终扎根于此,像一株倔强的老茶树,将根深扎于故乡麻雀湾的土壤,枝叶却放肆升向文学的天堂。
读戴志刚先生的新书《月光皎白》(天天出版社,2025年1月),全然不像捧读一本新书,倒像偎在湘西北某个老木屋里,围着一炉旺火,听一位抽着旱烟、眼神清澈的老根在那里闪经入白。他闪的不是虚头巴脑的经,入的不是不着边际的白,是扎扎实实从泥巴地里长出来的故事,飘着淡淡的木柴清香,带着烤糍粑的糯米香,掺杂老腊肉的熏香味,还有月光浸透茶树缝的那股子清凉与坚韧。这书,像极了原临澧县老国营酒厂的师傅用纯粮食、山泉水和着时光熬出来的一坛云雾白(这名字绝,喝高了云里雾里,然后闪经入白)。初尝绵甜爽洌,入喉回甘,细品之下,那股子香辣直冲天灵盖,那是岁月铮铮作响的吟唱,是行走山海湖海的回响,是“一吟双泪流”,将麻雀湾的故事窖藏成月光陈酿拿出来的分享。
二
《月光皎白》共上下两辑。上辑“人间有情”,下辑“大地有痕”。那让我们走进清辉,走近《月光皎白》。
品读之余,我不由得感叹,志刚的笔头还是一如既往的硬!他写乡土,不唱田园牧歌的高调子,也不扯着脖子搞诉苦,就那么波澜不惊地讲。像上火烧湾摘茶籽,“一颗一颗地摘,偷不得半点懒”,时而不时,那茶树皮上的灰,沾在皮肤上,再痒也得强忍着,“不然一挠就红肿一大块”。你心里正犯嘀咕,笔锋一转,让你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一动不敢动”。那神出鬼没的山蜂窝,铺天盖地而来,防不胜防。(《又到茶油飘香时》)。乖乖!这哪是摘茶籽?这是把一颗活蹦乱跳的少年心,直接扔进湘西北那绵延不绝的丘陵荒原,直面世间风雨,直面人间成长!读完我相信,它给了作者完整而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人生最初的力量和胆魄,它让作者心正目明,敢于面对日后所有人生风雨。
“在茶油飘香中,我一次次走向远方,又一次次毅然归来。”这手法,像极了黄永玉先生画那只破土而出的蝉,看着简单几笔,底下埋着十几年不见天日的憋屈和一股子向上冲的狠劲。少了一点“黄氏幽默”,多了一份“戴氏真诚”。
志刚写人,好比“茶油炒酢辣椒”,专往人心里头钻,绝!“生疼感”刻骨铭心(《嗲嗲》)。写《嗲嗲》,由梦始,读完泪流满面,又分明不是梦。志刚虽因意外而失去了到更高学府深造的机会,在我与他这么多年相处待人接物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受到了最好的文化熏陶。这也正是我读完《嗲嗲》后真切感受。嗲嗲的言传身教,真正的诚恳,朴实,忠厚,就是最好的文化,也是真正的快乐精神。“我小时候跟嗲嗲一直跑,他判别一棵树好赖的独特方式也直接影响了我。”我想这也间接催生了《桂子一地红》。《嗲嗲》里面也写苦难。但志刚不把苦水熬成哄人的鸡汤,也不把痛楚浇煅成扎人的标枪。嗲嗲一个泡在黄连水中长大的忠厚长者,“是一个承包了我童年时期所有快乐的人”,最终人生圆满。不得不说志刚这写人的眼光,绝准狠!像湘西北的老猎手瞄猎物,一瞄一个准,直击心灵。
三
志刚写乡土,不是站在城头看风景,而是抡起尖锄往地里刨。北瓜在我们老家有点像戏曲中的丑角,爱恨交织。俗语“长的像个冬瓜,短的像个北瓜”就是说一个人长得不好看。我一口气看完《北瓜记》,志刚对生活观察真是入微,把乡村生活场景细节完美重现,读之有种顿可即视的现场感。“我都会习惯地在瓷坛子里抓两把炒熟的北瓜子,装进裤袋,一边走一边像只小老鼠嗑着,嗑着少时的快乐,嗑着母亲的温暖,也嗑着缓缓流淌的岁月。”文章以北瓜为引,如话家常,娓娓道来,深情地描述了母亲勤劳持家的有道与智慧,把平常的日子过得如老北瓜一般香甜。这既是对乡土的顾念,也是对母亲的眷恋。《北瓜记》的路数,跟黄永玉写他那些“老头儿”有得一拼,专爱从“小人物”身上抠出“大乾坤”来。
主题小进大出,语言雅俗共赏,这也是志刚的乡土类文章的一大特色。《邵丹的鼓,邵丹的书》就是这样一篇杰作。我从小就喜欢听人打鼓说书,这可以说是我文学梦的启蒙。打鼓匠的地位在当时并不高,他们主要是在农村红白喜事或者茶馆谋生。我欣赏过邵丹老师的经典作品《传承》。邵丹的作品,从主题、语言、表演上都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和改革,演出时结合了唢呐、二胡等传统乐器,还融入了常德丝弦以及西洋乐器元素,特别是以《传承》为代表的一批演出时长在十分钟以内的曲目,通俗易懂,好记好传,更贴近生活,娱乐性更强。这些创新,其实已经突破了澧州大鼓作为丧葬文化范畴的局限性,成了一种让所有阶层的人们在所有场合都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当人们谈论澧州大鼓时,不再忌讳,不再投以异样的目光,让这门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走上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邵丹的鼓,邵丹的书》既是为民间艺术呐喊立传,也是留住希望与期盼。有些人因为艺人们演出赚钱而眼红,殊知人家也是用命在歌唱,用命在传承。没有市场的艺术是死的,只有市场与艺术相互搀扶,艺术的灵魂才永存!
四
志刚写乡土人情题材轻松拿捏,写历史文化题材同样驾轻就熟。他看世道变迁,眼光也冷峻异常,像剃头师傅的刀子,又快又利。比如在“大地有痕”《隐于泥土深处的时光》中,志刚以他那深邃的笔触,唤醒沉睡的稻耕文明,让我家乡澧阳平原六千年的泥土呢喃出震撼人心的人类文明史诗。其实,我一直想为家乡城头山写一篇文章,惜才能不及中人又没有亲临城头山,故迟迟未能落笔。今读志刚大作,方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真的汗颜!
读《永州慢》《不道衡阳远》让我受益匪浅,感叹颇多。同样是旅永州游衡阳,我也试图写过只言片语,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两相比较,我是豪迈于表,志刚则内敛于心。在永州,志刚与一众文友,“透过千年的灯影,夜观雨打潇水,看到的满是雾蒙蒙的久远故事,以及湿漉漉的千古文章。”而我则与至亲行,忘情于千年上甘棠的山水,一只土鸡三五分钟端上桌。
我与雁城衡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至亲生活在那里,因此每年都会去衡阳,次数不定,故数次写文章为衡阳鼓与呼,比如《雁城衡阳,气质与颜值齐飞》《船山书院在东洲岛的北端》等。而志刚仅仅因当兵和南下广东当兵的原因与衡阳邂逅而生心情愫,衡阳竟成了作者心里的一份牵挂。或许,哲人思想的大智慧,必邃必专,需要时间的沉淀。思想的幽幽之光,注定不能照耀当时,却能泽被后世。作品《不道衡阳远》就是志刚对衡阳的表白,对湖湘文化之根的探寻,对未来的期许。
志刚每有新作都会谦虚地发给我们几位常德籍毛泽东文学院同学先睹为快。《安乡行记》尤其如此。此行因我而起。2020年国庆期间,我从厦门回常德市澧县探母,约在常德的几位毛泽东文学院同学一聚,安乡同学伍月凤做东力邀,就有了此安乡之行,之后就有了志刚此记。《安乡行记》引经据典,文思泉涌,大气磅礴 ,情感真挚。“水低为海,人低为王。安乡以地势之低而形成了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继而接纳了我们的祖先,滋养了祖先的体魄,启迪了祖先的智慧。我们祖先又从这里出发,向东向南,催生了几千年来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的文明。然而,也恰是这片土地的低,让她承担了太多的灾难,承受了太多的苦痛,就像贫苦而倔强的母亲,倾其所有,乃至生命,也要让儿女遮体果腹,走向远方。时距月余,当我的思绪再次触及安乡那片热土,一股敬畏的寒意自后背油然而生。就像这深秋之季里,万古而来的洞庭罡风,猛烈强劲,入骨入髓。”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说《与一条河流的和解》。这篇文章是“青山碧水新湖南”征文的参赛作品,刊登在《湖南文学》2021年“青山碧水新湖南”专刊。这既是一部血肉丰满的散文,又是一篇历史与现实完美交融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将非虚构文学先河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这是志刚近年来众多文学精品中的又一力作。优秀的文学艺术是相通的,非虚构纪实文学也是这样。如果做到有情感,有画面,有故事,一定是一部优秀作品的最高标准。读完《与一条河流的和解》,我一时张皇得不知所措,惟有谦恭地回想我自己与道水河的过往,将思绪放在河面,随势而去。那一刻,我的身心,仿佛浸润了它的流波,一起吟唱……是无奈还是和解,其实更多的是一场救赎。在大自然面前,哪怕是一条不为旁人熟知的河流,我们人的自己都是微不足道的一颗尘埃。任何的傲慢和骄傲自大都最终会被吞噬得彻彻底底。
五
文字功夫上,志刚也是把好手。他的语言,像秋霜打过的萝卜缨子,脆生生,水灵灵,带着湘西北泥土气息。但在我看来,文字功夫恰恰不是《月光皎白》最重要的东西,只是标配。如果问《月光皎白》这书它好在哪里,好就好在它像那轮当空皓月,透着清辉,纤纤细细。细思之下,任它世间沧海桑田,依旧有股穿透古今的力道。志刚以笔当刀,把过往岁月和历史反思剖析给你看,书里有他苦苦寻觅、深情抚摸的东西;志刚用笔当犁,深耕记忆的冻土,他挖出来的是带着体温、烫手的精神炉火!
读志刚的文章,就如沙漠里远行,饥渴难耐时恰好得遇一泉,然后一饮而尽。当下有点浮夸,也有点吵。《月光皎白》像夏日的一杯冰水,阅之让人打个激灵,瞬间清醒。月光从古照到今,依然亮堂堂。照着今人的浮躁,也照着古人的沉默。
初看月光皎白,细品香辣入骨。这年头,志刚其人其书,稀罕!
最后,我用土话提一点小小要求,志刚写文章是薅佬(厉害),如果行文能取晚明小品文之长,更加精炼,那就真的乖致伤哒(漂亮之极)。


戴志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毛泽东文学院学员。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天津文学》《散文百家》等报刊杂志,出版散文集《风雨起心澜》《踏歌而行》《凉月微弄》《月光皎白》四部。曾获丁玲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湖南省散文大赛一等奖、湖南省影评征文一等奖、常德市原创文艺奖等。


李先平,笔名湖南丑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常德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新华书目报》《厦门文学》《朔方评论》《泉州文学》《湖南散文》《中国作家网》《福建日报》《江西日报》《兵团日报》等刊物或媒体。作品曾多次获省部级奖励。书评《找寻精神的原乡》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来源:红网
作者:李先平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