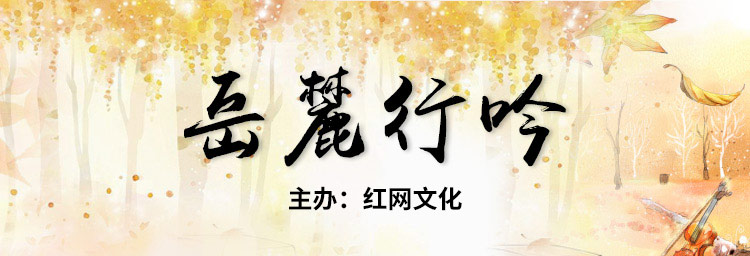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品《甲申十同年图》:
曾鉴参与一场历史上最牛的“同年会”
文 / 王琼华
我特别喜欢《甲申十同年图》,是在我喜欢上了画人物时。之所以喜欢得有点“特别”,是因为这幅名画中还有一个汝城老乡。
那是偶然的一天,我看到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甲申十同年图》。我有一习惯,喜欢上的画作,都会去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画作迅速生动起来。原来,这幅画是明朝时一次“同年会”的“合影”。
这些人是谁呢?
在了解他们的身份时,我惊呆了:这张画出来的“合影”中,竟然有一个叫曾鉴的官员,还是一位汝城籍进士。
(一)
我为什么说历史上堪称最厉害的一次“同年会”呢?
先来看看画中十个人物的身份:
官任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的闵珪,工部右侍郎张达,工部尚书曾鉴,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祭酒谢铎,吏部左侍郎焦芳,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户部右侍郎陈清,南京户部尚书王轼,以及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
在明朝官制中,文官最高职位为“七卿”,即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可见,出席这场聚会的大学士、都御史、尚书、侍郎,都是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那场面真是应了一则顺口溜:群英荟萃聚华堂,好友相聚喜洋洋;笑语欢歌映红颜,共赏良辰乐未央。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腕云集的“同年会”呢?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同年”情结。
“同年”一词,本是唐宋科举制度下同榜者的彼此称谓。明清时,乡试、会试同时考中的举人、进士都可称同年,他们称主考官为座师。与“同年”相类似的现象,在汉末察举中就已萌生了,“同岁”即是因同年贡举而形成的私人关系,“同岁”间存在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在科举时代,士人中举后进入官场,原来的宗党乡里的关系就远远不够用,为个人权利计,就必须在官场中编织新的关系网。利用“同岁”或“同年”而相交接即是方式之一。官场衍生出的“同岁”“同年”纽带,较之乡里亲缘纽带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帮助。在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同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往往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相互援引,结为纽带。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同年”条所谓:“其云同岁,盖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结而公义衰,非一世之故矣。”所谓“同年”之情,其实就是自古有之的“圈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共有247人,包括《甲申十同年图》中这十位人物,散布在全国各地。四十年后再聚首,当年的甲申进士已成为朝廷重臣。
在那个没有影像记录的年代,聚会之后,只能用画作“合影”。
也算超奢华的一种留念方式。
《甲申十同年图》就是一副中国明朝弘治年间的十位朝廷重臣的群像。
(二)
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
三月二十五日。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闵珪府第达尊堂内,正在举行一场聚会,众人燕饮唱和,热闹无比。赴会的都是当朝重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天顺八年(1464年)同榜进士。
原来,闵珪头几天看到王轼来朝,非常欢喜,当即就说自己做东,好让“同年”们也趁这机会聚一聚。
接到闵珪的邀帖,曾鉴欣喜十分。看看日子,便夜以继日把手头上的活赶完了。他得去见见王轼,还有其他“同年”。在朝中,曾鉴在交朋结友这事上算是一个低调人物,却从不缺席“同年会”。有一副傲骨的曾鉴,其实也是烟火气熏成的。普通而不普通,俗人而不俗气,就之如云,望之如月,知世故而不世故,这就是曾鉴。是呵,傲骨不在市井,却在人心。但曾鉴没料到,这场事前并没有计划的“同年会”,其档次竟被安排得超乎想象,非常温馨。
原来,祁闵珪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物,又是“同年”中的老大哥,便把这场难得的聚会筹备得十分完美,除了吃吃喝喝的细节做好了,还专门邀请了大名鼎鼎的画师现场画像留念。它当然比如今用相机拍几张照片更有意义,更见艺术价值。在现场,曾鉴没发现焦芳,便跟李东阳打听。原来,吏部左侍郎焦芳因赴湖南公干。这次出席聚会的“同年”,其实是有九人。曾鉴品茶时看到一张椅子没人坐,不由一吁:“有点遗憾!”祁闵珪当然不想有什么缺憾。李东阳《甲申十同年图诗序》中称,“十人者皆画工面对手貌,概得其形骸意态,”原来未能出席的焦芳,也是“预留其旧图者而绘之,仅得其半而已。”可见,仪式感满满的。
这幅十同年图卷,绢本设色,纵48.5厘米,横257厘米。画面人物分为三组,皆身着官服,正襟危坐,人物的排列坐次不以官位高低,而是按年纪大小安排的。因此,年纪最长的闵理居于中间,李东阳年纪最小,居卷最后。这个安排算是中规中矩。
画面共分三组,自右端卷首起依次为王轼、焦芳、谢铎、曾鉴、闵珪、张达、戴珊、陈清、刘大夏、李东阳。十人皆身着官服而坐,表情、姿势又各有不同,栩栩如生。
第一曹(三人):
王轼:时年六十五岁,高颧多髯,髯发半白,袖手而略向右侧坐;
焦芳:时年六十九岁,胡须不多,鬓发斑白,左手握带,右手扶椅,端肩正坐;
谢铎:时年六十九岁,微须多鬓,白发细长,左手扶膝,右手持一书册,略向左侧坐。
第二曹(四人):
曾鉴:时年七十岁,胡须稀稀,面色发红,左手握带,右手扶膝,略向右侧坐;
闵珪:时年七十四岁,虎头方面,大目高鼻,须髯长而微白,左手握带,右手持牙牌,稍偏左正坐;
张达:时年七十二岁,须发皆白,面容老皱,双手握带,稍偏右正坐;
戴珊:时年六十七岁,面色发红,不见长须,袖手端肩,正襟危坐。
第三曹(三人):
陈清:时年六十六岁,红面略长,双眉浓黑,须发斑白,略向右侧坐;
刘大夏:时年六十八岁,脸面略方而长,须发皆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正坐;
李东阳:时年五十七岁,脸面略长且消瘦,胡髭数根,左手扶膝,右手持书卷,略向左侧坐。
画面背景以梧桐、苍松、修竹、芭蕉及洞石衬托,象征人物的高洁情操和高雅情致,其间还穿插小童七名以及几案、书册、酒具等。画面简练有序,未作过多渲染,这让朝廷高官之显赫地位得到突出,体现了画作的宗旨。读画时,我发现,谢铎手持一书册,这般“设计”,忽然让整个画面多了几分文气。
卷后,有李东阳所书《甲申十同年图诗序》,钤白文“宾之”、朱文“大学士章”印各一方,并有十位官员的唱和诗。诗皆为七律,各人或一首、或两首,惟李东阳作三首,共计十八首,皆为本人亲书。卷尾还有聚会次年谢铎所作之《书十同年图后》,嘉靖十八年(1539年)刘栋书于之《书庄懿公同年燕会卷后》、隆庆三年(1569年)王世贞题跋、明亡后闵珪玄孙闵声所书之《甲申十同年图卷后跋》、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闵氏裔甥沈三曾所作之图考、沈涵之七言长诗以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谭泽闿之题跋。
此图当时共画了十本,每家各留一本。故宫藏品属闵家所留,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为法式善收藏,也是十本中仅存的孤本。
甲申十同年聚会与《十同年图》,即是对雅集和雅集图的继承和发扬。
“雅集”源于唐朝“香山九老”的聚会。唐武宗时,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故里香山(今河南洛阳龙门山以东)与胡杲、吉旼、卢真、张浑、郑据、刘真、狄兼谟、庐贞八位耆老燕集,有仰慕者绘成《九老图》,成为千古美谈,后人多有效仿。宋仁宗时,重臣杜衍致仕后在睢阳闲居,与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四位故官优游宴饮,当地人作有《睢阳五老图》,亦闻名海内。此类雅集活动深受文人士大夫追慕,而且成为常见的绘画题材。时至明朝,官员们的雅集,与前代雅集参与者多为致仕官员或山野名士有了一些变化,除追慕前贤之外,更愿意直观地彰显自身地位和赞美“盛世明君”的目的。
正如李东阳在《图序》中所言:“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阳,歌诗燕会皆出于休退之后。今吾十人者皆有国事吏责,故其诗于和平优裕之间,犹有思职勤事之意。”
由此可见,明朝士大夫阶层,当时盛行雅集宴饮,诗文唱和,这其实是一种时代标志,所诞生的画作就是一种时代的写实。
我在考证这画作历史与文化背景时发现,明孝宗在位期间,朝廷中有不少正直之士,可见当时的官场有一个清明环境。武宗之后,明朝由盛转衰,君臣其乐融融的情景再不复见。在我眼中,这画里十位大臣失去“个性”,所显露的皆于威严持重、儒雅从容的情态,于诗文中所体现的胸无芥蒂、忠君报国的情怀,俨然是孝宗朝修明政治的生动写真,也成为明朝繁盛时期的最终见证。 此次聚会之后,几乎在不长的时间段,画中十人相继谢世,而且明朝由盛转衰,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幅画,后人自然有不少触动,唏嘘万千,其中一感叹者给这幅画作跋称:“弘治之甲申,以得人成太平之隆;崇祯之甲申,以庸臣洒鼎湖之泣。人之云亡,邦国珍瘁。阅此图而益深今昔之感也。”当今的我们,观此图卷,是会追怀画中人投身仕途时的意气风发?还是明代极盛时期政治清明的图景?我想,盛筵易散,更是会让许多人无奈。
(三)
据汝城曾氏族谱记载,当年曾在县南门内建有一座尚书坊,以此纪念曾鉴。
明史对曾鉴也有记录:
曾鉴,字克明,其先桂阳人,以戍籍居京师。天顺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余人坐为盗,狱已具,鉴辨其诬。已,果获真盗。成化末,历右通政,累迁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进尚书。
孝宗在位久,海内乐业,内府供奉渐广,司设监请改造龙毯、素毯一百有奇。鉴等言:“毯虽一物,然征毛毳于山、陕,采绵纱诸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苏、松,经累岁,劳费百端。祈赐停止。”不听。内府针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鉴等言:“往年尚衣监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军器局、司设监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于是命减其半。太监李兴请办元夕烟火,有诏裁省,因鉴奏尽罢之。十六年,帝纳诸大臣言召还织造中官,中官邓瑢以请,帝又许之。鉴等极言,乃命减三之一。其冬,言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盗贼,乞罢诸营缮及明年烟火、龙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报从。
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鉴言天心示儆,不宜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御马监太监陈贵奏迁马房,钦天监官倪谦覆视,请从之。给事中陶谐等劾贵假公营私,并劾谦阿附,不听。鉴执奏,谓马房皆由钦天监相视营造,其后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毁改正,葺以己资,庶牧养无妨而民不劳。报可。内织染局请开苏、杭诸府织造,上供锦绮为数二万四千有奇。鉴力请停罢,得减三分之半。太监许镛等各赍敕于浙江诸处抽运木植,亦以鉴言得寝。
孝宗末,阁部大臣皆极一时选,鉴亦持正。及与韩文等请诛宦官不胜,诸大臣留者率巽顺避祸,鉴独守故操。有诏赐皇亲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鉴力争,不从。明年春,中官黄准守备凤阳,从其请,赐旗牌。鉴等言大将出征及诸边守将,乃有旗牌,内地守备无故事,乃寝。其年闰正月致仕。旋卒。赠太子太保。
这段文字很简洁,却生动描述了曾鉴一生为官中的三个特点:这人谏阻奢靡,这人体恤民力,这人正直敢言。
是的,在朝庭中,曾鉴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俗间日常中,曾鉴留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种印象:温纯待人,喜怒不形,处事裕如,不事矫饰。有两传说,一是说回家下轿时,总要跟轿夫聊上几句,甚至有一天还把两砣银子递给一轿夫,说是贺礼。原来这轿夫第二天要嫁女,也不知道曾鉴从哪听到这事,并记住了明天这个日子。一是曾鉴闲逛时,见一乞儿拿树枝在地上写字,便好奇凑上去看了看,发现这字还写得极其工整,十分惊喜。当日,曾鉴牵起这乞儿的手,送他进了一家友人办的私塾。后来,这乞儿做了曾鉴儿子的书童。
(四)
“追忆往时之少者、壮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识也。其以地以姓论之,无一同者。以官则六部之与都察院,其署与职亦莫能以皆同,盖所谓不齐者如此。然摅志效力,各执其事,以赞扬政化,期弼天下于熙平之域,则未始不同。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论也,又而爵齿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论成人以久,要不忘为次,而廉、智、勇、艺、文之礼乐者为至。兹九人者之才之行,汇征类聚,建功业于天下,固将以大有成。”
也就是说,孔子论述如何成就德才兼备的完人时已经强调:长期坚持修养是基本要求,始终保持初心是次要标准,而能够兼具廉洁、智慧、勇敢、才艺、文德,并以礼乐为行为准则的人,才算达到了最高境界。这九种品德与才能兼备的人,若能汇聚同类贤才,共同施展抱负,必能在天下建立功业,最终取得非凡成就。这段论述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功业有机结合,展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这是李东阳在《甲申十同年图诗序》一段话,我读过很多遍,次次皆有感触。
他少年得志,却很谦逊。
在这序中感叹:“惟予蹇劣无似,方惧名实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负也。”他觉得自己这个人笨拙无能,实在不成器,正担心自己的名声与实际才能不符。但心中的这份信念,他绝不敢辜负。
事实上,在画中这十人中数李东阳成就最大。李东阳“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人,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同时,李东阳四岁时便能作大字而名动朝野,《献征录》中称:“四岁辄能运笔大书至一、二尺,中外称之神童。景皇帝召见,亲抱膝上,命给纸笔书,赐果钞送归。”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李东阳有过这般待遇。并且留下一个花絮,入殿过门限时,太监调侃:“神童脚短。”李东阳一听,当即高声应答:“天子门高!”可见李某这一神童名副其实。
李东阳与曾鉴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抑或就是俩人一同在国子监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弘治年间,李东阳入内阁。弘治十三年,曾鉴升任工部尚书。之间的目标和理念较为接近,事务上也能相互支持与协作。比如曾鉴请求核减内府司监的不合理请求时,李东阳作为内阁首辅,给予了呼应。不过,在刘瑾乱政时期,李东阳选择忍辱负重、委蛇避祸;曾鉴则与韩文等阁臣请诛宦官。后来,韩文等阁臣知难而退,唯见曾鉴持正如故。在这种背景下,曾鉴与李东阳的关系并没破裂。原来李东阳仍在暗中助力过曾鉴等大臣。曾鉴没因请诛宦官而吃太大的亏,应该有其缘故。曾鉴知道,自己与李东阳在应对刘瑾这事上,仅仅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呵,人世间最靠谱的友谊,也就是四个字:心有灵犀。
曾鉴去世后,李东阳特意写了一篇《工部尚书曾公讳鉴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近两千字,在类似铭文中算是洋洋洒洒,宏大叙事了。其中由衷赞道:
“卿有六署,公居其三。幼学壮行,老且益谙。工曹最繁,公所终始。世历累朝,岁几四纪。夙兴夜寐,心矢靡他。日累月积,岁计实多。尽瘁而生,得正而毙。亦有余恩,为身后地。凡器之类,锐必先折。公最其锋,有用无缺。凡物之生,早必先萎。公敛其华,有实之理。公不言功,皇则念之。公不责效,天则验之。孰传厥宗,家有介子。孰最厥名,国有太史。”
同时,李东阳撰写了《祭曾尚书文》,祭文中“人生聚会,可谓甚难,南北殊踪,壮老异观。惟今之悲,乃昔之欢”几语,道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情。
在李东阳的印象中,曹鉴性情温和宽厚,平易近人,从不矫揉造作。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都坚持按时上朝处理公务,若白天未能完成工作,便挑灯夜战直至深夜。他天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和睦友爱,共同生活直到白发苍苍也从未有过矛盾。对待家族中贫困急难的亲属,他总是倾力相助,而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从不因俸禄高低或官职升降而改变操守。在吏部任职时,他主动教导年轻有为的后辈准备科举考试,甚至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读书所需的灯油费用。后来这些青年中有两人考中乡贡,一人高中进士,这些人都终身感念他的恩德。即便是府中最底层的仆役,也都由衷敬仰他,从未有人暗藏怨怼。能做到这般境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啊。
惺惺惜惺惺。
于是,曾鉴与李东阳做同事,让其跟汝城结了文化之缘。有了曾鉴悉心的“铺垫”,李东阳喜欢与不少汝城籍才子交往甚密,欣然跟汝城写了多篇文旅推文。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题,一是《龟鹤轩记》,一是《桂枝岭文塔记》。
一日,李东阳与汝城籍进士朱守恕茶叙。喝的还是朱守恕带过来的汝城旱塘茶。朱守恕跟他讲述老家龟鹤石的奇异景象,说:“在县城南寿江里,矗立着两座奇石,形状酷似乌龟与仙鹤。龟石伸长脖颈朝向右侧,鹤石拖着长尾面朝东方。鹤石略高一些,昂首展翅的姿态栩栩如生,翅膀以上的部分都浮出水面,无论是龟甲的纹路还是羽毛的细节都纤毫毕现,仿佛经过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两座奇石宛如活物般在江中游弋,人们甚至可以提着衣摆登上石顶,上面能容纳十几人。若深入观察,会发现石腹中空直通江底,江水灌入石腹超过半满。很多人都说,这属湖南境内的一大奇观。”
回到家里,李东阳仍沉浸在“龟鹤石”的传说之中,便提笔写成《龟鹤轩记》。他非常有触动地称道:“我感叹天地之间的气息,万物虽各有类别属性,彼此本不相同,但在差异之中又存在相似之处。人类对此感到惊异,然而造化的精妙奥秘,终究无法完全参透。”他认为,石头本是天地间寻常之物,由泥土凝结、水沫积聚而成,原本并无知觉与灵性。但当它们呈现出奇异形态时,竟能幻化万千形态。龟与鹤本是天地灵物,而奇石竟能与之相似,这样的自然造化尤为神奇。如此看来,人们对此感到惊异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感叹,“物之寿者,莫如龟与鹤。石之寿,殆有过焉者也。江以寿名,地以灵著,其将有征乎。”是呵,江河以“寿”为名,地域因灵气著称,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自然规律吧。
于是乎,汝城“龟鹤石”自古闻名于天下。
之前,进京参加会试的朱守恕也曾来拜访李东阳。李东阳愿意见这年轻人,他知道朱守恕即是同朝进士朱海的儿子。一番热聊后,朱守恕提了自己一个念头,请李东阳为自己家乡桂枝岭上的文塔撰写一篇记文,当然还做了形象生动的描述。李东阳答应了。但李东阳是一个大忙人,好些日子也未能动笔。不久,李东阳前往湖湘一带游历。他后来称,汝城明明就在南边几百里外,却因故未能成行,他为此颇感遗憾。李向东返回京城时,朱守恕已经考中进士,荣归故里。不久,与朱守恕同为进士的族兄、即朱英的儿子朱守孚也来拜访李东阳,茶叙时,说到朱守恕聊及文塔记文一事。李东阳当即欣然提笔,一气呵成。
在文中,他复述道:“吾徒生长乎此,出作入息,村行里至,不知山川之为胜也。”也就是在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般感叹。他同时点赞,这座文塔占据奇绝地势,形制简朴却气象万千,既能让人排遣郁结、舒展心胸,又可作为游赏休憩之所,实为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去处。
李东阳知道,汝城历来多出科举入仕的才子,世人议论说这是当地山川灵气凝聚的结果。相传那座塔的形影宛如一支文笔,虽曾一度黯淡,如今又重现光彩。但他在文中指出,真正的关键在于当地贤德之人的传承。比如朱氏一族,本就是德行昭彰的名门之后。这个例子举得特别有力。李东阳将这些缘由一一记录下来,希望能潜移默化,让后人们知晓其中深意。啧,真算用心良苦也。
从此,《桂枝岭文塔记》成了一篇汝城人追捧的热文。
时至今日,面对《甲申十同年图》,我们不仅仅可以欣赏一幅极其珍贵的艺术作品。同时,从这幅图中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汝城人完全有能力、也有品行地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我想,这该是曾鉴最欣慰的地方。


王琼华,笔名王京。籍贯嘉禾,生于汝城。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美协会员。湖南电影评论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入选作家。全国文代会代表。曾在郴州市文联工作。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公开出版《还我风骚》《官方女人》《咣当》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29部。
来源:红网
作者:王琼华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