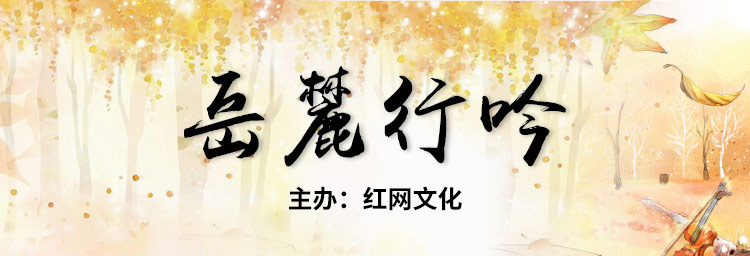

步数里的光阴
文/彭世民
点亮微信运动,今日的步数,静静地停在一万三千五百步。折算下来,该有八到十公里了。这数字,于我,竟成了一种安心的凭据。
父辈那一代人,走路是从不计步的。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扛着锄头,握着柴刀,挑着沉甸甸的肥料,踏着露水出门了。这一去,没有个准点。有时几个时辰,有时大半天。田埂上的稻禾,山坳里的柴火,都是无声的号令。活儿干不完,脚就不能停。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在粗布衫上晕开一圈圈深色的印记。他们脚底沾着泥,肩上落着尘,却从不知道自己一天究竟走了多少路。
那路啊,是长在日子里的,一步,一步,丈量着生活本身的重量。
小时候,我最乐意的事,便是跟着父母去走亲戚。那时候,乡下人家,谁家有辆自行车,已是了不得的物件。出门访友,进城办事,全靠一双脚。莫说乡下,便是城里,街上的车也稀稀落落。人们出门,若非迫不得已,总是安步当车的。脚步不慌不忙,路也就显得长了,情谊仿佛也在那长长的路上,被抻得更加绵密、醇厚。
那时节,似乎很少有人把“健康”二字挂在嘴边。可他们那般走着,劳作着,日晒风吹,筋骨却结实得像山里的老松。那种生活,或许便是最本真、最原始的健康了。
如今,日子是大大不同了。从前逢年过节才舍得端上桌的鸡鸭鱼肉,如今已是家常便饭。不知从何时起,身上紧实的肌肉,悄悄松软了,化作了一身不由己的肥腻。身子,自然也仿佛沉重了许多,不如从前那般轻便利落了。于是,“健康”这个词,便又成了大家嘴边常挂着的、沉甸甸的话题。
女儿在外,来电时总不忘细细嘱咐:“爸,妈,你们要多注意身体,少坐牌桌,多出去走动走动。”末了,总要轻轻添上一句:“毕竟,你们都不年轻了。”
是啊,不年轻了。自从转业到了这地方,安顿下来,早年行伍养成的锻炼习惯,便在不知不觉间,淡了,丢了。人一懒散,身子也跟着懈怠下来。不是深深陷进沙发里,对着电视屏幕消磨一整晚,便是外出应酬,在牌桌边一坐便是几个钟头。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竟也将这般慵懒,当成了生活的常态。
如今,健康成了人人心里头一件放不下的事。单位年年组织体检,不少同事查出的毛病,一年比一年多,报告单上的箭头,红的、向上的,也一年比一年叫人心惊。县里头也热闹,时常组织“毅行”“万步行”这类的活动,鼓励大家把脚步迈开。我也跟着,开始每日走上一走。起初像是完成任务,渐渐竟也尝到了些许甜头。偶尔在街上遇见老友,他们会端详我片刻,带着些许惊讶:“几个月不见,你倒是清减了不少。”
每日究竟走了多少路,自己是从不计算的,全凭手机里那个小小的程序记着。这也是自己给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每天争取能走上万步,于是,微信运动跳出来数字,像为我这一天的步履,作一个无声的、轻轻的注脚。
从小区出门,右拐不到一千米就是平江县人民公园、烈士陵园;往左拐,是甲山风光带和两个小型广场。每天,到了夜间,这些场地都是极热闹的,跳舞的、打太极的、各类小贩、跑步散步的……
白日的行走,总不免带着点任务的意味。清晨出门,空气里偶尔还能嗅到一丝清甜,那是夜与日交替时,残存的干净气息。可城市醒得快,不多时,车马的喧嚣、人语的嘈杂,便如潮水般涌上来,将那一点点清新,冲得七零八落。走着走着,脚步不由自主就急了,心里头也杂乱起来,仿佛赶着要去完成什么,又像是要抖落掉一夜积攒下来的、浑身的滞重。这时的步数,便也沾了些功利的影子,像个指标,催促着,也记录着。
而我更爱的,是夜间的散步。
当暮色像一张温柔的网,徐徐撒下,将白日的所有棱角与锋芒都包裹起来时,我才真正开始我的行走。心,一下子闲了下来;脚步,也跟着缓了。整个人,像一滴浓墨,落进一泓清水中,慢慢地、悠然自得地洇开,舒展,自在。
我常去家附近的一个广场。那儿,早已是音乐与舞步的海洋。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妇人,头发梳得整齐,穿着宽松舒适的衣裳。间或也有几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混在队伍里,丝毫不显突兀。他们跟着响亮又欢快的曲子,整齐地摆动、旋转,手臂扬起,脚步挪移,简单,却有种动人的力量。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专注的、甚至是虔诚的光,仿佛此刻天地间只剩下这旋律与舞步。我有时也会悄悄混进队伍的末尾,依样画葫芦,笨拙地比划几下。倒不为学什么,只是想被那片腾腾的热闹轻轻地托住,让自己也忘掉片刻。
离开那片喧腾的音乐,我便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慢慢地踱步。路灯的光是温润的,黄澄澄的,像一块块巨大的琥珀,一盏接着一盏,连成一条光的河。而街上穿梭的车灯,则是流动的了,划出一道道金线、银线,交织成夜身上一匹华丽的锦缎。路边的空地上,有时会聚着一小圈人,静悄悄的,只偶尔听见“啪”一声清响——那是有人落子了。我爱凑上去,做个沉默的看客。看那对弈的两人,一个蹙眉沉思,手指夹着棋子,半晌不落;另一个则气定神闲,仿佛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那方小小的棋盘,此刻便是他们的天下,楚河汉界,纵横捭阖,自成一个世界。那寂静里的厮杀,比广场上的喧闹,更引人入胜。
沿着甲山风光道的小河再往前走得远些,便到了汨罗江河边防洪堤,路修得很宽,路灯在十二点前都是亮着的。但汨罗江水是沉的,墨黑的一片。只有那些夜钓的人,还静静地守着,像一尊尊凝固的雕塑。最醒目的,是浮在水面上的那一粒粒夜光漂,碧绿碧绿的,在墨色的河面上,像一颗颗遗落的星星,格外分明。它们随着微不可察的水波,轻轻地起伏,一上、一下,像这夜的、悠长而平稳的呼吸。忽然,近处的一点碧绿猛地向下一沉,随即剧烈地抖动起来——岸上那尊“雕塑”瞬间活了,敏捷地起竿,鱼线划破夜色,在水面拉出一道转瞬即逝的银亮痕迹。那一刻,我隔得远,听不见他压抑的低呼,却仿佛能触到他心底满溢出来的欢喜。而我这个偶然路过的、岸上的看客,也便悄悄地、独自地,分享了这份属于夜的、静默的快乐。
妻子有兴致时,会穿上舒服的鞋子,陪我走上一段。两人并肩,步子便更慢了。聊的多是些琐碎的家常,孩子的近况,明天的菜蔬,话语轻轻的,落在软软的夜色里,即刻便融化了。不过,说句实在话,大多时候,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走。似乎只有独行时,身子和灵魂才真正挨在一起,妥帖地、温暖地依偎着。不用说话,便可以更自在地看,更专注地听,更无拘无束地想。白天里那些理还乱的思绪,缠作一团的烦忧,在这不紧不慢的脚步里,竟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慢慢地抚平了,舒展了。那些平日里微不足道的街景与人情,也才有工夫被细细地品味、咂摸。这独行的时光,于我忙碌的生活,实在是一段奢侈的、珍贵的留白。
回到楼下,抬头望见自家窗户里透出的、暖暖的灯光。打开门,家的气息便迎面扑来。手机屏幕又一次亮起,显示着今夜最终的步数。如今再看这数字,它在我眼里,已不再冰冷。那里面,有广场上我笨拙挪动的几步舞,有棋盘边屏息凝神的安静,有河面上那一点跃动的、碧绿的星光,更有我独行时,那片无人打扰的、丰盈而又完整的寂静。这一万三千五百步,一步步,都踏在真实的生活里。

彭世民,湖南省平江县人,毕业于国防科大,军队转业干部,平江县文联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岳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有《凤凰花开的路口》散文集,曾获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岳阳市第五届、第六届文学艺术奖。作品先后在《少年文艺》《散文选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西文学》《中国报告文学》《芳草·潮》《海外文摘》《江河文学》《小溪流》《岳阳文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湖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
来源:红网
作者:彭世民
编辑:唐雨欣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