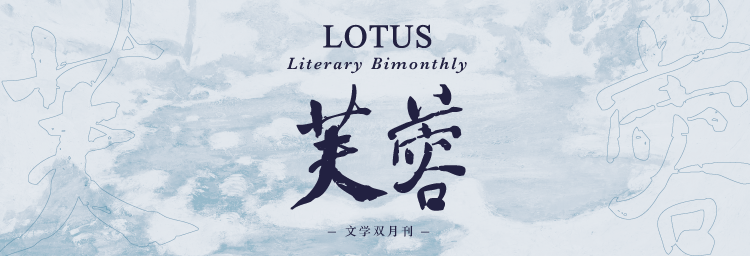

华野四纵/摄
大地上的事
文/王选
黑妹啊黑妹
天色又暗了一层。
黑妹,穿着臃肿而邋遢的衣裳,头发蓬乱,吸溜着鼻涕,两只手塞进似乎要脱落的裤兜里,拖着倒跟的运动鞋,在巷道里,迟缓地滑过。她走掉之后,巷道里就空无一物了。唯有风,把水泥路面的枯叶吹着,像一个人,在黄昏,清扫骨缝里的暗疾。
黑妹走了后,天,说黑就黑了。
不久前,她还在我家门口晃荡。母亲唤她进来,她走到院子,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似有羞怯之意,不再进屋。母亲捏一颗橘子,出屋,塞给她。她一手紧紧攥着,一手举起用手背狠狠揩了一下鼻涕,哧,吸了一声。母亲说,快点回去,天黑了。她一边用指甲扣着橘子皮,一边问,你们家王选有车没?
母亲笑着说,有自行车。
黑妹说,人家城里人都有车。她用指甲把橘子划开了一道口子,掏出橘瓣,把橘皮顺手丢在了地上。
快回吧,晚上吃啥?
方便面,有一箱子呢。说完后,黑妹带着有一箱子方便面的得意之情,出了门,走了。
黑妹大概是1990年左右生的,二十七八了。二十七八的姑娘,还留在麦村,说来话长。
黑妹姐弟四人。黑妹老大,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黑妹出生后,也无异常。长到两三岁后,同龄的孩子开始说话走路,而她嘴里还是含混不清,脚下依然站立不稳。长大一些后,其他孩子开始上学读书,独她在家里和尿尿泥。有时候,她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那时候,她家里人口多,肚子也是勉强填饱,自然没有余钱去给她看病,加之又是姑娘,也不上心。最后就一直拖着,最多,到镇子上的卫生院,抓几服药,熬着一喝,也算了事,终究没有查明病因,也没有治愈。
当我们都上初三的时候,黑妹还在大门口的青石板上,呆呆地坐着,浑身沾满泥土,一张脸,成天不洗,糊满垢甲。她到学校念过一小段时间的书,常犯病,怪吓人的,加之智力有缺陷,啥也不懂,上也白上,只会花一疙瘩冤枉钱,大人便让辍学了。
辍学后的黑妹,整天无所事事,坐在门口发呆,或者去村里晃荡。像一只塑料袋,风吹到哪儿,就飘到哪儿。
我们上学,放学,过寒暑假,而她,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活成了一天。我们都叫她瓜米子(傻姑娘)。她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任我们嘲笑和讥讽,都是一副一成不变的模样,蓬乱的头发,衔不住的鼻涕,肮脏的衣裳,在风雨里,暗自生长着。她懦弱,胆怯,甚至混沌未开。她远远地看着我们背着书包归来,远远地看着我们玩耍,远远地看着我们从小卖铺买来吃食,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像一截尾巴,直到被别人用碎瓦片赶开,她才悻悻然走掉,留给我们一个邋遢的背影。
她大多时候都是挨欺负的,任别人嘲笑,打骂,一直一言不发,低着头,抠着塞满黑色垢甲的指甲缝,最多哭一嗓子,便很快忘了。有时候,她也欺负人。她家门口有小卖铺,一些小孩从里面用毛毛钱换来零食,黑妹坐在小卖铺门口,看四周无人,便冲上去,夺小孩手里的零食,小孩死活不给,黑妹抬腿,在小孩屁股上踢两脚,再不给,肩膀上捅两拳,一把抓过零食,转过身,撕开包装,吃了起来,鼻孔上挂着一串明晃晃的鼻涕泡,破一个,长一个。小孩子吼叫着黑妹父母的名字,挂着两溜眼泪,说是回家告状去。
这事也就过了。没有一个人会跟一个瓜米子计较。
后来,我们都日渐长大,都日渐走出麦村,像灰鸽子,越过墙头,在泛黄的天空一圈圈飞着,不知所终。
而黑妹呢,黑妹依然留在村里,把二十岁左右的年华,完全呈献给麦村的山川草木。她独自一人,在山路上行走,在深沟里晃荡,在树林里漫游,在杏花泛滥的春天消失在地头又回来,在青杏寥落恣意腐烂的季节手揣杏核沉沉睡在杂草里,在紫娇花枯萎的暮秋坐在山顶坐成了一块石头。她拥有着怎样漫长的时光,我们无从知晓。她就那么长啊长,在我们的无视里,在我们的遗忘里,长啊长,和麦村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只野物一样,不知不觉,就长大了。
她是麦村唯一的闲人,不用耕种,不用干活,不用外出打工,不用伺候老小,不用担负生活的重压,吃饱穿暖,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了,其余的时间,灰扑扑地信马由缰,灰扑扑地自由生长。
然而大多时候,黑妹还是干着两件事。一件是在小卖铺边上的廊檐下靠墙站着,发呆。没有人知道她想着什么。有人经过,问,黑妹,晒太阳啊。黑妹嗯一声,就不再言语了。像一根木头,立在墙上,任时间、风雨,在暗处刻画一个人终究走向沧桑的模样。另外一件事,是谁家有婚丧嫁娶,或者谁家来亲戚朋友,或者谁家有人从城里回来,她都会去瞅一瞅。一开始,是站在门外,两手塞在袖洞里,呆呆地站着,站久了,便会一寸寸移进门,到院子站一阵,再移进屋子,看着屋里的一切。这时候,人们会端一碗粉丝菜,或者塞一个馍,让她吃,都想着她是一个可怜娃。有时,人们也嫌弃她碍事,嫌弃她丢人现眼。吃毕,便打发了。黑妹不情愿地出了院子,摸着嘴上的油,或者啃着馍,还在门口晃荡着,不肯离去。我想,有时候,黑妹真的是想吃一口人家的饭菜,混个饱肚子,但更多时候,她是害怕孤独的。没有人愿意和她玩耍、说话,她只好去别人家凑热闹,或者看看别人家的热闹,也算是有事干了,内心才不至于空荡荡的像梁口刮过的西北风。
在别人家晃荡久了,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看在眼里。去另外一家晃荡,她会冷不丁地说,贵福家堆了一炕桌钱,数着哩,数着数着,就打捶了。麻球娃又领回来了一个媳妇。大牛爷感冒了,挂水着哩。二两半家今天的浆水面,浆水里还切了豆腐。她把这些消息,像一个信使,传送到别人家,风一刮,满村人都知道了。一家人的事,也就成了一村人的事。一家人的喜怒、私密,也就成了一村人的话题和把柄。
这时候,黑妹,似乎不是瓜米子。她知道,通过传播这些消息,她才能在别人家换来一颗糖、一个馍、一碗饭,或者在人家多待一阵、多说几句的资格。
再后来,黑妹长大了,二十六七。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反正她长大了。
家里给她找了婆家,然后嫁了出去。关于她婚姻的细节,我不太清楚。我隐约听说,那是冬天,天寒,老牛风在梁上掠过,草木颤抖。黑妹穿着城里租来的红礼服,体体面面,坐上梁顶停着的一溜小车,离开了麦村。村里应邀参加黑妹婚礼的人,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席,男人们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女人们个个吃得油光满面。人们听说,靠着嫁黑妹,她父母挣了一笔不小的彩礼,具体多少,莫衷一是。
这十年来,广大的农村,所有姑娘全部出门去了城市。要在农村找一个姑娘,比登天还难。即便你攒够了十几二十万元,礼钱顶在额头上,也找不下。为啥?没姑娘了,一个渣渣都没有了。为了儿子有妻,为了不断后,为了在西秦岭一带抬起头,人们不惜重金,不论瘸子跛子,只要是个女人就行。娶妻难,在广大农村,这些年,成了父母们巨大的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黑妹就成了小伙子们无奈的必然的选择。黑妹是麦村留下的唯一一个姑娘。
人们都惊讶着连瓜米子黑妹都能嫁人挣彩礼时,黑妹嫁人了。人们后悔少生了一个姑娘,损失了一疙瘩钱时,黑妹回来了。
黑妹被婆家不要了。婆家一开始,以为黑妹瓜(傻)得不严重。不会干活,不知礼节,也就罢了,只要能养娃就行。但嫁过去以后,才发现黑妹瓜得严重。不但不会干活,不知礼节,还动不动犯病,瘫倒在地,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很吓人。最关键的是,黑妹不懂男女之事,也拒绝男女之事。当传宗接代的期盼被打碎后,无望的婆家只好把黑妹送了回来。当然,送回来之后,那笔巨额的彩礼,就成了两家人头疼的事。为此,矛盾不断,纠纷重叠,一时难以说清。
刚回来的几天,黑妹还带着一些新娘子的气息,比如梳理整齐的头发,穿戴一新的衣裳,洗净垢甲的手脸。人们发现,收拾之后的黑妹,竟然长得也很秀气,瓜子脸,棱鼻子,樱桃嘴,手是手,腿是腿,有模有样。但没过多久,黑妹又回到了当初的模样,穿着臃肿而邋遢的衣裳,头发蓬乱,吸溜着鼻涕,两只手塞进似乎要脱落的裤兜里,拖着掉跟的运动鞋,要么发呆,要么去人家门口晃荡。
再后来,黑妹的父母弟妹,都统统去了外面打工,长期照顾她的祖父也病故了。家里只留下了黑妹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院子,守着千篇一律的日子,守着麦村盛大的春夏秋冬,守着一村人死去活来的故事和秘密,守着她一个人不知所终的未来。
在无垠的乡村,似乎每个村里都有一个瓜球(傻小伙)和瓜米子(傻姑娘),和黑妹一样,生于泥土,长于天地,嫁不出去,或者娶不上媳妇,茫茫然,迷迷糊糊留守在村庄里,无路可去。黑妹一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她最远就去过十里外的集上。二十多年,没去过一次城里。或许,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外面的世界,留在麦村,就够了。
当我们都一一背叛故土,远走他乡,努力活成城里人时,最终,我们的村庄,被一个瓜米子守护着。想想,也让人心生悲凉。
天真的黑了。立冬后的天,说黑就黑了。亮起来的路灯,像一把把积满灰尘的伞,撑开来,把黑暗挡在了外面。
黑妹回到了炕上。吃了方便面。睡了。
黑妹的一天结束了。黑妹二十七八年的光景,如同这一天,结束了。明天,黑妹还过着今天的日子。后天,也是如此。作为麦村最年轻的留守者,她会一直陪麦村走下去。如此忠诚,如此别无选择。
老马,拖拉机
这是秋天的事,放在冬天说吧。吃食会过期,但事不会。
白露高山麦。麦村阴冷,白露时分,就该种山顶上的麦子了。太迟,地一冻,就出不来苗了。
以前村里牲口多,家家户户都有。少则一头毛驴、一头黄牛。多的,四五头,有马、有驴、有骡子。赶出圈一大阵,踢踏得地轰隆隆响,跑起来,踩得尘土飞扬。种地,自然就全用牲口了。两头驴搭一对,两头牛搭一对,驴跟马搭一对。牛跟驴、马,搭不到一起,牛性子慢,马和驴性子快。骡子不搭对,一头骡子扯一副犁铧,骡子命苦。
种麦,先扬粪。把秋里送进地卧起来的粪,用铁锨满地撒匀。然后撒土磷肥和尿素。一亩地,一袋土磷肥,四十斤尿素。最后撒麦籽。撒籽,是个手艺活。撒得好,麦苗出得匀。撒不好,稠的稠,稀的稀,对后面生长影响很大,最关键,会被田野里来来往往的村里人嘲笑。这可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撒完籽种,驾上牲口耕地,把肥料和麦籽翻压到土里。耕地,引地边子,得人把牲口拉上,要不牲口找不到边。一遍过去,开了边,掉头,牲口自己找到路线了。一头走在犁沟里,一头走在干地上。并驾齐驱,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一亩地,少说得一百个来回。捉犁把子的人,跟在后面,一手举着鞭子,吆喝着:呔——啾——呔,嗷——回——我把你喂狼的,连个犁沟都寻不见了吗?呔——再不走,把你吆到红河里,卖了牛肉——嗷——
一犁过去,再一犁过来。灰白干巴的土地,露出了黑褐色的骨肉,泛着细密的潮气。男人耕地,女人娃娃提着头、刨子,满地追着打基子(较大的板结土块)。一亩地耕完了,大地像翻过了它的旧棉袄,把半新的里子露在了外面。一溜子墨绿的牛粪,在土帮上,像盛开的一串花,点缀在大地的衣袖上。
基子打完了。满地都是均匀而细密的土壤,新鲜,温润,宽厚,埋藏着万千籽种的密语。最后,歇一阵,吸一锅旱烟,换一口气,等地晾晒一阵。
歇好了,挂上耱,从外到里,把地耱平展。小时候,我们爱站耱,扯着牲口尾巴,站在耱上,跟坐土飞机一样。但站耱有时也是危险的,万一牛拉稀,一泡粪下来,正好落在头顶,顺流而下,那就糟糕透顶了。有时,基子一大,把耱颠起来,会颠翻,把我们卷到耱下面,埋进犁沟里。所以大人很少让我们站耱,他们还嫌我们轻,没重量,压不碎基子,耱不平。
耱完地,这一亩麦就算种上了,得小半天时间。耱过的地,平整,展拓,像一匹灰褐色的绸缎,铺在田野,渐渐变成了黄色,变成了灰白色。种完地,收拾好农具,男人扛犁,女人背耱,娃娃拎着头,举着鞭子,吆赶牲口。忙活了半天的牲口,喘着粗气,嘴角上挂着一堆白沫子,闷着头,摇晃着,回家去。铃铛声,摇碎了十月的夕阳和薄雾。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村里的牲口屈指可数,种地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虽说寥寥无几,但好歹还种着点。这些种着的地,到翻耕时,要么没有牲口可用,要么人年龄大耕不动了。这时候,邻村的马北方开着大型拖拉机就突突突进村了。
马北方,五十来岁,人叫老马。
老马进村,把拖拉机停在梁顶,满村找酒友子去了。爱喝酒的一帮人,互称酒友子。就如爱鹁鸪的人,互称鹁鸪友子。村里留守的中年人,所剩无几,老马的酒友子也就他们三四个。这三四个人,女人清一色都常年在外打工。娃娃大了,不念书,也出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太大负担,男人守着摊子,没多少农活,家务也懒得干。对于他们来说,闲时间一把一把,多得跟六月的烂韭菜一样。
没事干,几个人凑一块儿,提两瓶十几二十元的酒,不够,再提两瓶。一边熬罐罐茶,一边划拳喝。黑乎乎的茶缸,蹲在电炉上,屁股灼热,嘴里冒泡。瓶里的酒,倒在大小不一勉强凑够的酒盅里。酒满心诚。酒水溢出盅,洒在炕桌上,一摊,一摊。老马好酒,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只要闻到酒,他的两条腿就软了。只要有人叫着喝酒,他就没命了。只要上了酒桌,就是天王老子也别想着把他拉下来。只要喝高兴了,就天不怕地不怕了。老马酒量好,四里八乡的人也知道。他号称西秦岭划拳一把手,曾经拳划黄河两岸,酒喝西北五省。他喝的酒,据说能装满两个涝坝了。他喝酒,从不碰盅,一律划,从不两盅、三盅,要喝,最少六个,十三太保也行,二十四个也可以,没说的。他划拳,没平局,必须要有个输赢,多少都要钻到底,谁输谁喝,不代不赖不卖。他喝酒,酒盅里要滴酒不剩,喝个底朝天,要是盅底“养鱼”,罚,三个,没说的。他划拳,手底下讲究个快,嘴尖舌头快,快刀斩乱麻,说时迟那时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置之死地而后快……六拳下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已被老马斩首落马,片甲不留。
满村子都是他们的划拳声,那撕心裂肺的吼叫,让十个数字字字沾血、字字溅着火花、字字藏着杀机。他们的吼声,把十月的一场雾,震成了小雨;把十月的一场小雨,震成了大雨;把十万片秋叶,震得哗啦啦,落满了地。
干六。老马咧着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得意地说,来,给你代一双,送个人情。一手捉一只盅,搭到嘴边,一饮而尽,末了,还要咂一口,要把酒盅吸进肚子里一样,才算喝干净。喝完,摸两把嘴角,啊一声,叫道,好酒,好酒。此刻,他原本黝黑的脸,变成了酱红色,跟腊月里挂在屋檐下的一条猪肝子一样。
老马拳好量好,但每一次醉的都是他。他贪杯。
醉了的老马,自由了,解放了,疯狂了。轻则掀桌子、摔瓶子,嘴里胡骂,重则上房揭瓦,杀鸡宰牛,简直如同土匪一般。啥人都拦不住,一拦,他东倒西歪,怒目圆睁,吐着酒气,就要拳头砸过来,要人门牙。所以,喝醉了的老马,就真成脱缰野马了。
老马来麦村,不是专门来喝酒的。喝酒是他的爱好,耕地才是他的目的。
喝大,睡一晚上,第二天,酒醒了。老马被人叫起,他揉着挂着两粒眼屎的眼,伸着腰,打着哈欠,满嘴汹涌而出的酒味依然能熏死一头猪。他一边点烟,一边把碾压成鸡窝的头发用手指梳一梳。下炕,从一堆空瓶子、烂酒盒里翻腾出鞋。鞋窝里装着一摊昨晚谁的呕吐物。他翻出别人的鞋,二话没说,穿上,脸也不洗出门了。
没有牲口,或者有牲口干不动的人,会叫老马去耕地种麦。拖拉机上架好籽种、化肥,突突突,冒着黑烟,进了地。地都是挑拣的平整的。给拖拉机挂好犁,撒完化肥、籽种,就开始耕地了。一犁过去,一米宽,湿漉漉的土在倒钩型的爪子缝里哗啦啦翻起来,黄扑扑的土雾腾起来,像一朵落雨前的云,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原先半上午的活,拖拉机不费吹灰之力,几个来回就种完了。
一亩地八十元,通价。老马不多要,你也不能少给。
种完一亩地,老马下车,和主家坐在地埂边的草坡上,摸一根烟,互相点上,歇缓一阵,说点闲话,听来的,看见的,或者无中生有的。不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撂荒地,长满了蒿草,已渐渐枯黄。
种完一亩,再去种下一亩。整个深秋的田野,只有老马的拖拉机,用单调而重复的声音把无限的寂寥涂抹着,涂抹成了黄昏的一块云,或者一汪落日的余晖。
麦村的几十亩地种完,老马就要去另外一个村子种地了。像赶场子。另外一个村子,情况跟麦村一样。临走前,老马还要最后喝一场。老马和主家,喊来那几个酒友子,又喝开了。这一次,五个人,先是三斤三星金辉,喝完,没够,商店没这个酒了,换成古河州。两斤古河州喝完,主家又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瓶珍藏的好酒。听说要三百元,他一直没舍得喝。今天看在老马的面子上,就喝了。老马再一次咧着嘴、眯着眼,把酒瓶搭在鼻子上闻了闻,说,好酒,今天就地解决,有酒不喝非君子,来来来,咱们两个,不对,五个,都是君子,把这一瓶消灭了。其他两个,吐的吐、睡的睡,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还有一个爬在炕桌上,摇晃着脑袋,嘴里叨叨嚷嚷,下巴上挂着的粉丝和胡萝卜丝,混合着唾沫,不知擦去。只有老马腰杆子伸得直直的,一边自斟自饮,一边骂着这帮孙子,一上炕嘴硬得很,要把我灌倒,你看现在,你们一个个怂样,真是丢人透顶了。最后,老马把一瓶酒喝掉了八两,眼仁喝得红成了血珠子,一张脸由酱紫喝成了煤黑。
酒到后场,老马突然想起第二天还要赶早去给人家耕地,得先回一趟家,取柴油,车上备的用完了。他在迷迷糊糊里想起了这件事,他觉得一定要回去一趟,不然明天耽误事。当这个念头在他脑壳里划过后,他只记得一件事,回家去。
他起身,下炕,穿上鞋,说,你们一帮软怂,有本事起来再战斗一圈,啊,你们这帮软蛋,嘴儿客,牛皮客。他爬在炕沿上,把几个喝倒的人,一人捅了一拳,带着无限的鄙视和得意,哈哈哈哈大笑着,差点翻倒在了地上。他扶着方桌,含糊不清地说,你们睡着,我走了,你们这群残兵败将,好好睡。炕上有人听他要走,使出吃奶的劲,抬起脑袋,眼皮都伸不起,说,走哪儿去?你喝大了,哪儿也不能去。你怂才喝大了,我好好的,你睡着。炕上的人伸胳膊拉他,没够着,一下扑空,趴在炕上,睡着了,呼噜打得跟杀倒的猪一般。
老马点了一根烟,好几次没点着,点着之后,找不见嘴。他夹着烟,东摇西摆,脚底下打着绊子,出了门。
夜色浓密。弯月挂在天幕上。明明灭灭的星斗,风吹,有嗡嗡之声。几只老狗,稀稀拉拉地叫了两声。
老马摸到梁顶,爬上拖拉机,打着火,开走了。突突突的拖拉机声,在黑黢黢的夜色里飘过。麦村,有没有人知道喝醉的老马开着拖拉机离开了?
第二天,跟老马一起喝酒的人,还在宿醉中,断片了,他们不知道老马已经走了。等他耕地的人,以为麦村的活,还没有结束。
第三天,酒友子又凑起了新的酒场子,把老马忘了。放羊的老财,把羊赶到湾子里时,隐隐看见远处不对劲,跑过去一瞅,惊呆了。老马的拖拉机从湾子里的路上翻下来,沿着坡,一直滚到了下面的酸刺林里。拖拉机下,只有两条腿,直戳戳伸在外面,光着脚板。
老马死了。
人们把拖拉机扯上路,拖拉机还能开。人殁了。
最后,老马在深圳打工的女人赶回来,向那晚上一起喝酒的三个酒友子和主家,一人要了四万元,私了了。老马的女人心想,人都死了,闹腾也不起作用了,还不如简简单单把事情处理了。老马的女人好像并不显得有多难过。那四个喝酒的人,从炕柜的烂袜子里掏出女人打工寄回来的钱,啥话也没说,给了人家。老马的女人办完后事,拿着钱,匆匆忙忙去了深圳。
那一夜,这几个人,缩在自家的被窝里,抽打着自己的嘴巴子。都怪这张嘴,太贱,太贱了。不光喝殁了一条人命,还喝光了四万元。他们抽打嘴巴的声音,在麦村的夜空翻动着,像犁铧把瓷实的泥土哗啦啦翻动着。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作品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散文选刊》《小说选刊》《芙蓉》等。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王选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