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场雪(选读)
文/蔡测海
游戏从游戏开始,故事从故事开始。我试图寻找从未开始的事物,很难。人强不过开始。一块石头,也有开始,成为峭壁,成为高山。石头的生长,会很缓慢,游戏也是。
跳房子,是从赣开始的,她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游戏。她的名字,是我遇到最难写的一个字。一开始,我以为是两横一竖。她告诉我,章、久、工、贝,合起来就是。一个难写的名字,变成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
画上九个格子,投掷沙包或扁平石头到格子里,人跟投掷物在那一格站定。沙包好控制,石头不好控制,她就像沙包,我就像一块卵石。我总会在格子里摇晃。我没有格子,是她慢慢把我变成格子。其实,择缓处爬坡,找浅处过河,吃适量的盐,吃煮熟的饭,那也是我的格子。因为没经历跳房子游戏,我从不知道,我也是有格子的人。我有一件粗格子棉布衣服,母亲纺一斤二两纱,换一斤棉布,互不找钱。从土里捡回棉花,母亲在桐油灯下纺纱,把我纺成格子少年,竹制的纺车,吃棉花条,吐纱,长出纺锤。在变成格子少年之前,我先变成纺锤。语文课本里有黄道婆的故事,母亲没有语文课本,她一边纺纱,一边讲舅舅的那些事。舅舅十二岁,外公外婆染瘟疫死了,舅舅成了孤儿,投奔姐姐、姐夫,也就是我的父母。多了一张嘴吃饭,就要多一份劳力。舅舅十二岁,历练太差,锄草时总伤了黄豆苗和包谷苗。父亲心痛庄稼,骂他。小男孩再没回家,跑去当土匪。他本来是要当红军的,天黑,又下雨,跑到土匪窝去了。压寨夫人留他当勤务兵,帮她背包袱。祝三部队剿匪,迫击炮弹把舅舅和包袱炸成碎片,压寨夫人当场就哭了,她心痛那些碎片,绸缎衣服和金银首饰的碎片,一块碎玉卡在小男孩的骨头里,金戒指卡在小男孩的眼睛里。她从碎片中捡出几样完好的。叫人把小男孩的碎片和衣服的碎片一起埋了。她说:等祝三部队走了,要给小男孩立个碑。
母亲说:你爹心狠。说完了接着纺纱。母亲没再给我讲舅舅的那些事,她大概忘了。忘了一些事,纱就纺得匀称。纱纺得匀称,我就能穿好的格子衣。我穿了好的格子衣,在风中行走,我会是一个好的格子少年。
这一切,都和母亲纺纱有关。
我穿上格子衣,就想和赣一起跳房子。地上的格子,总是由赣画好。赣说:你穿那么好看的格子衣,你来画。我画了九个格子,有半个篮球场大。每条线都很直,搭起来很周正。大格子,我投掷石头不会失手。赣投掷沙包有点费力,优劣算是扯平了。格子的大小影响游戏的胜负,并不改变游戏规则。我俩轮换着画格子,她画的小,我画的大。有时,我俩也交换投掷物,她叫我石头,我叫她沙包,我们都是投掷物。游戏套着游戏,我们用石头剪刀布竞猜,决定先后。起跳,像投掷物一样,在格子里落定。
南方的地平线不太明确,远处是山脊,河流隐没处,若有若无的回声和林子里的鸟鸣。我想画很大的格子,把风画成游戏。
游戏就是友谊,和人一起成长。直到某一天,我和赣交换投掷物,作为纪念。那一年,我十七岁,她十六岁,奇数和偶数相加,得数是奇数。
赣来自江西,她的名字是一条大河的名字。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两条河,小河大河。她爸那江西口音,听起来比写个赣字还困难。我们叫江西人老表,赣爸就是表叔。表叔是乡里一般干部。一般干部是什么干部,什么职责,我不知道。乡长对表叔讲,他当年也是一般干部,做到乡长,在一个地方干了八年。八年,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时间。表叔笑着说:八年我不会当上乡长,但我一定会当上哪个小崽子的老丈人。八年,我用八年时间跳房子,学会蛙跳、猫跳、跳蚤跳,立定跳高两尺半。我连跳十几块跳岩过河不湿鞋袜。乡长用八年时间,和村民一起修了十里长的悬崖穿山公路。八年,用棕绳拴在腰上,人挂在悬崖上,修路人叫他吊瓜。路修通了,村里人还叫他吊瓜。他本名叫南正,时间一长,就变成吊瓜。猴子偷了棕绳,吊瓜一样挂在悬崖上,崖上搭起人与猴和瓜棚,吊瓜找不见棕绳就骂猴:我是在修路,你装什么猴?
悬崖边还有人喊:吊瓜,县里罗部长来了,快下来。
县委组织部的罗部长告诉吊瓜:组织决定,你是乡长了。吊瓜说:报告部长,县里多给我钢钎、炸药、大锤、棕绳,等路修通,我给你当个好乡长。
乡长后来对表叔说:那时我是一般干部,也真想当个乡长,当了乡长,才知道我就是个吊瓜。
表叔刚来的时候,叫特派员,后来取消这个职务,他就是一般干部,不过,大家还叫他特派员,他反正算个领导。我怕他,他一双眼睛爱打量人,我生怕他打量出什么。每次见他,我会低眉垂眼,一双手在衣襟上不停地擦,人做过什么,会在手上留下痕迹。我这双手没干过坏事,当然,也没干什么大事。最大的事是拿根木棒学孙悟空。我还搓过棕绳,只能牵牛。吊瓜挂在悬崖上的棕绳,是父亲搓的,结实。父亲搓好一根棕绳,拴在自己腰上,一头拴在树上,吊下悬崖,这样先试一次,然后交给吊瓜。虽然父亲对他搓的棕绳很有信心,但还是要试一下棕绳牢不牢。只有关切他人生命,才处处安全。父亲骂了舅舅,舅舅当了土匪,被炮弹炸成碎片,父亲会一生忏悔。我想,这是父亲搓好每一根棕绳的原因。我会和父亲一起沉默,因为我曾杀死过一条蛇。它很可能是无毒蛇,于人无害,但是,我哪会知道呢?
表叔那眼神,让我心虚。
我患过麻疹,高烧,长许多疹子,很痒,不能抓挠,那样会变麻子。我问母亲,我会死吗?母亲说,不会,有观音菩萨保佑。梦见向深渊坠落,围绕着棉花一样柔软蜜一样甜的东西,以为那就是死亡的样子。病好了,脱了一层皮,蛇也会蜕皮,蛇蜕一层皮会长大一次。
表叔打量我,像是看见我的梦。和赣跳房子,她跳进一处深潭,我也跳下去。我不怎么会游泳,在梦里会游,踩着水像走平地。我把她抱上岸,她没死。我把她放在鹅卵石上,让太阳晒干她的头发和湿衣服。她问我,跳房子的格子怎么涨水了?
表叔那眼神,是不是看见我的梦了?
表叔问我:多大了?
我说:特派员,明年十二岁。
表叔又问:今年,多少岁?
我说:今年十三岁。
他笑了:我只听说土地会减产,年纪也会减产?明年你该十四岁吧?要不,你今年十一岁才对。
表叔的话很智慧。人间的智慧他全有。他是光,我是黑暗。他是火,我是一夜的雪。遇见一个人,无论他年纪多大,让我走近,如果他对我有期待,就是让我消失,像一滴雨消失在河里。从此随波逐流,又奔腾万里。了却一滴雨的厄难,做一泻千里的打算。
我出生在农历大年三十的午夜,往大处说,属龙,往小处说,属蛇,处壬辰癸巳的中间。毛泽东诗词,“山舞银蛇”,讲的是我。“金鳞不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讲的还是我。我讲不好自己的年纪。我和那一夜的雪花一起飘落人间。雪落无声,雪把声音留在浮云之上,把七彩颜色留在云霞里,无声洁白,惹不得的世界,好好落一场雪。我降生也没声音,没哭喊。俗说是梦生子,就是一生不会说话,只会呼吸。因为呼吸,母亲才会有母亲的宣告,这孩子是活的。我用小手拍了拍母亲,让她惊喜,让她放心,我是活的,生命比哭和说话重要。一条鱼也没声音,不哭也不说话。一滴雨落在河里,彼此问候,从来无声。蛙能唱能哭能说话,闹了池塘和水井,一哭破喉,一唱云雨,当它遇上东海来的老乌龟,它都说了些什么呢?
表叔问我多大年纪的时候,天开始下雪,我的年纪在十一岁和十二岁的连接处,我一直搞不清楚岁数。上学时报名,老师问我几岁。我说不是五岁就是六岁,要不就是六岁七岁。老师就在我年龄一栏填上六岁。老师说:从现在开始,你六岁,以后一年长一岁。还怕什么呢?多大年纪,在那记着呢。关于岁数和这“呢”字,老师没少提醒:你写一篇五十个字的作文,写了三十几个“呢”,句句有“呢”,你只会写这“呢”?我说,老师,那怎么办呢?帮我写年龄的老师,后来一直是我的语文老师,教我们语文和作文练习。她从我一大堆“呢”字里,找出几个好句子来。去年开过的桃花,今年又回到树上了呢。你们看看,有谁能写出这样的好句子?同学们就不敢再嘲笑我,我成了小有名气的“呢”字号人物。大扫除,我在废纸堆里捡到一封信,信封一角是一支梅花,清芝同志收。她要走了那封信,信是她的。才知道老师有个名字,叫清芝。她问我:没看信吧?她脸红了一下,比平时更好看一些。她又说:你也看不懂。我也红脸过,红脸有时是撒谎,有时是秘密。我不会说,不会让别人知道清芝老师的秘密。她脸红好看,一定是个好秘密。语文课本里会有一两首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赣问老师,两只鸟能说两个鸟不?清芝老师要我说说,我说:我们家有几个鸡,几个猪,一个狗。清芝老师说:你们看,那个味道你们慢慢懂,不过,你们写作文,树上有一只鸟,不要写一个鸟,这是语文课。语文课,三个字,一字一顿,她说的是重音。不经意的种植,有意愿的春秋。
表叔是普通干部,做一些普通的事。他是校外辅导员,体育健身运动委员会专干,计划生育抓得紧那会儿,他帮忙写标语,那些标语很有民间性,后来成为民间笑话。他本来会讲笑话。他有时也是农业技术员,有时又是兽医。
他问我多大岁数时,在下雪。他打量我的身高,说体育可以增高,还可以增智。他是不是嫌我矮,说我低智?他一打量,我就灵魂出窍。他的打量像一条鞭子,我的灵魂像一群羊,一只羊的碎片,满地乱跑。羊群是羊的碎片。灵魂撒满山岗。这一刻雪花飘飘,梅花开满山岗。他问我多大年纪,再打量我的身高、四肢和头脑,看我适合哪一样体育运动。
在他的打量中,我俩完成了一次聚合,一次统一。我们一致认为,跳房子也算一项体育运动。还有跳绳和荡秋千。他的体育分两类,一类是劳动的,捡牛粪、挖土、搬石头;一类是游戏的,跳房子、荡秋千、游泳、打球,还有武术。踢足球不行。能摆张桌子的地方,能收一升谷,一个足球场,能收几十担谷呢。山里也没地方安放一个足球场,篮球场也是小号的,从发球线可直接投篮,让对手防不胜防。他后来去体育学校当校长,训练出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据说,搬石头是他重要的训练方法。
表叔的来历很神秘,他怎样从江西来到这里?传说他是半个博士,没读完博士,去卖猪肉。从省里下到县里再下到乡里,一路飞流直下,当了一般干部。女儿赣和他一起来到这里。他在这里找了个老婆,妇女主任,也是拿工资吃国家粮的,漂亮,会唱歌,比他小,比他女儿大。她叫王礼花。她唱麦浪滚滚闪金光,鸟不吱声,河里的鱼会跃出水面。我被臭虫跳蚤叮咬过的皮肉,就是她的歌声治好的。王礼花教赣唱歌、拉二胡,被跳房子耽误了,我真过意不去。别人对我跳房子早有闲话,跳房子跳不出大房子来,跳不出宫殿大厦,跳不出好吃好穿。赣说:有什么呢?我爸妈从不怪我,只要我喜欢。
跳房子的格子里是我,教室的格子里也是我。这许多格子,有的装着约束和理想,有的装着自由和快乐。我把这些留给未来。我以我不明不白的年纪发誓,我并未耽误什么。当某一天到来,也就是一个人未来的那一天,查寻年龄的十一岁或者十三岁,当时不曾错过理想,那个年纪就是理想,年龄耽误不了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年纪,我从小学考取初中,又原则上要求回原校读小学。原则,原校,就此成为一生最深刻的两个名词。名词,常常是多义性的。时间折叠,方便携带。我记起那次,表叔问我多大年纪,我说明年十二岁,今年十三岁,我要给我的回答打一百分。
表叔和我说话,应该挑下雪的日子,万物朦胧,声音就明白。透明的声音穿透雪花,少年的影子在雪地上跳跃,一只脚站立,影子是投掷物。一抹雪野,田埂土坎,埋伏的格子,是我的祖先,劳动者的游戏,跳房子的痕迹。在这样的下雪天,我能听见祖先的笑声。他们裸出前胸,裤脚管遮不住的脚杆,烤出火斑,人皮红花,笑出摇晃的火苗。烤出肉香,祖先的皮肉和猎物的皮肉香混合成火塘的气氛。
穷人面前一朵花,穷不过三代,那些谜语和谚语就是在下雪的时候烤出来的。烧酒也是烤出来的。父亲给我一碗添蜜的热酒,漫天燃烧,群山起舞,大地摇晃,我变成一朵雪花。
雪地上有鸟的爪印,我画上一些格子,把鸟的爪印留在格子里,给那些鸟留下一些记忆,它们像是刚跳过房子。
赣落在格子里,尖叫。我想她是踩着了硬物,或者是一枚可怕的钉子。她叫我过去试一下,她踩着了一条鱼。格子,快过来,一条大鱼,它要跑掉了。我用右脚试了一下,又用左脚试了一下,没有一条鱼。雪水融化,淹了我的脚踝,淹了我的腰,漫过头顶,我在水里变成一条鱼。雪地里不会有一条鱼,那是自己的影子。我说:赣,没有一条鱼,你踩着我了吧?踩着你的还是我的影子了吧?
她踩着了大地,一条大鱼,大若鲲鹏。
积雪易化,新叶染绿南方,覆盖了我不舍的日子,一切忽然而至。清芝老师说:你们毕业了。我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最后为你们送行的人,你们留下桌椅陪我,我不能再陪你们。能陪你们的,是各自的理想。她给我们的,是理想,还有那些漂亮而工整的粉笔字。漂亮工整,是她的锦绣图,藏着她的理想,理想是一支笔,字写得漂亮。
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有桂花的气味。我熟悉这气味,每次经过她的窗前,灯光从纸糊的格子窗照出来,有桂花香。她的房间是卧室兼办公室。一张挂着蚊帐的床,花被子花枕头。一张办公桌,钢笔毛笔铅笔粉笔,还有点水笔和小蜡笔。一大堆学生作业本和语文课本,还有一个地球仪。一管竹笛用红丝线挂在板壁上,几张电影剧照。一个洗脸架,搪瓷脸盆和搪瓷刷牙缸,热水瓶和一副碗筷。这所有的物件,都沉浸在桂花的气息中。
她送给我几本新的练习本,把我的语文练习本和作文本留下。
我还留下了跳房子的格子,留下那条河,轻轻地说话和唱歌,昼夜,四季。
我记起借了她两本书,《唐诗三百首》和《青春之歌》。我还给她。她接过去,又递给我,说:你留着吧。除了跳房子,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本书。在《青春之歌》这本书里,她画了好多波浪线。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4月号)


蔡测海,1952年出生于湘西龙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文创一级,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地方》《家园万岁》等。多次获全国性文学大奖,并译成英文、法文、日文多种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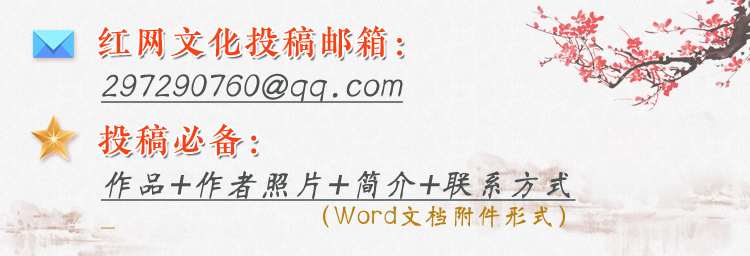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蔡测海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