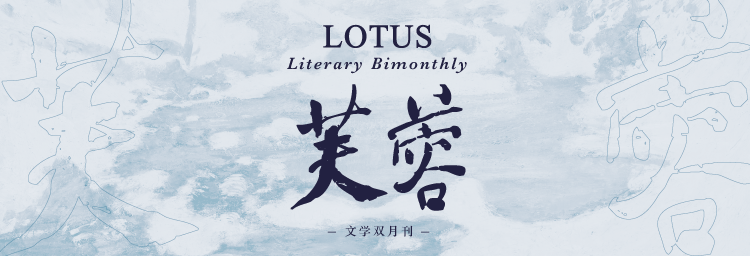

山雨(短篇小说)
文/东君
雨落在屋顶的时候你要庆幸,雨没有直接落在你的头上。老洪吐着烟,把目光从檐外的暴雨转向老麻的秃脑门说。晒谷坪上雨似蚕豆,发出一阵密实的噼啪声。老林和我坐在一个反扣的捣臼上,也吸着烟。
老麻望着檐下的旧灯笼问,这灯笼是不是上间佛灯?
老麻所说的上间就是中堂。上间有神灵护佑,故称上间佛;祭祀的灯,依例叫上间佛灯。但我还是要纠正老麻的说法,你看灯笼前面写着“三官”二字,就可以断定这是三官灯,祀奉的应该是三官大帝,我们这儿管他们仨叫三官爷。
老林抖落烟灰,说,你们再往左上方看,神堂阁里供着本家六神,一神一炉,是不是有点像大神们的烟灰缸?
老洪说,你们的说法其实都不太对。本家六神嘛,指的是门神、檐神、灶神、土地神等,不止六位——就像扬州八怪其实也不止八位——我们这儿的人习惯于把这些家宅内的本地爷统称为上间佛。所以,老麻说得没错,三官灯也可以称作上间佛灯。
老洪跟那些民间的火居道士打过交道,因此,我们一致认定他的说法最权威。从老洪口中我们还得知,上间佛只管家宅内的闲事,出了某个势力范围,他们就不管了,诸事拎得很清。这是一座废弃的老宅。六神尚在,人却没了。庭院间只有土花斑斓,野狗游荡。
老麻望着那一排溜摆放的香炉,说,这座老宅虽然不大,却供奉着好几位大神。难怪这一带的房屋都拆的拆,迁的迁,唯独它还孤零零地留着,像是被几位大神罩着。
老麻是拆迁办的主任,面对“本地爷”,他也不敢造次。我问老麻,你们为什么没拆这座老宅?老麻说,这是上头的意思。
说话间,一个老人走了过来,合拢雨伞,也没瞧我们一眼,就转到一隅,从纸包里取出一根蜡烛、四支香。他解开柱子上的绳子,把悬挂檐下的三官灯放下,打开灯笼罩子,在底部木板上插了一根红烛。我掏出打火机,递到他跟前,他也没理会,兀自掏出火柴盒,点燃蜡烛,继而盖上灯笼罩子;之后,就在灯笼上一个类似于茶壶嘴般的竹筒上插了三支点燃的香。这一切摆置妥当,他又回到柱子边,抽着绳子,把灯笼升至檐下,给绳子打了个结。剩下的一支香,插在一根柱子上的竹筒里。老人站在灯笼下,整了整了衣裳,对着三官爷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依旧在抽烟。微风。烟丝缭乱。雨水顺着檐口的沟头落下来,打在石阶上,滴答作响。老洪说,我跟你们讲一个跟三官灯有关的故事。一九四一年暮春,日本人打到我们这边来,飞机扔下两枚炸弹,炸毁了孔庙大成殿两边的屋子。那时,我爷爷的部队就驻扎在大成殿隔壁的一座祠堂里。他们自知势单力薄,就分成三股力量,打算跟日本人周旋。黄昏边,我爷爷想找个地方躲宿。他走到一座老宅,看见檐下挂着一盏三官灯,就合十给三官爷拜了三拜,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了过去,击中长桌上的香灰炉。他摸了摸头皮,似乎还有点发烫。我爷爷不知道这冷枪是从哪儿打来的,他端起手中的机枪,顺着子弹打来的方向追出去,也没发现敌人的踪迹,但他自知行踪已经暴露,赶紧趁着夜色撤退到后山。我爷爷说,那颗子弹就是在他鞠躬那一瞬间打来的,假如他的脑袋抬高哪怕一厘米,都有可能毙命。我爷爷还说,自那以后,他无论到了哪里,看到三官灯就会跪下来磕三个响头。
站在一隅的老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这样的事我也曾听过。
他长得有些清瘦,虽然颊萎腮瘪,但气色不错,两块颧骨上还泛着一丝红光。他没有笑。也许是因为他不太习惯冲着陌生人微笑。
我也给你们讲一个跟三官爷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微闭着眼睛说。
这座宅子,原本不是我们的,它的旧主人姓谢。谢家是本镇的名门望族。谢老爷身故之后,谢家就败落了,我们这些当年住茅草棚的穷人家就搬了进来。我们家分到了一间轩间,一间披舍。而谢老爷的弟弟就住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他有一个既难念又难写的名字,我们都管他叫谢先生。谢先生是独身的,我们暗地里都叫他天独自人。他跟邻里来往不多,跟我爹娘也没说过几句话。
谢先生怕不怕寂寞,我也不晓得。但凡有小孩子跑到后院,他总是乐意跟他们玩的。有孩子来讨零食,他就给他们每人分一颗糖果;有孩子来问字,他也会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饶有兴味地解释一番。也有些孩子,比如我,为了能吃到糖果,便故意向他问字。有一回,有个孩子拿了一根木炭在地上写了一个生僻字,问谢先生这是什么字?谢先生的喉咙里像是被痰塞了似的,过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学堂息,这个字,不许问,也不许提。
谢先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寂寞,他很会自得其乐。他有一方淳安的石砚,叫龙眼石砚,平常能呵气成雾,贮水不涸,他拿一支鸡毫笔蘸着,就在石板上写字。我不认得他写的字,但我喜欢看他手中的笔在石板上游动的样子。他家门口还有一个破水缸,月亮从天井上方投下影子,他就坐那里,跟水缸里的月亮玩。有一回,我口渴得厉害,想掬一捧水缸里的水,却被谢先生叫住了,他说这水不能喝。水面浮荡着几片落叶,细看,还有一些小虫子,一伸一缩。谢先生告诉我,这是蚊子的幼虫,当地人叫它赤虫,书面语叫什么孑孓来着,字简单,但很多人都不会念。谢先生还跟我解释,这水里面有很多细菌,喝了肚子会疼。他又舀去浮在水面上的赤虫,说,喝水一定要喝烧开的水。
可我从来没有把谢先生的话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我不知吃了什么“不净的东西”,忽然生了一种怪病。起初是发热、呕吐,继而像中了毒一般,浑身酸痛。次日,脸色发黄。有人说是黄疸病,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我吃了药,打了针,都不见效。爹娘四处求医问药,都说“冇解冇解”。问问地头鬼,求求上间佛,也冇结煞。
有天午后,我躺在床上,听得外面有人弹三弦。我爹说,范先生来了,不如请他算个命。那时节,算命先生出来算命,总会弹几声三弦,就好比挑卖猪肉的会吹牛角、劁猪的会吹笛。算命先生让我爹报上我的生辰八字,沉默了一会儿,就把我爹娘拉到外面,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什么。爹娘进来时,脸色异常难看。我娘原本动不动就骂我一声“短命儿”的,但自从听了算命先生的话之后,不管我怎么闹腾,也没有骂我一声“短命儿”了。我躺在床上,也隐隐约约觉着,我可能活不了多久。
有一天傍晚,外面下着雨,爹娘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眼睛黄热,脑袋涨痛,只想往墙上撞。疼痛加剧的时候,脑袋里像是有个带棱角的东西要撑破头皮,撑破帽子。我先是放长声哭,叫了一句“皇天三宝”,雨声中猛地传来一阵落地雷。我吓得不敢哭喊了。这时,谢先生走到我眠床边,拨亮灯,说,你爹娘一直把我这个邻舍当作阶级敌人,因此我都不敢上你家探望。前阵子我听人说起你的病况,依我看,你得的是钩端螺旋体病,今天一早,我特意去长春院的老道那里求了几粒仙丹,来来,吞下去就没事了。他见我半信半疑,就说,服用仙丹之后,还得跟我念一段《三官经》。我那时头痛欲裂,也不管那么多,坐了起来,就把药吞了。他说,这仙丹很灵的,记得每天早中晚各服三颗,你藏好了,勿跟别人说起,包括爹娘。我点了点头。他随即念起了《三官经》。我不晓得《三官经》是什么经,他念一句,我也跟着念一句。他念经的时候,我记住的不是经文,而是那晚的雨声。
临走前,他对我说,除了吃药,平日里念念《三官经》,也许可以帮你化解一些苦痛。我照他的意思,背着爹娘,偷偷吃药,默诵经文,不出几天,怪病果真就消失了。爹娘说,他们昨天去了福田寺,在佛前给我许了愿,现在总算显灵了。我病好之后,问谢先生,那仙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谢先生说,他给我吞的,并非什么仙丹,而是一种治疗钩体病的西药。至于这药是从哪里求得的,他一直笑而不答。
要说这个谢先生,真的不是一般的人。乡里的人说他早年留学日本,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嘛,他们说,就是农业大学。种田还要跑到人家小日本那里去学吗?日子久了,乡里的人就发现,他在日本并没有学会什么种田的本领。我只见他下过一回地。一双白脚梗插在田地里,连田头的妇人都掩嘴偷笑。他插秧的时候,是像先生一样坐在反扣的木盆上,然后把秧苗放在长长的指甲上,轻轻一顿,再往泥里插下去。冇范冇范,这哪里像种田人该有的范?谢先生又被大家伙狠狠地嗤笑了一通。
我在早稻田学的可不是插秧、割稻这类粗活。谢先生说。
那你学的是什么?
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明白的。
的确,谢先生做过一些叫人看不明白的事。他跟朋友办过酿酒厂,但因嗜酒,常误正事。酒厂办不下去,他又转而办酱园,起先经营有方,赚了一笔钱,还赞助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诗会。但酱油与诗,毕竟隔得太远。经营酱园,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与事。他干了一阵子,不耐烦了,就把酱园的股份全部送给了一位堂兄。他还在长春院当过道士,吃了一百零三天的三官素,就还俗了。人家问他还俗的原因,他说,想吃肉。
对我们乡里人来说,谢先生简直就是个异类。他们看不惯他那与众不同的样子。他们会说,他跟我们不是同路人。既然不是同路人,那么他的问题就来了。公社书记说,他那西装头太洋气,要剃掉;说话太文绉绉,要改。总之,从里到外,都要跟张三李四一个样。谢先生干脆剃了个光头。不说话。饶是这样,也不行。
有一年,乡里办起了一家樟脑油厂,工人就近取材,沿着山脚斫掉了一株又一株樟树,眼见着后山那十余株三四抱粗的古樟也躲不过斧锯,谢先生就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哀悼古樟的诔文贴在树上。可那些斫树的工人哪里会明白他的用意,树还是照斫不误。谢先生索性不顾斯文,跳了出来,说了一通不识时务的话,结果被公社书记在大会上通报批评了一番。不出三年,山上山下的樟树差不多都被斫光了,而樟脑油厂由于销路不畅,也停办了。原本被樟树覆盖的地方荒秃着,有点刺眼,公社书记就从县里面的桉树良种站引进一批桉树苗。书记听说谢先生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懂点农林知识,就向他请教引种栽培的知识,但谢先生又说了一通不识时务的话,惹得书记很不高兴。书记转过身,大手一挥,开始动员乡里的人:桉树要种,要漫山遍野地种,再过三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一片参天大树了。谢先生听了,不再作声。
谢先生对我说,桉树就是抽水机,既吸肥,又吸水,你看好了,往后这片凡是桉树覆盖的地方,土会板结,水会慢慢枯竭。他还告诉我一些水中盐分上升多少、土地肥力下降多少的知识,可我怎么也记不牢。
谢先生毕竟是读书人呀,读书人最大的毛病是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了几句桉树的坏话,可是,那年头,说树的坏话也不行。有一句老古话叫指桑骂槐是不是?谢先生指着桉树,责问的是谁大家伙都明白。
自从有了“黑五类”这个词,谢先生也就被他们归入“黑五类”了。连谢先生本人也不晓得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戴上了这顶帽子。我不黑,谢先生说,你们看我,长得白白净净的,我怎么会是“黑五类”?
谢先生被人关在福田寺一间黑咕隆咚的僧寮里,跟那个拒不还俗的老和尚一起,禁闭了很长一阵子。听说他在禁闭期间偷偷跟老和尚学习打坐,被人告发,就直接押到农场劳改。
一天清早,我挑水回来,看见了谢先生,头发乱蓬蓬的。他走得极缓,到了门口,上了一级台阶,门槛有点高,他想抬脚迈过去,可是,膝盖一抬,腿就松软下来,怎么也迈不过去。谢先生,我放下水桶喊了一声。谢先生回头扫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把谢先生扶进了门,对着空荡荡的道坦喊,谢先生回来了,谢先生回来了。谢先生的老母拄着拐杖从上间后面走出来,那时她的眼睛已经瞎了,站在儿子跟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瘦了许多,我说。谢先生的老母把儿子的脸和肩膀抚摩了一遍又一遍,才开口说,清减了没事,骨头还在,肉是可以长回来的。谢家老太太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把“瘦”说成“清减”,就文雅了许多。
有一阵子,我时常跟谢先生在一起。他已戒酒,但吃烟,单是吃那种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有时不晓得从哪儿弄到一些烟叶,自己包烟。他吃烟的样子像是要把肚子里的一股闷气吐出来。
我十五岁那年,还在读小学。学堂里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校长也姓谢,是谢先生的堂兄,他把当年接手经营的酱园并入学堂,辟作教室。谢校长给上面打了一份报告,说师资不够,因此就请谢先生当小学教员。谢先生一人可以教很多门功课,语文、算术、美术、书法,他都教。谢先生有个习惯,每天放学前,他会走到字篓前,把那些废纸一张一张捡了去。我们都叫他“谢字篓”。我很纳闷,谢先生捡这些废纸做什么用?有一回,我发现谢先生坐在书桌前,把那些废纸一张接一张捋平,在上面写字。他写完一幅字,时常自署“米田共翁”,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自己在劳改期间扫过厕所。他这样说时,嘿嘿一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过年时节,公社书记来到我们学校,让谢先生写几副春联送到县里面。墨是徽墨,纸是洒金春联纸。乡里的人哪里见识过这么雅致的春联纸,都把头伸过来,看了又看。
谢先生写字的时候,书记手痒,也在一边挥笔写了起来。书记说,你是书法家,我是书记,都带个书字。你的字比我好,我的字比你大。这样说着,手中的笔就跟棍棒似的划拉了几下。
谢先生写完春联,书记瞟了一眼,说,这些字跟眼前看热闹的人一样,都认得我,我却叫不出名来。谢先生干笑一声,走开了。书记隔空掼来一句粗话。大意是说谢先生净写一些叫人看不懂的字。
当然,也有人看懂谢先生的字。春联送到县里面,那人就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他的“反动思想”。这就给他埋下了祸根。
有时我就是不明白,谢先生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落场就那么凄惨?给谢先生算过命的瞎子也给我算过一卦。他说我命骨生得好,命主星也好。算命先生的话怎么能信?命骨生得好,我的脚骨却折了;命主星生得好,两眼却看不到星了。不过,我后来细想,比起谢先生,上天对我还算是很仁慈的,我虽然瞎掉了一双眼睛,折断了一条腿,但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
怎么?老人家居然是一个盲人?我说,我看你刚才点三官灯,一点儿都不像个盲人呀。
老人摇了摇头。我心里嘀咕,既然他什么也看不到,点不点香烛,又有什么区别?
啊,雨像是停了,老人说,我原本要讲的是三官爷故事,结果却讲起了谢先生,不过,在我心目中,谢先生就是三官爷。
我们转头望着檐外,雨不是停了,而是变成一片随风飘展的烟雨。老人在檐下站了片刻,就打开了雨伞,向外走。我们扶搀着他说,老人家,雨天路滑,我们送你回家吧。老人说,不必了,这条路我不晓得走过多少回啰,哪里有个坎,哪里有块石头,我心里头都有数。他走路时,身体是向一边倾斜的,看得出来,他的腿脚略微有些不太灵便,若是不仔细看,跟常人也没什么异样。
老林说,我可以断定,他的故事还没讲完。
老洪说,我也可以断定,他还有一根香没插完。
我问,四根香不是都插完了?
老洪说,这位老人家应该是“三官会”的信徒,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回家后还要在镬灶佛前插一根香。
老人的身影刚出台门,一片烟雨便飘了过来,我有一种错觉,他就是我和老洪、老麻、老林聊天时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我可以在另一个虚构的故事里把他移出这座老宅,移出这片烟雨。在我恍惚的时刻,老洪忽然追出台门,像想起什么似的唤道,老人家,请留步。老人想必是在我视线外不远处站住了。老洪又追了上去,不知跟他讲了几句什么,随后踅回,招呼我们一起送他回家。老洪在县志办担任编辑,我大致可猜到他的用意。
下坡,拐两个弯,就到了老人的家门口。是盲人给我们带的路,我有一种走夜路的感觉。门没关,外面的腰门却关着,分明是警告鸡犬不得入内。老人打开腰门时,从对门传来一声酒嗝,另一个老人从窗口伸出脑袋,隔巷递来酒杯,有客人呀,捉杯,捉杯。他又在吃寡酒,老人咕哝了一句什么,对我们说,我家可没酒,如果不嫌屋小,就喝杯白开水吧。屋子拾掇得倒也干净,有一股淡淡的煤灰气味。镬灶上有一个小小的佛龛,里面坐着一尊镬灶佛,外面有一个香炉,一个供奉干果、米鸡的盘子。镬灶旁是一个炉子,上头搁着一只犹如大肚佛般的茶壶。
老人给我们倒了四杯白开水——他不用问,就知道我们共有四人——然后又跟我们谈起了那位谢先生。
我十六岁那年读完高小,就没再念书。同一年,乡里出现霍乱,父母双亡。谢先生说,人世间有六种极凶恶之事,一是凶短折,二是疾,三是忧,四是贫,五是恶,六是弱。这六种事,你若摊上了,就念些经文,可以安神止惊。有人问我,你没读过几年书,为什么说话也文绉绉的?我说,你们不晓得,我有好几年,都是跟在谢先生身边的。茶余饭后,谢先生跟我讲的大都是一些文人轶事。有一回,我们喝茶闲聊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否可以跟他学作诗,他忽然变得正色起来。他说,空头文学家做不得,你已经成人了,应该学些实实在在的谋生手艺。谢先生放下喝了一半白开水的搪瓷杯子,又接着说,我给你指明一条现成的谋生之道。我说,我读书不多,嘴笨,手又拙,不晓得自己还能做什么。谢先生说,你可以开一间开水房,供应开水。我说,家家都有茶壶,人人都会烧开水,我单是烧开水,能养活自己?谢先生说,你照做就是。不过,你烧的开水要有一个条件,水要上等。
水从哪里来?
这一带的水不行,要从远处的上游挑过来,如果嫌远,就去福田寺那边挑。福田寺旁有一口古井,最是甘甜,庙里的和尚平日里喝茶煮饭,都是用这口古井里的水。谢先生说。
烧水的柴火?
就从西塔山上捡拾,乡里的解板厂有些木屑或刨花,也可取来当柴烧。谢先生说。
烧水,要有个大镬,可我身无分文,去哪里买一口大镬?
福田寺被毁了,和尚都跑了,有一口大铁镬,挺沉的,弃在荆棘丛中,没人要,你可以叫上几条壮汉,设法把它弄过来。谢先生说。
水有了,柴火有了,大铁镬也有了,事情就这样成了。起初几天,双肩被扁担压出了马鞍臼,后来那地方又隆起了一大块。日子久了,肩膀也渐渐磨得像水牛背一样厚实了。
我砍柴时会拜山神,挑水时会拜井神。走路时,我念几句谢先生教我的经文。别看我瘦小,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我可以从山上挑下一担柴火,也能从四里外的福田寺挑来满满两桶水。
有一天,我听得咔嚓一声。我以为是身上哪根骨头断了。上下摸摸,没有痛处。再看扁担,已从中间折断。我把这事说给谢先生听。谢先生说,从前有个和尚,天天给寺庙挑水,后来有一天,扁担忽然折断了,他却在咔嚓一声中悟道了。所以,你继续挑水,也会明白一些道理。谢先生读过很多书,说话总喜欢拐弯抹角。
我不明白他说的那番话,但我有一天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用无色无味的水,也能做出有情有义的事体来。
解板厂的工人喝了我烧的开水,都不再喝自家的开水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你烧的开水是甜的,我们的开水有点儿苦味?
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
我烧水,用的是福田寺的井水,每天挑两回,从不多要。有时落雨,就接点天落水;上山捡柴火时,顺便接点岩前水。总之,我没用家门前的河水烧过开水、泡过茶。
有几个干粗活的工人长年喝我烧的开水,身上的老毛病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于是就对人说,我烧的开水简直就是治病的神水。这话一传十,十传百,来我这儿买水喝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我每天供应的开水不多也不少,价格也没涨落,一年的收入大概要比撂摊卖艺略好一些。
我这人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讲着讲着,就讲到自己的老本行上去了。呃,我这就讲讲谢先生。老人说着,转身从篮子里摸出一根香,点燃,插在镬灶佛前的香炉里,照例是拜了三拜。老洪朝我们使了个眼色,露出了貌似得意的微笑。
这件事我会慢慢跟你们道来,老人像说书先生那样用悠缓的口吻说道。
要讲谢先生呀,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谢先生的谱名叫道晖,字味温,号观堂。谢先生经历过很多事:他留过学,学的专业是寄生虫学,曾跟随冯玉祥的部队做过军医,当过道士、居士,教过书,坐过牢,也有人说他做过和尚,其实是误解,他为了混口饭吃,一度替寺庙抄过佛经,至于留光头,是自然谢顶的缘故,并没有真的出家祝发。在我记忆中,他总是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长衫,戴一顶学士帽,跟我们常人不一样,他遇大恐怖不惊,遇大欢喜也静定。
有一阵子,谢先生不知道去了哪里,杳无音信。人虽不在,乡里的人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他们听说我是他的学生,就让我在谢先生家的门口刷一句标语。他们把一桶土朱和刷子交给我。我说,我不晓得写什么。带头的人就说,就写消灭社会的寄生虫谢某某。我没法子,硬着头皮写下一行字,但我没有在土朱里拌胶,不出几天,那一行红字就被一场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
最后一回见到谢先生,是在老戏院门前的榕树下。六月天色,他头戴一顶纸糊的帽子,面容益发消瘦,眼窝深陷下去,透着黑气。那天的太阳着实有点猛,当头照着,我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头闪着青光。有个年轻人举着一面镜子对着谢先生的身子晃动着,说是要照出他的原形来。有时,那一道道光亮如同尖刀般,在他脸上来回切割。谢先生闭起了眼睛,身子瘫软在地,一身黑衣罩着,看起来就像一条在风雪中蜷缩的黑狗。有个小男孩用树枝挠了一下他的光脚板,没反应。围观的人觉着无趣,就转头走开了。
我从河埠头借了一辆板车,把谢先生拉回家去。有人掩着鼻子问,死了?我不作声。随后,我又把谢先生扛到后院,他的身子有点发硬,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家中的老母早已去世,长年没人居住,有一股呛人的灰尘气。我粗粗清理了一遍床铺,让他平躺在床上,垫高头部,随即倒了一杯开水,把麦管插到他嘴里。他的舌头没动。我伸手探了探鼻息。那时是大热天,我却好像听到了冰窖里一滴水落下的声音。我的手也凉了半截。
我回到自家,烧了一镬水,打算给他清洗一遍。这可是福田寺的水,每一滴都是干净的。我按照习俗,给他擦身,前三把,后三把,然后挑了一件干爽的苎布衫给他穿上。
谢先生躺在床上,比从前似乎小了一圈。我念了一阵子经文,舌头累了,身子也乏了,就伏在床边一张布满灰土的桌子前,沉沉睡去。我醒来时,发现谢先生不见了。那一刻,我觉着他不曾来过这地方,自然也就没离开过。
我出了门,望着檐下的三官灯,对邻舍说,谢先生是个上间佛。邻舍不信。可我至今仍然相信谢先生就是三官爷的化身。
一炷香快要燃完了。老人背对着那炷香说。
一屋子的静。一段烟灰颤抖了一下,忽然掉落。我们都知道,老人接着还要说些什么。
这雨时断时续的,真叫烦人,老人说,小时候,谢先生给我们讲解一首《山雨》的古诗时,外面恰好也落着雨。他讲着讲着声调忽然变得异常低沉,他说,一个人在黑夜听雨感觉像是听瞎子在哭。那时候我不理解,雨和瞎子在哭有什么关系,我的眼睛瞎掉之后,才慢慢明白先生说的那番话。
这话说得真好,老洪转头对诗人老林说,你应该把它记下来,写到诗里面去。
老人说,我是背时佬一个,总想跟人聊聊过去的事,说不出什么高深的话,你们也不必记了。
谢先生在这边的小学教了几年书?我问。
三年,老人伸出三根手指说,我现在明白他当年为什么会留在这里教几个童子,那是因为他还留恋自己曾经住过的家。
他有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
一片纸都没。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喉头滚动了一下,像是有点哽咽,接着又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说,我们家族里出过一位教授,是我晚辈,早年间也在这边的小学念过书,做学堂息那阵子也不晓得从哪里捡到了一方石砚,偷偷藏着。他喜欢写墨字,上山下乡也一直带着它。后来他居然成了书法家,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当教授。有一年,教授回老家过年,带回那方石砚,我说这石砚眼熟得很,教授就问我是否晓得观堂这个号,我说观堂就是谢味温先生的号呀。他一拍大腿,说,我这石砚原来就是谢先生用过的。他把石砚翻转过来,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两个篆字:观堂。教授见多识广,我对他说,我家也有个旧物,不晓得值不值钱。我带他去看那个搁置在镬灶间的大铁镬。他看了许久,就说,大铁镬内壁刻有铭文,可以断定是宋代铸造的大镬。我的娘哎,那时我就想,这可是不寻常的文物。没多久,文物馆的人果然就来了,说是要拉到文物馆去。我跟大铁镬相伴几十年,也有了感情。送走它之前,我就像第一回见到它时一样,给它细细擦洗了一遍。
听到这里,我的脑子就浮现出一个乌黑发亮的大铁镬来:它在一个阴暗的屋角安放着,如同一块沉默的石头。
老人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后来,福田寺募缘重建,文物馆的人又把大铁镬送了过去,在一座亭子里摆放着。一位馆里面的老先生跟我说,你以为这大铁镬真是和尚用来做饭炒菜的?它可是大有来头。福田寺是坐西北向东南,对面有一座山,叫火焰山,从风水格局来看,是有冲煞的,因此,建庙之初,就铸了这口大铁镬作为厌胜的宝物。破四旧那阵子,大铁镬移走了,这座千年古刹居然就莫名其妙地毁于一场大火,有人说是一个疯头陀烧掉的,有人说是天火烧。总之,它是毁掉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想,我的罪过大了。可是,它移走了之后,我就接连碰到了倒霉事。我瞎掉了一双眼睛,后来又折断了一条腿。摊上这样的事,想来也是罪有应得。不过,眼睛瞎了,心里却亮堂了许多。
没了大铁镬,你怎么烧开水?
打那以后,我就不再卖开水了。我这日子过得也算安耽。再说,不久以后,乡里装了自来水,有了电茶壶,也没人愿意到我这里买水了。有一年,我手头闲着,打算在巷弄口的路廊里摆长茶,摆了几天,也不见人来喝,那年头乡里人都忙着办厂,谁还有闲工夫喝茶?不过,我每天还是用福田寺的井水给自己烧一壶。
你家门口堆积着那么多柴火,怕是二三十年也烧不完。
都是早些年从山上或解板厂捡来的废弃木头。
是桉树的木头?
对,我家附近的桉树早被人砍伐得一干二净,那一片地方建起了水泥房工厂。河流呢?这里的人对它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从前沿岸种满的桉树,让河水变了味,现在工厂里的污水排放到河里头,散发着一股更浓的臭味。可它毕竟是一条河呀。
老人这样说着,打开窗子。从窗口望出去,就是一条河。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是做出“看”的样子。
我已经看不见这条河了,只能听见河水流淌的声音,他说,我睡下的时候,河水在流淌,我醒来的时候,河水还在流呀流的。河比人活得长。在我出生之前,这条河就已经在这里了,在我死后,这条河还会在这里,还会日夜流呀流的。
老人说话的时候,我似乎还能听到一条河流在静静地流淌。那是从前的河流。
我们出来时,门外的雨已融入暮色,看起来只是一团饱含水汽的烟雾。远山浮在高低错落的楼房之上,仿佛随时都会飘走。我们出了巷口,站在一家小卖店的屋檐下,等待着一辆出租车。老洪转头对我说,如果你把老人家今天讲的故事记下来,稍稍整理一下,就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出租车迟迟没到。老洪在抽烟,老麻在抽烟,老林在抽烟。我在烟雨迷蒙里还是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车在雨雾中缓缓驶来。我坐在车里,望着前头黏糊糊的流动的车灯,感觉自己正从某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一点点抽离出来。
过了很长一阵子,我以为,老人和他讲的那些故事早已被我淡忘了,但今天,却莫名其妙地从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是我在雨天听来的,今天恰好也落雨,于是就想跟身边的人说点什么了。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著有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另有结集作品《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面孔》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
来源:《芙蓉》
作者:东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