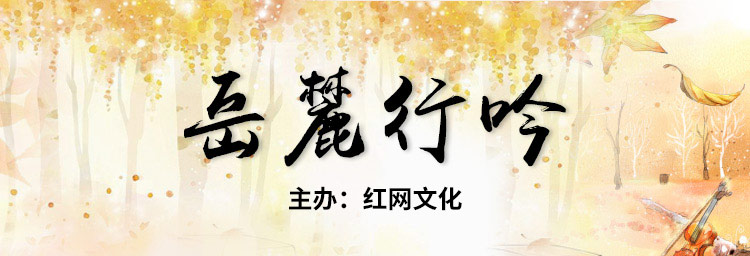

浯溪之溪
文/李旭
多数人去浯溪碑林,都是被“摩崖三绝”的光环吸住的,却忘了浯溪的溪是什么样子。
浯溪成了浯溪碑林的代名词,浯溪的溪呢?倒成了次要的了。它似乎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视了它的存在。从它的地理位置而言,浯溪的溪是划分浯溪碑林的最西边的界线,在导游的引导下,它在宝篆亭就错开了游客的视线,游客的眼球一刻都没有离开琳琅满目的碑刻,并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摩崖三绝”,谁还有闲心去关心一条小溪呢。而其实,浯溪的溪就在游客途经的左手边,偏偏碑林石刻全部在游客视线的右手边,所以没有谁去理会因它命名浯溪的溪了。或许还因为浯溪的溪位置太隐蔽,就算一眼望去,在高高低低的石头间,也难以发现它的踪影。看来,浯溪的溪只是流在概念中的一条溪了,除了象征性的意义,其本身似乎失去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浯溪的溪指的是湘江流经浯溪的这段河流呢。所以,跟其他的游客一样,每一次来浯溪都没有刻意来寻找这条溪。就在昨天,在陪同湘西师友的采风活动中,我是见到了这条活生生的溪了。正如一句哲理诗所说的:忽略了脚下,就失去了远方。它默默地退隐到历史的幕后,让浯溪碑林走向辉煌的前台。那么,是浯溪成就了浯溪碑林,还是浯溪碑林成就了浯溪呢?又或是它的前世今生遭遇了什么变故而落寞,这个似乎从元结命名浯溪开始就没有固定答案,但可寻得蛛丝马迹来重新定义它的意义和来龙去脉。
唐广德元年(763年),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舟过祁阳。他是逆水而上的,应该先看到摩崖,而后看见那条从西侧流下来的无名小溪。对那条无名小溪,他说:“溪,世无名称者焉,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因太酷爱这里,次山率先“抢注”商标,并独创三吾字。他将溪命名“浯溪”,在“浯溪”入河口的山峰上建庼,命名“吾(广吾)庼”,将最高石峰命名“峿台”,史上合称“三吾”,并各撰铭文,请人刻于石上,这便是浯溪碑林最早的石刻,也是浯溪之名的由来。有了名字,浯溪名正言顺纳入元结的“私人版图”。历来文人都有一点小私心,尤其是有了名气的文人,见了心仪的好东西,便想冠名,据为己有,元结也不例外。
那时,祁阳县治在今天的茅竹镇的老山湾村,现浯溪对河的祁阳市区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安史之乱”时元结曾率部痛击史思明,为朝廷立过赫赫战功。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所以,战后他为家眷寻得一处安身之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浯溪到道州沿途湘江边有三处摩崖,次山选择浯溪作为定居是经过慎重考虑过的,“为自爱之故”可能是他自我解嘲的一种文人说法。元结领兵打仗,懂得宜居之地首先应具有战略意义,“安史之乱”刚刚过去,谁会保证不会卷土重来?保护一家人的安全才是当务之急。浯溪,首先是它远离市嚣,却又不脱离城市圈,与县城保持一段合理的距离。老山湾到浯溪的路程约为八公里,陆路与水路相差无几。在浯溪和老山湾之间,浯溪具有可退可守的资本。浯溪摩崖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湘江在它上游水流平缓,过浯溪拐角处,水流突然变深变陡,暗流湍急,波浪拍岸有声。如有敌船逆水进犯,航速自然变慢,这有利于家人争取时间撤离到县城。再说,当时湘南地区还属“南蛮之地”。元结当时任命道州刺史,他深知道州素来民风彪悍。现又经战乱,匪患横行,加之地方官匪勾结,横征暴敛,此去定会得罪一些人,一家人居道州城,必然危险重重。他倒还不如先在此安顿好家人,只身前往,如遇仇家从道州方向追杀过来,不管对方走陆路还是水路,一家人可乘船借陡水落差迅速脱离险境。
如果治理有功,国泰民安,元结是打算在浯溪长居下去的。作为文人,他难得寻到如此的清宁之所。元结在此之前的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他便以老母多病,上表辞官。经安史战乱,元结身心疲惫,本来就有纵情山水田园,悠然了此余生之意。没想到,代宗诏许,特授元结著作郎之职(写史闲职)。元结遂迁居武昌樊口,以魏晋风度为范,放情山水,耕钓自娱,悉心著书。我想,元结为过上“两晋遗风”的生活定然下过一番功夫的。比如建一些与此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如栽竹、筑亭、引溪等。岂料第二年(763年),代宗一纸诏书,元结只得举家南移,朝道州赴任而来,他的人生规划一下子全部打乱了。任命途中突遇如此景致,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么?此处茂林修竹,奇石嶙峋,尤其是这一涧溪水,一切都是现成的。得闲时,约三五好友,席地而坐,听流水潺潺,对酒邀月,抚琴唱诗,人生岂不快哉!浯溪似乎专为元结而准备的一样,元结没有理由不停下来。史载,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确实做出许多贡献,把道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元结一家人在浯溪安安全全居住,时间达七年之久,如果不是另有任用,估计他会在此开枝散叶,终老一生。
这或许是浯溪原有规划的样子。其实在此之后,就连元结都没有想到的事,他自己命名浯溪的小溪,人们竟不知道浯溪的溪在哪里,反倒被“摩崖三绝”占了大部名头。按现在浯溪两旁的地理位置和场地范围推断,来一场“曲水流觞”的文娱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在浯溪的溪水旁边塑有一尊元结和颜真卿的合塑像,或许就是旨在印证当时元结他们确实在溪边过着魏晋遗风的文人生活。
见到这条溪的时候,时值八月初,太阳正火辣,午后更甚。好在浯溪景区高大的树冠层层叠叠,挡去了直射的紫外线。嘶哑的蝉声里,浯溪的溪静静地卧在石头间,现在的这个季节,它只剩下了细细地一股涓流,曲曲折折的隐行在低暗处,很明显,它是多么想带给游人一丝清凉。从它光滑露底的石头上反翘的干苔藓可以看出,它多数的时间是一路欢歌而来的。溪里没有一点泥,高低错落的石头就像一排排的琴键,给它一些流量,一定是叮叮咚咚地,非常的悦耳动听。要不,它如何打动元结呢。难怪古有佚名诗云:“百尺摩崖天凿成,一弯流水玉飞声”。一直来,浯溪的溪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浯溪漱玉”,并列为“浯溪八景”之首。可见,浯溪的溪由来是流动在浯溪文脉里的。到明代正德年间,永州知府曹来旬有诗赞浯溪:“水抱青山路,源通沧海渠,龙宫开玉闸,泄出碎琼琚。”他们不约而合地把浯溪的流水响声比作玉粹,声音清脆回旋,余音不绝。其实,今天的浯溪并没有失去原来的音韵节奏,只是我自己错过了最好的季节而已。不过,让我第一次认识这条小溪,我的视野突然被收缩了回来。一千多年来,它承载了除元结之外的所有感动。
永州大地有三条文化溪流。《徐霞客游记·卷二下·西南游日记二》描述:“浯溪为元次山所居,愚溪为柳子厚所谪,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就年代,浯溪最早发现,元结死后第二年柳宗元才出生,周敦颐则更晚,元结后差不多三百年才呱呱坠地。三条小溪,浯溪流程却是最短,据《旧浯溪志》记,“浯溪水自三泉岭发源,五里与湘水合”。它源流虽不长,流量也颇未丰盈,但从不断流,有模有样,也不易被汅染,供一家人取用绰绰有余。要不,他怎么会把一家子人安置在浯溪岸边呢。又据《祁阳县志》载:“三泉岭下一石洞内,泉水四季长流,距城十里,清时设为铺,故名长流铺”。原来在浯溪源头有一村庄叫长流,清代时期就有人居住。长流村有两口水井从不干涸,它是村民的生命之泉,到处湿漉漉的,难怪取名长流。这也更好地说明浯溪的溪,为什么在这个时节听不见如碎玉般的淙淙水声了。因为文化总是建立在人类生存之上的。这才至使浯溪在枯水期只剩一脉细流融入湘江了。而在此之前,浯溪应该是掷地有声的一泓清流,这些,当年的元结一定是认真考察过浯溪的源头的。没有这条小溪的甘霖滋润,《大唐中兴颂》可能也不会刻在浯溪摩崖之上了。所有的历史文化不光是巧合,更多的是有它存在的根源和理由。再说,这也是浯溪一千多年来碑刻文化传承有序的包容。元结应该早就想到,只要源头水长流,摩崖的錾刻声就会不断。一边是似击玉的流水声,一边是錾刀弹跳石头的“噌噌”之声,它们遥相呼应,不经意间,一千年过去了。再溯源浯溪,已经不是长流村的两口井的故事,它应是润泽着浯溪碑林,养育着千年不腐的元结时代。只要一息尚存,任何思想文化都会连绵不绝。
在浯溪的入河口有一尊滚圆的石头盘踞在那里,像是从“吾(广吾)庼”上面掉下来的,又像是飞来之石。它看上去与周围的石头非常地不相融洽,似乎随时要与之决裂一般。据说这是元结垂钓的地方,有元次山《欸乃曲》一首为证:“零陵郡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溪口石颠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此石后人称作“钓台石”,与摩崖下的“窊尊夜月 ”双双临水而伫,如一对金甲卫士守卫着浯溪碑林的一石一木。每逢雨季,浯溪丰水,滔滔浪花蜂拥而下。遇“钓台石”速变两条咆哮的巨龙,与怒吼的江水迎面相撞,顿时二水互殴,不容旁人正视,形成一道壮丽的惊涛骇浪般的江景奇观。而“钓台石”却是任其蹂躏,丝毫不动,仿佛被元结震蹑住了的“定海神针”;又如当年右金吾兵曹参军泰然自若地立于军帐,指挥着千军万马与叛军痛敌厮杀一样的“壮怀激烈”。这一尊石头像极了元结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守住文脉的传承,还要护得住国家的安危,如元结的好友颜真卿、南宋的辛弃疾等,他们是真有中国文人的风骨气节的,并历来为文人津津乐道。
浯溪溪口上行百十米处有一座单孔石拱桥。桥四周树藤葱郁,蔽日遮天,为初宋时所建,名曰渡香桥。一听名字脑海里不免浮现一串串好看的画面来,桥是不会生香的,许是踱过桥的绣鞋或是罗裙水袖夹带的花香吧。据说渡香桥的那一头当时便是芳草萋萋,蛱蝶忘返的好去处,于是,游客纷纷寻香而来,脚下踏香而去,此桥记住了游客来来往往的芳香,便成了渡香桥了。南宋宁宗年间,永州通判臧辛伯游过浯溪后,写了一首《浯溪》,诗曰:四山凝碧一江横,读书唐碑万感生。却想老仙明月夜,度香桥下听溪声。”当时,臧先生读完唐碑天色已晚,误了渡香桥“两岸细蕊浓花”的惬意,只好期待某个明月夜再来闻香听溪了。先生后来到底来没来不要紧,但游人足履渡芳菲,折瓣随溪水流香,这种融融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只剩下文字的体验和发挥。这种美好,不料被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捕捉到了灵感。他在《东风》诗里说“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最忆故园秋色里,满山红叶艳惊霜。”原来陶铸回忆故乡的一半情感源泉竟然来自浯溪水香。这浯溪的水亦香,不正是渡香桥落下去的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推论到人的情感都是一样的缘来缘去的轮回。这浯溪的溪就这样由古到今巧合地流动着,就连渡香桥的香都不知渡了多少人。如今,渡香桥那边的香花野草已不复存在,渡香桥也由木桥换成了石拱桥,但可以想象当年木头搭建的渡香桥该是如何的一番繁华景象。如此,我还有什么理由忘了这条小溪呢。
浯溪是祁阳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祁阳本地人,总觉得心里有愧。如果不是湘西的那位师友无意中问到“浯溪的溪”,我是真的不知道浯溪的溪在哪里。当时,走到溪边,面对他们递增的问题,我竟然一无所知,表情尴尬。好在吴主席前来解围,才使我不至于无地自容。浯溪的溪,来与不来,它都这样流着。你说它有形,它就有形;你说它无形,它就无形。在有形或无形之间,它的每一滴水珠都是饱含深情的。此时,它的那一股细流,我已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悄无声息地渗进我的血液了。
跳出浯溪的溪,放眼天下文脉赓续,浯溪不过是一根细小的毛细血管,但它同样是一根精神文化脉络。是它让“大唐中兴颂”屹立千年,让五百多块石刻碑林从来没有寂寞过;是它让历史的脚步在这里拐了一道弯,让每一块石头的回音响彻云端。从此,我会记住浯溪的溪的。
来源:红网
作者:李旭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