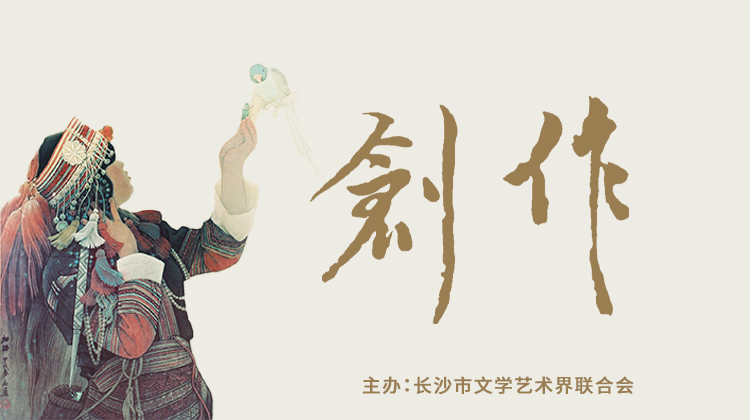

大茅山自然笔记
文/傅菲
毒
他是一个左手食指缺失的人。拎一个黑布袋,拿一根苦竹棍,穿一双沾满泥污的胶底鞋,沿着马溪边,低着头,在寻找什么。布袋深,袋底往下沉,有东西在蜷着身子扭动。我注意到他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豁口,结了一道皱疤。我一眼辨认出他是个捉蛇人。他斜着眼,很警惕地看我,故作镇定。
捉蛇的,你捉了几条蛇?我赤脚站在溪水里,问他。
我不是捉蛇的。捉蛇人说。他抬起了脸,露出右脸一道斜刀疤。
那我翻你袋子。我说。
捉蛇人嘴唇外翻,嗫嚅着,捉了一条蛇。
我上了沙滩,说:给我看看。
捉蛇人拉开束袋的麻绳,抖给我看。蛇头呈三角形,鼻眼之间有颊窝,有凸起的吻端,背部棕灰色,头侧土黄,斑块棕褐色。蛇翘着头,吐着信子,蜷曲着。我说:这是五步蛇,足足有两斤多重。
这么粗的五步蛇,很少见了。捉蛇人说。
你长年捉蛇吗?我问。
有空闲了就捉。捉蛇人说。他说话带有乐平名口镇口音,有些难懂。
你一年捉多少蛇呢?我问。
也捉不了多,600来条。捉蛇人说。
这里是国家森林公园,不可以捉蛇,你应该给蛇放生。我说。
可以卖800多块钱呢。我哪舍得放生。
捉蛇人说。
你捕蛇属于违法,会被刑拘。保护区的人在路上巡查,你跑不了。我说。
我穿上鞋子,去了公路边的灌丛,和他一起去放生。他抖开袋口,蛇爬了出来,嗦嗦嗦,溜进了灌丛。我说:你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蛇。
出来了一趟,我不能空手回去。捉蛇人埋怨我,低声说。
我跟他说了好一会儿话,想让他教我认蛇路。他不搭理我,骑上摩托车,拐过弯道,下山去了。他去别处捉蛇了。
蛇有蛇路,兔有兔路。每种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都会在路上留下自己的踪迹。踪迹是独有的。哺乳动物还会留下粪便。猎人根据路迹和粪便寻找猎物。
我认识一个捉蛇人,叫驼五,捉蛇非常厉害。驼五是个驼子,背部像倒扣着筲箕,在家中排行老五,捉了20多年的蛇。他认识各色各样的蛇:五步蛇、青竹蛇、犁头扑(眼镜蛇)、绞花林蛇、金钱白花蛇(银环蛇)、大扁头风(眼镜王蛇)、赤链蛇、乌华游蛇、乌梢蛇等等。不同的蛇,蛇路也不一样。他是个护林员,日日进山。我跟他去护林,他在溪涧边走着走着,突然伸出手示意我停下脚步,不要出声。他用一根竹梢,撩开草丛,蹲下去,捉起一条蛇。我说,你怎么知道草丛里有蛇呢?
驼五嘿嘿地笑,露出一口烟牙,说:蛇游过去,草丛往两边倒,草叶不倒草根倒,不是蛇是什么。
他知道什么蛇在什么样的地方出没。他经常被蛇咬。他伸出手给我看,手背斑斑点点都是蛇伤留下的白疤。他懂蛇药,就地取材,给自己医治。但他从不给别人治蛇伤。
他说,蛇毒致命,治不好出人命。他还知道阴山出什么蛇,阳山出什么蛇,不同季节,蛇出没的时间也不同。他说得神乎其神,玄乎其玄。但我信他的说法。因为没有他找不到的蛇,没有他捉不了的蛇。
他用大木箱养蛇,分类养。
一次,有一条五步蛇跑出了木箱,他寻迹,来到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对户主说:蛇到你家了。
户主吓青了脸,说:这个玩笑可不能乱开,会吓死人的。
驼五说:哪敢开这个玩笑?他兀自往后屋的杂货间去,找到一个圆肚瓮,往里看,对户主说:你看看,蛇在糠堆等鼠呢。
圆肚瓮装了半瓮糠,蛇盘在糠面上,翘着头。驼五用竹杈叉住蛇头,捉了上来。户主说:你怎么知道蛇爬进瓮里了?
蛇有腥膻,蛇爬过的地方会留下腥膻,三天不散。驼五说。
驼五不卖蛇。他长期观察蛇。夏天,他把乌梢蛇缠在腰上,当腰带;把蛇盘在头上,当遮阳帽。
从马溪下来,在双溪村,我又遇见了那个带乐平名口镇口音的捉蛇人。他抖抖布袋给我看,说:捉了一条五步蛇、一条犁头扑。他的布袋有腥膻味,浓烈的腥膻味。我问他:蛇怎么这样容易找呢?
捉蛇人仰起头看看天,说:暴雨快要来了,蛇兴奋。
我也看天。乌云盖住了半边天,厚厚的。坏天气远远多于好天气。低气压罩住了大茅山山脉,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烦闷、焦躁。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却异常兴奋、活跃。“呱呱呱”,淡肩角蟾叫声汹涌。蛙声鼓噪。我问捉蛇人:你手指怎么缺了一个?
五步蛇咬的,伤口处理不及时,肉腐烂、坏死,把手指截了。捉蛇人说。
大茅山山脉是不是有很多五步蛇?
我问。
算多吧,每次来,都不会空手。捉蛇人说。
你卖蛇,赚了很多钱吧。我说。
我不卖蛇,卖蛇酒。卖蛇酒更赚钱。捉蛇人说。
蛇越毒,蛇酒越值钱。我捉五步蛇、犁头扑、青竹蛇,其他蛇不捉。蛇不值钱,蛇毒值钱。捉蛇人说。捉蛇人束了袋口,挂在摩托车上,突突突,消失在林边公路。竹林在山体蔓延,云团垂了下来。鱼在湖面翻跳。
在野外,我没有见过犁头扑,五步蛇倒是常见。五步蛇盘在地上,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堆枯枫叶。五步蛇喜欢在溪边,捉蛙、鼠、小鸟、蜥蜴吃。有一年,我去灵山北麓,口渴难忍,伏在石壁上喝山泉。喝了水,我抬眼一看,石壁旁边的一块崖石上,盘着一条五步蛇,吓得我魂飞魄散,夺路而逃。
五步蛇即尖吻蝮,是剧毒蛇,被它所伤,人走五步即倒,故称五步倒。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毒之剧烈,却绝非耸人听闻。有山民在拔秧,秧扎好,抛在田埂上,用簸箕挑走。山民捡秧,被蓟尖一样的东西扎了一下虎口,刺痛一下,他也没在意。挑着秧,走出田埂,虎口肿胀起来,火辣辣地痛。山民查看虎口,是两个并列的针口,溢出血丝。他知道自己被五步蛇咬伤了,坐在田埂上呼叫来人。人来了,他的手臂红肿起来。来人把他搀扶到溪边,清洗虎口,嚼烂浮萍、半枝莲、野芋叶、三白草,敷在伤口上,包扎起来,背回家请蛇医救治。
作为山民,最易被蛇所伤的地方,不是在农田或菜地,而是在晚上去看村戏或电影的路上。村散在各个山坳,看一场戏得走山梁或山腰小路,蛇盘在路上歇凉,像一堆烂草绳。月光灰扑扑,人凭感觉走路,一脚踏在蛇堆,反被蛇咬。2021年8月,我去仙山岭采访一位老蛇医,当年他新婚的妻子就是这样被五步蛇所伤的。蛇毒发作,他妻子腿部肿得像冬瓜,火烧一样痛。
老蛇医姓占,七十多岁,有些耳背,眉毛白白长长,说话很温和。他给我讲了很多山民被蛇所伤和他治蛇伤的事。他不懂医理,只知道怎么治蛇伤。他的医术是三代传承的,没有他治不好的蛇伤,且不留任何后遗症。他用草药治。他自己上山采药、捣药、敷药,还负责病人食宿。他看了伤口,就知道是被什么蛇所伤、什么时间所伤。我和他夜谈一个晚上,他反复对我说:治蛇伤没什么神秘的,就是驱火、镇痛、祛毒,以最快的速度抢救,收好伤口。
在仙山岭,我意外地遇见了另一位张姓蛇医,六十多岁。他说,治蛇伤不太难,难的是识遍山上的百草,不识草就采不了药。
张蛇医健壮,年轻时在山上伐木,常被蛇所伤,都是自己治。他说,及时、科学地处理伤口是至关重要的,就近采药,满山草木都是蛇药。
不用望、闻、问、切,怎么下得了药呢?我问占蛇医。
占蛇医说,凭伤口就可以。我不得其解。他儿子告诉我:蛇医是草医的一种,中医需要望、闻、问、切,找出病根,去药铺抓药,而草医无药可抓,临时去野外采药,因草制方,方子十分灵活,药性厉害,去病也快。
我上网搜索,关于草医的解释是这样的:
草医属于中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没有严密的科学体系,无法给草医作出严格的定义。大体上,草医是这样一种医学方式:使用草药(自然界的植物),以及接近于对抗医学的原理,对症下药。
草医出现在2000多年前,医学方式为使用草药对症下药。
蛇毒有血循毒、神经毒和混合毒。五步蛇是血循毒,眼镜蛇是混合毒。从仙山岭回来,我查阅了很多有关治蛇伤的资料。我才知道,蛇毒是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溶血毒素。论蛇医医术,我最信服在湖南莽山自然保护区工作的九指蛇医陈远辉,他以身试毒、以身试药、以命配药,研究毒蛇数十年,并命名了毒蛇“莽山烙铁头”。他说,蛇毒就是毒素蛋白,把蛋白破坏了,蛇毒就没了。被毒蛇咬伤时,迅速以烟头(或小火)灼烧伤口,让蛇毒蛋白变质,是解毒最有效的方法。莽山烙铁头被誉为世界上最毒的蛇之一,陈蛇医被其咬伤数次,一次次命悬一线,一次次写下遗书,又一次次生还,继续配制和完善蛇药,造福众生。
五步蛇牙长,排毒量大,人被咬伤后,伤口剧烈疼痛,火烧感蔓延,蔓延之处肿胀;时隔2小时,起水泡、血泡,甚至流血,伤口大面积蔓延;时隔6小时,出现畏寒、发热、心慌、头昏眼花等症状;时隔12小时,淋巴结肿大,呼吸困难,甚至休克;时隔24小时,难以医治。这还是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运动(走路回家、走路或骑自行车去就医),很可能在1个小时内死亡。这是占蛇医告诉我的。占蛇医说,假如是虎口、脉门、脚后跟三处中的任何一处被毒蛇咬伤,会加快毒性进入五脏,危及生命。
祛毒不尽,伤口会留下严重后遗症。伤口始终不愈合,常年流脓液,甚至局部肌肉坏死,不得不截肢。
人不侵害蛇时,蛇不会咬人。蛇怕人。
任何野生动物都怕人,对人抱有深切的戒心。即便是与人亲近的动物,如麻雀、松鼠等,也不例外。我对爬行动物深怀恐惧,从没抚摸或捕捉过。蜥蜴是最常见的爬行动物,夏秋季节,活跃于溪涧边。我也不敢捉。它黄黄绿绿的皮鳞让我觉得怪异。我恐惧,是因为爬行动物冷冰冰的。
其实大部分人对蛇怀有恐惧,由恐惧而生敬畏。在灵山北部与大茅山南部的乡村,这种敬畏已经演化为民俗。蛇进了农家,是不可以打的,需以拜香作揖驱赶。他们认为蛇是已故旧友或已故亲人的捎信人。蛇捎来了口信,得敬着送走。
人以道德,给动物分良善与邪恶。鹿是善的,牛马是善的,兔是善的;蛇是恶的,虎狼是恶的,鹰是恶的。温驯的动物大多是草食动物,凶残的动物大多是肉食动物。其实动物无善恶之分,食草食肉,皆为生存。
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保存物种基因。
部分昆虫、两栖类动物、爬行类动物、海洋生物进化出了毒腺,分泌毒素,以自卫、猎杀。毒是它们的秘密武器,给对手以致命一击,使其绝无反抗之力。
人为了提取毒素,猎杀它们——用毒素解毒、祛风湿。毒素的药性是化学药品无法替代的。毒素堪称完美药品,人工无法合成。毒蛇、胡蜂、壁虎、毒蚂蚁、毒蝎子被用来泡酒,供人享用、治慢性病。
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成了自然中心主义者。人主宰了万物的生命。这是自然的不幸,却符合人性——人的占有欲。占有欲是一种毒。人类需要构建自然道德。何谓自然道德?它区别于社会道德。它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种关系。人的行动、行为须服从于自然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个体,尊重并维护自然界的天然美学,不杀戮、不豢养、不掠夺、不破坏、不污染。
被人钉在木板上剥皮取胆,被烹煮或煎炸而食,被塞入酒缸,封缸泡死,毒蛇何罪?
圆篓记
“圆匾圆篓圆腰篓,米筛豆筛宽边筛。”
我在有兰早餐馆吃馄饨,听到有人吆喝。一个七十来岁的大叔,挑着竹器来到村子,从村口走来,边走边吆喝。我站起来,招招手,说:看看竹器。
我取了圆匾,对着阳光照照,摸摸匾边,放了回去,又取下圆篓,倒下篓底,细细地查看。篓底是青篾板,扎得厚实,篓角煻得黑黄,整篓用青黄的篾丝编造,篓口箍得很紧。我说:你家竹器地道,还用砂布磨了篾丝尖,摸起来就舒服。
大叔身材矮小敦实,脸宽,额头有一层层叠起来的皱纹。他鼻大,头发硬短而浓密,笑起来,眯着眼,露出一口白牙。大叔说:一把老篾刀编造不出好竹器,对不起大茅山的老毛竹。
有兰,再下一碗馄饨,加一个鸡蛋,给这个老师傅吃。我说。
我吃过了,吃过了出门的。大叔说。
你还要挑竹器卖呢。我请。我说。
哪好意思呢。大叔说。
他吃馄饨,我选竹器。我有一座阁楼,墙上挂了许多竹器,有二十多种圆匾、篮子、筛子、篓子。翠竹的青黄之色,篾丝造物的弧形之状,竹片的火煻之气,都令我爱不释手。我选了一个敞口的圆篓,对大叔说:这个圆篓,多少钱?
四十五。你买的话,算四十吧。大叔说。
价钱不能降。价钱是物钱。我说。
大叔挑着竹器往村巷走去,吆喝着。我抱着圆篓回去了。圆篓四方底,篓腰收圆,往上慢慢收缩,篓脖子往上敞开,形成一个圆敞口。它可作鱼篓,可作腰篓,可作茶篓,可作菜篓。我无茶可采,无菜可摘,便一直挂在阳台上。
一日,花桥的同学来看我,带了一袋冬笋来,说:你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也不去花桥走动,不走动走动,人就生疏了。
我说,明年开春就去,去爬大茅山。
我们东拉西扯,说了一个下午。我送他下楼,他走前面,我走后面,看到他脑后的头发都白了。我说,一转眼,我们有三十二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喜欢吃冬笋。
他送来的冬笋还裹着黄泥,笋壳很是新鲜,有二十个,一个约八两重。冬笋沙埋才保鲜,否则笋壳长菌毛,笋肉霉变发黑。这么多冬笋,一个月也吃不完。我拣了笋壳没有破的冬笋,塞在圆篓,编织绳绑着篓底,束紧篓脖子,吊在阳台的挂钩上。想吃了,取一个下来。吃过了元宵,冬笋也没坏一个。
大茅山北麓盛产翠竹、毛竹。竹多,造竹器的手艺人也多,在冬春农闲时节,常见挑竹器的乡人走村串户,摇着响铃吆喝:筛子篓子篮子,烘笼笸箩筲箕。
也有卖竹凳子、竹躺椅、竹摇椅的。夏日,在枣树下摆一张竹躺椅,午睡一会儿,神清气爽。我买来竹躺椅,倚墙靠着,第二年夏天搬出来纳凉。搬它,落下一地的齑粉——被虫蛀空了。春夏,竹躺椅暴晒数次,便不会被虫蛀。我忘了。
竹丝竹篾编造的器物,不会被虫蛀,陈放日久纤维会硬化。我常把圆篓作鱼篓,插上鱼竿,抱去河边钓鱼。长久泡水,竹纤维会软化,越用越好用。圆篓浸在河里,钓了鱼,扔进篓里,盖上一把竹节草,鱼在草下窸窸窣窣。夕阳下山,从水里提出圆篓,水哗哗哗四泄。水滴跟着我走。
过了霜降,乡人开始挖芋头。芋头田松软,土层干燥,挖起来并不吃力,锄头挖下去,翻上来,子芋挂在母芋上,一捧捧。开杂货店的曹师傅对我说:你跟我去挖芋头,捡几个大的子芋留着吃。
他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挑拣。圆子芋,芽头嫩红,毛糙。这是最好的红芽芋。捡了半篓多,我背了回来。芋头沉实,篓口的篾板被绳子拉脱了,篾丝翘了出来,芋头散了一地。
圆篓无法挂了,也无法背了。
每天晚上,卫生间呜呜叫,听起来,像大电风扇在转动。其实是风灌进了天窗。天窗没有玻璃,风震动了天花板,发出呼呼的叫声。我不胜其烦。我请师傅来安装玻璃,他见破圆篓搁在书架下,说:圆篓脱箍了,还留着干什么,当个废纸篓还差不多。我去给你找一个新圆篓,看起来也有个样子。
我说,圆篓用得少,只是喜欢竹器,不在意新旧。
竹器再旧,我也舍不得扔,即使破了,请师傅加几条篾丝编编就可以。我有一个圆篮,从井冈山买来的,用了十余年,加了三次篾丝修补,还在用。器物,有自己的脾性,也有自己的记性,还留有使用者的痕迹。
芋头吃完了,春天甩着闪电的鞭子,赶着雨水的马车,顺着叶脉,停在树梢上。在溪岸,垂珠披散着满树的花。一日,我去双河口,见一个蜂农在刮蜜。蜂箱挂在岩石崖下,他登上木楼梯,掀开棕衣包裹的箱盖,提着蜂框,刮蜜。蜜呈琥珀色,浓稠,岩浆一样滴在铁桶上。一箱蜂巢,刮了八斤多蜜。山坞里,他放了八个蜂箱。蜂农说,在蜂框涂蜂蜡,野蜂会自己钻进来,两年就可以刮蜜。
第二天,我抱着圆篓去了雷打坞。那里有一个十余亩大的山塘,塘下有一片乔木、灌木混交林,木荷、枫香、大叶冬青有二十多米高,野山茶、柃木、乌饭树占据了半边山坡。混交林在一个狭长的小山坳,被一片高大的针叶林包围着。我用一件旧圆领衫套住圆篓,外裹一张塑料皮,以电线扎紧,篓内壁抹了一层蜂蜡,倒挂在一棵山矾树的斜枝上。
过半个月,我去一趟雷打坞,站在山矾树下,瞧瞧圆篓,查验一下,是否有蜂飞进去了。每半个月去一趟,去了十来趟,我再也不去了。去一次,我要洗一次澡,洗一次鞋,洗一次衣服。没有一条路进山坳,钻树林进去,衣服、头发、脸上,蒙了很多蜘蛛网,鞋也沾满了叶屑、黄尘。去一趟,去见鬼一样,灰头土脸。
隔了三个月没去,差不多忘了雷打坞还挂着一个圆篓。一个破圆篓,哪值得记挂呢?其实,人就是忘性很大的物种。我们在外生活久了,会忘记了乡音。归来的人,都不是当年的少年。在城市长居,忘记了头顶的月亮,忘记了井边的秋千,忘记了杨柳岸。
那个开杂货店的曹师傅,又叫我去捡芋头,我才想起了挂在树上的圆篓。我去新营找那个卖圆篓的大叔,他家门紧闭。一个穿大花棉袄的邻居说,他在去年底,因病去世了。我很惊讶,说,他好好的、壮壮的,怎么就病逝了呢?
还不是那种病,咳嗽、发烧、头疼。他病了三天,都好了,他去砍毛竹,扛了八根毛竹回来,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他就这样倒下了。他都没喊疼。穿大花棉袄的邻居说。
你见过牛倒吗?她问我。
没见过。看过别人杀牛。我说。
牛倒下去,是怎么拉也拉不起来的。牛瞪大眼睛看着拉它的人拽绳子,犟着不动,犟着犟着,眼睛就闭上了,四肢僵硬。人倒下去,也是这样的。她说。
紧闭的门,是一扇木质小门。门的两边,有两个小窗,像两只空洞的眼睛。他的手指粗壮,编造的竹器却细腻、有质感。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因此他的手格外温柔,从他指尖滑过的篾丝,带有一种恩情。
我问穿大花棉袄的邻居:他还有竹器留下吗?我想买。
人走了,哪还会有物什留下。她说。
雨下了多日,绵密,细润。又阴了两天。太阳出来了,大地蒙了一层厚霜。黄土路上的水洼,结起针状的冰凌。阴湿的土层,倒竖着冰碴,昆虫冻死在里面。桃胶在桃树上凝结,如一颗颗瘿瘤。空山不见鸟。
有人在山冈上伐木,电锯吱吱吱作响,杉树的树冠在剧烈地摇晃。
圆篓还在。没看到一只蜂。我取下了圆篓,带了回来,放在屋顶天台的飘檐下。天台有约三十平方米,栅栏门有一个飘檐。
五年前,我患过十二指肠溃疡,落下了怕冷的病根。霜雪天,冷得身子都缩起来。
这是人的身体走向衰老的信号。以前,我不怕冷也不怕热,不用空调不用电风扇。现在,一入冬,我便早早上床焐被子。中医小廖对我说:你去剥老松树皮,煮水泡脚,通通经脉。
窗外就是千亩松树林。松老了,树皮会皲裂,手掰一下,树皮脱落下来。松树皮掰出巴掌大,塞在圆篓里。晚上,取几片煮水,滗水出来,泡脚。泡了几次,我就不想泡了。太麻烦。好多事情,我都没毅力去完成,半途而废,比如每天走一万步,比如练毛笔字。刻意去完成某一件事,我就觉得别扭,不得劲。
焐着被子,翻翻书或者发傻,太舒服了。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发傻。有时能发傻一个下午。
嘁嘁叽叽,大山雀闹出新绿。柳条一下子垂了下来,丝丝缕缕,柔柔软软。水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南风一吹就皱了,哗啦哗啦地流。花钵移到天台,晒太阳。飘檐下的圆篓,有一对山斑鸠在衔枯叶、棉花、干草营巢。它们从楼侧的山冈飞来,呼噜噜,铺了巢室,又呼噜噜飞走,浅灰的翅膀旋出伞状。
这可是个安家的好地方。松树皮垫实了篓,山斑鸠铺上软软的草叶,便是一个安安稳稳的暖窝。我又把花钵移回室内,关了栅栏门。我不能惊扰那对“小夫妻”。我用一个搪瓷碗,盛了半碗绿豆(去年剩下的两斤),放在栅栏门外,由它们取食。
过了二十六天,小斑鸠破壳了,探出毛茸茸的脑袋,“兮兮兮”地叫着。亲鸟轮流护巢、觅食、喂食。“苦苦苦”,亲鸟叫着,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可亲。看着它们,我们明白,生命的诞生源自爱,而非别的。
为什么是这粒种子(而不是那粒种子)
发芽,为什么是这颗卵(而不是那颗卵)孵化,是有缘由的,绝非无缘无故。山斑鸠有恋巢习性,一年繁殖1~3窝,食物丰富时,可达5~6窝。它们在圆篓多繁殖几窝,该多好。世上事,哪能那么遂愿呢?有了斑鸠巢,我再也不移动圆篓了。它是小斑鸠的摇篮,是爱的家园。假如山斑鸠有记忆,那么圆篓将带给它们终生暖意。圆篓是它们的圣殿。
在院子,在树林,在屋檐下,在窗台边,我设置了五个人工木质鸟巢,期待有鸟在“木屋”安家。两年过去,一只鸟也没招来。有时,我看着柳莺在树林“木屋”顶跳来跳去,嘁嘁鸣叫,但仅仅是跳来跳去。我在窗台撒了米,鸟吃光了米,我又撒米,鸟又吃得光光,鸟吃完米就飞走。这是缘分没到。我便没了痴妄的想法。
三只小斑鸠在天台上跳来跳去,很想飞的样子。我想起了那个挑竹器吆喝的大叔。
佛说,生命有轮回。其实,不仅仅有轮回,还有转化。此生命转化为彼生命。而转化的媒介,叫“渡”。一个(种)生命渡向另一个(种)生命。圆篓就是渡生命的媒介。竹筏也一样,从此岸渡向彼岸。此岸与彼岸,隔了迢迢之河。
渡向彼岸,便是神迹。我愿意做一个目睹神迹的人。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减少了很多苦涩。人是在苦厄中积淀的,需要去解除苦厄。所以,惜已有之物,惜已有之人。
渡向彼岸。四十五岁之后,我才明白其意。把自己渡到彼岸去,在渡中获得安宁,然后去往乌有之乡。那里彩云飞卷。
(原载于2023年第3期《创作》)

傅菲,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元灯长歌》《深山已晚》《我们忧伤的身体》等30部,获三毛散文奖、百花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等,以及多家刊物年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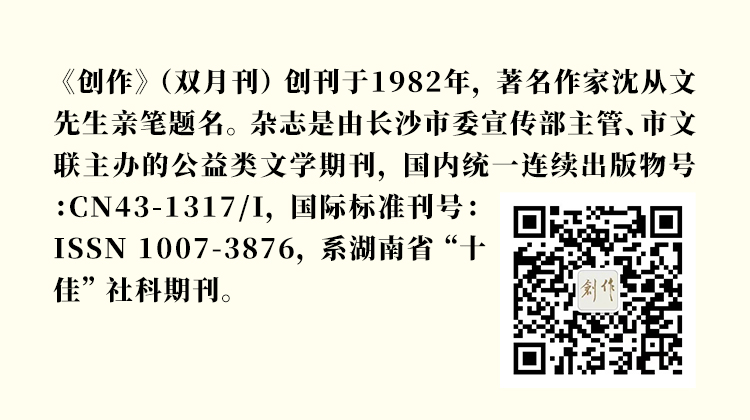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傅菲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