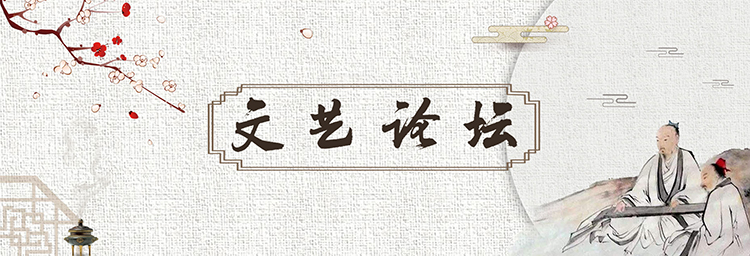

“地方性”与世界文学的形态、演进及审美特性
文/邹建军 卢建飞
摘 要:世界文学的第一属性是“地方性”,地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始基形态。“地方性”是文学实现世界性的逻辑前提,作家的地方情感、经验和价值观念创造出文学的地方品格,为世界文学的演化提供了动力基础。“地方性”又是世界文学形成的基本路径,世界文学通过地方文学的跨国旅行演进而来。地方文学在翻译、传播、接受与形态重构,包括意义增值、价值转化和审美认同激活的整个传播—接受活动过程中,依托于人的“恋地情结”的期待视野,即地方经验的横移、外化和延展构成了地方与世界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地方文学的世界形态。基于此,世界文学的审美模式应是以人—地关系为根基结构的地方性审美,观照文本空间中的地方语言景观、地方形象景观、地方民俗景观和社会生活景观,展现超越时空性的地方族群记忆、精神空间和文化原相的审美特性。通过探究地方性与世界文学的内在关系,为世界文学如何存在、发展、演变以及审美规律提供一个“地方性”的考察视野,这为回答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何为乃至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等基本问题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地方性;世界文学;地方形态;恋地情结;地域审美
自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以来,世界文学成了全球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想象。世界文学以经典性、总体性和全人类性的特征超越了区域文学、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的狭隘视野,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一切具有文学性的文学形态,彰显了其包容性和理想性。然而,歌德虽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却没有给“世界文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世界文学”定义的模糊和含混,使世界文学成为无限开放与可持续探索的公共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多重语境下的历史争论,如文学总体论、经典作品论、共同价值论、研究视角论、阅读传播论等。在韦勒克看来,世界文学是一个世界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等人誉满全球、经久不衰的作品。②泰戈尔则提出世界文学是普遍人性与人类集体价值的艺术呈现,“揭示人类灵魂渴望现实自身的那些亘古不变的艺术形式”③。所以,当世界文学无法获得全球公认的概念来统摄世界文学现象时,其合法性、有效性及可能性会被严重质疑,或导致世界文学潜藏暗流涌动的存在危机。胡塞尔现象学的概念“悬置”似乎给世界文学提供一条可行的出路,即抛弃形而上的本质观念,反观现象本身,分析世界文学运动生成的历史过程,寻求概念规定性的实在性证明,也即考察世界文学的活态现象。具体而言,从鲜活的个体文学考察世界文学形而上概念的抽象性过程,由能指现象推导世界文学的本质、内涵及形式范畴,走向存在论的实践性考察,破解本体论的难题。正如大卫·丹慕厄什所言,为了理解世界文学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艺术作品的本体论,而是现象学。一个文学作品在国外以不同国内的方式展现自己。④因此,返回世界文学的现象及其本源,这涉及世界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在地理学意义上,“地方性(localty),是指在某一自然地带内部由于局部因素作用所形成的小范围地域分异。因为地方性分异属于小尺度分异规律,多数情况下在野外可直接观察,所以它更具有普遍意义”。⑤ 所以,“地方性”是某一地域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的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地方性”常常表现为地方色彩,即散文体小说作品中对具有某个地方特色的背景环境、方言、风俗、服饰以及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细致描写。⑥不过,在“地方与文学”的论域中,“地方性”包含了文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如文学的地方形态、作家的地方情感与地方观、作品的地方审美与地方风格、地方与文学史书写等。因此,通过“地方性”与世界文学形态、演变及其审美的内在关联探讨,可以为世界文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地方性的考察视野,也为世界文学是何及其何为提供思考与参照。
一、地方文学:世界文学的始基形态
在“悬置”世界文学概念的前提下,世界文学的现象或实在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第一问题。作为经验与现象存在的地方文学,是世界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主体形态。波斯奈特认为,世界文学的首要特征即文学从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分离出来——文学的普遍化⑦,强调了世界文学的地方性演变与地方性要素的综合抽象。那么,什么是地方文学?首先理解“地方”的概念。“地方”(place)指的是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地方”是一个弹性的概念,可以指狭义的特定地点,如成都、上海、武汉等,也可以指中性的特定地区,如湖北、湖南,西北、华南等,同时又能指向广义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域。“在这样的意义上推而广之,相对于更加广大的现代世界和全球化的空间背景,中国,以至于东方,其实也只是一个被发明的‘地方’。”⑧由于“地方”概念的伸缩性,我们只能通过参照系确定地方的边界和范围,如以世界版图为参照,“地方”即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因此,与世界文学相对的地方文学概念,更多指向的是以地域文化为边界的文学区域样态,如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或阿拉伯文学、拉美文学等。那么,地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始基形态,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作品形态的世界文学产生于地方文学。一部作品的诞生必然有其归属地,即原生地,如《战争与和平》是俄国的文学、《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文学、《呼啸山庄》是英国的文学、《红楼梦》是中国的文学、《百年孤独》是拉美的文学等。世界文学原生于地方,通过地方文学的传播、翻译和接受,最终才会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文学。所以,没有地方文学就没有所谓的世界文学。要注意的是,地方文学并不直接等于各个国别文学或者民族文学。如勒克莱齐奥是法国与毛里求斯双国籍作家,一生行旅于非洲、南美、西欧、南亚与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创作了《流浪的星星》《沙漠》《奥尼恰》等超越国家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世界文学作品。显然,勒克莱齐奥所创作的作品就不具备传统意义的单一民族性或国家性特征。但是,他的作品又极具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即非洲书写。地方文学不是强调作家或作品的国族或民族归属(民族或国家政权可能因为历史演变而不再存在),而是强调其产生的地域特点,即地方原生性。文学的地方原生性强调了所有的文学都是地方性的,没有超越地方而处在“真空”状态的文学作品,也没有超越地方性而存在的“理念性”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存在必然以地方文学作为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剥离了世界文学中的各种内容要素如国族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最后剩下的必然是“地方”。
第二,文学作品从地方性转化为世界性,存在一个长期的形态演变过程,它们最初以地方文学的形态存在。在过去,由于人类经济、技术以及交通条件有限,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几乎为零。文学被自然山脉、语言文化、宗教差异等诸多因素隔绝,处在一种原始孤立的状态。现在我们称为“世界文学”的文学作品如古巴比伦地区的《古尔伽美什》、印度的《梨俱吠陀》、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在过去是地方性的文学,因为它们只在特定的民族和区域内传播与流行。直至世界各地区人民产生交集,特别是生产生活全球化后,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地方文学才有溢出地域的可能性。从历时的角度看,地方文学从诞生之初,经历了从文学发源地到文学圈再到文学区,最终形成世界文学形态的演变过程。以《一千零一夜》为例,《一千零一夜》的成书过程,是一个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不断吸收、融汇和创新的过程。故事发源于阿拉伯地区,流传于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地区,形成文学圈,再经过西欧、中亚、南亚和北非的作者、译者乃至学者的采录、编辑、转译、传播、重组、写定等,最终在16世纪成为中东文学区的典型代表,最后通过全球性跨国旅行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即世界文学。这就阐释了作为地方的文学如何演变为世界的文学的历史过程。当然,世界文学始终还是依托于地方文学形态,作为民间文学的《一千零一夜》,“有一个朴素简陋向繁复精美的演变过程。每一个重要题材,都有它的原始形态,也都有一个发生的时间和原始的发祥地”⑨。可见,世界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凸显了地方文学的建构性和本源性。
第三,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由“地方文学相互交流,彼此借鉴,构成多元并存的共时形态”⑩。世界文学的共时形态是现时地方文学的活态组合,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点与面、段落与篇章、局部与整体的结构关系。不过,有几个概念需要厘清,即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首先,要区别“地域”与“区域”两个概念。“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而“区域”往往指的是地理学的区域范围,如东北地区、华北地区,有行政规划和地理方位的意义。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地域”强调的是文化的共同性,而“区域”强调方位和行政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反之,其内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不一致,二者之间的融合度并不高,其地域性并不同一,其地理边界又很清晰的文学,就是‘区域文学’”,如“巴蜀文学”属于地域文学,“湖北文学”属于区域文学。地方文学与区域文学、地域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地域指向文化,区域指向地理方位,而地方则兼具二者属性,即地方文学既有地域文化的属性又有地理方位的指向。地方又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存在不同的边界范围,相比地域和区域更具有通约性和涵盖性。如在中国文学地图中,莫言小说的地方指的是山东高密乡,地域则是齐鲁文化区,而区域则是山东文学区。如果将莫言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地方又指的是中国,地域指的是东亚文化区,区域则是东方文学区,即中国—东亚—东方—世界的地理区划递进关系。所以,世界文学的共时形态由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层级结构组成,不过其本源形态仍是融汇区域与地域内涵属性的地方文学。
第四,地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存在形式,强烈的“在地感”使世界文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只有通过地方的特性,地方文学作为现象才可能被归类综合为概念的世界文学。哈代的“维塞克小说”、狄更斯的“雾都”、巴尔扎克的“生活场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勒克莱齐奥的非洲书写……这些著名作家和作品无不烙印着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从阐释学的维度上看,只有对世界文学中“地方性知识”的深入体悟,发掘地方性背后人性的书写,思索地方的思维、情感、价值以及独特的审美与艺术理念等,才能有效解读世界文学内在的价值和时代意义。因而,“地方性”使得世界文学作品具有了深厚与广泛的阐发空间,也使得世界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空和葆有鲜活生命力的深厚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高度肯定地方性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时,地方的膨胀又可能让我们倒退回影响研究的窠臼,即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历史伪律——将西方作为源而世界其他地区作为流,构成了世界文学“冲击/回应”的文学史观念。不过,在波斯奈特看来,世界文学普遍化过程“可以在亚历山大和罗马文学中观察到,随后也可以在希伯来和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学中观察到”。世界文学并非西方的独家起源,多源论为地方文学的平等性与自由性作了有力辩护。然而,地方文学演化成世界文学并非简单的形而上的概念综合,地方文学到世界文学之间仍存在一道鸿沟。为此,丹慕厄什在《世界文学是什么》一书中,从地方文学的流通、翻译和知识再生产角度,详尽考察了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性、跨文化性和变异性,实际上就是对世界文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普遍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但是,丹慕厄什仅仅考虑到地方文学生成之后的世界文学转型路径,而忽略了地方文学如何具体生成与接受及其审美特殊性的问题。由此,必须要回到世界文学的“地方性”生产与接受问题,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地方文学演化成世界文学的原动力及其审美规律。
二、“恋地情结”:世界文学演进的心理机制
世界文学的第一属性是地方性,其原始形态也是地方文学,那么地方文学如何演进为世界文学?地方文学演变为世界文学首先是一个传播学问题,即信息符号的传送。剥除控制论和社会系统论的复杂结构,纯粹的信息传播模式或路径即如拉斯韦尔的5W模式:传者—讯息—媒介—受者—效果。作为信息素的地方文学,传播模式即为生产—出版—传播(翻译)—阅读—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地方文学演变为世界文学的核心要素是生产—传播—接受,即地方性生产、跨域传播(翻译与流传)和异域接受(经典化)。过去,人们主要关注地方文学如何传播的问题,如丹慕厄什详尽考察世界文学的历时传播问题;又如曹顺庆关注翻译的变异问题,“没有翻译的变异,就没有世界文学的形成”;再如胡良桂《国外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书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考察被战争、资本、经济与文化全球性流动裹挟下的世界文学交流史问题。然而,传播研究仅仅关注“过程论”,即世界文学传播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考察方式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地方文学如何演变为世界文学的活动两极——创作与接受。此外,并不是所有地方文学的异域传播都能成为世界文学,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有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可知,传播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作品自身价值及其接受的效果同样是重要的指标。所以,对世界文学演进研究应该要回到创作与接受上,即“发生论”和“结果论”。
回到世界文学的“发生论”,也就是作家创作的基本问题。文学创作是作家主体创造性的结果,但是作家创作受到诸多因素如人生的经验、文化的传统和作家的个性等影响。创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经验尤其是审美经验是作家创作的源泉。“经验”是人通过嗅觉、味觉、触觉、视觉的综合实践方式,对真实世界及其规律的认知与建构。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看来,人类经验的生成、建构、演变与“地方”相关。“地方乃是生物所需价值的中心所在,例如有食物、水、休憩和生产的场所。”地方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空间环境条件,而人向地方投射主体情感和意义,人与地方形成了特殊的情感关系——“恋地情结”,也即人对地方特殊的爱。在文学作品中,“家园”观念的形成与“恋地情结”心理机制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那些远离故土的诗人,“故土”集中展现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和依恋,如余光中的《乡愁》即是对祖国大陆的深切思念。恋地情结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机制,使人对地方产生独特的感觉、知觉和观念,深化为人对地方特殊的感情、知识与价值认同。由此产生地方性的审美经验,为作家为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和精神资源。
在人地关系影响下,人的恋地情结的历史文化积淀,促使作家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地理基因。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作家身上留下的印记是各不相同的,出身平原的作家与出生盆地的作家,其文学视野与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不同地理基因的作家创作出不同形态与风格的文学作品,“是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对人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之创作是通过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就是对作家的影响而实现的”。这种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在人的认知、心理和思维上,以至于在文艺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地域性的文学色彩。所以,黑格尔认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史达尔夫人甚至认为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性留下更多的痕迹。恋地情结中人地的双向互动关系,使得地方文化不再单向地作用于人,人也会主动认同地方乃至建构地方。因此,在恋地情结的特殊心理机制影响下,形塑了作家独特的地理感知、地理思维以及地理想象,并通过地理叙事创造出地方性的文学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池莉的“汉味”小说,西方文学中的雾都伦敦、巴黎圣母院等。这些地方性的作品蕴含着地方独有的时代和历史文化精神,又包含着丰厚的审美价值。地方文学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无限价值才是地方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真正的深层动力。因此,作家只有紧握住地域优势,才能创造一个准确的、亲切的、鲜活丰韵的艺术世界。这也是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内在逻辑。
尽管地方文学独特的精神价值是其走向世界舞台的基础,但是如果地方文学不能实现跨域传播,不能被其他族群接受,那么这些文学作品仍然是“地方性”的。因此,地方文学演化为世界文学的根本标准在于跨域性的族群接受。地方文学的跨国旅行如翻译、传播、接受与形态重构等依托于人的“恋地情结”,即地方经验的横移、外化和延展,构成地方与世界的“视域融合”,实现人们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有两种形式。一是现实需要。五四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学大量的翻译和接受,源自西方文学作品中科学民主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与国民性改造的巨大作用。从“恋地情结”的角度看,这也是人对“地方”环境、思想改造的迫切渴望。胡良桂认为接受“取决于异域文学交流的内容是否与我国特定的时代要求、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结构、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相适应、相契合”,鲁迅模仿果戈里写《狂人日记》,胡适主张“新诗”改革,这都是西方文学思想价值观在中国的影响和再现。由此可知,恋地情结所激发的现实需要是地方文学跨域接受的重要原因,它们能够牵动或引发广泛的社会思潮或集体心灵激荡,最终在异域“落地生根”。二是审美需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审美是一种高级需求,审美的目的在于获得精神的愉悦。在异域读者的接受中,文学作品的异域原始风貌常带来新的审美感受,如《一千零一夜》,描绘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风情与民俗,故事中随处可见沙漠、骆驼、飞毯等富有诗意和想象的民间色彩,满足了各地人民对阿拉伯的异域想象。这种异域情调本身也是恋地情结中地方经验的横移、外化和延展的结果,其本质在于地域性审美的差异,构成了陌生化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异域情调是一种审美态度,是对异己之物的理解和对美的崇拜,其中一个核心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差异性。”与现实需要不同的是,审美需要使世界文学超越时空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如巴尔扎克小说对资产阶级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没有因为在当下多元化的语境中丧失其意义,其原因在于人们超越现实性或政治性的审美鉴赏,认同作品中丰富的审美内涵与价值。所以,“恋地情结”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是地方文学获得世界性认同并且超越现实需要而获得生命力的关键一环。
从接受的前阶段来看,地方文学获得广泛接受的前提条件是作品的翻译。由于人地关系中“恋地情结”的心理影响,作品翻译就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适合地方人阅读习惯和审美需要的意译。朱生豪认为,“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这种译法显然是为了适应地方的审美习惯。张谷若所译《德伯家的苔丝》充满浓厚的山东色彩,将外国小说变成了中国故事。傅雷反对翻译的“中国化”,“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另一种是保持作品“原貌”的直译。鲁迅强调直译甚至是“硬译”,其目的是为了还原作品的本真形态,让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结构,建构跨域性的审美视野。孙致礼认为翻译“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这种翻译原则就是要保持作品原始的地域风貌,还原作品的地方本真性。所以,翻译与接受强调回到作品的地方性,说明了“恋地情结”在世界文学翻译传播的重要意义。
总之,世界文学的翻译、接受、传播与再创造的整个文学活动过程,包括意义增值、价值转化和审美认同的激活,其内在依据是内化于人的“恋地情结”的期待视野。“恋地情结”对地方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影响,构成了地方文学演化为世界文学基本动力。如果没有“恋地情结”,那么就没有认同和接受的基础。所以说,地方主义性质的“恋地情结”不是世界文学接受与演化的绊脚石,而是强化文学自身世界性书写的核心动力。
三、地域审美:世界文学的审美特性
审美特性(aesthetic property)亦称“审美特质”,即事物所具有的能唤起人美感的性质、特征。在文学自身的审美要素中,地域性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最基本的审美要素。在小说中,地域是人物塑造、历史事件、群体情感与价值凝结的空间载体。如果鲁迅笔下没有江南多彩的水乡鲁镇,那么阿Q、祥林嫂和孔乙己就会变成生硬干瘪的抽象符号;如果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湘西自然优美的凤凰古寨,那么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以及湘西人民的纯朴善良就难以呈现;如果失去了辽阔阴沉的威塞克斯乡村,那么哈代小说中的悲戚的审美价值将难以生成。恩格斯在评论《格林童话》时说:“自从我熟悉德国北部草原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格林童话。几乎在所有的这些童话里都可以看出它们产生在这种地方的痕迹。”这说明只有依托文本历史发生的地域现场,才能发掘与理解文本内部的审美意义。同样,中国民间文学调查者有意识地记录民间文学发生与流布的生态环境,尽可能保持民间文学的地域原貌和形态,这说明了还原文学作品地域性对民间文学作品意义阐释与增值的重要意义,离开地域性就难以获得民间文艺真实的审美形态及其本真价值。因此,无论是作家性还是民间性的世界文学,只有立足文本的地域性,才能进一步追溯和探求世界文学作品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共通的审美特性。可知,地域审美是世界文学审美模式及其审美规律的重要考察视点。
那么,世界文学的地域审美是什么?地域概念本身具有自然环境空间与族群文化的双重属性,并深刻影响着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审美文化选择,由此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特征的差异明显,如中国南北文学就呈现出细腻婉转与热情奔放的审美差异。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差异巨大,东方美学特别是中国美学追求形神兼备、中庸和谐之美,而西方追求形真意切、科学理性之美。当然,地域审美不代表其审美内部的绝对同一性,“我们不能假定同一个地域文化圈中的所有民族都遵循着完全相同的时序和路径发展,事实上,各民族审美文化既有各自连续的发展,又有各自不同的断裂,东方各民族在审美文化领域中形成了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格局。”多元的统一性是地域审美的存在形式,这类似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不过,地域审美更强调共性,即统一性。所以,地域审美就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融合统一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即生存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统一”。巴尔扎克小说将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融汇,传达出底层人民破产的绝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从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以《高老头》为例,小说一方面在细致描绘圣-日内维新街上那座阴沉、暗淡、丑陋、凄冷以及死气沉沉的伏盖公寓,另一方面刻画庸俗众生相如年迈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穷苦大学生拉斯蒂涅、奸诈狡猾伏脱冷、形容枯槁的老处女米旭诺等,呈现法国底层市民以及落魄贵族的生活残败景象。伏盖公寓所象征的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即是审美地域性生动的表征。
世界文学的地域审美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滋生于文本的不同层级而呈现出层级结构形态,具体表现为地域审美的语言层、现象层和意蕴层。首先是语言层,这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外观,即语言与文字的音义符号系统。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即便是经过翻译之后,仍然具有地域的风格习惯,或表现为“不可译性”。“不可译性”在诗歌文体中更为常见,与地域文化心理、情感,诗歌体裁自身的节奏、对称、修辞、意境、韵律等相关。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由意象叠加而成,转换成英语文法形式,需添加主谓宾结构的语法规则,诗歌的韵味和意境将全无。傅雷认为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文字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习惯、修辞格律、俗语、风俗习惯、社会背景也不同,不能完全对译,所以他主张保持地域语言原本的样态。“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杀,把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末(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腔’。”所以,理解但丁《神曲》的丰富内涵就不可避免去领悟意大利方言的个性滋味,品味中国唐诗宋词就要体悟一唱三咏的节奏韵律之美。其次,文本语言层面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表现出具象化的文学形象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文本现象层。而地域审美的现象层指的是语言符号系统所指的具象化地方性形象,即地域性的景观、环境、人物、情景,这些意象或景观图式凝聚着人丰富的情感、心理以及思想。在地域审美的现象层中,这些人物、情节和环境被赋予了与生活材料完全不一样的特征和形态。在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表面展示的是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独特的地方自然景观以及风土人情、民俗风格,书写一个纯朴农村女性的悲剧故事,但是,小说中威塞克斯乡村的沉郁寂寥、女主人公苔丝曲折悲剧的命运与农村在资本主义的侵入下破败时代景象联系起来,形成了哈代独特的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环境性格小说”。最后,地域审美的意蕴层即是超越语言层和现象层,深入到文本独特的地域思想观念和地域审美价值。图式化外观(即现象层)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审美价值因素”,这些因素(审美价值因素)与“同一种形而上学性质相关”构成了“作品的顶点”。“作品的顶点”即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作品除了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之外,“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情感,灵魂, 风骨和精神”。意蕴具有含蓄性与多义性,这是由于语言层与现象层丰富且多变的能指所致,而地域审美的意蕴层则是现象层所指向的深层审美形式。
地域审美的意蕴层具有层次性。首先是文本现象层所指的表层审美,如《狼图腾》对生态、环境以及草原文化的认同与反思。其次是“人化自然”后的“人”的生存问题,即人—地关系下人的存在之思,如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的哲学思考。最深层次是在人—地关系下人与自然、文化等历史积淀凝结而成的地方“民俗图式”。任何人的生活、思想、行为都离不开最基本的民俗文化存在结构,即便是所谓的人的生存环境,“本身已灌注了以民俗为核心的人类文化进化的印记,尤其是人物环境展示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以民俗的宗法、家庭制度,亲属、行业关系,伦理道德观念,婚丧喜庆、日常生活习俗惯制为基础的”。所以,地域审美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民俗审美思维,观照地域独特的民俗景观及其文化特性。例如,在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如果没有民俗节日“愚人节”的狂欢化序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限无法解除,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将无法正常开展。小说中丑怪卡西莫多、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国王兵士长菲比斯和光怪陆离的乞丐王国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怪诞情节,小说的黑暗、罪恶、丑陋、分裂、冲突与善良、真挚、关爱、和平的多重声音交织在一起,共同展现了小说美丑对立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这些瑰丽的想象、浪漫的复调与多声部可以和谐交织,共生共融,依托于法国狂欢化的民俗精神。由此来看,世界文学的审美模式理应是以人—地关系为根基结构的地方性审美,观照文本空间中的地方语言景观、地方形象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地方民俗景观,展现超越时空性的地方族群记忆、精神空间和文化原相的审美特性。
审美意识的地域性根源于世界各区域自然环境的根本差异以及人类族群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是人地关系互为运动的审美积淀。然而,世界文学是一种超越地方性的普泛价值论,追求思想价值的普遍性、审美共通性及人类命运共同性。世界文学的审美普遍性指向似乎与地域特殊性审美追求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隔绝的姿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世界文学地域审美的本体论问题上,即地域审美的本质。“地域审美本质上是鉴赏判断的差异问题,而鉴赏判断的差异来源于种族、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丹纳认为艺术创作与审美趣味的生产与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的客观因素,就是说,人类的审美差异是必然的,读者对世界文学的接受和审美判断基于内化了的种族、环境与时代的地域文化的审美视域。所以,对于世界文学的鉴赏与批评来说,显然不能简单地抛开地域性要素,形而上阐发世界文学的普遍性意义或者审美的共通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表达的是“人类永恒孤独”的精神困境主题,但这个主题的呈现离不开地方性书写。没有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拉丁美洲马孔多小镇的百年兴衰,缺少拉美神话传说故事的魔幻色彩,《百年孤独》的“永恒孤独”旨义则缺乏渗透力和艺术张力。没有巴黎和伦敦两城人民与贵族之间严酷的社会矛盾冲突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动荡,《双城记》的“人道主义精神”主题将失去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鲜活的支撑材料。可知,世界文学的普世价值观念或者审美情感的人类共同性是其作品内部意蕴的核心属性,但其离不开地域审美的特殊性呈现。因此,地方性审美不是世界性审美的对立者,而是世界文学的审美源点和立场。所以,米勒认为文学研究应兼具地域性与全球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一方面,虽然几乎每一种理论都来自特定的区域文化,却无不寻求阐释和方法的有效性……在理论和细读的必要结合中,文学以一种称作‘全球区域化’的方式兼备地域性与全球性”。尽管在这段话中米勒没有直接涉及世界文学研究的地域性问题,但是他实际上强调了地域与世界并非对立概念,地域审美与世界性审美相互指涉、互为互存。总之,世界文学是基于地域审美的世界性审美方式,只有认同地域性才能实现世界文学审美的自洽性与超越性,建构世界文学的普遍性意义。
近年来,“地方”成了一个学术热点。文学的地方性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描述对象或空间元素,而且还具有理论话语、史学方法乃至学科建设的意义。李怡认为“地方”是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因而提出“地方路径”的史学概念,其价值在于“地方路径可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改编沿袭多年的外来冲击/回应模式,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演变的内部事实”。张光芒认为地方路径可以“重构现当代文学史”。文学地理学则探讨地方与文学的知识谱系问题、文学的空间批评问题、地理诗学问题等,如曾大兴高度关注地方、地域对中国文学观念影响以及地方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思考,邹建军依托地方性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体系等等。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学科而言,重新思考地方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可以为世界文学如何存在、发展、演变以及审美规律提供一个地方性的考察视野,而且还可以为世界文学的翻译问题、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世界文学史书写,乃至在中外文学关系中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从地方走向世界中心以获国际话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德]爱克曼著,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②[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版,第43页。
③[印度]泰戈尔著,王国礼译:《世界文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著,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④[美]大卫·丹慕厄什:《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⑤刘敏、方如康: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页。
⑥[美]爱布拉姆斯著,吴松江等译:《文学术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⑦[美]哈奇森·波斯奈特:《世界文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译,《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⑧何言宏:《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⑨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81页。
⑩王金黄、邹建军:《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基本方式》,《江汉论坛》2018 年第9期。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⑫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⑬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⑭[美]哈奇森·波斯奈特著,田溪译:《世界文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⑮[日本]山田实:《大众传播研究入门》,日本芦书房1988年版,第6页。
⑯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⑰曹顺庆:《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
⑱王宁:《“世界文学”: 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
⑲[美]段义孚著,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台北编译馆1998年版,第2页。
⑳[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
21.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2.邹建军、张三夕:《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长江学术》2015年第4期。
23.[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24.[法]史达尔:《论文学》,选自《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5.胡良桂:《国外文学与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6.张隆溪:《异域情调之美》,《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27.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载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7页。
28.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载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7页、第547页。
29.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30.朱立元:《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31.[苏联]伊瓦肖娃著,杨周翰译:《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83页。
32.邱紫华:《东方美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33.钟仕伦:《地域审美:历史、性质与原理》,《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34.[波]英加登著,陈燕谷、晓末译:《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页。
35.[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25页。
36.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37.钟仕伦:《地域审美:历史、性质与原理》,《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38.[美]希利斯·米勒著,易晓明译:《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39.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40.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41.张光芒:《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
42.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壮族文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1KY15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邹建军 卢建飞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