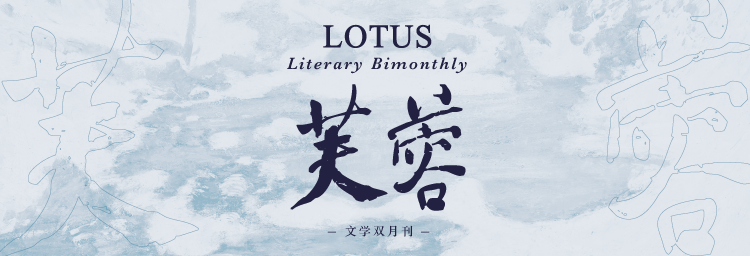

守墓人(中篇小说)
文/陈集益
一
曾经有段时间,我也反对父亲死守这片墓园。那是我们家最艰难、最不团结的一段日子。“艰难”之说不单单指存款不多,更指守墓之事让家里家外危机四伏,母亲为此要闹离婚:“我这辈子跟了你,被你拉进这个坑,生下四个子女吃尽人世苦。可你不能再毁他们的前程啊,你这个老虎叼的,这坟里埋的是你的祖宗,还是他的后人每年给你钱?你到底图什么啊!”父亲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沉默。
父亲是个固执、诚实的人。据父亲讲,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我们的先祖就奉命来到这大山中守护无名将军墓,四百多年来守墓事业世代传承,自他记事起他爷爷就带着他一起守墓,给他讲守墓人要遵守的义务:一要负责打扫墓园,清理杂草,种植花木,培添新土;二要每日巡逻、守夜,防止盗墓贼或野兽破坏;三是定期上香,祭祀节日须供奉祭品。并说,尽管守墓这个职业现在没人愿意干,但是古时候一般人还没有资格干呢。
“我们的先祖,是戚继光部下一名忠诚的士兵,这才被派到这里,开始在这个小山村繁衍生息,与无名将军墓可谓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父亲说,他爷爷小时候即闹匪患那阵儿,吴氏家族还有五六十口人,这么多人就靠祖上获得的这份守墓职业的庇荫而活。“那时候,守墓人有墓田可种,范围很大,每年打下的粮食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而且墓园背后的倚靠山,树木每年可以间伐着卖。这些山林田地直到1950年‘土改’,才分给村里人。”
我无从想象那时的墓园,亦无从想象早已不存在的古人。如果没有这座古墓,我不敢相信我的先祖竟然是抗倭英雄部下的一名士兵。而且据说,我家守护的这座无名将军墓并非真的无名,他其实是戚继光长子戚印之墓。你一定听说过戚家军在浙江抗倭的故事吧?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掠夺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勾结中国海滨的土豪、奸商、流氓、山寇,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史料记载,仅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杀害的就达数十万人。后朝廷参将戚继光奉命抗倭,经十多年奋战才将其肃清。
或许,你也观看过不同剧种的地方戏《戚继光斩子》?在不同剧目中,戚继光抗倭事迹可能有不同的开始与发展,却有着一致的结局,那就是在一场发生在山谷的交战中,戚继光率领戚家军设下埋伏,准备诱敌深入再一举歼灭。然而,戚印将军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擂鼓展开总攻,结果让部分倭寇逃脱,以致未能全胜。戚继光回营后因戚印未按军令行事,下令按军法处置。尽管手下诸将苦苦求情,说戚印也曾大败倭寇是有功之臣可将功抵罪,但于事无补。戚印之死,让戚家军以纪律严明闻名天下,而当年在事发现场,也有将士为失去戚印这位勇将唏嘘痛哭。毕竟,在那些出生入死共同抗倭的日子,他们与戚印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相传,戚印的尸首在刑场外就地掩埋后,半夜却被一位与戚印情同手足的将士从刑场秘密运出,然后一众人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翻越仙居与缙云交界的官盐驿道,经野苍岭于两天后运抵吴村葬于倚靠山下。尽管此事因秘密进行不见正史记载,以至于到了今天真相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且不论地方戏剧或者经过演绎的故事,关于戚印的确切落葬地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争论不断(一说葬于义乌,一说葬于台州)——但是,它对我们这个守墓家族而言,是整整四百多年确凿无疑的历史。
我们相信,在当时之情境,那位同情戚印的将士,只能以如此方式将尸首秘密运抵神秘的后方,以无名将军之名下葬。只可惜那本为无名将军墓以及吴氏家族守墓之由来留下只言片语的吴氏族谱,在我出生之前就被“破四旧”抄走烧掉,墓碑也遭到同等毁坏。又由于守墓职业素来与外界交往甚少,家族中保存族谱记忆的老人一个个过世了,仅靠口口相传的世事更迭已经无从历数,甚至连我们先祖姓甚名谁、原籍何方等,这些原本可供后人考证或凭吊的人事,我父亲——这位注定会是家族中最后的守墓人——也越来越难以记得清楚、说得准确。
二
我是十九岁高中毕业,才真正离开吴村去金华城里谋生的。我的离开,一是证明我已经成人无须再靠父母生活,二是我决意要逃离这穷乡僻壤,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害怕守墓这件事最终落在我身上。对于我的离开,最伤心的当然是父亲。他送我去井下村坐车(那时公路还未通到吴村),帮我挑着铺盖、衣物、书本等东西。那是我第一次要去金华这座离我的出生地最近的城市,所带东西跟我十六岁那年去汤溪中学念书差不多。只不过这一次,我乘上出山的汽车不会在途经汤溪镇时下车了,我要继续往前、往前,一直坐到终点。
一路上,父亲没怎么说话,但我看得出他是有话要说的。当我察觉到这一点,就开始怕他说出守墓的事,我走得很快,或者故意落在他身后数米之远。那个清晨天气已冷,雾气很重,乡间小路旁的杂草上挂着露水,金塘河两岸山的暗影让人压抑。到了凉亭附近我的心陡然紧张起来,因为距离这里不远,在倚靠山下的一片稻田的尽头,就是埋葬戚印的墓园。曾几何时,多少个如此这般的清晨或者夜晚,我跟随父亲走向通往墓园的田埂。
父亲果然停下了,他把担子交给我,独自向墓园走去,可是走了几步又回转来。我劝父亲不用再送我,父亲从我肩上夺过担子,又是一路沉默。
到了井下村,汽车还没有来,但是等车的人已经站满汽车停靠站。我和父亲选择路边的石头坐下,他掏出竹根做成的烟斗,不一会儿那熟悉的呛人烟雾把我包裹。“这条路啊,山里人走了一辈子,以前背树、挑木炭、桐油,山里货运出去,再运烟酒、粮食、化肥、农药回来。如今通上车,再也不用那么累了。”父亲停顿一会儿,看着我,突然说了一句,“路通了,人也都走了。我没想到你妈给我生了四个孩子,一个也不愿留在身边。”听父亲这么说,我的脸红了。“其实,我也不希望你们留在山里,天是方的地是圆的。要不是出生在这个家,或者咱不姓吴,那该有多好!谁能想到吴村、吴村,这个因先祖来此守墓慢慢发展起来的村子,吴姓就剩下我们一家,可我老了啊……”父亲说着话,一通咳嗽让他停下。这个牛高马大的硬汉,唯有说到这件事会变得芦苇般脆弱。我很害怕看到他无助的样子,怕他再说下去我会哭起来。幸好这时候汽车来了,它在公路拐弯处发出“嘟嘟”声,仿佛将堵在我和父亲之间的难受释放了。我慌忙拾起担子,与那些同样出门务工的青年挤到了车门口……
几分钟后,汽车又“嘟嘟——嘟嘟嘟——”叫起来,那是预告还在奔跑的赶车人它就要走了。我知道,父亲最不能接受的是我的背叛。我不敢朝车后张望。因为在四个子女中,只有我亲口答应过他愿意守墓。那时候,我怎么可能想到今天……
记得小时候,还是生产队年代,父亲就爱带我来到荒芜了的墓园,有时候背着我,有时候把我放在肩上。那时守墓并未公开允许,父亲却等不及。他在歇工后,就带上砍刀、锄头,披荆斩棘,砍去生长在墓园里的灌木、细竹,挖掉它们的根。日复一日,一座巨大的坟墓在夕阳余晖中显出清晰轮廓。我当时还不了解这座墓的历史,仅仅被它的雄伟震撼。事实上,我当时也不会运用“雄伟”这个词,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视觉的本能,感到它如此规整、气派。
它是一座封土石室墓(这是根据我现在的判断),坐西朝东,依山势逐步升高,外部主体呈覆斗形,最高处约五米,宽约十五米。墓前有好多块砌得齐整的巨石,有横有竖,横的是梁、竖的是壁,有的梁上雕有双龙纹饰,其正前方有石碑高约二米,宽一米二三,顶为尖圭形,碑正面没有镌刻文字,可能正是“无名将军之墓”名称之由来。至于整个墓园四周,曾经有过的青砖花墙、墓庐、墓道、翠柏青松,均已损坏。唯一剩下的就是坟墓本身。
“清朝还未亡的年月,土匪三番五次来打盗洞,均被赶走……”
“青砖花墙是一九四几年国民党军队拆走的,拉去修建碉堡……”
“几棵古木在1958年‘大跃进’时砍了炼钢,烧炉子……”
“墓庐是后面不准再守墓了,木头拆了造桥……”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祖上发生的事更多了,历朝历代都有掘墓的……我们家的人以前都要练拳。盗墓贼来了你要去挡啊!……做守墓人,平平安安的年月种墓田、繁衍后代,安享田园风光,遇到盗墓的情况就得挺身而出。祖上的人口就这么损失一些,又繁衍一些,又损失一些。都说,这坟里有金银财宝、龙泉宝剑啥的……戚印是偷偷下葬的将军,有没有金银财宝我不敢保证,但是大家都这么说。说这墓园的形成是被追封和赐祭后所建……”
从记事起,父亲就爱跟我讲这些。我对父亲讲的很多事情半懂不懂,不感兴趣。忘不了的是,一天,父亲在墓前清除杂草,又跟我讲起一些掐头断尾的老皇历,内容无非是我们家的守墓史和衰落史,然后就是我们作为吴氏家族的后人,该如何继续守护无名将军墓,恪守祖训,记住忠义二字——那时候,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小学生,放学后虽然还会跟着来守墓,但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因为在生活里,我经常遭到小伙伴们嘲笑,他们说我老去墓地,身上阴飕飕的,有一股鬼的气味,以致没有同学愿意跟我做同桌。而在过集体生活之前,不瞒你说,我因为我家是戚印将军的守墓人,一直感到自豪。
我记不清我是怎么跟父亲说的,但记得父亲错愕的表情。很显然,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在我哥哥姐姐身上发生过,又发生在了我身上。如果说前三个孩子出于这个原因不愿跟他来守墓,他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今已是退无可退:“二兵,你不用管别人怎样的态度,我们从一出生就跟别人不同。我们是身负使命来到人世的。”我问为什么。他的眼里射出一团怒气:“你永远要记住,这里埋葬着一位抗倭英雄。一位在前线抵抗倭寇入侵,然后由于草率出兵被斩首、只能偷埋在这后方大山里的英雄。他虽然违背了军纪,但无法改变他是英雄!”说完,父亲丢下手中的活、丢下我。我追上去,解释我真的没有逃避之意,我是真的受到歧视了。父亲的口气软下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生来是一群麻雀,有的人生来就是一只雄鹰,你想过大山里只有麻雀没有雄鹰会是怎么个情况吗?”我说没有想过。父亲说:“要不是因为有抗倭英雄戚印葬在这里,要不是我们的列祖列宗忠心耿耿地守护,那么这个狗屁地方要么是一片普通杉树林,要么是一片稻田,要么是一个荒坡。这里什么都不是!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不明白。假如是一片树林、一片稻田、一片荒坡,有何不好?我甚至觉得吴家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将守墓这份事业以及把先祖的血脉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守墓有墓田可供耕种、有山林可供砍伐。而现在呢,只剩这不断长草的、被毁坏了的墓园,只剩下守护的义务,还有被世人歧视的目光——我常听村里人说:“他吴兴(我父亲的名字)天天去坟上转悠,不就是想哪天偷偷把坟掘开,把公家的古墓占为己有嘛。”有人甚至怀疑他已经把坟里的金银财宝偷拿回家了,只是现在还没有露财:“等到两个儿子再大些,看着吧,就拿出来造新屋啦!这戚印又不是他家祖宗,凭什么……”面对流言蜚语,父亲常常暴跳如雷但无言以对。他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家里,越来越严肃了,面色铁青。母亲受不了,抱怨说:“为了守墓,当初你过的是什么日子,怎么都忘了?我还想,中间隔了这么多年不敢去,这回可跟这个坟一刀两断了,没想到你吴兴是不撞南墙不死心!”父亲那时还有些脾气,他不屑与娘们你一句我一句顶,单是两眼一瞪、把饭碗往桌面狠狠地一放,母亲噤了声。
“咱不能吃了几百年墓田的谷,砍了几百年倚靠山上的树,一等这些没有了就撒手不管。这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区别?吴家十几代人生生死死守护戚将军的英灵,就为了得到必要的口粮和钱财吗?如果是那样,土匪来了,盗墓贼来了,有必要拿命去拼吗?他们挖了坟还能把墓田墓山带走?换了村里有的人家,哼,说不定还勾结土匪强盗来挖一起分赃呢!可咱能做出这样的事吗?你们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一说,你能干出这样的事吗?来,先大兵(我哥的名字)说……”等母亲走开后,父亲就会跟我和哥哥滔滔不绝。我们自然不敢说一个不字。尤其哥哥生性谨慎、冷漠,人也长得瘦弱,他从不与父亲辩论,但是也从不爱跟着父亲去守墓,他只关心自己的学习和前途。我怀疑他从那时起就想着怎么逃离了。
“你们的太公说过,自明亡清兴,这座坟实际就没人过问过,全凭咱吴家人额头上写着忠义两字守下来!尽管传到我这辈,吴家败落了。而我啊,为了活命,为了一家子老老小小,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墓园被毁被污!你们可知我心中的痛吗?!……咸丰年间,一帮平原上的强盗一路打进山,山里人闻讯逃的逃躲的躲,留下空村。这时就我们吴家一个没走。因为我们家族,流着戚家军的血啊!当强盗打到井下村,你们的太公带着人马在巷子里与他们交锋。那时候没有枪,全凭刀剑、棍棒、武功,井下村留守的壮士们见状纷纷加入。
(节选自2023年第4期《芙蓉》中篇小说《守墓人》)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花城》《十月》《钟山》等文学期刊,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曾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09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2—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首届东吴文学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等,小说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出版有小说集6部、长篇小说1部。
来源:《芙蓉》
作者:陈集益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