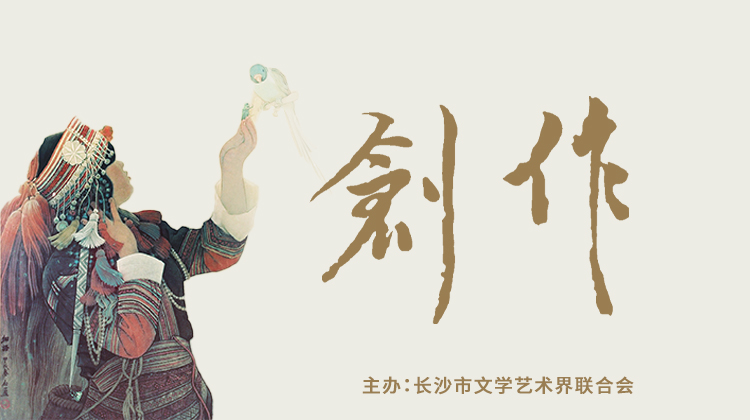

遁地“狂魔”
——“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隧道施工纪实
文/龚盛辉
桥隧比高,是中老铁路标志性工程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老铁路沿线地质,被地质学家喻为“不安分的地质博物馆”,溜坍、突涌、大变形等不良地质灾害频发。
曾有人断言:“这样的地质条件,根本打不了隧道。”
中国工人有勇气、有力量、有智慧,与“地妖”掰手腕,大战“水帘洞”,降伏“火焰山”,智钻“水豆腐”,蹚过“地雷阵”,搬掉“三座大山”……
不安分的地质博物馆
中老铁路沿线80%为山地和高原,地势北高南低,山川走向沿构造线延伸,山地、峡谷、山间盆地交错分布,地形陡峻,横向冲沟发育,地形地貌极为复杂。线路经过区域属中国西南“三江”造山带的南延部分,地处琅勃拉邦通过兰坪—思茅地块、南海—印支地块两个一级构造单元的缝合带,地质构造和云南有相似之处,具有岩性复杂、构造发育、岩体破碎、不良地质发育的特点,工程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铁路、公路的建设难度,通常以隧道、桥梁所占比例的高低来衡量。中老铁路桥隧比极高,仅玉磨段就有隧道93座,长398公里,隧道比78%,长10公里以上的隧道就多达15座,全长17.5公里的安定隧道为全线最长隧道;桥梁136座,长50公里,桥梁比9%,全长3.5公里的橄榄坝特大桥为全线最长桥。桥隧比达到87%,这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
沿线群众形象地说:“中老铁路不是在天上,就是在洞里,看见它时在车站里。”
中老铁路线路不仅桥隧比高,而且地质条件差。中老铁路沿线地质构造复杂,全年降雨充沛,隧道多数穿越断裂带,围岩破碎、地下水丰富,具有“三高”(高地热、高地应力、高地震烈度)、“四活跃”(活跃的新构造运动、活跃的地热水环境、活跃的外动力地质条件、活跃的岸坡浅表改造过程)的特征,被地质学家喻为“不安分的地质博物馆”。
在“不安分的地质博物馆”进行隧道施工,神神秘秘、形形色色的怪事层出不穷。
这里有强大的地应力。所谓地应力,就是由于岩石的变形而引起的介质内部单位面积上的作用力,是引起地壳运动的动力源,是造成地震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各种隧道施工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在民间还有另一个极具恐怖色彩的名字——“地妖”。它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它神秘莫测,且“法力”巨大——它可以让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处于不断抬升的状态;它把隧道被覆的比手臂还粗的钢骨架扭成“麻花”,不过是小菜一碟。
这里有凶猛的涌水。严重时平均每天涌水达4万立方米左右,可灌满17个标准游泳池。
这里有能量巨大的突泥。它能够瞬间把数十吨重的施工机械推出数十米远,一天在隧道里积泥一米多深。
这里有令人猝不及防的坍塌。常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轰隆”一声,一大片围岩从天而降。
这里有“地下火焰山”。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下边,常常藏着一个“大火炉”,使隧道施工掌子面的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个别施工面甚至高达60多摄氏度。
这里有“水豆腐”。以炭质泥岩、炭质页岩为主的围岩,岩体极易破碎,加之丰沛的地下水渗透,就像一盘流动的散沙,给隧道施工带来极大挑战。
这里有“地下盐库”。中老铁路多个地段属于食盐结晶之后形成的盐岩,强度低,遇水就变成盐水,侵入混凝土结构后,对钢筋腐蚀性极大。
这里还有“地雷阵”。美军在老挝投下的200万吨炸弹,不仅时刻威胁着老挝人民生命安全,而且严重阻碍着中老铁路施工。
…………
过去,有专家考察过中老铁路沿线地形、地质情况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这样的地质条件,根本打不了隧道!”
与“地妖”掰手腕
2016年12月,中老铁路建设总算全线开工了。中铁昆明局滇南指挥部指挥长、中老铁路总指挥刘一乔那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一些,他连着睡了两晚好觉。哪知第三天凌晨三点多,睡得正香的他,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天还没亮呢,什么事不能天亮再说呀。”同时被吵醒的夫人嘟囔道。刘一乔说:“八成是铁路工地出问题了。”
刘一乔拿过手机一听,果然传来中老铁路万和隧道项目负责人李峰急促的声音:“刘总,昨天刚被覆的隧道,一个晚上就塌陷了1.5米!”
隧道施工险情,是刘一乔最担心的问题,也是预料中的事情,但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刘一乔是个“老铁建”,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铁建”,已经在“铁建”工地上摸爬滚打了近30年,组织并参与过数条铁路线建设,足迹遍布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数省。
中老铁路玉磨段,是刘一乔数十年“铁建”生涯中碰到的地形最复杂、地质最恶劣、挑战最大,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领导最重视的项目。从中央到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再到昆明局集团公司,都高度重视中老铁路建设,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政策,予以强有力保障。
中老铁路建设,既是交通项目、基建项目,也是政治项目!
刘一乔为自己能担任项目总指挥而倍感荣幸,同时也深觉责任重大、压力如山。自从走马上任的那天起,他就经常对自己说:“一定不能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多年的铁路建设组织管理实践告诉他,组织铁路工程建设就像弹钢琴,能否弹出高山流水、行云飞霞的效果,关键在于能否用好右手,弹好主旋律。通过深入分析、综合比较,刘一乔认为中老铁路建设,核心是确保五年建成通车,关键是隧道尤其是几个一级风险隧道施工。只有紧紧扭住这个龙头,才能带动全线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刘一乔赶紧穿衣起床,给车队负责人打电话安排车辆,并通知玉磨段总工程师龚庆五等技术人员,立刻和他一道前往万和隧道。
当刘一乔、龚庆五一行乘坐的越野车风驰电掣地赶往万和隧道时,万和隧道项目负责人李峰和几名工程人员,正手足无措地望着前方深深塌陷的隧道。素日里,李峰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暖人的笑意,此时此刻他帅气的四方脸上神情严峻。这十几米隧道,是昨天掘进并已做好支护的,昨天傍晚下班时,它还是笔直的,没想到不到十个小时,就变成了一根弯弯曲曲的“大肠”,一排排比手臂还粗的钢质支护架,被扭成了一根根“大麻花”,其中不少断成数截,一些地方隧道下沉1.5米!
李峰也算是个“老隧道”了。他一参加工作,就与隧道打交道,至今已参与和组织多个隧道施工,并多次与软岩过招,也算经验丰富。李峰带领大家很快掘进到第一个大断层。他深知地质断层地应力的破坏力巨大,早有心理准备,特意让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加粗了防护支架,并加大了支撑密度。然而这里的地应力之强大,还是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时,隧道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峰知道,是指挥部的领导们来了。他回头迎上去,一把握住刘一乔的手:“刘总、龚总,半夜三更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啊。”
“别着急。”刘一乔拍拍李峰的手背,“走,咱们一道看看去。”
刘一乔走过去一看,神情一下子严峻起来:“这是地应力要和我们掰手腕呢。我们没有退路,也无法绕开,只有勇敢地接受它的挑战,而且必须把它压下去!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说完,刘一乔望着一旁的龚庆五:“龚总,你有什么办法把它镇住吗?”他知道,处置各种隧道施工险情,总工程师龚庆五很有经验。
龚庆五是一名出生于“铁路世家”的“老铁建”。1997年7月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铁二院昆明集团公司后,参与过10余条铁路的设计、建设,泛亚铁路东、中、西线,他都参与了设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2009年,中老两国正在酝酿从云南昆明到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项目。与此同时,经济亟待发展、人民生活亟待改善的滇南地区,亟待铁路运输的牵引与助推。但这时,滇南地区仅有的昆明至玉溪铁路线,时速仅有80公里,远远满足不了客观需要。为尽快提升昆玉铁路运力,并为未来的中老铁路建设探索经验,国家启动了昆玉铁路扩能改造项目,特任命龚庆五为副总设计师,建设工程启动后,又任命他为项目总工程师。
昆玉铁路沿线,位于滇南地区的北部,其地形地质与中老铁路沿线大致相同,有着三大特点:一是隧道围岩柔软多变,地下水丰富;二是地面湖泊、珍贵树木多;三是矿藏丰富,采矿采空区域广。这些,都给铁路施工尤其是隧道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
基于上述地形、地质、植被特点,龚庆五创造性地采用地质选线、环保选线相结合的选线法,让线路巧妙地避开九龙湖等敏感区、采矿采空区,为国家保护的古树让路,设计了一条经济、生态的铁路线。
昆玉铁路施工过程中,龚庆五不仅经常与地应力、突泥、涌水过招,还与饱和粉细砂地质鏖战了一回。饱和粉细砂地质就像石头磨碎的粉末,一遇水就变成水,在国家隧道围岩标准中,属于最差的地质。龚庆五带领大家绞尽脑汁,反复试验,历经数月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克敌”良方。
龚庆五说:“地应力掰手腕,使的是蛮劲,我们要想掰赢它,一是要使出比它更大的劲,二是要善于使巧劲。”
在刘一乔的领导下,龚庆五结合自己过去与地应力过招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考察、仔细研究,决定采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见招拆招”的策略,即随着地应力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支护参数,同时加大支护钢架预留变形量,并增设套拱,形成强大支持力,以控制围岩变形。在此基础上,在初次支护锁脚上增加锁脚环装置,应用新型隧道拱顶注浆系统提高注浆质量,并自主研发了液位联通式二衬防脱空监测装置。形象地说,就是过去是用一只手与地应力掰手腕,现在要用两只手、三只手……
这些措施实施后,不仅万和隧道变形的问题解决了,而且为其他隧道施工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把万和隧道的“大麻花”捋直后,刘一乔、龚庆五决定返回滇南指挥所。哪知返回的路上,又突然接到通达隧道的涌水险情报告:短短10分钟,据估计突泥超过1200立方米了!
刘一乔急忙让司机调头,又带着龚庆五等技术人员,心急火燎地赶往通达隧道。路上,刘一乔忧心忡忡地说:“沿线地质情况这么复杂,险情如此频繁,工程进度恐怕难以保障哪。”
龚庆五说:“这样下去,落实五年完成中老铁路建设的计划,是有些悬。”
刘一乔预测道:“现在看来,接二连三出现险情,以后可能是常态,其中很多问题在设计时是想不到的,变更设计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出现,咱们的设计变更流程要改革、要简化,要从中挤出时间来。”
龚庆五点点头:“确实如此。”
按过去的施工流程,施工单位发现图纸设计与现场实际不符时,要首先向上级报告,上级向设计单位转达更改设计请求,设计单位再到现场勘测,再根据现场情况作出新的设计,经过上级审查后,再返回施工单位,一个流程走下来,十天半个月就过去了。
“过去那种设计变更模式,显然不适应中老铁路地质复杂、情况多变的实际需要。”龚庆五说,“我们可以让设计人员与监理人员、施工人员一起生活、一道工作,这样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组织会商,及时拿出新的设计方案,实现一次设计变更,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对,采用动态设计,隧道施工进度肯定会大大加快。”
刘一乔充分肯定这一思路后,回头望着龚庆五:“龚总,你有没有办法预知掌子面周围的地质情况,这样施工人员就能早做准备,早采取措施,就能大大减少事故及其损失。”
龚庆五说:“现在还没有办法,但我们可以想办法。”
在刘一乔指挥长领导下,龚庆五迅速组建起科技攻关小组,通过请教技术专家、反复探索,创新性组织编制了超前地质预报细则、隧道防涌突施工预案等办法,研制出为隧道围岩做“CT”的专业设备,预知前方围岩情况,做到围岩瞬间“变脸”,施工人员瞬时“变法”,为施工中预防各种事故、调整支护参数提供依据,确保施工进度。
大战“水帘洞”
通达隧道位于云南省元江县与墨江县交界处,进口地处他郎河,出口位于阿墨江,横穿哀牢山,全长11.3公里,最大埋深745米,最小埋深15米。隧道需穿越4条断层和1个大断裂带,属于国家一级高风险隧道,是中老铁路建设指挥部重点关注和管控的十大项目之一。
刘一乔赶到通达隧道,来不及喝口水,就往隧道里钻。只见泥浆还在“突突”地往外冒,整个掌子面都已经被突泥填满,掌子面后面刚挖的隧道堆积着厚厚的淤泥。
刘一乔、龚庆五当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大家一道寻找对策。经过研究讨论,最后拿出了“排、堵、截”的处置方案:立刻安装排水、排泥设备,清除淤泥;采用小导管注浆加固件封堵突泥口;建立完备的排水、排泥系统,提升涌水、突泥险情处置能力,减少对施工的影响。
掌子面的泥一时被截住了。但这里的地质条件实在太恶劣了,Ⅳ、Ⅴ级围岩占70%以上。Ⅳ、Ⅴ级围岩是什么样的围岩呢?按国家有关标准,隧道围岩共分为六级,分别是Ⅰ、Ⅱ、Ⅲ、Ⅳ、Ⅴ、Ⅵ,数字越小的围岩性质越好。其中的Ⅳ、Ⅴ级围岩,指的是极易破碎的软岩、松散的土层、流动的淤泥。生活中,有些人欺软怕硬,但隧道施工人却“欺硬怕软”。因此,Ⅳ、Ⅴ级围岩,是隧道人最不愿交手的“天敌”。在这样的围岩地质进行隧道施工,各种各样的“不速之客”经常不期而至,尤其是涌水、突泥。
通达隧道施工中,平均每天涌水达4万立方米左右,可灌满17个标准游泳池。而且隧道设计为大坡度隧道,进口到出口的坡度为22.8‰。隧道顺坡水小,反坡水大,反坡段排水难度大,处置不当,整个掌子面都会被淹没。为确保施工正常进行,施工单位组建了40多人的反坡施工排水队,设置6条专用排水道,安装了20台固定水泵、3套移动泵站,不间断抽水。
突泥现象也接二连三,2019年1月隧道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突泥险情,大家日夜奋战三个月,清理突泥,加固围岩,隧道施工才得以恢复。哪知刚干了一个月,一股更加强大的泥流,又冷不丁从地下冒了出来,6分钟突泥量达到1800立方米,施工再次受阻,又耽搁了近两个月。
这样的施工进度,如何保证国家要求的中老铁路五年内开通?其中,有地质恶劣的因素,也有组织管理的原因。
2019年3月,通达隧道项目中标单位中铁五局,决定临阵换将,强化通达隧道项目组织管理力度。于是,中铁五局玉磨段项目部副经理付军,被紧急空降到通达隧道任项目负责人。
付军走进项目部放下行李,就让大家带他进隧道看情况。来报到前,就有人告诉他,通达隧道是个“水帘洞”。果然走到隧道口,他就看见一排大水泵“哗哗”向外抽水。一进洞口,只见满地厚厚的泥浆水,一股湿湿腻腻的热流扑面而来,身上的毛孔迅速张开,不住地向外渗出汗水。渐渐地,付军听到了“咚咚”声和“哗哗”的流水声。走到掌子面时,只见隧道壁的涌水倾泻而下,形成了壮观的洞中飞瀑。洞内的高温把水珠化为雾气,整个隧道水雾弥漫,让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来。工人师傅们穿着背心、短裤,有的甚至赤膊上阵。工人师傅告诉付军,这里的温度在42摄氏度以上,拱顶的温度高达55摄氏度。通达隧道不仅是个“水帘洞”,还是名副其实的“桑拿房”!
从基层施工员一步一步干到标段项目领导的付军,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局面,知道自己最好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就是紧贴一线、靠前指挥。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隧道掌子面上,尤其是在出现险情时,他必须和现场作业的工人师傅们待在一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组织处理。
付军说:“待在隧道里,又闷、又热、又潮,很不舒服,但心里很踏实。而一离开隧道,心就会不由自主悬起来,哪怕睡觉时,都不敢把眼睛闭得太紧。”
他确实时刻都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一只眼盯着前面,指挥大家运用指挥部研制的专用探测系统,给隧道前方岩层做“CT”,获取前方岩层“影像”资料,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人师傅们进行超前水平钻探,全面掌握前方岩层第一手资料,再结合上级提供的超前地质预报,对掌子面前方围岩风险情况做出预判,随时调整施工方案,提前做好各种防范。他的另一只眼睛盯着作业现场,随时掌握施工进度,及时发现、排除各种安全隐患,确保隧道施工有序进行。通过这些措施,各种地质险情显著减少,哪怕出现险情也能根据预案迅速得到处理,施工进度显著加快。
但有些险情,就像狭路相逢的“拦路虎”,绕不开、躲不掉。既然如此,付军就带领大家勇往直前。他担任通达隧道项目负责人的1000多个日夜里,先后战胜各种险情200多次,其中软岩变化114次,最大变形量达到80厘米;突泥、涌水39次,涌突量达8.2万立方米;小坍方、溜坍等近40次。平均每周成功处置一次险情。
通达隧道终于提前半个月全线贯通!
在全线贯通的那一瞬间,迎面掘进的两个团队会合,大家尽情拥抱、大声欢呼,兴高采烈地抛着安全帽、挥舞着国旗。
看着这一切,付军流下激动的泪水:“通达隧道,全长11.3公里,在隧道施工行业,算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了。我们这次长征,和当年红军的长征走得一样难啊,也经历了无数个战役,翻过了许许多多的雪山、草地。虽然只提前了半个月完成任务,但这是我们工人师傅、技术人员,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历尽千难万险赶出来的呀!”
(节选自龚盛辉的报告文学《遁地“狂魔”——“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隧道施工纪实》,原载于2023年第4期《创作 》)

龚盛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退休军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铸剑——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纪实》《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中国北斗》《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战火催征》《沧桑大爱——湖南桑植脱贫攻坚故事》,长篇小说《绝境无泪》,中篇小说《导师》《老大》《通天桥》《与我同行》《野火》等。曾获鲁迅文学奖1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次,中华优秀出版物奖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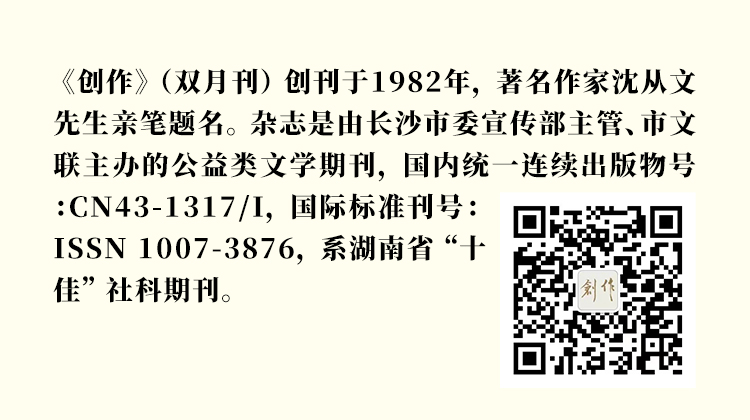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龚盛辉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